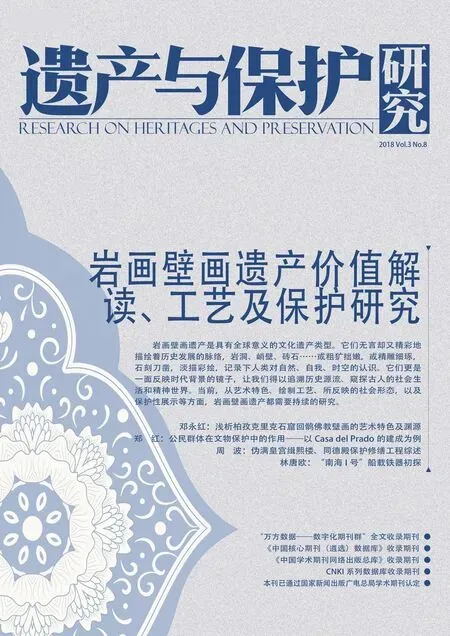浅析柏孜克里克石窟回鹘佛教壁画的艺术特色及渊源
邓永红
(吐鲁番市文物管理局,新疆 吐鲁番 838000)
吐鲁番,古称高昌,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中东部,在北纬41°12′~43°40′,东经87°16′~91°55′之间,是天山东部的一个山间盆地。火焰山横卧吐鲁番盆地中部,山上丛寸草不生,飞鸟匿踪。而在火焰山的木头沟谷中,有天山雪水潺潺流过,常年不息,草木茂盛。昔日那些脱离世俗的僧侣便选择在这里开窟建寺。柏孜克里克石窟就建在火焰山木头沟沟谷西岸的山腰上,现存洞窟83个,其中有壁画洞窟40多个,现存壁画面积1 200多m2(图1)。

图1 柏孜克里克石窟全景(来源:作者自摄)
1 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历史沿革
柏孜克里克石窟开凿始建于约公元5世纪(高昌王国时期),在这里曾发现过写于高昌建昌五年(公元559年)的《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残卷。公元640年唐朝统一高昌,设西州,唐贞元二年至六年(786—790年)间,唐北庭大都护兼伊西庭节度使杨袭古曾为宁戎寺大规模重修寺院。柏孜克里出土的《杨公重修寺院碑》记载了修缮的详情:“窟下造厅四所……修冬厨一所……窟下广栽葡萄”[1]。敦煌文书《西州图经》中记述:“宁戎窟寺一所,右在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宁戎谷中”[2]。宁戎谷即现在火焰山的木头沟,唐代称为“宁戎寺”。8世纪末期,吐蕃人控制吐鲁番盆地,他们信仰的藏传佛教也传入吐鲁番,因吐蕃人在吐鲁番统治较短,开凿的洞窟也较少。
高昌回鹘国时期(9—13世纪),宁戎寺改称为柏孜克里克(装饰绘画之意),佛教发展达到鼎盛之时,也是柏孜克里克最为辉煌的时期。回鹘人早期生活在鄂尔浑河流域的漠北草原(蒙古乌兰巴托西约500 km),信仰摩尼教,在《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碑文中记载了的回鹘可汗接受摩尼教。9世纪中叶,回鹘因遇到天灾人祸,其中一支部族到达吐鲁番,驱逐了吐蕃势力以高昌为中心建立回鹘高昌王国,初期推行漠北时期信奉的摩尼教,在9世纪晚期到10世纪初期左右[3],高昌回鹘皈依了当地盛行的佛教。柏孜克里克成为回鹘高昌王国的王家寺院,历代高昌王及王后修建洞窟用于礼拜。此时代表洞窟有15窟以及20、21、27、31、33窟等。除柏孜克里克石窟外,吐鲁番的吐峪沟石窟、雅尔湖石窟、胜金口石窟、伯西哈尔石窟等都保留有回鹘时期开凿的洞窟。公元1283年,高昌王室因战火迁徙到甘肃永昌,佛教衰落,柏孜史里克石窟沦为民间寺院。
14世纪晚期,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吐鲁番盆地,15世纪中叶后,吐鲁番的统治者被迫改信了伊斯兰教,石窟寺废弃。
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纷纷以到吐鲁番以考古为名,掠夺了大量的壁画和文物,柏孜克里克石窟更是满目苍痍。
2 高昌回鹘佛教艺术特色
誓愿画(国内学者多称为本行经变画)在柏孜克里克石窟数量最多,气势雄伟、色彩艳丽,是高昌回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绘画题材。
2.1 誓愿画的布局特点
2.1.1 程式化
誓愿画宣扬释迦摩尼成佛前,虔诚供养先世佛,最终自己成佛的故事,同时表达了这些供养人今生虔诚供养释迦牟尼佛,希望来世自己也能成佛的心愿。在柏孜克里克誓愿画在构图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格局,如为受记者确定者的祈祷[4](图2),主尊佛为中心,两侧分别绘有精舍、宫殿、菩萨、比丘、金刚、婆罗门、国王、王后、商人等,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一个洞窟内多幅誓愿画依次铺开,画面大小一致,画面之间用竖条花纹边饰隔开。尽管各窟誓愿画在数量、内容、位置有所不同,但构图形式基本相似,并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模式。

图2 为受记者确定者的祈祷(来源:《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第六卷《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52页)
2.1.2 绘画艺术的夸张运用
在誓愿画中,人物比例进行了夸张,将主尊佛放大,2 m多高,气势雄伟,占到画面的三分之一,突出了主尊佛的形象与地位;围绕主尊佛的其他形象进行缩小,人物明显矮小,1 m多高或几十厘米或半身,所占空间比例也较小,以突出主次地位。
在身体绘制中,佛头与身体的比例是1∶4,包括其他站立的菩萨、供养人,也都是这个比例,头大、身体健壮。这种绘画特点,让礼拜的人在狭窄的通道上,无论仰视还是俯视,都能感受到画面人物强大的震撼力,增强了视觉效应。
在人物面部形象塑造上,强调了中庭的长度,这明显的与常人的比例不符。壁画是平面艺术,二维空间里如何利用长与宽的关系,来表现三维空间的透视,即高度,于是对人物进行了一定的变形,强调了中庭的长度,目的为了把鼻子画高,因此在这一时期就形成了一定的特定模式。
2.1.3 对称与变化中反映的艺术灵动性
主尊佛位于画面中央,左右两侧空间大小一致,整个画面形成“左-中-右”对称的布局,这与中国传统的对称审美观念有关。但主尊佛两侧对应的人物又富于变化,全身或半身、跪着或站着的、成人与童子、朝左或向右等不同姿势。并且人物面部表情丰富,金刚怒目圆睁、咄咄逼人,菩萨眉目清秀、端庄典雅等,以及绘制胡商骆驼等异域风情的画面,打破了构图程式化所造成的呆板,让画面生动灵活,具有艺术气息。
2.2 人物特征及蕴含的社会理念
释迦牟尼佛位于画面中央,用线条勾勒佛的轮廓,眉目清秀,宁静平和,手施法印,着袒右式红色袈裟,疏密相间的线条,勾勒出佛陀的形体和衣纹的结构,表现出佛仿佛身着薄质而十分贴体的衣服。佛的背光纹饰线条刚劲有力,组成不同的图案。
金刚与比丘,一般都绘在誓愿画佛两侧的中上部,做为佛教的护法者和传播者,也是释迦牟尼的跟随着的形象出现。只有“袈裟供养”时,比丘才画在佛脚的位置。金刚怒目圆睁,眼球向外突出,面部肌肉隆起,手持法器,身穿铠甲,咄咄逼人,显示出护法的气势。老年比丘(图3)满脸沧桑,表情凝重,留着络腮胡子。年轻比丘,面部饱满,脸色红润,表情恬静,其实他们是佛的二位弟子阿难与迦叶。

图3 老年比丘(来源: 俄国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
菩萨的形象在柏孜克里克广泛存在,大慈大悲的菩萨在高昌也得到广泛信仰,菩萨的形象几乎遍布回鹘时期的每一个洞窟。“捻花菩萨”(图4)现收藏在韩国国立博物馆,菩萨仪容端庄、神情静穆,头梳高髻,戴华丽的冠饰,头发绕过耳后披肩,体态丰满,上身半裸,下束锦裙,珗脚。27窟的菩萨更具特色头发卷曲披肩,或辫发,辫上还有装饰物,半裸。高昌回鹘时期人们把菩萨绘成女性的形象,温柔端庄,富有亲和力,但女性“丰乳、细腰、大臀”的特征有所收敛,显得稳重、健壮而庄严。

图4 捻花菩萨(来源:《中亚宗教壁画》韩国国立博物馆 第97页)
菩萨是脱离世俗的神,不受世俗观念所约束,半祼的形象是可以被接受认可的。但世俗的人似乎受到了更多的约束,所以,我们便会看到一幅画中开放与保守共存的局面。如国王、王后本是世间的俗人,虽在誓愿画中有带有光圈,具有了神的特征,但人与神毕竟有所不同,他们一般都位于画面的下部。“端着供品的王和王后”“举华盖者”等,国王王后身着圆领窄袖上衣,腰上系有腰巾,下身穿窄腿的裤子,脚上穿黑色平底鞋。他们体态丰满,穿着保守,并且他们的头与脚、腿与身,并不符合人体比例关系,甚至出现了“小脚”。供养人以严谨的形象出现,这应该与宋代保守思想影响,以及儒家思想的传播有着必然的联系。高昌地区汉族人大量聚居,社会理念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人们在思想上也逐渐趋于保守。而在人体特征上,吸收了盛唐时代体态丰满的审美观。开放与保守并在,这也高昌回鹘时期特殊的审美艺术特征。
不同民族的贵族、胡商、婆罗门等,他们多来自世俗社会,有浓眉、大眼、深目、高鼻、长有浓密胡须的胡人,头戴各种帽子,手里拿着食品、钱袋等供品,身后牵着骆驼、驴、马等动物,为我们展现了丝绸之路繁盛之时的场景(图5)。吐鲁番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有来自中原的商人,更多的是来自中亚的胡商,在吐鲁番都有他们的聚落。同时,高昌王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外交政策及馆驿制度,保证了丝绸之路的正常运转。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可能与画工生活经历有关,这些来源于世俗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用笔传神,使画面也显得生动有趣,也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珍贵写照。同时,这让我们明显地感觉到,这里的绘画已经本地化了。

图5 商人的供养(来源:《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第六卷《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25页
《燃灯佛受记》中记载,释迦牟尼还是善慧童子时,遇到燃灯佛在路上走着。善慧童子发现地面有一滩污水,怕污水弄脏了佛的双脚,所以他亲身扑在地上,用自己的头发铺在污水上面,让燃灯佛从他头发上走过去。当时燃灯佛看到善慧童子这种布发掩泥的情景,就授记说:“善男子,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
“燃灯佛受记”在15、18、20窟都是位中整个窟的中心位置,运用了写实来表现(图6),儒童匍匐在地,长长的头发铺在佛的脚下,而在33、48窟则运用了象征的写法,把童子画在位于佛头的圈内(图7),不再是脚下。本生故事穿插于经变之中,并运用了象征手法表现,对考证来说增加了难度。从内容上主尊佛应为释伽佛本身,而童子受记象征着他过去成佛的经历;在表现的形式上,由写实发展到后期的象征手法,这不仅说明了艺术手法的转变,更说明了洞窟之间时间的差异。同时突出了供养人建造洞窟的目的,即今生虔诚供养释迦牟尼佛,来世自己成佛,即使今生还未成佛,也就得到尊重和膜拜,并且这不仅是回鹘时期艺术发展的问题,更是时代政治背景的反映。

图6 燃灯佛受记1(来源:《柏孜克里克石窟艺术》第50页)

图7 燃灯佛受记2(来源:《柏孜克里克石窟艺术》第85页)
2.3 融入了回鹘本民族的文化特色的佛教
壁画中城池宫殿屋顶的吻兽为狼头(图8),而不是中原地区流行的龙头。狼是回鹘氏族或部落的象征,是其先民崇拜的图腾,也是突厥各民族共同崇拜的图腾。他们相信自己崇拜的图腾有超自然的力量,甚至相信自身与图腾之间存在某种血缘关系,乃至于是其后代。《周书·突厥传》记载:“旗纛之上,施金狼头”。而其这一时期的龙的造形也具有狼的特点,它不同与早期的龙的造型,与蛇的形象相接近。也是为政权所服务的。
从33窟的王子举哀图可看出其十六国王子既不是印度的,也不是龟兹的,在高昌被本地化了,如正中的王子是汉人的形象,而最末端的发鬓中插入两根箭的应为狩猎的民族。28窟的供养菩萨手持托盘,盛有葡萄、瓜果等为本地特产。在其旁边梳着小碎发辫的回鹘公主像与今天的维吾尔少女发式有一定联系。在胜金口的窟内券顶还运用了葡萄图案作为装饰,卷草、藤蔓纹做为边饰等等,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艺术。
在柏孜克里克15窟殿堂窟内及20窟,就融合了密宗的思想,绘制了忿怒明王像,这说明840年回鹘逐出吐蕃势力,反而又接受其宗教思想,在18窟中心柱的正壁,鹿野苑说法图的壁画中,两只对鹿既有受到北方草原文化影响的“火焰”形状的鹿角,又有来自于波斯的呈“扇”形的灵芝冠,反映出受到草原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影响。

图8 屋顶吻兽(来源:作者自摄)
2.4 思想信仰出现了整合
根据资料证实高昌回鹘时期出现了伪经。伪经之所以被推广,说明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佛教也融入了多种宗教思想内容。这一时期大面积使用红色,红色象征火而火代表光明,甚至把植物及鹿角有意画成火焰形状等等(图9),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起回鹘人信仰摩尼教的思想。这次改革把多种民族、多种宗教、多种艺术、多种政治融合成一种符合高昌回鹘自身统治利益的思想体系,并成为其长达400多年统治的重要理论依据。

图9 卧鹿图(来源:《柏孜克里克石窟艺术》第50页)
2.5 回鹘艺术对后世的影响
回鹘艺术并没有伴随着高昌国的灭亡而消失,她根植于人们的生活之中。14世纪末伊斯兰教传入,因其反对偶像崇拜,这一时期在宗教的建筑上,各种花卉、几何图案丰富起来,形成了今天人们的一种审美标准。但在中亚15、16世纪的一些手抄本经卷中,细密画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从中比较不难看出回鹘时期人物画的特征,并且一直传承延续。
3 高昌回鹘艺术渊源初探
3.1 佛教在高昌地区的兴盛,源于高昌相对稳定的政治及经济基础
公元前一世纪,丝绸之路畅通,汉朝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管辖西域,在吐鲁番设立“戊己校尉”,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做为丝绸之路交通树立枢纽的吐鲁番政治稳定、经济日益发达。而中原河西走廊一带为躲僻战争的汉族人及流亡政权,不断迁徙到吐鲁番盆地,高昌人口迅速增加,经济快速发展。公元442—460年,北凉沮渠无讳、沮渠安周率部众一万余人,西迁至高昌建立政权,高昌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崇信佛法的沮渠氏在吐峪沟开凿石窟,时称“丁谷寺”,这里成为吐鲁番最早开凿石窟的地方。在沮渠王室的支持下,佛教在高昌得到长足的发展。
公元460年,建立高昌王国,高昌成为吐鲁番盆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先后经历阚氏、张氏、马氏、麴氏执政。其中麴氏执政长达140年之久,政治相对于稳定,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中转站,高昌经济也较发达,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并且麴氏高昌王国崇尚佛教,高昌王麴乾固供养抄写的多种佛经,麴文泰盛情款待玄奘法师,在吐峪沟石窟出土有玄奘著《大唐西域记》残卷,这是玄奘赠予麴文泰滞留在长安后代的善本。在高昌城出现了大量的佛寺建筑,佛教不仅有王室的支持,在社会层面上也有着广大的信徒支持。
公元640年,唐朝政府在此设立安西都护府,并在高昌设立西州,下辖5个县,高昌政治稳定、经济发达,高昌也成为西域汉族最集中的地区,丝绸之路空前兴盛,同时儒教、道教以及汉化的佛教,也在高昌传播。
在9世纪晚期到10世纪初期左右,高昌回鹘归依了当地盛行的佛教。柏孜克里克成为回鹘高昌王国的王家寺院,历代高昌王及王后修建洞窟用于礼拜,同时在高昌王室的支持下,回鹘王国开凿洞窟、修建寺院、彩绘壁画、翻译佛经、讲经颂法、蔚然成风。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贸易集散地,高昌王国经济繁荣,国势强盛,地域东接河西走廊,西到龟兹,北越天山与准噶尔盆地的南缘相连,南隔大沙漠与和田相邻,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佛教发展达到鼎盛之时[5]。
3.2 高昌回鹘佛教的多元性
吐鲁番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古代先民以博在的胸怀,兼收并蓄吸收了多种文化艺术之长,创造了本地区、本民族独特的高昌回鹘佛教艺术。高昌是多种民族生活的地方,如古代的姑师、汉族、高车、柔然、吐蕃、回鹘等民族都曾在此生息繁衍。同时,中亚栗特人、印度天竺人、龟兹白姓人等也在此生活。这里曾流传过多种宗教,萨满教、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等。这里曾出土了汉文、回鹘文、婆罗米文、西夏文、梵文、藏文、突厥语、波斯语、叙利亚语等17种文字拼写的24种语言的各类文书。高昌石窟佛教艺术因受到诸多方因素的影响,并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与融合,内涵丰富多彩,形成具有多元性的艺术特色。
3.3 相邻地区佛教文化的相互影响
高昌位于龟兹与敦煌之间,在佛教沿丝绸之路东传途经吐鲁番传播的过程中,融入了来自龟兹的文化和艺术风尚。同时,汉传佛教的向西的回传,又给高昌注入了黄河长江文明下的文化艺术传统。外来却扎根于中国文化的佛学,深深影响着高昌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这种多元性的文化元素,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融合在一起,创造了瑰丽多姿的高昌石窟艺术。
3.4 佛教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在传承了麴氏、西州到回鹘时,期而成为王家寺院,在保留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同时不难看出形成与发展的脉络。麴氏高昌王国时期,高昌石窟壁画受到了来自于波斯、印度、龟兹等画家绘画的影响较多,在佛教早期传播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壁画边饰图案的连珠纹饰、仿汉地木结构的平棋图案、“小字”脸、佛座背光“蛇”的浮雕造型等。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经过吸收融会贯通后,隋唐时期进入独立创新阶段,摆脱了佛教原有的框架,开始构建中国佛教的新体系,它的特点是更多地结合中国社会传统的实际,建立宗派,使佛教教义更进一步结合中国国情。宋元明清以后此一时期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得更紧,形成三教合一,以儒为主导的局面持续了近千年,形成儒化佛教,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汉传佛教善于随着时代发展而随时变易,充实其内容,能够与中土主流思潮配合,取得生存、发展,并以自己的思想影响、丰富中国本土文化。随着汉族的大量迁入,以及中原王朝的有效统治,柏孜克里克石窟受到汉传佛教影响,也融入高昌佛教艺术之中。尤其是绘制壁画的工匠,大多来自当地的汉族,即使在回鹘王国时期,绘画者依然是那些汉族画匠,他们利用娴熟的绘画技巧,将回鹘佛教与汉化佛教有机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昌回鹘佛教艺术。
4 结束语
高昌石窟是经历近千年的漫长岁月逐渐形成的,内容丰富多彩,在时间上相互蝉联,是一部完整而形象的高昌佛教史和艺术史,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高昌石窟是古代生活在这里的汉族、吐蕃、回鹘等民族共同创建的历史丰碑,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民族风格的典范,彰显了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吐鲁番是多民族、多宗教和平共处,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昌盛的盛况。吸收融化各种艺术营养,促进了民族艺术的发展,创造出独特的具有中国地方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彰显了历史上中国各民族审美理念和艺术风格。
柏孜克里克石窟从开凿以来已经1 000多年,先后经历了人为和和自然破坏,那些幸存下来的壁画,至今仍向人们展示了古代文明的风采,见证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再现了吐鲁番回鹘高昌王国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吸引了当今世界各地研究佛教历史、佛教艺术的专家学者们的眼光,是研究我国佛教史、佛教美术史、民族史的历史依据和实物资料,具有无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