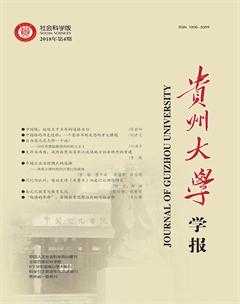失序与再造:咸同兵燹与清水江流域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
李斌
摘要:
在清代“咸同兵燹”这样社会大动荡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如何自救、如何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成为有识之士思考的问题。文章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民间文献,以流域“三营”为具体对象,分析在“咸同兵燹”期间清水江流域的乡村社会组织从款组织而演变为团练,团练在组建及其经费筹措、所产生的作用及其影响,进而探讨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在社会动乱中的自我治理,并从中发现了一些对当今社会仍有一定借鉴价值的治理举措。
关键词:
款组织;三营;清水江流域;咸同兵燹
中图分类号:C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4-0053-07
Disorder and Reconstruction: Wars during Emperor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Order in Qingshuijiang Area
LI Bin
(Kaili College, Kaili, Guizhou, 556011,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urbulent war period from Emperor Xianfeng to Emperor Tongzhi, learned people considered how to realize self ̄savings of country society, how to maintain local social stability. To analyse the influence and function of regional country organization which developed from Kuan organization to Tuan org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uan organization, its raising finance during wars, the article concentrates on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together with other local documents, through specific study on “three battalions”. Thus, to further discuss self governance by country society in social turbulence, and figure out some useful governance measures for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Kuan organization; three battalions; Qingshuijiang area; wars during Emperor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
“款組织”作为清水江流域苗侗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在维护乡村社会平衡与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咸同兵燹”期间,作为团练的杰出代表——“三营”,成为清水江中下游地区对抗张秀眉起义军和姜应芳起义军的一支重要力量,通过武力对抗等强制性措施来恢复地区的社会稳定。
一、“咸同兵燹”及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1850年代,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贵州各地先后爆发了少数民族领导的起义。其中,尤以台拱(今台江)张秀眉等领导的“咸同苗民大起义”、清平(今凯里)岩大五领导的苗民起义以及天柱姜应芳领导的侗族农民起义声势最大。1855年4月30日,张秀眉在台拱起义,张老九(九大王)响应于偏寨,高禾、九松继起于乌结,出现“千里苗疆,莫不相应”的局面。在起义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攻下凯里、施秉、清江、台拱、黄平、清平、古州、都匀等府厅州县城。到1858年,攻克黔东门户镇远府。随后,兵分两路。东路攻柳霁、天柱,出邛水,经青溪、思州、玉屏,直抵湖南晃州、会同、靖州。西路出平越、贵定、瓮安、龙里,直逼贵阳。面对丢城失地,湘黔“莫不震动”。
地方碑刻文献史料也有许多相关破坏情况的记载。如锦屏《彦洞记述碑》详细记载了咸同时期张秀眉、姜应芳等起义及战争破坏情况,“清(江)、台(拱)异类,苗性犬羊,于咸丰四五年,怀吞业之恶念,起骗账之狼心,蓄造叛逆,肆行滋扰”。“同治元年勾结教匪姜映方,盘距汉寨,山名呼为九龙山。擅造旗帜、王号,自称定平王,破陷天柱,抄出平秋、石引,使我首尾难应。所仰黎平府宪,府宪遥阻莫救;所慕附近苗光,苗光自雇不出。仅只我卡四面受敌,独力苦拒,从四月二十七日击至五月十六日,药完铅尽,难支败走,被逆杀追岑顿、大平、中仰一带,房廊概被烧毁,人民受尽戕殃,哀声满地,铁石难闻。”“至同治三年六月初二日,逆苗乘危而害,团因灾而莫雇,卡练惊奔,被贼又烧一次。”“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被贼又烧一次,尸骨充塞道路,血滴成渠。”“陈大六聚扎江口屯,自称陈大帅;杨万洪把住滥木桥,自号公平王;关将军盘距寨头,时出时入;宝元帅霸占硐却,肆横无忌。”“想我黎民遭此乱世,前后十有余年,受尽许多苦楚,八口之家无一口得耕,八亩之田无一亩之得种,出力者吐尽血浆,出资者捐尽家业,为国捐躯,身归黄壤,欲待罪因忠结恨,无门招慰,亦不安。”
《彦洞记述碑》(光绪二年),碑无额题,笔者根据内容所加,碑现立于锦屏县彦洞乡彦洞村。
据剑河《流芳百世》碑记载,“咸丰乙卯之秋,贼风竟起,猛兽挺生,由革夷高禾、九松、方乜,下自清枱张秀弥、包大肚、杨大六此等逆魁,三五成群,千方结党,烧杀乡村,攻打屯堡”“壬戌年,忽有柱属姜、龙、陈、李四逆窜入抬邦,协合主叛,引领攻下柱邑,设营九龙山,兹扰各属,惨遭其害,鸡犬不宁。”“大寨复原其半,小村十仅存一,迭重受害,苦不尽言。”
《流芳百世》(光绪六年),碑现立于剑河县敏洞乡沟洞村。榕江县《瘗骨碑序》记载了朗洞地区深受战乱影响,“朗城自咸丰丙辰遭兵燹,而后吾民、墟墓同毁于苗,烽火蔓延垂二十载。”
《瘗骨碑序》(光绪二年),碑原立于榕江县朗洞镇,后被移至榕江县城红七军军部旧址后院。
二、传统款组织及其演变
款组织由一个或多个自然寨联合组建,跨地方圆数十公里,村寨之间有严密的组织形式。款有款规、款约。“款”是寨与寨之间结成的防御和反抗外来侵扰的组织形式,由村寨自愿参加,有“大款”“小款”之分。“小款”由周围几个家族或村寨结合而成,“大款”也叫“团”,由若干个“小款”或乡村甚至区域结合而成。寨子大、户数多的一寨为一款;寨子小、分布邻近者,或三五寨、或数寨为一款。款组织结合并非长期不变,其格局经常有变。大小款都有“款首”,少则一人,多则数人。小款“款首”由各寨寨老公推,大款“款首”由各小款“款首”選举产生。“款首”由热心公益、有威信、组织能力强的寨老担任,无特殊报酬。一般每年“议款”一次,各户户主参加,商讨款内有关事宜,制定“款约”。“款约”主要内容多为惩罚盗贼、内奸、恶棍,保护农林生产,消防,解决财产纠纷等。公议后的“款约”一般都会勒碑立于寨门等显眼处。“款脚”鸣锣喊寨,宣讲“款约”并督促众人共同遵守。秋冬时,各户凑钱凑米到款首家会餐一次,总结当年执行“款约”情况或修订条款,俗称“吃款”。各寨各姓各户,不分贫富,男性青壮年必须参加团款组织,每人自备武器一件,或长矛、大刀,或鸟铳、火枪;平时,还要随时配备草鞋一双,有事则立即上路。每年各小款首带本款人员在约定日期集中,相互检阅各寨的武器装备,称为“亮团”。
款组织定有款规或款约,用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习惯,具有较强的法律威力。款约款规是由公众共同制定的“法规”,凡合款的村寨必须共同遵守,不得违反。其作用和任务是:对内保护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调解纠纷,维持地方秩序;对外抵御外辱,彼此相援。大款一般在山坳上设有哨卡,轮流守望,有警即鸣枪为号,各寨鸣锣聚众,寨老带队出发。一旦发生对外争斗,只需闻报,各寨迅速集中,适应出征者都视为己任,人人乐从,各个争先,生死与共。
清水江流域有众多款组织,较大的有青山界四十八寨、湘黔边四十八寨、九寨(今锦屏县境内)、婆洞十寨(今锦屏县境内)、黎平高东款、注溪十八寨联款(今天柱县注溪乡和蓝田镇的侗族村寨)等。
湘黔边四十八寨具体是指哪些村寨,没有完整的记载。据龙更清收集整理,分上二十四寨和下二十四寨,位于今天柱、锦屏和湖南靖州一带。
龙更清:《“四十八寨”的由来》,《天柱苗韵》(内刊),2010年第1期(创刊号)。有关四十八寨中具体寨子的范围、名称等各种文献记载很不一致,有的记录的具体寨名超过50个,且范围均在今天柱县境内,如《物华天宝——天柱风物录》(天柱县政协文史委编,2001年内部印刷本,第243页);有记载包括今天柱县30寨、锦屏县6寨、湖南靖州12寨(天柱县政协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编纂委员会编:《天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4页),位于今天柱和锦屏境内,面积约140平方公里,现有人口近2万,苗族占90%以上。分上二十四寨和下二十四寨,包括地坌、菜溪、窑田、翁冲、妈羊、高坡、栗木坪、下粮田、豆墦脚、兴团弯、马路村、杨家、秀田、竹寨、刘家寨、荒冲、黑岩脚、老硬冲、翁晒、棉花坪、汉冲、牛田口、淘金、架枧、新寨、矮寨、湳头、坌处、宰贡、清浪、勾刀、偏坡、地冲、雅地、三门塘、大冲、铜鼓坡、盘溪、孔阜、地抑、旧楼、圭井及今锦屏县的平金、乌坡、亮江、银洞、合冲、令冲等四十八苗寨。靖州、天柱各有二十四寨,其中包括靖州由一里九寨(地笋寨、地背寨、菜溪寨、岩咀头、地庙寨、黄白寨、弄冲寨、万才寨、水冲寨),靖州由二里六寨(小河寨、皂绿寨、孔洞寨、排洞寨、官田寨、铜锣寨),靖州寨市里,统称三锹九寨(烂泥冲、圹保寨、高营寨、大溪寨、银万寨、圹龙寨、楠木寨、三江寨、高坡寨)。天柱由义里(今竹林乡、坌处镇)二十四寨,包括“上六寨、中六寨、下段十二寨”,其中,“上六寨”即茅坪、亮江、银洞、平金、合冲、乌坡,民国三年锦屏建县时,六寨由天柱划归锦屏;“中六寨”指的是,雅地、偏坡、中寨、抱塘、龙家冲、水大溪(1952年划归锦屏);“下段十二寨”指的是湳头寨、新寨、棉花坪、竹刘寨、下粮田、高坡寨、栗木坪、秀田寨、杨家寨、地坌、菜溪、妈羊。
青山界四十八寨是锦屏、黎平、剑河三县交界地区的大款,其范围100多平方公里,苗族聚居,包括今锦屏县24寨,即苗吼、培亮、宰格、苗庄、苗里、扣文、九丢、晚楼、美罗、控俄、格朗、卑祚、苗亘、瑶光、苗馁、文斗、平鳌、彰化、塘东、番鄙、摆尾、格翁、锦中、中仰,黎平县22寨,即己得、己迫、乌潮、己迫上寨、岑同、乌腊、苗丢、高下、苗举、唐错、平空、高仲、高练、塘朗、岑己、格东、八东、平信、岑弩、岑拾、苗格、鄙栽和剑河县2寨,即高椅、康中,共48个苗族村寨。
九寨位于今锦屏县西北部,面积约210平方公里,侗族聚居,由王寨、小江、魁胆、平秋、石引、黄门、瑶白、高坝、皮所9个大寨子组成大款。
地处九寨的彦洞属中林验洞长官司管辖,不在九寨之列。每一小款又包括若干子寨,如平秋款,以平秋为中心,包括圭宿、富库、开了、更我、盘寨营、更豆、兰托、洞万、略威、桥问、大坝、晓岸、岩有等村寨。魁胆款以魁胆寨为中心,包括平翁、孟寨、凸寨、破鼎罐、各龙、圭开、三德、平岑、石桥冲等自然寨,因咸同年间组织十六甲,故亦称“十六”甲。
黎平高东款,辖高孖、大稼、高培、高面、邓蒙、荣咀、平途、盘现、岑奉、岑柳、腊亮、姚枝上、平空、革东、唐旧、俾雅、高绍、高重、高殺、高练、唐朗、唐赖、归奉、归坟、高梦、丈巴、基兰、岑胡、宝塘山、纪迫、纪德、党觉、岑同、岑优、格韶、平底、周家坪、乌勒、下八里、岑泵等侗族、苗族和汉族村寨,包括现在的大稼乡、平寨乡以及孟彦镇的岑湖、高秋等村寨。
其他如婆洞十寨是以今锦屏县启蒙镇者蒙村为中心,包括边沙、流洞、魁洞、者楼、者抹、便晃、寨五、八教、西洋店10个寨子组成的大款。注溪十八寨联款是由今天柱县蓝田、三合、两坌、贡溪、翁溪、蒲溪、双溪坪、坪坤、塘涧、闪溪、碧雅、风阿、德江、公闪、关坪等18寨组成的“联款”。清道光年间,盗匪猖獗,百姓为自保在黎平府所属西北部地区组成六合团,其中纪德为一合,纪迫包括高倚、党脚为一合,乌朝为一合,堂灼为一合,格朗、扣文为一合,岑同、平空为一合,共六合,统称六合团。
不同款之间,有时是有交叉的,如青山界四十八寨与高东款,重叠的村寨就有平空、高仲、高练、塘朗、己得、己迫、乌潮、岑同等。
三、经费之筹措:以三营为中心
清朝咸同年间,台拱张秀眉和天柱姜应芳等苗侗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反抗清庭压迫,出现了“千里苗疆莫不响应”的局面。面对混乱的局面,清水江中下游地区士绅们在官府的倡导下,纷纷寻求自保,在款组织的基础上组织团练,“三营”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它以锦屏文斗为中心,辖地30个村寨,包括今天锦屏河口、平略两乡镇,当时人口近3 000户,近20 000人。“三营”以原始款属村寨为基层,由上、中、下营组成,直属黎平知府。营以下以村寨为单位设团。营设总理,为最高指挥官,由黎平府任命。此外,还设协理、书办等。“上营”由瑶光文举人姜吉瑞率领,统辖瑶光、韶霭、塘东、格翁、锦中、苗吼、培亮、甘塘8寨,以瑶光为中心,团丁驻扎甘塘坳;“中营”由文斗武生姜含英率领,统辖文斗上下寨、平鳌、岩湾、加什、中仰、九佑、彰化、南路、鸠怀、丢休、松离12寨,以文斗为中心,团丁驻守大坪九岗坡;“下营”由河口武生姚廷桢率领,统辖甘乌、八洋、平略、新寨、岩寨、寨早、扒洞、岑梧、高贞、归固10寨,团丁驻守高贞坡。
“三营”的足迹遍及清水江中下游以及都柳江一带,包括今锦屏、剑河、天柱、黎平、从江、榕江及湖南靖州等县。“三营”共扎营25座,各寨与外相通的每条大路津要处都设有关卡,在村寨周围筑工事、布竹签阵、修寨门,在高处修烽火或瞭望台。一寨有警、各寨相救,一营有事、三营齐帮。至今,在文斗、平鳌、瑶光等还保存有寨门、围墙、烽火台等。
为使团丁乐于效力卖命,同时能保证后勤供应,“三营”制定和并实行“抽田制”、按户派捐和认捐等三种方式筹集经费。
一是抽田制。规定:凡有田者,将其三七开分,田主留其中之七,其中之三交给团款(村寨)安排给出力征战者。出田、领田者都要与总理或村寨团首签订交、领田合同,出田者永不得追回其田,受田出力者战死无怨。所需粮饷,仍照原有田亩和实际家庭情况从富户进行摊派。富户如有隐瞒田产或拒派,则要受到重罚。“自至人人欣愿,众志成城。”
《三营记》成书于光绪十九年,系手抄本,由中营书办平鳌人姜海闻著述,中营总理姜元卿作序。有关《三营记》的内容,详见姜高松:《文斗苗寨》,2011年内部印刷本,第132-144页;又见《贵州档案史料》2001年第1、2合期,第78-88页。
据立于咸丰九年(1859)锦屏瑶光上寨《万古流传》碑记载:
尝思诗咏同胞,书云同德。当兹干戈扰攘之际,难取其一视同仁也。咸丰五年,清抬苗乱,攻城劫堡及南加焉,而我境安堵无恐,弗遭荼毒,非仗地脉龙神之庥乎。六年冬,扰及黎邑,一十二司相继变心。我九寨同仇偕作,决战于婆洞地方,三战三捷。我里大众力解城围,地方富户欢腾眉睫,愿将田亩存七抽三,酬出力劳。我上甲兄弟四十余家,将抽三田,共留十担,地名九党田六丘,永祀后龙龙神及南岳香火,以垂久远。是为记。
军功姜应兴、军功姜凤歧、姜述维、姜应相、姜乔龙、姜老毛、姜老凤、姜述理、姜安邦、姜恩荣、姜添寿、姜富洪、姜丁贵、姜五生、姜绞寿、姜丙祖、姜三龙、姜应生、姜保寿、姜乔成、姜丁卯、姜继林、姜丁寿、姜成生、姜生龙、姜岩乔、姜木生、姜丁福、姜一保、姜恩高、姜发祖、龙老福、姜凤鸣、姜凤生、姜乔贵、姜乔生、姜继宗、姜光才、姜发恩、龙召光。
此神地二间,姜恩良、□□捐。
匠人唐文清
写碑人吴必魁
咸丰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立
《万古流传》(咸丰九年),碑现立于锦屏县河口乡瑶光上寨。
据锦屏《彦洞记述碑》(光绪二年)也记载了九寨团练筹款情况,“幸我黎平府主多札饬我寨罗兴明充当乡正,倡连九寨合为一款,贫者出力,富者出资,各寨各招长勇十五名,公议卡首杨积瑶调户编棚,防堵犁元大凹,卡名呼为验洞卡,团名号曰太和团,无事长勇堵御,有事一踊抵敌。”“蒙府主徐札我寨团首等设局定章,照货价值轻重,每百抽钱二文”。
《彦洞记述碑》(光绪二年),原无额题,笔者根据内容所加,碑现立于锦屏县彦洞乡彦洞村
在文斗和平鳌有两份关于抽田办团练的契约文书:
契约1
立分合同字人塘東、河口、加池、岩湾、文斗上下两寨、平鳌、中仰、韶霭、干塘、大坪界上款内众等。因逆匪逼近款地,众等公议设立,将各地方有田者三七均派,业主占七股,出战出力者占叁股。众境有无得力同心,如翌日匪徒一战尽殄,复转屯所业。现有田者首四股,出力战斗者受六股。其中富户米粮见丁除八石,一则曰永清四海,再则曰国泰民安。恐后无凭,人心不古,立此合同字,永远存照。
塘东姜朝魁、姜沛霖,河口姚廷桢、姚廷煊,加池姜世明、姜沛清,岩湾范本清、范玄祖,文斗姜含英、姜钟英,中仰陆景嵩、潘国干,韶霭李国梁、龙家琼,大坪干塘孙鱼龙、黄世刚、吴绍春。
咸丰六年十二月初九日众等公立
契约2
立抽田字人姜东仪、之玕、上锦、国干、启先、姜卓、东吕、东滨、德清等。为因贼匪作乱,扰害地方,富者出资,贫者出力。无如地方穷苦,无资所出,富户情愿将田叁柒抽给。出田者占柒股,受田者占叁股。除上田在外,余者照谷石出叁与众抵贼。自抽之后,任凭受田子孙管业。所有贼匪临境,官府提调随传随到,不得躲闪萎靡退缩。如有此情,将田退出充公,逐出境外。凡开仗有损伤者,抚恤俱在叁股田之内。今欲有凭,立此抽田字为据。
凭中:乡正文清国干
存字人:则相 国望 文光 东佐
代笔:姜子清
咸丰柒年柒月初五日姜作弼笔立[1]
从上述三段史料来看,至少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富者出资,贫者出力”原则;二是“存七抽三”原则。在两份契约中,分别有11寨和8寨的人参与立约,其中包括“三营”中首任中营、下营总理姜含英和姚廷桢以及中营第三任总理陆景嵩。
二是按户强行派捐。这一规定不仅仅是适用于“三营”,清水江流域其他地区莫不如此。如天柱中和团系“照粮摊派,每石粮出米一石按当为一斗,出钱四千文。”天柱保安团则“上户派钱二百串,中户百五,下户八十,花户照粮一斗三升,统名军费”。
黄峭山樵:《天柱县五区团防志》,第7-8页。在锦屏亮司,“見十抽三,司內共抽田八百余石养练兵,各司內外共抽田七千余石。”
锦屏(同治)《本支家乘迪光录》卷四《纪乱》。
据《本寨众人卖清河塘约》记载:
立卖清河塘约人。本寨众上人等因为红苗作反,老爷派我寨火绳八盘,众人无处出处,众上自愿将河边地名塘叫做顽列出卖,与亦本寨姜廷德名下承买为业,当日议定价银四钱整,银契两交,不欠小厘。自今以后,任凭廷德下塘毒鱼管业,而寨内人等不得异言争论塞塘之事。今欲有凭,立此卖字存照。
中人: 姜文德、文献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日书[2]
这一则材料反映了乾隆末年湘西、黔东腊尔山区爆发苗民起义( 即乾嘉苗民起义) ,官府向清水江流域苗民摊派军需物资,加池苗寨需交火绳 8 盘,由于无银筹办,只得将本寨公共池塘出卖与地主姜廷德的情况。而《龙氏迪光录》也记载铜仁府石柳遁爆发农民起义后,亮司 “殷实之户”也要“派买军马”一事,“嘉庆元年,铜仁府红苗石柳遁反,亮寨司殷实之户派买军马,赴营听用,各户计亩运送军粮至麻音塘交代。”
同②。
这也算是体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了。
三是捐资也是筹措经费的方式之一。
《姜兆璋等领捐田字》记载了地主捐田办练的情况。
立领捐田字人姜兆璋、玉光、兆清、开周、凤克、开望、开廷、开庆、玉连、龙文明,头敌共叁拾六人,与站墙众寨人等,为因贼匪临境,扰乱烧杀村寨,殊堪痛恨。我等挑选精壮练丁弟兄叁拾六人,与众寨努力抵敌,连获捷胜,奏凯而还。今贼匪四散,蒙众头公将本寨姜世泰、世道、世显、世泽、世明、克昌、遇昌、沞清、兆珊、宗保、显弼等并寨内所有多少之田,见十抽三,打头敌之人占两股,站墙之人占一股。自今抽出,日后不得再捐。如有日后贼匪仍行扰乱,打头敌之人与站墙贫富众寨,听从头公随时调遗(遣),奋勇争先进剿。以上数条,我等情甘自愿,绝无抗傲躲闪,如有抗傲躲闪,我地方将他屋宇并所抽占之田尽行充公,并无怨言。恐后无凭,立此领抽捐田字为据。
乡正:姜世太、世明、大荣
妙白老抽单世明乡正收
凭中:高老五
咸丰七年二月初九日,世元笔立[3]
四、清水江流域社会秩序重建之效果
清水江流域地方乡绅通过捐资等方式,成为地方团练武装的主导力量。作为三营的核心和中坚力量——“中营”,其团务基本上是由姜氏宗族担任。三营设立时首先由姜含英总理,咸丰八年(1858)三月被地方官府札保“赏戴蓝翎”,不久“因团劳卒”。姜含英的堂弟姜弁英继任总理,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姜弁英“劳故”。中仰寨的陆景嵩接任,一年后请辞。“总理中营团务”的重任又落到姜名卿手中,姜名卿是姜含英的长子。可见,姜氏宗族在对抗“咸同兵燹”中所发挥的作用。姜氏宗族中或因军功加官进爵、或子弟入学补廪,或捐监拔贡,屡见不鲜。姜含英之子、姜名卿之弟姜佐卿在《姜氏族谱》中写到:“同治四年,选哥与佐咸捐例贡。越年,佐以军功保五品顶戴。平靖后,八弟元卿、十弟贵卿次第入学补廪;癸酉(即同治十二年),元弟选拔,名哥改捐同知。”
锦屏《姜氏族谱·世系纪略》。通过参与地方事务并发挥主导作用,姜氏宗族的地位和权势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锦屏县河口乡文斗村,现存有五通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诰封碑”,分别是姜兴渭(姜含英之父)、姜含英的神道碑,姜母姜宜人(姜兴渭长媳、姜含英兄毓英之妻)、姜母姜宜人(姜含英之妻、姜名卿之母)的神道碑以及姜母范孺人(姜佐卿之妻、姜德相之母)是节孝碑,足见姜氏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地位和影响。
“三营”从咸丰六年(1856)组建到光绪十二年(1886),先后出战70余仗,辉煌战绩有三解黎平府城之危、四救柳霁县城(今剑河县南加镇柳基村)
柳霁县是镇远府天柱县的分县,雍正十二年(1734年)建土城,乾隆元年(1736年),分天柱縣丞驻柳霁,仍属清江厅;乾隆二年改建石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撤。、三救锦屏县城(今锦屏县铜鼓镇)、协助清军围攻姜应芳起义军的根据地——天柱九龙山。正因为有如此功绩,朝廷对“三营”有功人员大加封赏。如“上营”总理姜吉瑞赏戴蓝翎分发湖南候补知县,“中营”总理姜含英、“下营”总理姚廷祯赏戴蓝翎免补把总以营千总补用。
笔者在锦屏县平略镇南堆村收集到一份民间文献,称:李秀精因“奋勇出力、屡见奇功”,赏篮翎五品顶戴。其曰:
为给发功牌事。照得本兼署部堂查有府属南堆寨李秀精奋勇出力、屡见奇功,合行给发功牌,此牌仰该军功遵照准此用篮翎五品顶戴。如能再行立功,随时赏,务奋勉,不得籍牌生事端。切切须牌者赏。
右牌给篮翎五品军功李秀精准此
咸丰十年八月十九日
兼署总督部堂行
《兼署总督部给发功牌事》,该文书由笔者收藏,锦屏县三江镇李宏斌先生提供,李宏斌系李秀精的第7世孙。
笔者在剑河县南加镇收集到一份民间文献,称:杨顺思“练团勤慎,堪以赏给五品顶戴”,如今后又立新功,“再行升赏”。
钦命督办军务兵部尚书总督部堂署理贵州巡抚部院张
为给发功牌奖励事。照得本部堂督办军务,凡有在事出力人等自应择尤奖赏,以示鼓励。查有军功杨顺思练团勤慎,堪以赏给五品顶戴。除录案咨部外,为此牌仰该弁遵照祗领,如后有功,再行升赏,务各奋勉图报,不得籍牌滋生事,切切须至功 牌者。
右牌给五品顶戴杨顺思 准此
同治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督部堂
《贵州巡抚部院张为给发功牌奖励事》,笔者2011年7月31日在剑河县南加镇收集,文书由培由村杨再余族长保存。
即使在“咸同兵燹”之后,苗疆社会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但在应对盗匪时也需要“家家相劝惩,寨寨相联络”,需要“一家有惊,合家救之,一寨有惊,合寨救之”。因此,“三营”这一地方团练组织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光绪二十年(1894)时,由于匪患严重,“三营”重整规条,议定款规九条,足见“三营”影响之大。
谨将上中下三营合□□条开列于左
盖闻团规不整,虽有守望相助之心而约束恐懈。约束既懈,虽有和衷共济之志而元气已伤。所以欲培元气,莫善于严。约束欲□□□,莫先于整团规。如我上中下三营地方。近来盗匪横行,不独团中受害,即邻近往往遭劫,总因人心涣散,团练不行,故耳。于是特邀集三营绅奢人等,合其大款,重整团规。会议禁条,使家家相劝惩,寨寨相联络,以期闾里,无所容奸。而地方渐臻醇模矣。
一议联团。实为保卫□□□,前此先辈,创立之初,整齐约束,能彼此相顾。近来团规不整,人心涣散,固此盗匪横行,不独孤村受害,即大寨亦往往遭劫。我们大家齐心,从今大众,誓整顿器械,方是备御事体。倘遇盗匪来寨抢劫,拿获贼盗,大家自逗柴一块,定将贼身,全将火化。
一议和款。原期痛痒相关,我们情同共揖,唇齿相依。一家有惊,合家救之,一寨有惊,合寨救之。相交相助,毋稍躲闪,竟分畛域。自议之后,愿大众齐心,家家相扶持,寨寨相联络,并无殊于此界彼疆,则外匪闻风远遁,而地方乐业相安矣。
一议地方闻盗。惊偷劫谁家,左右街邻,宜各协力相救,奋勇拿贼。万一贼势凶杀,鸣锣呐喊。大家齐心捕捉。倘或视抢劫,定是与贼通同舞弊。谚云:一家有事,拖累九家。被贼失物若干,众团坐问邻右坐视□□□还。如遇家贫如洗,不能赔还失主,大家禀官究罪。
一议不准停留面生歹人。窃拦路打劫,明火掳抢等蔽,缘近无窝家,强盗不能展翅飞来。此后凡遇面生不识之人,无论火铺人家,必问姓名来历,方准住宿一夜,不可久留。至于游食乞丐,三五成群,可怪之人,立地驱逐。如有敢犯,一經发作,大众定将窝家罚处。如此则究无容,而贼亦可息矣。
一议不准聚赌博之流。始则十百,继而千万,不可限量。输者无钱偿还,势则偷盗。又其甚者,相通(逼)太过,彼此持刀斗杀,酿成人命,连累地方,为祸不少。此后不论大小子弟,各家父老劝谕,毋使聚赌顽(玩)钱,各劝正业。如此敢犯,一经发作,众款罚钱叁千叁百文。当窝家,不独众声罚处,而且报官究治。
一议不准偷田园谷菜,并杉木油树。窃我地方山多田少,谷菜固是养命之源,杉木亦属资身之宝。不知费劲艰辛,而后栽植得出。此后遇偷窃贼赃两获者,大众罚钱壹千叁百文,仍将贼人声传大款,议连者逐出境外。
一议不准放火烧山,以及放浪牛马羊。盖山靠有水,田靠有埂,园靠有菜,各勤栽种,养活身命。此后如有烧山者,大众给报口钱壹千叁百文。照烧山多少议罚。契杉木者,每蔸罚钱壹百文。至契木菜者,仍照罚钱壹千叁百文,概归款内。
一议婚姻,宜从古礼。近□□□□甚。先辈求亲,祇已请男媒为说,即得一话。不放多炮,亦不杀猪只。至于过门,不是至亲友谊,不必贺赠木联,省此浪费。果是至亲友谊,宜琢料木联,方成体面。幸为劝勉,是为厚望□也。
一议油山费尽工苦。不许入山砍伐,以放捞为名,患意强捡。所有放捞,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倘敢固犯者,罚钱叁千叁百文。
实贴晓谕
光绪贰拾年四月初八日特谕[4]
从上述材料可知,清水江流域宗族在应对苗疆社会动荡以及猖獗的匪患时,以传统社会组织形式为基础,在政府无钱可出的情况下,采用“抽田”等形式筹集经费,兴办团练。正因为有经费保障,才使得地方团练很有战斗力,成为对抗“咸同兵燹”、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在“咸同兵燹”期间,清水江流域以宗族或村寨为核心,组织了众多的地方团练组织来抵御社会动乱,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如在天柱,咸丰九年(1859),保安团在坌处率先成立。此后,各乡里纷纷效仿,先后建立了新三团、江东定清团、太和团、水洞中和团、牛场三和团、远口聚星团、邦洞团、蓝田团、北岭团、兴隆团、协和团、杨山团等民间武装组织,团首均由当地乡绅担任。在天柱县的团练中,实力最强为坌处保安团,次为远口聚星团、江东定清团,他们与农民起义军对抗多年,在处理咸同时期清水江下游地区的社会变乱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概言之,不管是在“生苗”或“熟苗”地区,在王朝势力进入之前,地方乡村社会主要依靠传统的社会组织如议榔、款组织等进行治理。王朝势力进入之后,也要依靠这些社会组织,因为“皇权不下县”。在社会动荡频发的清水江流域,以宗族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组织肩负起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功能,为保境安民而衍生出像“三营”那样强悍的地方武装势力。
参考文献:
[1]王宗勋.清水江历史文化探微[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3:35-36.
[2]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一辑: 3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7:9.
[3]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一辑:4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20.
[4]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一辑:8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69.
(责任编辑:王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