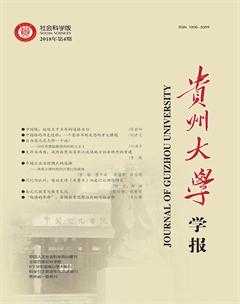麻山苗族“亚鲁”吹打乐复兴传承研究
梁勇 袁伊玲
摘要:
贵州麻山地区的毛龚“亚鲁”吹打乐的复兴传承,是民间音乐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得以传承的代表个案之一。以“局内人”的身份通过多年不间断的田野考察,认为表层因素的主客作用和深层因素的身份认同与传统礼俗是毛龚“亚鲁”吹打乐复兴传承的重要条件,文章就上述条件对其复兴传承的具体体现逐一展开论述。
关键词:
“亚鲁”吹打乐;主客作用;身份认同;传统礼俗;复兴传承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4-0108-05
On Revitaliz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Hmong Yalu Wind Instrument
and Percussion in Mashan Area
LIANG Yong1, YUAN Yiling2
(1.Colleges of Arts, Anshun University, Anshun, Guzhou, 561000,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Hubei, 443002, China)
Abstract:
The revitaliz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Hmong Maogong Yalu wind instrument and percussion in Mashan area, is a typical case of the successful transmission of folk music und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s an engaged one, the author holds that subject and object function belonging to surface factor, identification and traditional customs belonging to in ̄depth factor are both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Hmong Maogong Yalu wind instrument and percussion, according to consecutive year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article aims at discussing the conditions above embodied in specific performances one by one.
Key words:
Maogong in Mashan area; Yalu wind instrument and percussion; subject and object function; identification; traditional customs; revitalization and transmission
在現代化进程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推进的三大浪潮下,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采取何种应对举措,使传统文化得以“逆境重生”成为当下民间大众、社会学界和政府机构的当务之急。近年来,地处贵州省麻山边远村寨毛龚的“亚鲁”吹打乐悄然复兴,成为这片贫瘠地貌上的一道亮丽民间音乐风景线。笔者来自麻山毛龚,自幼喜好音乐。如今更多时间寄栖都市,时常有“对于飘逝的往昔乡村生活的伤感或痛苦的回忆”[1],每逢节假日都要回老家跟踪调查“亚鲁”吹打乐。
一、田野点概况
毛龚隶属麻山地区,行政区划为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格凸河镇坝寨村,距离镇政府所在地(羊场村)13公里,距离县城约27公里。
毛龚寨三面环山,东面、南面和北面分别被几座大山包围,西面脚下为格凸河的水系上游。很多到过毛龚的学院派易经学者和民间风水先生,都说毛龚寨坐落区位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在300余人的毛龚寨,就有20多人在国家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工作,有人认为与毛龚的风水有关联。毛龚寨在坝寨的16个自然村寨中,坐落位置最高,在没有修通村级硬化路之前,外人常以“毛龚人三天不爬坡就要爬柱头”贬称毛龚寨的高和陡。修通硬化路后,大家觉得毛龚寨坐落位置好,反之以“一览众山小”来打消以前对毛龚的负面印象。除此之外,毛龚人重视教育的程度闻名方圆百里,这同样也为毛龚人在外赢得很多尊重与赞誉。
毛龚寨50余户人家以三块大田为界较为有序地聚居在村寨的两旁:20余户坐西朝东,另外20多户坐西南朝东北,两旁住户形成明显的“对门对户”群落特点。坐西南朝东北的20多户民居一旁有很多古城墙,并且有多栋房屋就建在原城墙内的老屋基上。2016年底,人口总数为301人,苗族占大多数,以梁姓和杨姓为主,另外还有几户王姓和韦姓。毛龚村以祭祀先祖“亚鲁”为盛,民间音乐以“亚鲁”吹打乐为主。2013年12月11日至13日,举行了规模较大的“祖先‘亚鲁祭祀”纪念活动。
二、“亚鲁”吹打乐复兴的表层因素
“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总是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和一群人来发扬一种新风气。我想,当前需要的新风气就是文化自觉”。[2]“亚鲁”吹打乐的复兴无疑就是毛龚人乃至“亚鲁”后裔文化自觉的体现。对于本文所论述的对象“亚鲁”吹打乐的复兴传承而言,这“一个地方”就是上文所述的毛龚村寨,而这“一群人”主要是毛龚人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80后中青年人。
(一)“亚鲁”吹打乐复兴的主观因素
1.推动者——本土文化的传承人
由于毛龚重视教育,十多年来已有10多位大学毕业生。通过多年跟踪调查,在“亚鲁”吹打乐复兴的过程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毛龚人,具有主要的推动作用。其中,杨正江是位核心人物,他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和人文熏陶,从小父亲给他传授苗族历史文化,他开始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产生好奇。杨正江于2001年被北京某高校录取,但是因专业不对口,意识到所学专业将来很难为自己的民族文化事业发展服务,因此读了一个学期后,就瞒着父母自动退学,翌年考取贵州民族学院(现已更名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这个专业与他的理想一拍即合。之后,他常利用节假日时间独自一人穿梭在麻山腹地,用笔和相机记录着麻山苗族文化的点点滴滴。2006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紫云自治县松山镇人民政府工作,期间不断奔走在麻山腹地了解民情民风。通过多年的田野调查,杨正江获得了大量第一手麻山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史材料。时值紫云自治县为了突破无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瓶颈,2009年初,县政府将其调到县文化局专门从事民族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在相关专家的指导和带领下,他的田野调查团队通过两年多辛劳的工作,由其负责搜集、整理和撰写的文本《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于2011年6月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自此之后,紫云县不仅突破了没有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现状,而且由此改写了苗族没有英雄史诗的历史。同时,为了更好的搜集史诗“亚鲁”的口传文本,杨正江还将自己老家的房屋作为史诗搜集整理及传承的工作站即“史诗‘亚鲁王工作站”。通过多年的努力,苗族史诗《亚鲁王》开始焕发新机,麻山苗族各种传统习俗也正在恢复。如今,《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不仅成为紫云县的一张名片,更为重要的是,麻山苗族藉此而获得了文化自信,对自己的文化更加自觉地重视和传承。在社会转型发展的今天,杨正江成了麻山苗族文化发展的一面旗帜,正引领并推动着苗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传承。毛龚“亚鲁”吹打乐正是在此背景下得以复兴传承。
2.支持者——国家企事业单位就职的本土人
民族文化的复兴发展传承,有旗帜性人物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得不到族群的响应和支持,民族文化的复兴传承发展只能是一厢情愿。毛龚“亚鲁”吹打乐的复兴,正是由于毛龚有这样一群积极的响应者和支持者。在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毛龚人是“亚鲁”吹打乐复兴传承的积极因素。
在杨正江的倡导下,2014年12月21日组建了“毛龚青年‘亚鲁吹打乐班”,并拟定了建设方案,明确了组建吹打乐班的目的,即“面对‘亚鲁吹打乐目前传承的严峻形势,毛龚青年應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过习艺、保护和传承‘亚鲁吹打乐为己任,使其得到长久地发展”;成立了学习小组,组长为杨正江,吹打乐艺人杨正合、梁正委及笔者等5位中青年毛龚人担任副组长;根据乐班人员对“亚鲁”吹打乐乐器的喜好,还对学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分工,如笔者由于较为熟悉唢呐而被分到唢呐演奏组。同样的,也根据毛龚“亚鲁”吹打乐师傅的相关专长而被分到相应的组队去教授学员;方案还明确了学习的方式、时间和地点。学习的方式有集中学习和分散学习两种,学习时间为寒暑假及全年空闲时段,学习地点在史诗“亚鲁王”工作站或自行确定;方案还专列经费来源。时年杨正江在紫云自治县文广局任副局长和“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因此经费来源主要利用紫云县文广局的民族文化传承的专项资金。经费的开支主要用于(乐)器材购买、师傅授课补贴和就餐生活费三方面。最后,方案还明确了组织要求,即“在方案小组的领导和统筹安排下,所有成员和师傅务必高度重视,积极参加,尽快学会吹打乐的演奏,日后能在各种民俗活动中担当重任,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毛龚“亚鲁”吹打乐的复兴传承,在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毛龚青年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在老百姓看来,领国家财政工资的青年人还要积极学习被他们视为老古董的“吹打乐”,这帮青年人的积极参与,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当地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和传承信心。
3.传承者——热爱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
据统计,50岁左右的毛龚人中,就有20多位 “亚鲁”吹打乐艺人,其中以(唢呐手)杨正合与梁正委组合的毛龚“亚鲁”吹打乐班最有知名度。这些中年人是“亚鲁”吹打乐承前启后的骨干力量。正是他们在年少时期与老一辈吹打乐艺人的习艺积累,才使毛龚“亚鲁”吹打乐未出现断层,并通过他们传至毛龚青年一代具备了师徒传承的重要前提。
50多岁的杨正合是坝寨小学教师,幼年时跟随父辈从宗地镇红岩村三角坪寨迁至毛龚,因为新的居住地没有“亚鲁”吹打乐队,为了能保持今后民俗活动的完整性,父亲杨再明用竹筒制作唢呐,并与伙伴杨小保根据各自搬迁前对“亚鲁”吹打乐的记忆自学唢呐。经过几年的习艺,杨再明和杨小保等人成为当时小有名气的“亚鲁”吹打乐唢呐手。杨正合从事教育工作后,为了能学到更多的唢呐知识,每有空闲就到宗地镇红岩村去拜访著名唢呐艺人韦金安习艺。58岁的梁正委与杨正合一起作为毛龚“亚鲁”吹打乐唢呐手经常参与各类民俗仪式。由于常在一起切磋技艺,如今由他俩组合的吹打乐班在麻山地区的“亚鲁”吹打乐班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新一代毛龚“亚鲁”吹打乐传人是一批20岁左右的男青年,当然他们也是“毛龚青年‘亚鲁吹打乐班”方案拟定的重要参与者。随着毛龚寨附近大力发展旅游业,这批毛龚青年人得以在自家门前就业或创业,这为他们在时间、地点和拜师等方面学习“亚鲁”吹打乐创造了的条件,可谓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前提。
(二)“亚鲁”吹打乐复兴的客观条件
传统文化的复兴传承,人的在场因素是不可低估的民间力量。同时,与民间力量相对应的“国家在场”的政府力量同样不可或缺,并且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就本文所讨论的对象而言,“国家在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更为突出。具体而言,当下国家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启动精准扶贫等政策,为毛龚“亚鲁”吹打乐的复兴传承提供了历史机遇和客观条件。本部分从发展旅游业角度,探讨旅游业在毛龚“亚鲁”吹打乐的复兴传承中的作用。
首先是格凸河风景名胜区。格凸河就在毛龚寨附近,从毛龚步行约20分钟即可到达,景区总面积约70平方公里,集岩溶、山、水、洞、石、林组合之精髓,融雄、奇、险、峻、幽、古为一身,构成一幅完美的风景图画,是珍贵的喀斯特自然公园。格凸河风景区开发至今已近20年,2005年被评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201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首批国家自然与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5A级风景名胜区。随着政府的投入和宣传,每年到格凸河风景区的游客都有增長,2016年国庆期间,景区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门票收入近600万元。因为旅游开发带来的可观收入,格凸河景区附近很多村民不用背井离乡到外地去打工赚钱养家,而是在自家门口就解决了养家糊口之大事,如毛龚就有5名青年人在格凸河风景区就业,旅游淡季空闲时间较多,在景区上班的毛龚青年王宇扬和梁忠平都会带着唢呐到景区去学习。
另外就是毛龚附近新开发的旅游景点。新开发的旅游景点主要有“世界攀岩基地”和“格凸帐篷酒店”两处,都是格凸河风景区的延伸景点。其中,“世界攀岩基地”就在毛龚寨的门坎脚下,攀岩的山即耸立在毛龚门砍脚西北面的两座大山。目前,“世界攀岩基地”的附属设施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格凸帐篷酒店” 工程项目选点在毛龚组和临寨格备组的农田和集体土地上。与在格凸河景区就业不同,这两个新开发的景区项目提供附近另外一种形式的就业,即参与项目的施工建设。同样的,也有多位毛龚青年人在“格凸帐篷酒店”工程项目参与建设,当然,在“格凸帐篷酒店”工程项目里就业,其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等都与在格凸河风景名胜区不同,没有所谓的空闲时段。但是,因为都是在自家门前就业,所以下班后都可以回到家中。因此不仅具备了学习“亚鲁”吹打乐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学习“亚鲁”吹打乐的主体可以集中在一起,并且师傅就在身旁亲临赐教。
三、 “亚鲁”吹打乐复兴的深层因素
是什么原因使麻山毛龚“亚鲁”吹打乐得以复兴传承,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一个地方”的“这一群人”去复兴并传承“亚鲁”吹打乐呢?这是下面部分我们要进行讨论的问题。
1.身份认同
有学者研究认为,身份认同具有如下方面的特点:“1.身份认同是由主观认同和客观认同组成的, 它包括人们在主观上意识到的认同和体现并显示人的社会认同的某些
客观的特征、标识码和符号(如身份证、护照等);2.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 在表层上是人们显而易见的行为模式, 在中层上是个体对于同类群体的共同性的认知和对自我身份的觉察, 在深层上是有关身份所带来的情感体验;3.身份认同是对自己所归属群体的共同性和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的认知……”[3]显然,身份认同在“亚鲁”吹打乐的复兴传承中起着内核作用。据调查及相关研究表明,“亚鲁”是西部麻山苗族敬崇的先祖,有关他的故事或神话在西部苗族口传文学中都有传颂,在丧葬祭祀活动中传唱。先祖“亚鲁”作为西部麻山苗族的共同“标识码”,藉由这个标识码,毛龚人就可以与“亚鲁”族裔建立所属群体的共同性认知和其他群体差异性的认知。因此,我们认为在西部麻山苗族中,对先祖“亚鲁”的认同是其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
文化符号的认同也是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我们在田野调查中获悉,铜鼓和唢呐是“亚鲁”文化的重要符号。比如关于“亚鲁”吹打乐中的唢呐来源,在麻山腹地西部苗族关于“亚鲁”的故事传说中的“造唢呐造铜鼓”片段就有记载:“最早是谁造唢呐?最早是谁造铜鼓?最早是善多拉木(“善多拉木”即“亚鲁”族人,笔者注)造唢呐,最早是善多拉木造铜鼓。造了十二面灰鼓,在十二个山头,造了十二个黄鼓,在十二个山崖。造成唢呐不叫,造成铜鼓不响。……善多拉木说:我杀妻子祭唢呐,我宰妻子祭铜鼓。今后把白色铜鼓叫白龙鼓,今后把黄色铜鼓叫黄龙鼓,今后把青色龙鼓叫青龙鼓。”
参见陈兴贤:《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民族古籍资料》(内部资料),第58-63页。
铜鼓和唢呐作为“亚鲁”文化的符号,无疑也是“亚鲁”后裔身份认同之客观认同的重要基础。同时由于“身份认同具有社会属性”[3],因而我们即可推知,毛龚人对“亚鲁”吹打乐的文化自觉和复兴传承,其实就是他们身份认同建构、确认和完善的必经社会属性过程。
2.民俗活动的需要
麻山苗族有很多独具特点的民俗活动,以葬礼、婚姻和乔迁最为浓重。丧葬活动的环节和仪式程序最多,在这些环节仪式中,入(棺)材、做客(即吊唁)、节甘(即吊唁当天晚上唱诵史诗《亚鲁王》的环节)和安葬这四个环节及仪式程序是不能省略的。此外还有一个环节,即给已过世的人立碑,只是立碑的时间不固定,也即是说,如果死者家属时间允许,经济宽裕,可以在“安葬”当天进行,反之则另择吉时进行。无论四个环节还是五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亚鲁”吹打乐的参与,并且每个环节都有专门对应的吹打乐曲演奏。
麻山苗族的婚姻一般包括请媒、认亲、结婚和回娘家四个过程,其中以结婚活动及其仪式为重点。结婚当天,男方内亲都要邀请吹打乐队前来演奏助兴。当然,作为红喜事的婚庆仪式乐曲,也是有专门对应的曲目,如《恭贺调》和《喜调》等。总之,麻山苗族在婚庆当日,人们是在吹打乐声及鞭炮声中共同祝贺新郎新娘白头偕老,恩爱美满。
麻山苗族“进新房”活动中的“挂红”仪式中,前来“挂红”的都是内亲,“挂红”仪式旨在祝愿东家发财兴旺。所谓“挂红”就是进新房房东内亲或要好的朋友用红布挂在新房大门或从房顶往房屋两侧长挂,并请“亚鲁”吹打乐队一起前来奏乐。前来“挂红”的吹打乐所演奏的乐曲具有一定的规约,一般而言要吹奏三个类别的曲目:第一种类别,即进入新房前要吹奏一首苗语称为“zhangf pul blad”( 汉意译“进屋调”)曲目,并且所吹奏乐曲要持续从屋外到屋内的整个过程;第二种类别,即“挂红”“亚鲁”吹打乐队进入新屋并在东家安排就坐后,演奏曲目类别即为平常红喜事(包括婚庆)所演奏的曲目;第三种类别,吹打乐队就餐后,待前来恭贺“进新房”的各方亲朋好友大都散去,吹打乐队也要即将回去,此时所要吹奏的曲目是苗语称为“zhangf heik biad”( 汉意译“多谢调”)一类的曲目,并且和进屋所吹奏的一样,要持续从屋内到屋外的过程。
四、“亚鲁”吹打乐复兴传承的思考
如何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入现代生活,是学界一直以来的期待,同时也是政府和民间共同关心的话题。近年来,在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政府制定了很多政策,如申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学界也提出了建议,重视并复兴传承传统文化逐渐形成气候。同时,如何使傳统文化融入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本地族群在思考的命题。麻山毛龚“亚鲁”吹打乐的复兴传承是一个具有典型代表的个案。
1.一个“作为传统文化自然屏障的地理环境”
贵州麻山,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有着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生态环境,这种生态成了历史上不少弱小民族在被自然、人为等多种因素的逼迫下,经过长途跋涉的艰辛,在西南高原和大山中寻觅到了更易于保存、保留自己民族文化的生态背景。”[4]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亚鲁”吹打乐的传承地域麻山毛龚寨,由于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外部文化与自身文化很少发生交融,同时又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而难以受到异文化或新文化的侵染,从而使英雄史诗《亚鲁王》及其“亚鲁”吹打乐得以较为原生性地流传至今。
2.要有热衷并坚守本族文化的一群人
毛龚“亚鲁”吹打乐的复兴传承,地域因素不可忽略,族群作用同样没有缺位。在这一族群中,杨再明及其儿子杨正合和梁正委是承袭传统的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们的先行实践,毛龚就不可能有一支属于自己的“亚鲁”吹打乐队。即使有如麻山苗族青年文化精英杨正江一样的人物出场,也无法成为文化宝库的看门人。是巧合还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原本路径,这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对的地点对的人遇到了对的事物”。杨正江就是这样一位对的人物,在传统文化亟需发展的关键时刻,成为文化传承的指路牌和警醒者。当然,只有先行践行者和指路牌的人,没有人愿意在路上继续前行,那传统文化传承也只能留于口头或书面建议中。正好在这个时候,“国家在场”即发展乡村旅游,留住了“亚鲁”吹打乐复兴传承的路上继续前行的人,如梁忠平、王宇扬和梁晓志等毛龚新一代有识之士。留住了人,就留住了文化。
3.身份认同的效用
要建立身份认同,就要有共同的文化信仰和文化习俗。对于毛龚人而言,其共同的文化信仰就是西部麻山苗族的共同“标识码”先祖“亚鲁”;共同的文化习俗,如丧葬活动、婚嫁活动和乔迁习俗等。因为“亚鲁”吹打乐是“亚鲁”文化的共有符号,因此,毛龚人复兴传承先祖的文化也是理所当然的。有学者指出,“文化身份本身不是显现的,而是蕴含于音乐的象征性行为之中的,但却是建构整个西南信仰地区音乐生活的重要核心。”[5]另外,我国的传统习俗正在呈恢复之势欣欣发展,当然,麻山苗族的习俗也不例外。而“当我们走向乡间社会看到鼓吹乐之所以为乡民们有文化认同,主要还是在于其参与民间礼俗的仪式性意义……应该明确,这种类型(原文指‘当下鼓吹乐在各级专业乐团是以乐曲的样态而存在,本文指麻山苗族很多习俗里都需有‘亚鲁吹打乐的参与)在民间之所以存在,恰恰因为诸种民间礼俗的需求所致。”[6]就如毛龚新一代有识之士所说的那样,学吹唢呐如果觉得仅仅是为了好玩娱乐的话,那可不必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现代社会娱乐的方式很多。因此,就麻山苗族习俗来看,各种习俗离不开“亚鲁”吹打乐参与吹奏的同时,也为“亚鲁”吹打乐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和养分。
参考文献:
[1]
王一川.断零体验、乡愁与现代中国身份的认同[J].甘肃社会科学,2002 (1):7-10.
[2]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J].中国社会科学,2000(1):37-51.
[3]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1):21-27.
[4]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5]杨曦帆.音乐的文化身份——以“藏彝走廊”为例的民族音乐学探索[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
[6]项阳.加强对音乐“非遗”分类综合研究的深层探讨[J].人民音乐,2016(6):35-37.
(责任编辑:王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