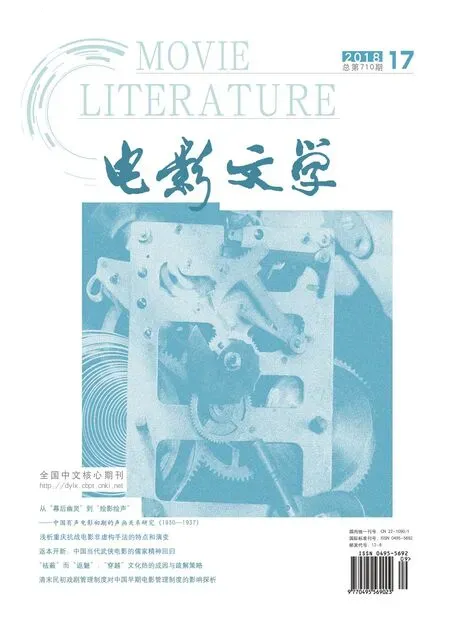新世纪中国都市电影的空间意象及其缺失
张书端
(扬州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国产都市电影的数量迅速攀升,与此同时,在电影文本内部,中国都市电影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转向”趋势。空间的解构与重构,都市社会中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固化以及人类主体性的变迁,成为都市电影的首要主题。然而,在种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用下,新世纪中国都市电影的空间再现出一些相对固化的模式,它们夸大或宣扬了中国都市的一些面向,同时却又掩盖了都市生活的其他维度,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新世纪中国都市的社会现实。本文将对新世纪中国都市电影中的几种主导性空间意象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都市电影空间书写中面临的问题与缺失。
一、透明性空间
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时代语境下,以光鲜亮丽的现代都市为背景的国产电影大量涌现,在《夜·上海》(2007)、《杜拉拉升职记》(2010)、《我愿意》(2012)以及《小时代》系列、《情圣》系列等都市电影中,时尚浪漫的都市生活成为中国电影的首要表现对象。在这些电影中,北京的国贸大厦、央视大楼,上海的外滩、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以及上海中心等都市景观总会在镜头中不时闪现,并且经常会作为比人物更为重要的对象而得到浓墨重彩的书写。例如,《非诚勿扰》(2008)一开始,镜头就长时间停留在国贸大厦和央视大楼,不知疲倦地描摹着新世纪北京时尚繁华的都市范儿。电影《大灌篮》(2008)中,篮球场居然也被置放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借助大景深镜头,东方明珠塔和金茂大厦总在不远处闪耀着难以遮挡的光芒。《小时代》系列中,男女主人公的很多活动也被安排在黄浦江畔,导演郭敬明还不惜花费巨资在黄浦江上燃放大量烟花来映衬上海的都市魅力。这些空间和场景之所以被反复强调,就是因为它们集中体现了新世纪中国的强大经济实力,而我们的都市电影也正要借此来彰显中国都市中资本的强大力量。
在这些电影中,内部空间的取景大多是在现代风格的写字楼、高档奢华的购物广场或温馨浪漫的餐厅、咖啡馆中。在《杜拉拉升职记》《我愿意》《情圣》等影片中,写字楼中出入的都是光鲜亮丽、身着各式高档品牌服饰的男男女女,他们的身体仿佛成为各种流行时尚的展示空间,时时处处都在展示着现代都市中“物”的价值。购物广场更是各种高档商品展示自身价值的所在,电影中的都市男女经常会在此类空间穿梭逗留,引领观众体验现代都市的感性魅力。餐厅、咖啡馆是最具小资气息的都市空间,自然也成为新世纪中国都市电影的重要取景空间。《夜·上海》《非诚勿扰》《我愿意》《情圣》等众多都市电影中,都有大量戏份被安排在高档餐厅、酒吧或咖啡馆,男女角色在其中静静品味着价值不菲的西餐、红酒或咖啡,尽显现代都市的优雅与奢华。
与购物中心、酒吧和咖啡馆相比,家庭本应是最具日常生活气息的空间。然而,在《非诚勿扰》《我愿意》,特别是《小时代》系列电影中,家庭也成为交换价值的展示空间。新世纪中国都市电影中的男女角色大多居住在高档社区甚至是别墅区,在新世纪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呈爆发式增长的时代背景下,电影中的豪华房屋在观众心目中更加凸显出它们的市场价值。而且在这些电影中,室内空间也成了现代化家装的展示空间,《非诚勿扰》中范伟饰演的暴发户的家庭空间装修无比繁复奢华,《小时代》中的室内空间亦是考究无比,墙壁上悬挂的名画更是在肆无忌惮地展示着它们的高昂价位。在此类家庭空间中,人类饮食起居的痕迹荡然无存,丧失了烟火气的洋房别墅也必然失去它的人性特质。
可见,在新世纪的众多都市电影中,都市空间中一切事物的价值仿佛都被货币所通约,由此,都市空间成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一种均质的、透明的空间。玻璃橱窗是此类都市空间中的典型意象,在这些电影中,整座城市仿佛幻化为玻璃橱窗中封存的展示品,我们可以站在橱窗外欣赏它的时尚与奢华,却无法在其中生存栖居。
米歇尔·德·塞托曾经区分过两种观察都市的方式,一种是站在摩天大楼顶端俯视都市的“上帝视角”,另一种则是“步行者” 的与街面齐平的视角。前一种视角把这个世界“变成了呈现在观察者面前和眼皮底下的奇观”,而后一种视角才是“城市平凡生活实践者”的视角。在“上帝视角”之下,都市空间成为一览无余的奇观胜景,都市社会中的一切差异都被掩盖或抹平,现代都市成为一个个同质化的消费空间。显而易见,在以上提及的都市电影文本中,观察都市的视角无疑就是一种来自“上帝之眼”的俯瞰视角,它凸显的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浮夸魅力。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用之下,电影中的都市空间彻底沦落为资本逻辑掌控下的“景观都市”。在这样的都市空间中,“大量商品充斥着货架并侵蚀着思维能力;各式各样的商品在商店中闪闪发光。靠着那些诡计、噱头和流行时尚,弥散的景观得以兴盛起来。它沉迷在商品中,热衷于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与它相伴,商品拜物教达到了‘热情高涨的时刻’。”
二、区隔性空间
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2000)关注的是北京城里几位青年的生存状态。来自农村的阿贵是一位快递员,终日骑车飞奔在北京街头。然而,即便他对北京的大街小巷烂熟于心,却始终不能融入都市生活,对他而言,都市空间中到处都是有形无形的“栅栏”。在一次送快递的时候,他误入一家高档沐浴中心,由于不熟悉环境和规则,竟在其中彻底迷失,并糊里糊涂地洗了个澡,结果因为付不起账而遭到扣留。周迅饰演的小保姆经常偷穿雇主女儿的裙子和高跟鞋,试图以此种方式扮作都市人,从而更快融入都市生活。然而,她的这种行为很快就被发现,她也因此被赶出了都市。由此,新世纪的中国都市中,农民工面临的生存问题通过空间隐喻得以形象化地再现。
在彭小莲执导的电影《假装没感觉》(2002)中,吕丽萍饰演的阿霞妈因为丈夫外遇而离婚,由于住房在丈夫名下,阿霞妈在离婚后竟然没了住处,只能暂时寄宿在阿霞外婆家。然而外婆家住房也不宽裕,并且阿霞舅舅很快就要结婚,拥有房屋继承权的舅舅并不欢迎自己姐姐的到来。面对这种状况,阿霞妈只能通过改嫁使母女俩有了落脚的地方。不过好景不长,阿霞的继父老李总觉得房子是自己花钱买的,因而对阿霞和阿霞妈极其苛刻、吝啬。在忍无可忍之下,阿霞和妈妈只能选择再次离开。母女俩狼狈地走在城市街头,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里,偌大的上海,却没有母女俩的安身之处。在这部电影中,阿霞和阿霞妈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空间问题。母女两人的性格都很坚强、独立,然而他们却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究其原因,就是男性占据着都市空间中的支配权。
在《十七岁的单车》和《假装没感觉》中,都市空间依然是电影中的核心叙事要素,不过此时的都市空间已经不再是透明、均质的空间,而成为不平等的阶层和性别关系主导下的区隔性空间。在这样的都市空间中,都市人/男性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农民工/女性则只能寄人篱下,面临随时被驱逐的风险。在此类影片中,都市空间成为都市社会中不平等权利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媒介。正如亨利·列斐伏尔所指出的:“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一切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最终都会通过空间形式得以再现。以《十七岁的单车》中的阿贵为代表的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保障,他们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城市建设以及城市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建成后的都市空间中,却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现代化大都市中,“流光溢彩的全球化表象对弱势群体来说是异化的象征”。他们只能在都市边缘和灰暗地带逡巡游移,试图抵达中心区域的努力只会一次次遭遇失败。恰如《苹果》(2007)中佟大为饰演的安坤,他每天攀附在高楼大厦上擦洗着玻璃幕墙,看似与大楼内的生活一墙之隔,却永远难以突破阶层的限制而真正进入大楼内部。《好奇害死猫》(2006)中的保安刘奋斗(廖凡饰)居住在地下停车场的小房间里,他经常站在大楼下仰望着楼顶的玻璃屋,甚至觊觎着玻璃屋中美丽的女主人千羽(刘嘉玲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终于可以接近千羽,却不知道自己其实成了千羽的一颗棋子,最终,他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车人的七月》(2005)中,范伟饰演的下岗工人杜红军,兢兢业业地看守着高档夜总会外面的停车场,却始终未能踏入夜总会半步。《到阜阳六百里》(2011)中秦海璐饰演的女农民工曹俐,和同乡谢琴同住在一间不足7平方米的阁楼里。在这样一个逼仄的空间里,她连作为女性的基本隐私也难以保障。
通过对都市语境中空间区隔性的再现,这些电影触及了当下中国都市中的一些社会症结,使我们得以直面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不过问题在于,在这些电影中,创作者们仿佛又陷入了探索都市空间权力关系的迷局之中无法自拔。他们对现代都市中的阶层分化问题形成了僵化的认识。仿佛新世纪中国都市中阶层流动的通道已经被彻底切断,生活在中下层的人们所面对的只能是冰冷绝望的未来。因此,他们对都市生活的认知以另一种方式背离了新世纪中国都市生活的现实。
其实,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都市中,出身都市底层或来自偏远农村,经过拼搏奋斗,最终突破阶层藩篱而获得人生和事业成功的例子不在少数。而我们的电影创作者们仿佛忽视了这类故事,只忙于编织底层人生的苦难。与之相比,现代都市中的励志故事更能打动观众,给予他们生活的热情和动力。例如美国电影《当幸福来敲门》(2006)中,威尔·史密斯饰演的克里斯·加德纳是一位被妻子抛弃的单身爸爸,由于推销医疗设备失败,他即将面临经济破产,与此同时,他还需要养活年仅六岁的儿子。不过,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克里斯·加德纳一直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他凭借超常的毅力,争取到进入一家股票公司的机会,自此彻底改善了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最终成为现代都市中的成功典范。这样一个反转极大的励志故事绝非向壁虚构,而是根据美国著名黑人投资专家克里斯·加德纳的真实故事改编。与此相似的故事,其实在中国都市中也不鲜见,只是我们的创作者们仿佛对这类故事不感兴趣。
三、异质性空间
李玉执导的《今年夏天》(2001)是中国第一部女同性恋电影,作为一部边缘题材作品,这部影片把取景空间放在都市郊区。镜头中凌乱的街道和市场,使我们很难将其与大都市北京联系在一起。其实,这种空间选择也是导演的一种创作策略,李玉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边缘—中心的空间隐喻,来再现女同性恋在当前社会文化中作为异己的他者的存在状况。影片结尾,女同性恋者君君以一种自杀性方式与警察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展开对抗,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身的毁灭。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都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现代都市中的一些社会病症也随之出现,尤其是在一些都市青年中,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步富足,精神空虚和贫乏的问题却凸显出来。这些也得到电影创作者们的关注。程裕苏导演的《我们害怕》(2001)聚焦于几名都市上海中的问题青年,其中涉及毒品、性等诸多社会问题,该片的取景空间大部分是在昏暗的都市街角或嘈杂的地下夜总会,通过空间的隐喻,再现都市边缘群体空虚、绝望而又无助的存在状态。同样由程裕苏导演的《目的地,上海》(2003)表现的是类似主题,影片取景于破败不堪的苏州河沿岸以及一些废弃的城市建筑,其中的都市青年在精神空虚的状态下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与此同时,影片还涉及中年群体在社会变革的语境下价值观坍塌等深层社会问题。
不可否认,在快速都市化的发展进程中,都市人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总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心理不适,这些都需要通过电影媒介来做出再现和调节。然而问题是,《我们害怕》《目的地,上海》等影片走向了又一个极端。创作者在电影中塑造的是一个极度冰冷,毫无生机和希望的中国都市,所有人物精神空洞,内心无所依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我存在的价值。这种对新世纪中国都市的再现方式无疑也是脱离现实的。愤世嫉俗,过度标榜自我的电影表现方式其实成为导演寻求“作者”地位的一种便捷途径。在此类电影中,人物和都市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导演自我表现的工具,而这也使得电影离都市社会生活越发遥远。
四、缺失的日常性空间
无论经济如何发展,都市首先应当还是人类生存栖居的空间,是现代人展开衣食住行等各项日常活动的场域。然而,在新世纪中国都市电影中,日常生活却以各种方式被遮蔽起来。在《小时代》《杜拉拉升职记》等影片中,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掩盖和消解了都市空间的日常性,使都市空间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能指。《假装没感觉》《看车人的七月》等影片原本取景于都市日常生活空间,然而由于创作者过度聚焦于都市空间中的权力格局而使日常生活空间成为一个个象征和隐喻。而在《我们害怕》《目的地,上海》等影片中,都市日常生活更被创作者的先锋性追求彻底掩盖,在这种乌托邦式的再现模式中,现代都市空间中的一切价值和意义皆被消解。
然而,日常性恰恰是最能激起观众共鸣的都市电影元素,因为它能使最广大的电影观众从中看到自己的存在状态。例如日本电影《深夜食堂》取景于大都市东京,然而创作者并没有去展现东京的时尚繁华,而只将镜头聚焦于偏僻街巷中的一个小饭馆,在食客们日常饮食的过程中引出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小故事,那种浓重的日常生活气息使观众感受到了都市生活的温情和热度。正因如此,这部电影不仅在日本取得良好反响,甚至在中国也俘获了大量观众。《家族之苦》也表现日本一户人家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并同样获得国内外众多观众的热捧。另外,韩国电影《奇怪的她》亦是围绕家庭生活展开叙事,并重点关注中老年女性的生存状态,同样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这部电影在改编为《重返二十岁》之后,在我国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回顾中国电影史,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日常性空间在中国都市电影中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都市电影中,《太太万岁》(1947)围绕都市上海一位已婚女性展开故事。陈思珍是一位持家有道的家庭主妇,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良好运转,她在丈夫、婆婆和小姑间左右逢源。虽然为家人操持忙乱,却也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和疏漏,不过凭借她的隐忍和努力,并在家人的帮助下,她终于使自己的家庭生活重新归于平静。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虽然琐碎,却也非常考验这位女性的心智和能力。围绕一系列小问题,整个大家庭中的每个人物形象都被活灵活现地树立起来,而这些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也使观众从中找到了共鸣。另外,李安电影《饮食男女》(1994)围绕一个台北家庭中父亲和几位子女间的关系展开叙事。影片一开始,郎雄饰演的父亲老朱便做了一大桌的美味佳肴,摄影机从各个视角充分展现了中华美食的制作过程。并且,在整部影片中,人物的饮食起居特别是家庭宴席的制作,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篇幅。同时,李安导演又在人物的饮食起居活动中注入了充分的故事性和情感元素,使得这部影片不仅饱含中国文化特色,同时又在更深层面触动了中国观众的内心。还有杨德昌的电影《一一》(2000),从一个孩子的视角观察一个台北家庭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反而实现了对现代台北生活的全局观照,并对都市现代性特别是都市人性的异化进行了深度刻画和反思。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历来重视家庭和人伦,因而,都市电影对家庭日常生活和亲情关系的再现与书写,也正是中国都市电影区别于西方类型电影传统,从而建立自身的文化主体性的有效途径。因而,在今后的中国都市电影中,创作者们应该更多从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寻求创意和素材,表现普通群体的喜怒哀乐,并洞察快速都市化进程中,家庭伦理关系的发展与变迁,只有这样,才能在最深层面上打动中国观众,为中国都市电影奠定良好的观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