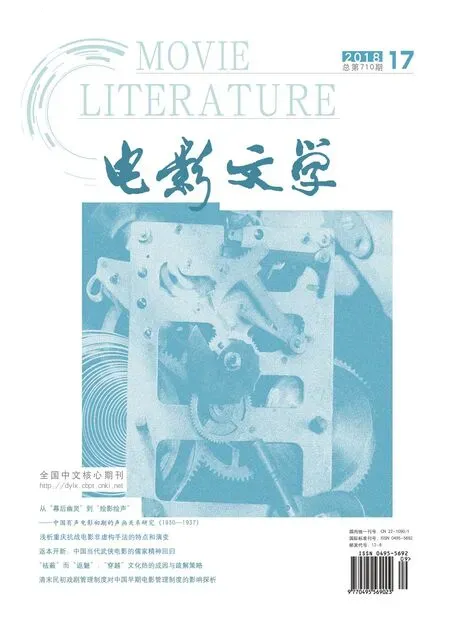返本开新:中国当代武侠电影的儒家精神回归
潇 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
武侠电影是华语电影体系中最能体现中国文化,发展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类型电影之一。当代武侠电影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灵根自植和源远流长,纵观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中国电影发展轨迹,“儒家思想”犹如一根看不见的红线,深深地影响着武侠电影内在品格的塑成、转型和超越。退去刀光剑影的斑斓外衣,“武侠”归根到底是对“公共善”的一种浪漫主义狂想,是将仁者之心与反抗力量嫁接后产生出的一种文化憧憬。它的精神核心正是儒家文化的利他性,是凡人善举,是舍己为人、扶危济困的仁义,是一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道,更是在复杂环境中的自我人格完成,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修身”之道。
一、港台武侠:保守主义的民族电影叙事
中国侠文化源于先秦时期的“招士养侠”,可见于秦汉史书中关于侠士的传记,这些形象与故事经由士大夫阶层的书写,带有先天的儒家文化审美取向,反映着传统知识分子追求道德理想主义和内在超越的一种精神自慰,构成了“侠”与“儒”同源的内在机理。在此后数千年的各类文本演绎中,“侠”文化被不断地丰富与巩固,并与儒家以自我心性修养为基础的“内圣外王,天人合一”思想产生了深度融合。创作群体身份的交织,也让武侠电影与儒家文化产生了精神同源的基础,儒家精神也成为支撑武侠电影叙事的民族心理根基。
当代武侠电影的发展起源于中国武侠电影史上第三次创作浪潮(1958—1978),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数量多、影响大,其中《龙门客栈》(1967)、《独臂刀》(1967)、《三少爷的剑》(1977)、《楚留香》(1977)等都堪称中国武侠电影的经典之作。此类武侠电影遵循着儒家文化的规定性情境,讲述着“克己”“取义”“天命”等传统人伦价值,呈现出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风格。如,儒家文化充分肯定人的独立意志,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宣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人格标准正是邵氏武侠电影中诸如侠女徐枫、楚留香、独臂刀王等正义人物激活联想、引起共鸣、产生民族认同的重要元素。
胡金铨堪称这一时期历史武侠类型片的集大成者,他执导的新派武侠片《大醉侠》《独臂刀》《龙门客栈》《侠女》等都或多或少植入了亦实亦虚的历史内容,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古装武侠片怪力乱神的艺术旨趣。历史元素与武侠风格的互植也让胡金铨的武侠电影呈现出厚重、深邃的传统文化情怀,侠士、侠女和侠僧形象都或多或少地寄托着武侠电影试图从中国文化中寻求精神慰藉的内在渴望。在《龙门客栈》中,“反对暴政”的主题设置就是对孟子所说“羞恶之心,义也”之道德自觉性的生动演绎。正因儒家文化“抗议精神”传统的长期存在和深入人心,锄奸救忠的主角行为获得了民族文化心理认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具有“汇聚了各种艺术类型和哲学传统,形成一种综合的‘中国性’形象,凸现鲜明的中国传统抗衡西方文化的立场。”
这一时期,武侠电影的发展并不是单线递进,现代转型也在悄然进行。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社会经历了经济体量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现实的严峻动荡,为了满足人们逃避现实困境及年轻人英雄崇拜的心理需求,武侠电影中对个体生存和情感状态的关注逐渐张扬。《独臂刀》(1967)创造了香港电影票房的新纪录,影片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浪漫塑造,蕴含着对中国宗族观念、儒家伦理的现代化改造。一方面,屯堡村落、村镇茶社、溪畔郊野,视觉空间链接着传统文化的暗喻,极具象征意味。电影中对父子、师徒、师兄弟情谊的反复强调也反映出儒家传统伦理对以五伦为代表的普遍秩序的尊重。另一方面,被颠覆的江湖叙事、被隐喻的个人主义反映出了邵氏武侠的现代新变。在《新独臂刀》(1971)中,武林虽是法外之地,但却不再是理想主义的乐园,雷力“断臂”,封俊杰“断身”,龙异之“断命”是对争霸的反思,更暗喻了“社会”对人的无情吞噬,反映了“法制社会中的当代观众对武侠电影的一种新的现实和审美需求”。
在多方话语权的博弈中,以邵氏武侠为代表的港台武侠无疑为全球华人世界填补了一个富有诗意的民族想象空间,儒家精神以保守回归的方式几乎出现在所有的武侠电影中,“文化中国”的憧憬为国人提供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心,维护了民族想象的权威。
二、新武侠电影:现代改造后的喧哗与骚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武侠电影”迎来了中国电影市场复苏,成为华语电影票房与口碑的大赢家,涌现了一批大制作。其中,两类题材最受热捧,一种是以改编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人的武侠小说为主的古装刀剑片;一种是以霍元甲、黄飞鸿、洪熙官、方世玉等真实历史人物为主人公的人物传记片。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香港武侠电影史上的黄金十年,观众多、影响大。新武侠电影借助特效、美术、音乐刻画出了极富东方情调的武侠世界,重新阐释和定位了儒侠互通互补,但异族内容、特效元素的大量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中国文化精神和普遍人性的关注,形成了一个融合华人世界共同想象的喧闹乌托邦。
作为开创香港“新武侠电影”时代的著名导演之一,徐克武侠电影表现出了新武侠电影审美的鲜明个人风格以及对侠义文化的传承。在《新龙门客栈》(1992)这部致敬胡金铨的新武侠电影中,一代名将周淮安被塑造成了一个几近完美的形象,他不仅是一个侠客,更是一个持剑行义的儒士,他心系家国、扶弱救困、智勇双全,是儒家精神“忠、仁、义、智”的理想人物形象,而他的重义重情、尊重女性改写了70年代武侠电影中以男权为主的保守主义形象。在6部《黄飞鸿》电影中,黄飞鸿布衣长袍、亦文亦武的形象直白地预示了儒侠互补的天然联系。无论是对于敌人、对手还是伙伴十三姨、猪肉荣、牙擦苏,黄飞鸿与他们产生关系都离不开儒家说教,以德服人和身怀绝技在一个人物身上的重叠让我们看到了儒家精神的质朴与刚烈。
新武侠电影对江湖传统进行了大量改造,如《笑傲江湖》(1990)中的江湖是被掩藏在夺宝争斗下的帮派与官府的利益角逐,《新龙门客栈》(1992)中的江湖是明末宦官专制黑暗笼罩下的法外之地(大漠边城),《精武英雄》(1994)中的江湖是近代民族危机之下中国民间组织的自强与抗争(武馆与道场)。但无论何种江湖,人物形象塑造更多地带有现代审美意味。同为日本人,既有军国主义狂人藤田刚的凶暴残忍,也有日本武士船越文夫的公正与道义,更有与陈真互相爱慕的山田光子。而陈真在面临家、国选择时也并不是一味冷酷处理,展现出了兼具传统与现代美德的丰满人物形象。
这一时期的武侠是英雄的武侠,也是民族国家的武侠。徐小明曾说:“武侠精神随时代变迁而变化,我始终认为武侠精神与家国意识密不可分,也与人们的生活现状密切相连。”武侠“人物传记片”往往将个人与国家命运、时代悲剧紧紧捆绑,“清末民初”成了电影创作者们最热衷的时代口味。各种武林故事中充斥着大量族群意识的民族主义印记和后殖民主义话语情境,传统武侠中的杀富济贫、对抗公权逐渐演变成了建立在“保种、保国、保教”基础上的中西对立、善恶对抗,中华武术技能突然间变成了变法、变政和变教乃至“救国”的应对措施。这种民族心理补偿机制使得这一时期的武侠片呈现出了徐浩峰所言的“晚会”气质,大量诸如“反清复明”“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男儿当自强”的口号充斥银幕,“凑场面、凑名角成了武侠故事的核心”。上述观点虽偏激,但也反映了被掩盖在市场光环下新武侠电影模式化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在被极度符号化的民族情绪和历史语境中,儒家精神被异化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推动武侠创新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将其引向了消费性、娱乐化和奇观化道路。
为营造极具视觉冲击的场面和氛围,武侠电影大量使用技术特效和大型道具,加入神怪元素和异度奇情来演绎现代人的爱恨情仇。以《倩女幽魂Ⅲ:道道道》(1991)和《白发魔女传》(1993)为例,两者都以豪华明星阵容、视觉特效获得了票房成功,但对于连体妖人姬无双、黑山老妖等怪异、扭曲和阴森恐怖形象和神异打斗场面过度渲染,正邪对立的简单绝对化,都使武侠片失去了“侠义”精神的底蕴。为了迎合大众文化审美趣味,武侠电影又被植入不少戏说、恶搞的因素,造成了文化表达的杂糅与生硬,一如徐小明先生所言,如果武侠电影“只有技术和动作,没有内心与灵魂,只是展现如何打斗,而不挖掘武术背后的文化特性和内涵的话,总有一天,武侠影视会走到尽头”。
三、21世纪武侠:回归生活的人性隐喻
21世纪华语武侠电影的起点始于《卧虎藏龙》(2000),此后众多名导们相继推出了《英雄》《叶问》《功夫》《一代宗师》《刺客聂隐娘》等一批代表性作品,成为中国商业影片冲击全球化市场的重要力量。“弱武”成了这一时期武侠电影的精神暗潮,复仇、争霸、御辱等套路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人之生存困境、精神困境的象征性呈现,此种转向看似武侠精神的弥散,实则是儒家文化现代转型后的一种新型叙事路径。
儒家文化是一个涵盖性极强的人文景观,它关注现实、关注生存、关注人性,注重“人和社会的互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人心和天道的合德”。今天,儒家思想(仁学理路)被认为是“以现世人本主义的、经验理性主义的、专注于人际间公平正义问题本身的伦理信仰体系”。正是基于这种强大的文化包容性、开放性和心理存在性,武侠电影方能在百年发展中不断借力发力,演变生新。
纵观这一时期,导演类型的多样化间接推动了儒家精神在武侠电影中的复兴。一方面,来自香港地区的徐克、陈可辛、王家卫、尔冬升、叶伟信、陈嘉上、李仁港继续深耕武侠;另一方面,来自内地的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徐浩峰、陆阳,台湾地区导演李安、侯孝贤也都涉足武侠题材,这些创作风格各异、文化背景迥异的电影创作者既具备文化寻根与宏大叙事的人文关怀,又具有解读民族文化历史与心理结构的叙事功底和表现策略,为“21世纪武侠”带来了更为开阔的文化视角和细致的情感体验。
千禧年之后,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电影市场化的成熟,江湖叙事最终完成了从体制外到去体制的分化,成为生活世界人际关系网络的诗意延伸。江湖胜负、武林争霸不再是影片的终点,胜之不“武”、回归“人性”似乎成为当下武侠电影的一种全民心理暗示。《一代宗师》中叶问对家庭的温情脉脉,对一颗纽扣的执着,“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地抽离叶问的‘侠客’品质”。在《武侠》中,唐龙隐身为农夫,与家族决裂,不惜断臂甚至弑父以求自绝于江湖的故事,更彰显了人性的魅力,或者说是对人性枷锁与人格自由的终极追问。武侠的泛社会化让武侠电影逐渐退去了江湖的外衣,也退去了中西对立的叙事逻辑,反映出当代中国电影人对于去体制化的人道主义的深沉反思,而这种思考之所以深沉的内在机理仍是源自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即“天地之性以人为贵”(《孝经》)。
“侠”的人性化推动了“全民武侠”实现。侠客已经不再局限于经典文本和传说中的江湖大佬或盖世枭雄,小人物、草根大众亦可成“英雄”。《功夫》中的街头混混变成一代武术家,《刺客聂隐娘》中的侠客是背负杀人使命的职业杀手,《绣春刀》中的侠客是拿着俸禄的朝廷官员,《师父》中的街头车夫成为市井传奇。在这些武侠形象中,英雄可以不问出处,可以不拘小节,但必定要有仁爱之心。这种恻隐之情本是人类自然流露的情感,实则也是一种推向天地精神的人际关系,即儒家文化中推己及人的仁道。
不依附于政权的生存之道是中国武侠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侠者“反抗”本身就富于儒家文化色彩。中国儒学领袖向来和世俗权力的联系不深,关涉较少,他们的批判与反抗“不是来自现实政权的既得利益,也不是全出之于超越的理想,而是由文化历史的感受与个人人格自我完成的自觉,两者长期交互影响而来”。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中,侠者的反抗呈现出新的人格光芒,即反抗不是为了一家一姓而卖命,不是为了自己生存环境的改善,而是透露出某种悲天悯人的自我牺牲。在《英雄》(2002)中,武侠叙事突破了20世纪90年代个人与国家的一致性,走向了个人与国家(社会)关系的紧张对峙,最终无名面对天下时,选择了放下与成全。这种带有悲剧意味的殉道精神与儒家价值观具有一致性,具有浓厚的悲剧性。在《霍元甲》(2006)中,领悟了武道精神后的霍元甲没有让自我在一己的得失中继续沉沦,而是身中剧毒仍自强不息,电影想传递的正是这种“人可以选择死亡”的崇高悲剧性。霍元甲是乱世之中的一介武夫,他的死带有某种时代必然性,但他最终选择超越小我的自我牺牲无疑带有强烈的儒家人文精神色彩。
“武林人士”并非来自官场,没有世俗权力的庇护,也并不依附于权势,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身份。伴随着传统职业的逐渐消亡,武林侠客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们或从行伍流向市井,或从乡村走进近代都市。身份的变化,让他们褪去了“正邪对立”“逞强好斗”的简单逻辑,面对更为复杂的人性和社会。在《倭寇的踪迹》中,随着戚继光的离世和所谓的“天下安定”,主战派的朝野立场被否定,不愿放弃戚家倭刀的梁痕录失去了人生依靠,被迫走进霜叶城开始了抗争之路。在《师父》中,陈识虽是南派咏春传人,但家世早已没落,跑过镖、从过军,还在海上讨过生活,是一个无根无基的无名武术家。徒弟耿良辰更是一名底层青年,从事脚夫工作,以贩书糊口。因此,他的反抗也更剧烈,靠一己之力打败八家武馆,成为整部影片的一种精神暗喻。耿良辰之死是一剂猛药,最终让陈识觉醒,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而打”,不是为名、为利,而是为人、为义。
同样是打擂开派,从梁痕录的“被收编”,到陈识的“争名”,再到叶伟信《叶问3》中的“不争”,21世纪武侠电影讲述了何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这种理念区别于西方浮士德精神所代表的征服和社会进化论所强调的适者生存,体现了中国儒家精神中的天人合一与阴阳协调。在儒家价值体系中,社会角色与个人角色是统一的,人可以抗争,追求现世,亦可以隐退、反省,寻找内在生命的意义。从这一视角观察,这种“弱武”“侠变”并非是对中国武侠精神的肆意消解,而是对武侠电影类型化发展和元叙事困境的突围,希望借助更加多元化的题材、写实化的风格去创造回归人之本真,回归生活世界。
四、结 语
从“江湖—侠客”,“民族—国家”再到“人性—社会”,儒家精神经历了“重拾—新变—回归”的发展历程,这种回归的“内在超越”赋予了当代武侠电影更多的生活维度和人性实现。面对商潮涌动、价值多元的全球化时代,武侠电影中的儒家精神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基于民族文化认同的亲情感和家园感,调和着当代人伦理情感、价值态度、自我理解乃至信仰方面的诸种危机。因此,评价中国21世纪武侠电影的类型发展之路,不能盲从于票房市场和眼球经济,而应理解、分析与接受武侠电影艺术的文化原点和重要尺度。只有充分意识到“在当代社会,不是消费决定文化,而是文化引导消费”,才能让“武侠”回归武侠,让“武侠”根植人性,让“武侠”拥抱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