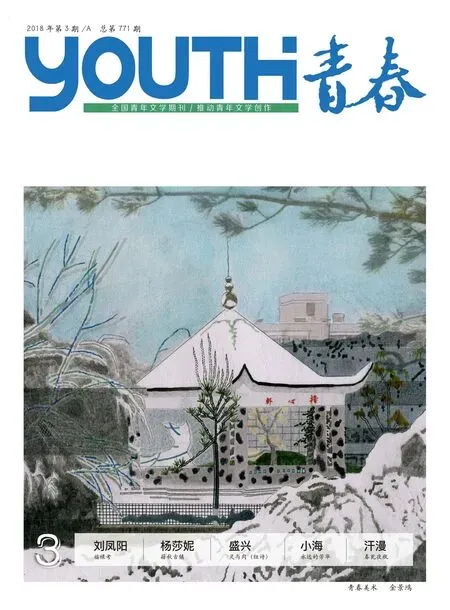春瓮夜瓶
1 万里归心独上来
“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磨青铜。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 苏轼这样写孤鸟,也是写孤人、自我——孤独,如果以大海为背景,就尤其醒目。
远离大海的人,比流放于海岛上的苏轼稍微幸福?在铜镜里消磨孤独——镜子边缘,在摹仿海岸的蜿蜒。
苏轼写过海棠,不知道与大海是什么关系:“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为失眠症患者们作了一种美好的阐释——他们是在陪花朵一同醒着。当下,许多失眠者床头柜上的台灯醒着,窗外,已经没有海棠可陪。铜镜,也在整容术盛行的现代生活里消失踪影。
苏轼曾经写过一首标题很长的诗——《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有名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辛弃疾《鹧鸪天.和人韵有所赠》中有句:“事如芳草春长在,人似浮云影不留。”两句酷似。
我猜测,辛弃疾也爱苏轼,并受其影响。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似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两个诗人,在长江的中游和下游,怀抱北宋与南宋,悲凉四顾,无家可归。
在上述两句中,苏与辛二人对“人”“事”的去留态度,微有差异:苏轼说,人在而万事皆空,秋鸿一行传寒意;辛弃疾说,事在而人迹已空,芳草满地春色旧。其共识在于:紧紧抓住眼前的春天,“走马还寻去岁村”(苏轼),“趁得东风汗漫游”(辛弃疾)——
辛弃疾在呼喊多年以后一个笔名为“汗漫”的人?趁东风走马寻村,寻找、会晤那芳草般绵绵不绝的古人:李白,杜甫,王昌龄,苏轼,陆游,辛弃疾……
苏轼作过一首集句词:“怅望送春杯(杜牧),渐老逢春能几回(杜甫)?花满楚城愁远别(许浑),伤怀,何况清丝急管催(刘禹锡)。吟断望乡台(李商隐),万里归心独上来(许浑)。景物登临闲始见(杜牧),徘徊,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隐)。”
所有诗人都是同代人,一种以诗语相认复相亲的游牧民族——“万里归心独上来”,归于故园、故国,多么艰难,就多么动人。苏轼用集句向前辈致敬,为自己安神——只有在隐秘的同类人、同类项中,一个人、一个代数式,才能活下去。
贬谪海南儋州时期,苏轼诵诗壮胆、煎茶解忧:“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我没有大瓢小杓,只有铅笔和水笔——水笔,也能把月色贮藏到墨水瓶中来。铅笔,也能够从一张又深又清的白纸内,分解出江水,进入内心。
当然,苏轼的春瓮与夜瓶,比我的墨水瓶与内心更加巨阔、绚烂。
德语犹太诗人保罗•策兰,在送给女诗人巴赫曼的诗集上题词:“给巴赫曼,一小罐蓝。”
古今中外,爱与忧愁都是蓝色的、清澈的,无论一小罐,还是一大瓢、一春瓮。
2 游泳池与江湖
苏轼以欧阳修为师。北宋时代,两人都是诗、文、词、赋兼善并美的名家。
古代士子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大都善于用不同文体,来分别解决俗务与内心、公众与个人之种种疑难,视诗歌为文章之余事,词又被视为诗歌之余事。
但也正因为把诗词视为文章之余事、伴奏、配角、后花园,从而使其保持了独立、自在的美学品质。
陈寥士在其编著的《宋史选讲》中谈到王安石:“从来登大位而诗有蔬笋气的,以他为首屈一指。”登大位者之诗,容易有酒肉气。陈寥士以菜蔬青笋气,来品鉴诗之格调,别致。王安石的书桌大概离菜园很近。读有菜笋气之诗,可清热解毒、静心安神——把脂肪肝,缓慢改造成小菜园。
“如何以诗作为我们的凭借,参与社会,体验生息,而不被动地为浩荡浊流所吞噬,甚至为虎作伥?”台湾诗人杨牧在谈到诗人的社会责任时,给出这样一个答案:像欧阳修、苏轼们一样,掌握各种文体来处理不同题材,避免强化讽喻功能而造成对诗歌这一文体的伤害,“你既然是诗人,也是一个弘毅的知识分子,你怎么能置身度外?”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则以卡夫卡为例,就“诗人的介入”这一命题,做了回答:诗人如果去为已知的、预想到的真理服务,就是放弃了诗人的天职,诗人只为有待发现的真理(炫目的真理)服务。他这里所言的“诗人”,指的是以诗性为最高境界的广义的作家。也是在这本书中,昆德拉认为小说要接受诗的苛求,“小说,反抒情的诗。”
“八月二日 ,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学校。”这是卡夫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天写下的日记。语调淡漠、冷静,像降温了的游泳池,不像中国古代文人隐喻中的江湖。卡夫卡不写公文。他喜欢中国的袁枚,袁枚也是一个不喜欢公文的人。
像卡夫卡、袁枚这样以不介入的姿态、诗人的姿态,维护文学的尊严,在孤寂中思考被遮蔽的真理,很艰难。像欧与苏那样写入世的檄文、出世的情诗,脱俗而又还俗,更艰难。
自古至今,无效的写作比比皆是,帮凶、帮闲式的写作,混淆了文体责任的写作,比比皆是——没有孤独的游泳者,也没有隐居湖边的忧思之士。
3 明月直入
李白《独漉篇》中的句子“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让我想起司空图《诗品》,像诗论。李白的写作标准就是:自然而然——风吹罗帷明月来。他有理由把月亮写得出色动人,比如:“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李白之外,写月亮的名人杰作太多。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博尔赫斯:“守夜的人们已经用古老的悲哀/ 将她填满。看她,她是你的明镜”……
后代诗人继续抒写月亮是危险的事情:如何能够区别前人,写出属于自己的月亮?
着迷于白昼里的奔竞,当代诗人的数量、才华都低于唐宋,高楼缝隙间难以被一轮明月所青睐。即便拧亮圆形台灯,这盏虚拟的满月也低于夜空——一个人在公寓楼里写月亮,难度大。但克服这一难度,反而能够写出杰作。王小妮在广州市做到了:
“月亮在深夜照出了一切的骨头。/ 我呼进了青白的气息。/ 人间的琐碎皮毛 / 变成下坠的萤火虫。/城市是一具死去的骨架。/ 没有哪个生命/ 配得上这样纯的夜色。/ 打开窗帘/ 天地正在眼前交接白银/ 月光使我忘记我是一个人。/ 生命的最后一幕/ 在一片素色里静静地彩排。/ 月光来到地板上/ 我的两只脚已经预先白了。”
《月光白得很》,句子白得很。尤其喜欢结尾处的句子∶ “月光来到地板上/我的两只脚已经预先白了。”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细节,拥有了动人的、纯银般的力量——月光,没有放弃救赎尘埃里的生命,从两只脚开始,慢慢上升,让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一点一点白了。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不拘泥、不沉溺于某种妄念与信条,自由地思想与表达,就能生发出佛意禅心——像明月,毫无心机可供猜度。明月下,参禅的人也需要破禅,像破茧而飞的蚕,得以转化、延展。
元好问赞美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像在赞美一轮月亮:一语天然,万古常新。
4 醉花阴里春声碎
晚唐诗人韦庄写诗之余,开启对“词”这一文体的探索。在《菩萨蛮》中,他写出这样的句子:“劝君今夜须沉醉,樽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
当下,微信、口语交流过程中,回避尴尬和难题时的小盾牌,就是“呵呵呵呵”。韦庄在千年前就熟练使用“呵呵呵呵”了。后来,苏东坡在信札中也常呵呵呵呵。良宵美酒春漏短,需要借沉醉为掩护,强作欢颜——我已经继承了这种能力和手段。
韦庄之后,去酒楼茶肆给女子们写歌词的文人渐渐多了,词牌就渐渐多了。
读词牌,从中间选取若干两两组合、对仗,解除它们的孤单:
“风入松”与“浪淘沙”,“九张机”与“一剪梅”,“少年游”与“阮郎归”,“定风波”与“忆江南”,“沁园春”与“西江月”,“扬州慢”与“湘江静”,“减字木兰花”与“添声杨柳枝”……
这些词牌若与书写的意境相契合,可进一步解除其孤单感。如,“风入松”适宜写隐居、幽思,“一剪梅”适宜写春愁、爱恋,“定风波”适宜写征战、离乱,“少年游”适宜写青春、江湖,“扬州慢”适宜写声色犬马、万念俱灭,等等。最性感的词牌应该是“点绛唇”“忆秦娥”——回忆在秦娥嘴唇上点燃的那一抹火焰。
南唐后主李煜被拘押开封,写作,喜欢使用的词牌是“虞美人”“玉楼春”“相见欢”“清平乐”——仿佛一个个抵达前欢旧梦、“晚妆初了明肌雪”的指路牌,传达的却是“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悲凉。他大概常常对着这些词牌、指路牌,发呆,恍惚,无家可归,无路可走。
“春声碎”,也是词牌。碎碎的,是鸟鸣、雨滴、花瓣坠落台阶、女子足音和抽泣……张先初创这一词牌。张先,因“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这一句而成名,因“云破月来花弄影”、“柔柳摇,坠轻絮无影”、“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而被呼为“张三影”。一个人喜欢“春声碎”,就不会喜欢谴责、辱骂、告密、辩论、讽喻,一生葆有孩子的纯真——墓地上,春雨淅沥春声碎。
“雨中花慢”也是词牌,最早的写作者是苏轼和辛弃疾。雨中的花,慢慢开,慢慢落。站在花朵前的人,慢慢开心、衰落。以雨水的慢,来清洗、加固情感,反对暴雨和淋浴的快,这似乎泄露了诗歌写作的秘密——抒情,只有在恐惧美好事物的丧失之时,才能产生。比如,张若虚,因为“江水流春去欲尽”,才引发出《春江花月夜》这伟大如长江的一首长诗。
抒情的人,不仅仅是写诗作词的人。爱着、痛着、回忆着、梦想着的人,一概充满抒情的气质。即便那叙事的人、奔竞于事务中的人,在病床上 ,也终于有了被他嘲讽、拒绝了一生的诗人气质——对最彻底的丧失,充满预感、紧迫感。
唐诗、宋词之间,出现了过渡性的“花间词派”——唐和宋,这两朵大花之间的光影里,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韦庄、牛希济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前不见李白杜甫,后不见苏轼欧阳修,就感伤,沉醉于花间月下、美人怀抱,以浓艳词句对抗伟大时代之间的过渡感、多余感——“醉花阴”,一个新词牌就出现了。
尤其喜欢牛希济的一个句子:“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看到芳草,我往往就想到绿罗裙、牛希济、牛。
这个姓牛的诗人,内心温柔得像不忍吃草的牛。
5 莲与怜
古人有以下句子,写完荷与莲的一生: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小荷像少年,蜻蜓惊喜地落上明净的少年头?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依然是杨万里)——人处盛年,无穷且别样的盛年,与少年迥异,但凉意已经蛰伏。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李商隐)——林黛玉只喜欢李商隐的这一句诗,阻止宝玉清除秋天池塘里的荷叶。实际上,是曹雪芹在喜欢这句诗。晚年的荷叶、莲叶,尚有余力让雨滴通过自身发出声音。一个落发秃顶的老人,须戴上假发、草帽、斗笠,雨滴才会降落他的头顶。双脚和立场,须像池塘深处的莲藕那样充实、坚定,才会拥有在来年继续转化的可能。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依然是李商隐)——身体像荷叶那样存在,春恨秋恨才有了依附,即便荷叶枯。所以,体检是必要的,锻炼身体是必要的,药物是必要的,像枯荷一样每天晚上在淋浴房中挺立十分钟,消解恨意、获得解脱,是必要的。
“心如莲子常含苦”(黄仲则)。荷与莲,身体已经消失了,尚有莲子供有缘人品味,也是好的。
莲子,就是“怜爱你”,经历一生风雨霜雪,渐渐熟透……
6 醉眼看秋鹤
以饮酒为题材的诗很多,尤其是唐代,如李白的《将进酒》——“呼儿将出换美酒”,为了美酒,连五花马、千金裘都可以抛弃了。似乎无酒不成唐朝、无酒不成唐诗——无酒不成人。
初唐王绩,爱酒、写酒,比李白早醉了百年——《醉后》:“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题酒店壁》:“昨夜瓶始尽,今朝瓮即开。梦中占梦罢,还向酒家来。”《过酒家 》:“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
在古代,一个人醉了,可随意在酒店、酒家的墙壁上写诗——酒店、酒家在建筑之初,就考虑到诗人、诗歌的存在,建筑几面白墙,等候一个人的沉醉与狂喜。墙角的瓶、瓮、酒也在静静等着。真好。
与酒有关的诗,我还喜欢孟郊的《小隐吟》:“我饮不在醉,我欢长寂然。酌溪四五盏,听弹两三弦。”小隐很美妙,四五杯溪水就醉了。在两三琴声里午睡片刻,就是对未来的漫长寂然进行一次小实验。
在上海,我假装“大隐隐于市”,周围没有溪水只有水龙头,没有琴弦只有唱片。要体会醉意和寂然,只能喝酒,但可能遇到假酒。所以我基本不再喝酒,也对自己作为诗人的合法性缺乏信心。“你不喝酒,咋能成李白呢?”朋友质疑,我忐忑。
陆游的学生、浙江黄岩人戴复古,不知道酒量如何,但似乎深得酒中趣:“心平无险路,酒贱有欢颜。”这句子只有在素朴中年才能脱口而出——在贱酒微醉之后,无限欢欣,脱口而出。
他的《沁园春•一曲狂歌》结尾出现酒瓮:“开怀抱,有青梅荐酒,绿树莺啼。” 平常字眼,因毫无心机而动人。以下句子,复如是:“谁能多载酒,来此共登楼。山立阅万变,溪深纳众流。”猜想他身躯高大、砚台深沉,立于书桌前,就可以阅万变、纳众流。
戴复古的《论诗十绝》中没有出现“酒”字,但属于酒后真言:“飘零忧国杜陵老,感遇伤时陈子昂。近日不闻秋鹤唳,乱蝉无数噪斜阳。”他的好诗标准是“秋鹤唳”。但南宋以后,诗坛上“乱蝉无数噪斜阳”。
一个真正的诗人,需要在他人趋时附势的炎热感里,确认自我的寒意,认领一只秋鹤的身份和命运。
7 忽独与余兮目成
明代文人王世贞有文论集《艺苑卮言》,只言片语,见解独具。
他谈到,读嵇康独造之语,“跃然而醒。吾每想其人,两腋习习风举”——成为风中的鸟了。读前人好书,可避世、可避暑、可风行雷厉于云间。
他觉得,晚唐诗押二“楼”字:许浑的“山雨欲来风满楼”,赵嘏的“长笛一声人倚楼”。把一个晚唐押在这两位诗人的表达上了。
他认为,屈原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是“千古情语之祖”。的确,《古诗十九首》的无名作者们大约都热爱《楚辞》,所以才有了“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其实,屈原的南方情语,源头仍可上溯至中原《诗经》——其中,《燕燕》,可谓“万古送别之祖”,“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将兄妹分别之痛表达得异常动人;《小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生发出了刘禹锡的“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柳管别离”,王维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李颀送魏万入长安,离别之际也赠诗一首:“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我最喜欢前两句:游子唱歌,微霜渡河。
李颀与王维是同代人,应该也热爱《诗经》。他好交游,作品中送别、赠人的题材占了很大比重,如《送崔婴赴汉阳》《遇刘五》《送顾朝阳还吴》《送人尉闽中》《赠张旭》《赠苏明府》《送刘十一》……送别比迎接更有痛感和诗意,一次送别,一次死。
“天下美的东西,都是使人看着心酸的。”现代诗人梁遇春《春醪集》中的这一名句,大约受启发于屈原《九歌》中的“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美来到面前,使一个阅读者、观察者心酸,那是由于他意识到了时间的力量——转眼就别离,瞬间就凋零,转眼、瞬间就是丧失和眷恋。需要艺术、需要诗,来挽留、挽歌。
“古今人情不远。”(孟子)别离之悲与相拥之乐,不远。我们与他人的差别仅仅在于衣饰、发型,先秦以来的杨柳和雨雪完全相同。当然,工业化的雾霾、土地沙化、转基因粮食、人工智能等等新词汇、新境遇,前所未有。当代诗人的抒情难度就加大,重复表达或者失语的危险在加大——如何能得到美的眷顾,“独与余”、唯独与我目接而神动?
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时,与幕僚做同题诗“雪”,约定不能用柳絮、鹅毛、瑶华、玉宇等等旧词来比附。苏轼与人谈起这一韵事,说:“当时号令君记取,白手不许持寸铁。”诗人就是要白手起家,空手套白狼——用拳术,而不是剑术、枪术,远离一切习用的陈词滥调这些兵器。
新词语就是新经验、新发现——用一张今天的脸,来流古人的泪水、盐分相同的泪水,有难度,很动人。
8 常熟的一幅对联
在常熟兴福寺读到一幅对联:“山中藏古寺,门外尽劳人。”
那门槛内,尽是闲下来的风声、鸟声、诵经声?
兴福寺也叫破山寺,与唐代诗人常建的一首名诗《题破山寺后禅院》联系在一起。某个清晨,常建跨进这一座古寺,就闲了——“潭影空人心”。
现在,破山寺或者说兴福寺,一潭清水,被祈求幸福的人扔进去一枚枚硬币,像在贿赂菩萨。祈求者踏进寺门,依旧揣着尘世里的俗愿。
古寺门槛的意义,因人而异,像一行诗横在那里,领悟得如何是读者的事情。误解也是正解,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才值得一过。
“金鸭香消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宋代诗僧圆悟克勤,初入禅林,作诗《无题》,以少年艳情之不可言传,表达开悟心得。师父断定其已经见性悟道。后来,圆悟克勤果然成为高僧。
禅意如私情,“只许佳人独自知”,难以言传,难以为外人道。诗,亦如此。
白居易大概也不迷信深山古寺,他说:“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忘便是禅。”放弃了忧喜心、荣枯事,这就是参禅,也是破禅。
佛经中的“苦”字比比皆是。僧人床头需要放一杯蜂蜜水,缓和夜色与肝肠?
《论语》通篇倒没有一个“苦”字,生意盎然。寺门外的人、志士仁人、劳人,在书桌上、茶几边、会议室里,需要一碟苦瓜来败火、消炎。
我想把兴福寺这幅对联修改一下:“山外藏古寺,门内尽劳人。”似乎也邻于理想、合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