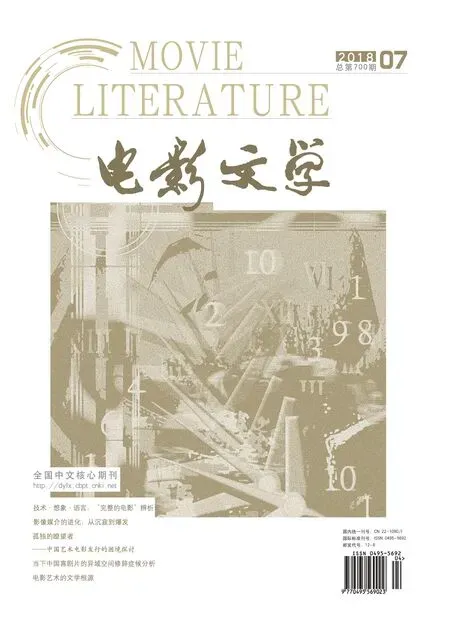《血战钢锯岭》的人文视角
房志新
(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0)
“人文”理念最早提出是为了伸张对抗神权的人权,而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数百年间,它又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但其关怀人,重视人的自由、解放和完善人的本性是始终没有变化的。梅尔·吉布森执导的电影,根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英雄戴斯蒙德·道斯真实事迹改编的《血战钢锯岭》(Hacksaw
Ridge
,2016),从人文性的视角来讲述残酷的战争故事,给予参战个体现实与终极两个层面上的人文关怀,而电影之所以能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也与电影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有关。一、人文视角下的个体
电影中的人文性首先便落实在对个体的关注和尊重上,关注和尊重的对象包括人的价值、尊严、生存的权利和意义,乃至人的精神生活等。而人文性又是多层次的,其中包括现实层次上的人文关怀和终极层次上的人文关怀,现实层次的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对人的世俗生活中的各种基本生存需要的关怀,而终极关怀则包括对人的道德理想、命运归宿、生存意义等的关注,也就是说,终极关怀指向人类的“彼岸”。《血战钢锯岭》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这二者经由战争这一载体结合到了一起,电影的人文视角既是仰望星空的,也是俯视大地芸芸众生的。
电影主人公戴斯蒙德是一名“良心拒服兵役者”,更为传奇的是,他又是二战中唯一获得荣誉勋章的拒服兵役者,这主要便是因为他建立的显赫功勋。出于爱国热情,他加入军队投身到太平洋战场上,在一个名为“钢锯岭”的地方和驻守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是由于家庭造成的童年阴影以及他所笃信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仰,他拒绝使用武器,并希望成为一名医疗兵来解决当兵和不拿枪这个矛盾。从基本生存的角度来说,手无寸铁的士兵在战场上无疑便是敌人的活靶子,戴斯蒙德自己已经命悬一线,而作为一个军医,他的行为也很有可能导致其他个体的牺牲。吉布森在电影中也大量表现了惨绝人寰、血肉横飞的战争中无数个牺牲的个体,戴斯蒙德的其他战友同样也是人文关怀的对象,观众和戴斯蒙德一起目睹了惨烈而真实的死亡。在这种景象面前,戴斯蒙德没有失去勇气,而是在主力部队撤退后,不断地穿行在枪林弹雨之中救人,提着血浆给战友输血,给濒死的战友注射吗啡止痛,甚至去救被炸断了双腿,在他人看来已经必死无疑的战友。“救人”成为戴斯蒙德唯一的信念。最后,戴斯蒙德孤身一人救下了75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为美军在周六拿下钢锯岭做出了贡献。对生命的高度重视成为电影浓墨重彩表现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文关怀精神,戴斯蒙德甚至连日军伤员也想方设法地运送下钢锯岭,他在战火中一次又一次地爬行,反复地给运送伤员的绳索打结等行为,具有“生命高于一切”和“人人生而平等”的情感意义。
另一方面,电影又将戴斯蒙德作为一个在主流中的“非主流”案例,体现出了一种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终极关怀。戴斯蒙德的信仰对于军队来说无疑是荒谬的,电影也用了大量篇幅表现了戴斯蒙德之前受到的排挤,如战友们殴打他,长官惩罚他等,主流选择扼杀他的想法。然而戴斯蒙德却拒绝了主流的“收编”,甚至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以一种伟大的博爱精神,实现了对他人的超越,用自己的双手拯救了曾经敌视过他的战友和长官,最终使主流充满敬意地接纳了自己。电影一军官心怀愧疚地对戴斯蒙德说:“我不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但我知道你的信仰如此坚定。”以及在周六美军发起第二次攻势之前,让已经成为大家精神支柱的戴斯蒙德带领大家一起读经祈祷,来书写影片的另一个感人之处,即作为个体,戴斯蒙德有权做一个少数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题材本身是宏大叙事视角,而选择了戴斯蒙德这一传奇的战争英雄作为主人公也很容易使电影的话语表达变为精英式的,但吉布森有意识地给观众还原了一个不凡中又有平凡的普通人形象,让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小人物”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生存状态,并通过关注这一个小人物来指向某种具有现实价值的、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尽管观众并不拥有戴斯蒙德的奇特经历乃至精神信仰,但也完全可以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
二、人文视角下的家庭
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美国是一个高度重视家庭的国度。在《血战钢锯岭》中,观众就不难看到基督教文化孕育出了主人公浓烈的家庭观念,如戴斯蒙德受到母亲的感染,也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在陪伴母亲去教会的过程中,戴斯蒙德因为见义勇为而结识了美丽的护士多萝茜,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亲情伦理价值是人文关怀的组成部分,来自家人的爱慰藉着每一位家庭成员。在大量美国电影中,主人公往往都出身于平常的百姓家庭,感受着来自父母、兄妹、夫妻等家人的正面影响,如晚辈对长辈的孝顺、平辈之间的和睦相处等,这种来自家人的影响有时候会扭转主人公的命运,如《阿甘正传》(Forrest
Gump
,1994)等,便有淋漓尽致的亲情、爱情伦理的书写。在《血战钢锯岭》中,戴斯蒙德的信念养成是与家庭密不可分的,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两个事件:一是在童年时期和哥哥打架的时候,差点失手将哥哥打死。就是在这一次教训中,“不可杀人”的信念开始进入戴斯蒙德的心田。二则是在长大之后,由于父亲长期的酗酒和精神失控,父母爆发了严重的冲突,父亲甚至拿枪对准了母亲,戴斯蒙德为了维护居于弱势的母亲而差点开枪将自己的父亲打死(在现实中,是父亲差点开枪打死戴斯蒙德的舅舅,最后父亲被警察带走)。这一次事件也差点使戴斯蒙德背负了弑父的罪名,“不可杀人”的念头不仅得到了巩固,也变得更为具体,即戴斯蒙德拒绝触碰枪支,以让自己尽可能地远离杀人的危险。电影并没有选择一气呵成地叙述这两个故事,而是将它们分开叙述,让观众对戴斯蒙德的理念有一个从难以接受到最终理解的过程。
另外,电影还将戴斯蒙德的行为做了另一种更为积极的解读。这种解读也同样与戴斯蒙德对家庭关系的反馈有关。美国电影中对于战争创伤的阐释主要分为两种:一类是PTSD综合征,又名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这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便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美国狙击手》(American
Sniper
,2014)、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Billy
Lynn
's
Long
Halftime
Walk
,2016);而另外一个则是“存活者罪恶感”,如“为什么其他人都死了,我却还活着?”在《血战钢锯岭》中,戴斯蒙德的父亲便有着非常明显的存活者罪恶感。从这一点来说,戴斯蒙德的家庭给予他的影响是负面的,父亲的暴躁、乖戾等差点造成戴斯蒙德的童年家庭悲剧。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促成戴斯蒙德后来“只救人不杀人”一系列行为的动机。在西方故事中,人物行为的动机主要都是爱恨、嫉妒、恐惧等强烈的感情,而自古希腊神话中,这种情感往往就附着在人物和父亲的冲突上。当一个人从父亲处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后,立誓不再成为父亲这样的人,这种思维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坚定的动机。而父亲一生困扰于存活者罪恶感的悲剧就是戴斯蒙德后续行为的动力。他极为不愿意重复父亲的悲剧,不愿意成为“众人牺牲而我独活”的父亲第二,于是在这种他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心理支配下,戴斯蒙德不断地救人,尽可能地让自己距离那个唯一的幸存者越来越遥远。从这个角度来说,吉布森以一种更为理性的方式来解答了戴斯蒙德的“神迹”,让观众能感受到相对于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来说,这样一个化戾气为动力的青年更有让观众感到亲切的人性。三、人文视角下的国家
《血战钢锯岭》中的最高一层人文关怀意义是国家层面上的,观众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电影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标识。并且这种爱国主义并不指向狭隘的、非此即彼的民族主义,国家成为电影叙事的一个立足点,在这个立足点上,吉布森建构的是与他参与制作的《勇敢的心》(Braveheart
,1995)、《爱国者》(The
Patriot
,2000)一脉相承的某种人文传统的传承:从维护个人利益上升到的对国家利益的维护。而这正是美国在当前激荡的世界文化潮流中能够站稳脚跟、掌握话语权的根基之一。人文主义一方面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又需要从个体扩展开来,关注个体所在民族是否能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再扩展到关注、珍视人类传承下来的各类精神文化财富。《血战钢锯岭》和《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
,1998),甚至科幻题材的《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
,1996)等电影一样,尽管电影并没有明确对观众提出“爱国”,但是在电影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表现出了勇猛无畏、敢于牺牲精神的人是为美国服务的军人。在这一类电影中,观众在将情感投射到主人公的身上,为主人公的安危而担心的同时,主人公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也能够引起观众深切的情感共鸣。并且,《血战钢锯岭》和《拯救大兵瑞恩》中的背景都为美国人深以为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独立日》的背景则是外星人在美国国庆日那天发动的对地球的袭击。由于叙事文本对正义性的把握,因此整个观影过程是增强美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的。《血战钢锯岭》中的战斗是在美军付出了大量牺牲的太平洋战场上。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后,美国青年人踊跃入伍,电影中也借上军事法庭的戴斯蒙德之口表现了,在他所居住的堪萨斯小镇上,甚至有年轻人因为体检未通过不能入伍而失望自杀。戴斯蒙德也拥有着一心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在入伍后他也很快发现了一群虽然性格各异,并且不断遭受打击,但和自己志向相同的战友。美国在电影中的定位无疑是自由的捍卫者。戴斯蒙德让战友帮他从战场上取回《圣经》的行为虽然危险却得到了战友的认可,这其实隐喻的就是一种对人类精神文化财富的珍惜。而处于人文性另一端的则是在军国主义指导下发起战争的日本。人文主义者穆勒在《论自由》中曾指出:“从长期而言,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事业的。”在军国主义的控制下,人显然是无法得到健康发展的,甚至电影中也表现了大量日军在战局恶劣的情况下,被当局命令以假意投降,实则绑手榴弹自爆这种自杀式攻击来对付美军,这无疑便是反人文性的一种表现。
梅尔·吉布森一贯致力于在电影中表达人文精神传统,看似平凡而又不凡的人物往往是他关注的对象,因为在这一类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是最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的。《血战钢锯岭》也不例外,从人文性视角来观照这部电影,不难看出处处都是人文精神的烛照,这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品质。
——拒绝拿枪的“开挂”战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