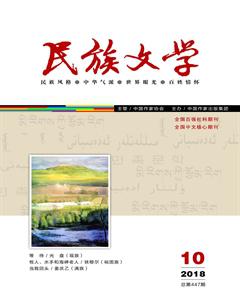远去的沃土
谭成举
我是农家出身,曾经是有过土地的。三块,都不大,小者两个平方,大者两亩。可惜如今它们都离我远去,我只能在记忆中、睡梦中去翻耕、播种,并快乐地收获了。
——题记
童年的沃土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的谷雨过后吧,那时我六岁,未上学,农村自然也无幼儿园可上,瞧见生产队安排全队的妇女去田边地脚打窝种南瓜,我在看守好为生产队代养的猪牛的同时,便跟了去,小心地从妇女队长分发给母亲的瓜种中偷偷摸下几颗瓜子“也傍桑阴学种瓜”来。
无疑,种瓜是偷偷进行的。那时,一切作物都是禁止农户私自栽种的,否则就是资本主义。私自栽种的瓜豆等物,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那是要被割掉的。所以,我之种瓜必须秘密进行。如若被他人知晓,告到生产队,不仅瓜要被铲除,家里大人还要被戴高帽、受批斗,另外还要遭处罚、扣口粮。所以,生产队不准种,家人也是不准种的。
而我却偏偏还要去偷着种。一是好奇心使然。那时不仅物质生活匮乏,精神享受也几近为零,小孩子除了能找同伴打打闹闹外,什么娱乐都没有,看到大人种瓜,这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自然心痒难耐。再说,好奇和模仿也是小孩子的天性。二是饥饿所致。生产队每月分的那点口粮远远不够吃,大人小孩每天都饿兮兮的,其滋味实在是不好受,若能种得瓜来,瓜叶可以吃,瓜花可以吃,南瓜无论是切片炒着吃还是切砣煮着吃,都是难得的充饥佳品。就是将瓜切碎了,掺几瓢水,煮成稀稀浪浪的南瓜汤,也是聊抑饥饿的。你说我能对种瓜不急切、不心动吗?
六岁的孩子本该懵懂,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却催生了我的早熟。既然是偷着种瓜,就要在“偷”字上狠下一番功夫——不能让人发现,至少要不能让人抓住把柄,否则,割起资本主义尾巴来,实在是让一家人受不了的。当然,这种瓜之举是连家人也不能让其知晓的。于是,我便将瓜地选在了离家一里之遥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岩氹氹中间,那地两米见方,四周有刺围遮,很难让人发现,即便发现了,若非抓到现行,根本找不到是谁种的。这就是我那时的小聪明。
整地选择在大人都出工,别的孩子或上学,或被大人带去工地了,而我将为生产队代养的猪牛赶上山并割满一挑牛草之后。工具不敢用大人常用的锄头,怕被发现遭追问,再者人小力薄也拿不动,只能选择大人一年用不上几次的小镐锄,轻巧,在那岩氹氹翻耕也实用,用后擦干净,往门角角一放,谁会注意?地,我整得很细致。先将地翻过来,挖泡、整细;再将草根、树棍、碎石之流捡拾干净;其后打窝,铺底肥。地窄,我只在四角各打了一个窝。铺底肥,原本最好的是发酵过的猪水粪,可我挑不了,人还没得粪桶高呢,也没那么大的力气挑,再者目标大,害怕被发现,我只得改用牛圈里的牛粪——牛粪是固体的,分几次少少地往地里运,目标小,不费力。牛粪运走后,留下的坑氹铺点草,把牛往里一关,一踩,几脚就踩没了痕迹,谁也发现不了异样。铺完底肥,还要在上面盖一层不薄的细土,如若直接将种子下在底肥上,底肥一发酵,产生高温,是要烧坏种子的。下完种子后,还要用细土将种子盖住,上下接地气,种子才能发芽。
从翻地到下种,我足足用了四天。这几天,苦和累自不需说,搞得我十分疲惫,每每吃完晚饭就睡,再不像往昔与同伴们疯癫个没完,不到午夜不归家,以致父母以为我身体出现了问题,吓得问这问那的。我卻喜悦,却满足。白天老是满脸挂笑,夜晚睡觉都笑醒几次。
也是天公作美,下完种这天,晚上飘起了细雨,这无疑为我的瓜子变为瓜苗起了催化作用。第二日我偷偷跑去抠出瓜子来看,它们的尖嘴上竟已开裂,探出了细细的、白白的、弯弯的萌芽。
我自然喜不自禁。自此我全身充满了活力,办事也格外有动力,眼光看什么都一片喜色。
几天后,芽苗就冒出了土,先是白尖,再是两豆瓣样的嫩叶,再是叶片的不断增多,再是长出了藤蔓。
随着瓜苗的每一次变动,我的喜悦就增加一份,激动就增加一份。我看着那不断变长的藤蔓,眼前就不由幻化出黄红黄红的鲜艳的瓜花,还有瓜花底部不断长大的南瓜,进而闻到了瓜花的味道、南瓜的味道,直让我饥饿的肚子咕咕造反,诱发出口水忍不住地长流。其间,我宝贝样呵护着“我的”瓜地我的瓜,除草、松土,喷水,几乎每天都要来一次,尽管那土是松的,草可以说看不到一星半点,可我仍然要将不多的“业余”精力全部投放在那两个平方的希望之上。
然而,好景不长。正在我信心满满、自我心醉地憧憬着如何烹食我的南瓜时,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从“我的”瓜地旁传来了嘈杂的人声。那时我正在为家人做着早餐——熬制苞谷糊糊。听到声音,我心头猛地一颤,感觉一定出事了,这也正是我在希望和喜悦中最担心发生的事情。我急忙将火熄灭,来不及关上灶屋的门就匆匆往出事的地点赶,这时也见出早工回来的大人们陆续向那里集结。
果然就是“我的”瓜地出了事。
我从那嘈杂的声音中知道了原委。原来,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小男孩因早上饿极了,便出门找三月泡充饥。找到“我的”瓜地旁,正巧有一棵三月泡树,尽管上面的果实还是青色,远远不到采食的时候,可饥饿难耐的他管不了那么多,统统对它们一扫而光。还不够,他又去周围细细寻找,这就发现了“我的”瓜地,这就叫嚷起来,引来了生产队长和他的不少“臣民”。
队长大发脾气,说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这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得割,这样的行为必须严惩……
接着,自然是展开调查。那时队长没有“破案”的技术手段,也没有有效的“破案”方法,靠的是淫威和敷哄吓诈。但是,那事的后果谁都知道,又有谁敢承认那是自己搞的“资本主义”?更何况那本身就不是他们的“杰作”。队长就把目光刺向了历来老实懦弱的父母,说我们家离这瓜地最近,不是我们家种的还是谁种的?想不到这次父母没有懦弱——大概也是想到了“资本主义”这顶帽子不好戴,后果我们家也无力承担——幸喜我也丝毫没有向他们泄露我的种瓜秘密——他们这次竟破天荒地顶撞这队长,死不承认。找不到证据,队长也没法,却又放不下脸面,便强行要我的父母将那四蔸南瓜秧扯掉,将地刨平,还压上几块大石头。
当时,我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我强忍着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悄悄地溜回了家。
其后,队长还多次来查看那块地以及别的地方是否有人栽种,是否还有人敢“复辟资本主义”。
至此,那块沃土夭折,成了我一世的记忆一世的痛!
第二年春上,我搬开石头,偷偷在那块地里种上一棵小小的岩桑树,后又将那些石头压在树的周围,造成树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假象,这才再没人发现。这树后来茁壮成长,每至初夏,都结满桑葚,饱了我等的口福,饱了鸟雀的口福,成了我不灭的念想,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风景。
我的土地我的情
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我们家有了自己的土地,我们成了土地的主人。那种喜悦真是无法言表,总感觉在那土地上劳作时有使不完的劲,就是在那土地上站一站,也感到温馨,感到踏实,感到再也不会有饥饿的降临。我每每从学校回归,都是要去土地一趟的,或耕作,或看看土地上的庄稼,或感受土地的滋味。那不是父母的强迫,而是发自内心的自觉。
一九八三年,二哥成了家,于是,父亲便让我们三弟兄分家立户,当然土地也分成了三份,其中就有我的一份。两亩。
那时,我正在县师范读二年级,还有一年就要走出校门参加工作了,原本我是不打算要分给我的那份土地的,我不知道我将来会去哪里工作,但我知道我工作后是肯定没有时间好好伺候土地的。我既然无法正经地去亲近土地,我就不能荒废了它,愧对了它,否则,那会成为我新的痛,我会感到我的无耻,我会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但父亲不依,他有他的思维,他有他的考虑。他说,你今后无论在哪里工作,你是农村出去的,你就永远是农村人。农村人怎么能没有土地呢?你将来就是没时间回来种它,还有我们种,你还要找媳妇,还有媳妇要种,再说,你今后万一什么都没得了,你还有土地!你要老,你要退休,你还得回到农村,你还得种你的土地。我拗不过父亲,只得勉强接受了,但我真的没时间正正经经去侍弄土地,我只得将我的土地交给父母。父母爽快地接过了土地,但父亲却说,你记住,这土地是你的,我们只是暂时代你耕种,今后你还得自己来种。
一九八五年,我师范毕业后,分回了我老家的学校任教,老家学校教师少,除了数学课外,我任教那个班的其他课我全包,还要当班主任,我哪有时间回去正经地伺候土地?
第一个周末我回家休息,自然要去亲近我那份土地。我那份土地被父母他们种上了苞谷。此时苞谷正蔫须胀砣,那个大籽满的苞谷砣,散发着诱人的清香,让我从教学的疲劳中一下子解脱出来,瞬时感到神清气爽。我不禁闭上眼睛,深深长吸了几口气,深切心肺地感受一下苞谷的温馨和土地的恩惠,感受父母的辛劳付出和他们对土地的深爱。
见此,陪我同来的父亲笑着说,朗门样?
我不假思索地说,那当然,您侍弄的土地那还有说!
父亲深情地说,土地是个好东西啊!土地有情,你对它好,它就使力地回报你!
我也深有感触地说,人有情,土地自然也有情啊!
父亲看了看我,严肃地说,这回你感受到有土地的好了吧?
我说,自然,有土地什么时候都好!
父亲又说,你也分回来了,学校离家也不算远,这地,我还得交回给你种。
我听父亲这么说,一下子急了,说,除了周末,我哪有时间来种地?
父亲沉着脸说,那我不管。
我说,你不管哪个管?当初分我地时,我说不要,你偏要给我!
父亲说,你刚才不是还说有地好么?
我说,有地是好,可那也得有时间种啊!没时间种,让地荒废了,那是心中愧得慌的事啊!
父亲想了想说,这个道理我自然懂。可是,我不能总种着你的地呀。我们也老了,种不动地了,也怕愧对土地呀!这样吧,我给你找个人来种,好不好?
我叹口气说,那也只得这样了。不过,别随便找人,把地种坏了。你得找个种地的好手,那才对得住那地。钱我来出。
父亲不再说什么,只是满脸的笑。那笑,在我看来,既有满足,又有狡黠。我不知道向来老实的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笑。
而我,则只剩下满心的苦笑了。
第二个周末,我又回到我的土地上,我抚摸着不断走向成熟的苞谷砣,心中说不出的滋润。
这时,原本去赶场卖鸡蛋的父亲匆匆赶了来,要我赶紧回去,说是帮我种地的人找到了,并且来到了家里,要我赶快去见面。
我自然心中一喜。
母亲正在刷锅做饭,满脸喜庆。堂屋里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女人,正在交谈着什么。老者我认得,是我的舅娘;少者我却不识,只是觉得与我年纪相仿,有些娇小,但长得蛮清秀,很入眼。我却不知她们俩与我要找的“种地的”有什么关系。舅娘自己有一大家人,她是家里的顶梁柱,自家的地她都耕种不过来,哪还有精力来帮忙种我的地?那个年轻的女孩长得细皮嫩肉的,又那么小小个的,也不是种地的料呀?
我正疑惑,想问问父亲怎么回事,舅娘却眼尖,发现了我,我只得急忙走过去给她们打招呼。那女孩羞涩地站起来,对我点点头不做声,只低垂着眼睑红着脸看着自己的脚尖微微地笑。舅娘也站起来,笑着向我介绍那女孩,说她是我某某姨娘家的表姐,大我几个月,现在在学裁缝,是应我父亲之请找的帮我种地的。
听完舅娘的介绍,表姐轻轻地叫我一声“表弟”,便抿着嘴,搓着手,不知所措了。我也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脑中瞬间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是怎么逃离她们的。
我找到父親,他正在灶屋帮做饭的母亲烧火。他正与母亲商量着什么,他们俩都一脸的喜不自禁。见我走来,便问我,人,你也见了,朗门样?
我低着声音板着脸没好气地说,您上次说,是给我找一个帮忙种地的,这次您却让舅娘帮我找来个裁缝。裁缝只会和布打交道,她哪里会侍弄地?
父亲仍喜色不减,说,裁缝朗门了?她就配不上你?
我说,我要您帮我找的是来种地的,这种下力的活,只有男的才耐得活,您找来个女的,还是个只会拿剪刀不会拿锄把的,长得也那么单薄,她种得了地?
一直没说话的母亲听了,忍不住哈哈一笑,忙伸过头去偷偷瞧舅娘她们一眼,后才低声对我说,你个傻儿!亏你还是教书的!讲给你找个帮忙种地的,你以为就真是种地的了?那是给你找的媳妇呢!
父亲也说,对农村人来说,媳妇不就是“种地的”?找到了媳妇不就是找到了“种地的”?
父母这么一说,我一时懵了。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观念?!
等舅娘她们吃过饭走后,我与父亲大吵起来。大致的意思是,我还年轻,才十八岁,还不想这么早找对象;我工作还没稳定,端公家碗服公家管,说不定哪天我就调到别处去了,找个“半边户”在家,我还是没法回来帮她种地,到时她身累我心累,难免会搞得吵吵闹闹的,大家都不舒服;再者我和表姐是近亲,近亲结婚将来对子女不利,国家法律也不允许……
我的坚决反对,父亲也没得法,这门亲自然没开成,搞得舅娘对表姐不好交代,很尴尬,以致好久都不理我。而我那表姐,自那一别,她是再也不见我了,就是我母亲过世,她也没到场,只是请她的母亲带了个“人情”,直到三十年后的一天,她的母亲去世,我去吊唁,才再次见到她。这时的她,已是儿孙满堂,而当年的风韵仍然留存。我们只匆匆地打过招呼,没时间进行交谈,我不知道她的景况,其实我是很想知道的。母亲过世的悲戚明显写满她的脸上,而丝毫看不出她对我的幽怨,这,也许是时间的磨砺让她淡忘,也许是阅历的递增让她理解了我当年的拒绝吧。
我没有找到帮我种地的人,父母只得继续,但父亲有言在先,只给我再种一年,一年内,我必须要自己找一个满意的“种地的”。这一年,尽管父亲时常问我找到“种地的”没有,我也不急,只一味地拖延,一味地应付他。正当父亲下最后的“通牒”时,我被调离了老家的学校,我知道我今后回家的时间就少了,我是再也没时间侍弄我的地了。不得已,我将我的土地,还有包括山林、房屋,一应分给了我的两个哥哥,白白送给他们,不要一分钱的补偿。
离开老家的前一天,我特意去了一趟我的土地。地里还是种的苞谷,苞谷比往年长势更好。我先是站在地边看,看个大籽肥的苞谷,看肥沃出种的厚土;再是毫无目的地在地里往复地慢慢行走,穿梭在那密密的苞谷林间;其后是一屁股坐在地里,双手捧起泥土慢慢地搓,深情地闻那泥土的气息。我不由得想起了六岁时私自开垦的土地,还有那地上长出的瓜蔓……
离开那地时,我没有流泪,却满心伤感,默默地将地在心里记了又记。
汗洒贫瘠地
一九九二年,我成家了,妻子不是种地的,她是我们学校旁乡里医院的护士。这似乎有违父亲的初衷。我们两边家都在农村,家里条件都不好,双方父母又多病,那时还没兴外出打工,双方的兄弟姐妹都只得待在家里耕种土地,这就缺钱用,双方父母一病,就只得往我和妻子这里送。那时工资不高,我和妻子总计只有五百多一点。我们的日子就过得很艰难。这就让我萌生了要找块地种种的想法,这样,除购买国家供应的粮油以及偶尔去场上买点肉、蛋之类外,在蔬菜方面自种自给,也是可以节省出不少的钱来的。那时的人都珍惜地,把地看得像命根子一样,谁还有多余的地送给我们种?
没有地,就自己开垦吧。刚好在医院的驻地后面有个打岩场,大致两分地。土是取岩后留下来的,贫瘠,里面多碎石,而且经过拖岩石的车辆的反复碾压,变得极其死板。没有人要,便闲置了,稀稀拉拉长了些芭茅草。我便与妻子商量,把这块地耕种起来。妻自然同意,贫穷人家走出来的人都能吃苦,也能放得下脸面。
锄头和镰刀是妻从她的老家专门找她的外公、舅舅打制的。她外公和舅舅是她们那一带有名的铁匠。给外孙女、外侄女打制的器具就自然格外上心,使用起来自然就耐用、好用。只是没有锄把、刀把。妻的娘家在城郊,那里生长稻谷,却不生长树木,我只得利用周末徒步三四十里路去老家。老家那时交通还很不发达,无公交不说,车路也还没修到家,回一趟老家是真不容易的。
趁这次回家也正好去看看父母,看看我的曾经的土地。
父母见我回来,自然高兴,特别是知晓我回来找锄把、刀把,要开荒种地,更是喜欢得不得了。他马上就上楼,将楼上炕得干透了的一节米多长、碗口粗的青树取下来,用他那多年干木匠活的手艺,斧砍刨削起来。他说,你能重新把土地种起来,好呀!土地是个好东西,不管任何时候,你只要有了土地,你就能生存,你就能过日子!
我去了我曾经的土地一趟,那地被哥嫂们种得很是厚实,末秋时节,收割后残留的粗壮的苞谷秆,告诉我这方沃土没有亏待庄稼,没有亏待种庄稼的人,这让我欣慰又让我依恋。
开挖那块地很是费了我们一番心血的。那段时间,一有空,我和妻就忙碌在那块地里。妻负责捡拾并运走碎石,我负责开挖整土。开挖土地自然是个苦差事,一锄下去,往往与躲在土层下面的乱石发生碰撞,迸出的火花四处喷射,也让锄头弹出老高,将我的双手震得发麻剧痛,即刻爬满血泡。好在我吃惯了苦,凭着毅力坚持了下来。一周后,我的双手已变得木木的,好像那手已是别人的,硬是不听了我的使唤,以致写起字来十分难看,形若蒙童学书,引得学生大笑,当探知此状的原委后,见我掌上血泡重复着血泡,便又生出一片感佩,我也趁机现身说法,对学生进行一番热爱土地、勤劳自给的教育,也算另有收获。而妻的两手也是粗糙硌人,远远与她护士的身份不相符合了,让她苦笑,让她无奈。
整出来的土瘦弱不堪,要使它变得肥沃厚实,可得花上不一般的功夫。好在学校和医院不缺农家肥,一有空我就挑來泼洒。泼洒一遍后,让太阳晒一周,我又将地翻一遍,接着再泼洒农家肥。如此反复三遍,直到农家肥在土中发酵,使土地发生质变,看到昔日那死板的黄土变成现如今松软的黑土,我才开始种植。
时序已是冬日,许多品种的蔬菜早已过了种植期,我只得买来青菜幼苗——那种在寒冬中勃勃生长的爱物,避开日照,在傍晚之时栽种,又淋上水,只盼它们能好好存活,以不枉我这么久以来的苦心和下的苦力。第二天起来一看,这些菜苗无一不活得新鲜,让我大喜大慰,感谢土地对我的赐予!感谢菜苗对我的怜惜!
至此,我每早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察看青菜的长势,捉去喜食嫩叶的青虫。从学校归来,每每见了土地缺水或是稍有板结,亦或长出了野草的幼芽,我都及时洒水、松土、除草,按当地老百姓的话说,我是“把它们当成幺儿来盘了”。
毫无疑问,我的青菜获得了大丰收,除了能够自给,给我省出不菲的菜钱外,还让妻子的同事们有了尝新的去处,也给我的同事偶尔带点去,博得了一个好人缘;有时逢场,恰好又遇到我或妻休息,我们还摘来去场上卖,因我家的青菜叶大梗细,肉头肥厚,脆嫩新鲜,很有卖相,故特好卖,这也给我家挣下些闲钱,聊补工资度用之不足,也算意外的财富。吃不完、卖不赢的时候,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将青菜叶采来洗净,划破菜梗后,于开水中一焯,捞出来在太阳下晒干,使之微黄清爽,很是抢眼。储藏一段时间后,需用时再用温水浸泡,发软,切成细段,做扣肉蒸用,或与猪蹄、排骨炖食,都是绝佳的美味。以致医院的美眉们常来我家蹭饭,直夸我的手艺好,人又外慧内秀,可惜她们下手迟了,竟让妻将我占了去!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让我更加勤奋地侍弄起这块土地来,也更加频繁地赠予她们菜蔬,更加频繁地请她们来我家品尝我做的菜肴,直到我离开那里二十余年后,每与她们相遇,她们还对我的手艺念念不忘、夸赞有加。
第二年,我根据季节的转换,种辣椒、种红薯、种黄豆、种茄子、种豇豆、种南瓜……林林总总,品种繁多,巴不得什么都种,只嫌土地窄小了。自然,种出来的蔬菜瓜果,让我的资金短缺有了更大的改观。
四年后,我改行进了城,然土地我却没有丢弃,平日叫妻伺候,每至休息和节假日,若不加班,我都远涉四十余里赶回去,去侍弄“我的”土地,侍弄我的蔬菜瓜果,从中种出快乐,种出成就,种出一世人缘,种出念念难忘的好口碑,也种出与土地的一世情结。
三年后,妻调往另一家医院,我们再没有理由占据那地了,我便将其赠予了他人,直到后来那地被新修的房屋挤占,那块地才无奈地结束它的辉煌,承受它别有滋味的新的使命。
然而,那块地与我的走出困窘,与我及他人获取的快乐,一直息息永存,在于我情深致远,永世难忘了!
特别的怀想
我是个很怀旧的人,一旦什么植入我的记忆,我就情感难变,永世不忘了。我对我曾经的几块土地就是如此。
我和妻都进城后,就丢失了土地,尽管每日忙碌,尽管有不少新的事务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可对土地的那份情愫却难释怀,在没有找到新的土地的日子里,我一旦闲空下来,就显得手脚无措、心慌躁动。这就招来一些旧识的笑骂,说我人贱,好不容易逃离了乡村,渐渐脱离了泥土的气味,却偏又对土地念念不忘。说现在不少农村人都外出打工,远离“农”字,在城市安家,不事农事了,还有不少在校的农村小孩只讲享受不识农物,而我却若旧时的农人,老对土地念念不忘,好似离了土地就不能生存……
我无言以对,我的确如此。
一九九八年,我告别租住房,有了自己的家。在购买新房时,我特意选择了顶楼,并与开发商协商,楼顶归我使用,在不改变楼层结构,不影响楼层承重的情况下,我要在上面栽瓜种菜、植花养草,以之眷恋土地、怀想土地。
搬进新房后,空闲之余,我便在楼顶将盆钵缸罐之属沿女儿墙摆了一长溜,再用塑料袋从郊区一袋袋地将泥土提回来倒入其中,开始种植起菜蔬花草来。在楼顶的种植,由于盆小砵浅,远远找不到那种在大地上耕耘的那种感觉,那种快慰,真是有劲使不出,浑身憋得难受。这就更加怀念我乡下的曾经的土地来,才真切感受到土地之对于我的重要。于是,每至耕种季节、收获季节,我常常站立楼顶,眺望我曾经的土地的方向,想这时的土地怎么样了,庄稼怎么样了,并遐想出土地的如何倾力奉出、庄稼的如何长势喜人、瓜果蔬菜的如何肥美丰收!以致妻常说我痴了呆了,丝毫没有国家干部的样,仍旧是一个跳不出农门的旧时典型的农人。
每至假期,我都相邀妻子回归老家,走访尚未外出打工、移民城市的不多的亲友,更多的是看看那些土地,当看到大片大片的土地被闲置抛荒,我的心中便五味杂陈,有为当下农人再不为填饱肚子而土中刨食成为新型农民而高兴,又为曾经维系农民生命的土地如今被拋弃,只留下满目的荒凉而悲戚。至此,我便关注起各种媒体来,从中探寻农村土地的出路问题,我便想,除了退耕还林,除了土地流转,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新的让土地焕发生机,让土地回归本质的举措来的。
我又想,十年后,一旦退休,我是要回归我的老家,回归我的农民本真的!
因为,土地是我一世的情缘啊!
责任编辑 郭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