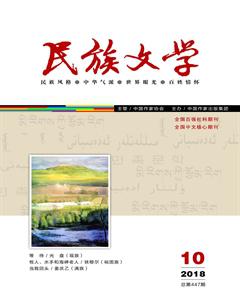大化绿雨
阿慧
在大化县城住下,刚要出宾馆买一条毛巾,站在廊檐下一看,下雨了!伸头淋了一脑袋,雨点打在头顶软凉凉的。抬眼一望,雨丝密密地糊了我一脸,仍是凉凉的软。小雨下得如老婆婆纺棉花,不急不慢,有条不紊,细细柔柔地哼呀哼。咋也不像我居住的中原夏季的雨,那可是个急性子,那阵势,就像壮妇人端簸箕朝铁锅里倒豆子,噼里啪啦,稀里哗啦。我想再享受一会儿大化雨的温柔,一低头,雨停了,就像它来时那样悄无声息。正面一座山,尖着绿脑袋,透过高耸的楼缝,眯着绿眼睛看我。我看它,也看东西两边的大山,才明白,我和来自全国的二十多位作家,被大化的山们紧紧地包围了。
山洼里的宾馆很静,梦境犹如一面没有皱纹的湖水。一声鸡鸣陡然亮起,好似瓦片划破湖面。我从梦里活过来,翻了个身,正赶上这只敬业的公鸡又一声高歌,“喔喔喔——”
竟听出了几分韵味。那鸡叫的尾声还带着一股水波音儿,湿润柔长,婉转动听。天大亮时,鸡不叫了。我扒开窗帘,没找见那只艺术范儿的鸡,却见楼下一地水湿,五六片被雨水摘掉的芒果树叶,把水泥地面映成水绿。雨是夜间来的,悄悄地润湿了地皮,也润湿了那只公鸡曼妙的嗓音。
去七百弄国家地质公园参观的途中,阳光正好,似一张纵横交织的明晃晃的大网,把密匝匝的山尖,一股脑地给网住了。在游走的中巴车上,我很细密地把游到眼前的大山给看了。山体上的泥土薄薄的,酷似一片没有发育完好的面包皮,但这些许的热量,足够滋养树木、藤萝、竹子们长大,丝毫不影响它们一代代快活地开枝散叶,把个大山从头到脚披挂得绿光闪亮。山洼里生长着一片片碧绿的玉米,绿腰带似的叶片之间,嫩绿的玉米棒娃儿笑逐颜开,明黄、淡紫的玉米须动情地抖动。坡地上的梯田水纹般扩散,一层层波到山底,似大山肚皮上黑褐色妊娠纹。红薯的嫩叶在使劲地伸展,它正努力抓紧头顶上疏散的阳光,给地下的宝宝蓄足力量。
人和车在七百弄山里转悠,我稠密的目光,无法锁定大山的群像。
大化县的山,密集得像是图省事的懒婆娘,一锅蒸出来的绿豆面窝窝头,一个挨一个,团团围一锅,没有下手的地儿。但是,终究,锅底还是富裕了一小块儿,那么水深火热的一块地儿,却足够使几千年,一批批因政治和战争的逃亡者安身立命。追击者强悍的视野、弓箭、铁骑,终被密不可分的大山严严阻隔,无数个深不可测的“锅底”,让强者们无处立足,无法下手。难怪,世代居住在“锅底”的瑶族人,把这无数个陷在山底的洼坑叫做“弄”。
站在这七百弄高高的垭口,我颤抖的视线无法翻越那蛇形于乱石灌木丛中的1418级石阶路。台阶如一条毛绒绒的井绳,系上五百米深的弄底,和二十七户瑶族人家。我瞪着大眼珠子,使劲朝下望,只望见最近的一处农舍。它背对垭口,背影弥漫着一股拒绝喧闹尘世的情绪。两间小瓦屋一红一蓝,红的那间,看似土法烧制的红瓦片覆顶;另一间,修缮不久的模样,屋顶用天蓝色塑钢瓦覆盖。两间房紧密相连,似一对绑定命运的夫妻,一个紧靠另一个的肩,没有缝隙。房前屋后似乎是树木和庄稼地,巴掌大一小块儿,像泼了颜料水,绿得很不真实。我正看红蓝房屋时,阳光已经从房顶错开了,探照灯似的去聚光弄底更深的人家。西边的山脚顿时明亮了,南、北、东三座大山埋在阴影里,像三个身披墨绿盔甲的威严卫士。
我伏在水泥护栏上,眼睛和心魂都被弄底人家给挂住了,一时半会儿很难拽上来。
我担心他们的家被水淹没,毕竟这里雨水多,毕竟水往低处流。而当地的一位女作家却说,弄里的房屋从来没淹过。因为这里是特殊的喀斯特地貌,石灰岩地质,有许多隐形的地缝和地洞。“有水也存不住,都流到地下暗河去啦!”她说。听后,我又担心太干旱,人畜饮水怎么办?女作家说,半山腰岩洞有的地方有泉水。再者,家家户户备有水柜,还修了小池塘,水泥糊底,储存雨水。以前没有水泥时,就人工练塘,用牛踩,用棍舂,把塘底夯实,水就可以被留住。
“不淹不旱呢!”她笑着这么说。
我也笑,但忧虑依然存在。
担心女人半夜生孩子,毕竟洼深路远。女作家说,弄里有经验妇女专门做接生,生过孩子的女人也学会了接生。
“现在啊,孕妇们提前住医院待产。妇女娃儿都好着呢!”她脆生生地说。
担心有人突然生病,毕竟台阶陡,山难爬。她说,病轻不用治,家传的土方子,瑶医草药,银梳子刮痧、竹筒拔火罐,穴位放血,月子药浴。病重的人,靠人背,或亲邻们帮忙抬到弄外。
“有瑶医啊,还是巫师呢,会巫蛊咒语,主持婚丧嫁娶。”
我又瞪大了眼珠子,看大山,看弄底,看飞鸟,看白云,心底升腾一股悠远的神秘。
大山庇护了山民的祖先,大山也阻碍子孙们的视线,但大山却给深洼里的瑶家人,世世代代浸染了灵魂的底色。他们在生存中相携,在幽谧中相爱,在苦难中智慧,在寂寞中造化,在孤独中纯净。他们幸福地生活在自己单纯的世界,他们深爱着这里的家,哪怕是峰峦叠嶂,雾气苍茫。
出了垭口,阳光一闪就不见了,天在车窗外暗了一下,就像一片云走亲戚,走着走着就停了,待在空中想心事,想着想着就哭了。我看见车窗玻璃上小水粒越积越多,眨眼间汇成股股水流,风把它们吹成四散的白蚯蚓。想起昨晚和今早的雨,明白了,大化的雨说来就来,似乎哪片云彩都会下雨,哪株小草都顶着水珠,哪个生命都有色彩。
在北隘码头下了车,不远处两条游船歇在那儿。作家们纷纷撑起伞,雨珠在伞面上跳动不安。我不打伞,想让雨点在衣裙里藏匿。
意外地遇见两只鸡,在路边一株绿藤下躲雨,公鸡伸长脖子抖了抖雨水,金色的羽毛立马蓬勃起来。母鸡没有抖,它什么也没有做,它只是望着公鸡抖羽毛。突然想起资料上提及的著名的七百弄鸡,它本是山里的野鸡,吃草药、喝泉水,住山崖,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后被山民捉回寨子家养,仍是喝雨水,吃虫子,没有宠幸过鸡饲料。据说,宰后的七百弄鸡,鸡皮淡黄,肌肉柔白,切面有光泽,皮下脂肪少,肉质鲜嫩有弹性。我在瑶族布努人家的长桌上见过这道菜,鸡被包裹在一片油绿的芭蕉叶里,鸡皮黄亮亮,金闪闪。作家们都说口感脆软,味道清甜。我没有入口,因为饮食习惯,还因为那只鸡,那只在宾馆之夜独自高歌的文艺范儿公鸡。
脚边一簇小黄花,五片花瓣,黑色花心,组成一张娇憨的小笑脸。接连不断的雨点,砸得它支不住脑袋。我歪着脑袋看它,见雨点稍微一松懈,它就摇晃着抬起头,稳住了,仍是一张可人的笑脸。
低头看,雨水藏在草窝里,绿汪汪的,疑心下了一阵绿色的雨。
上了船,我不舍得进船舱,在尖圆的船头多站了一会儿,与岩滩水库两岸的山,来了一个湿淋淋的凝视。这里的山,很安静地沿湖站成两排,细密的雨丝中,犹如披上了一层缥缈的轻纱,看上去有些仙气。的确是仙儿,山间接连吐着白烟儿,这儿一缕,那儿一丝儿,袅袅地蒸腾,在山尖汇成洁白的一片儿,又亲热地黏上旁边的一片儿,越黏越大,团团的不分开,飘来荡去,把两岸的群山欢腾得云雾缭绕,山间人家的瓷砖白楼、红瓦老屋在白雾里时隐时现。
想起《搜神记》里这么说:“下雨时,神仙们从山上下来了,刮风时,神仙们都回去了。”想到大化常下雨,想必神仙们常下山。他们常常披着白云,到弄里人家坐上一坐,和上妇人灶膛里的炊烟,随上老汉烟斗里的白烟,弄得小瓦屋到处都是仙气。
湖面没有风,静静的、平平的,让人心生安然。风是游船撩拨起来的,雨丝就斜斜地飞,落上水面,水皮唰地起了一层麻坑,像谁冒然撒了一把细砂。
我站在船头深深地吸气,负氧离子裹带着雨气,排着队滑入我的肺,我贪婪地吸補这绿色的“空气维生素”。在中原吸惯了粘稠的雾霾,乍一换气,一时间身心还有些小激动。
湖水是绿的。岸边慈竹、木荷、香樟碧绿的身影,远近高山墨绿的倒影,把一百多公里长的湖水,映照的得润绿如珠。真应了它诗意的名字:“绿珠长湖”。
雨中,大化的山水,美得不像是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