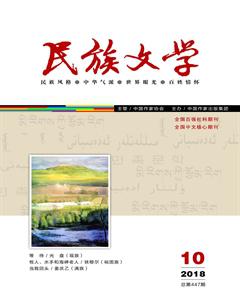坡头传奇(小说)
向本贵
一
老林开始来坡头的时候,人们还以为是周大树家的什么亲戚,戴一顶旧草帽,脚上穿一双黄跑鞋,背上还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袋子。正月,没有一丝儿暖气的太阳挂在天空,寒风呼呼地吹,略显单瘦的身子微微发抖,走在坡头蜿蜒崎岖的田埂小路也是小心翼翼。
周大树是坡头村的村主任,这些年一直在县城的一家厂子打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住些日子。春节过去才几天,还没来得及去县城做活呢。
这天晚上,坡头村召开群众大会,人们才知道,来周大树家的这个中年男人不是周大树家的什么人,而是县扶贫工作队派到坡头村扶贫的工作队员。人们就更加不待见了,有人还在老林说话的时候离开了会场,听他说已经听过不知多少遍的现话,不如回家睡觉。况且,说到最后,就要大家在搬迁的进度表上签字画押。
过去,田坪乡也来过扶贫工作队,都把坡头村当作扶贫的重点,但他们住在乡政府,平时也就来坡头走走看看,开个会,要说带来了什么实惠,坡头村的几户困难人家,是他们给办的低保,一些遭受天灾人祸的人家吃的油盐和大米,基本也是他们给弄来的,经常还弄来一些旧衣服分发给那些冬天穿得不怎么厚实的老人。如今农民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要是家里有人去城里打工,也不愁没钱用,这些,他们实在是不怎么看得上眼。当然,坡头村的人们也是有奢望的,谁来给他们办了,他们就给谁立功德碑。按照坡头村人自己的说法,祖宗留给他们安身立命的家园百样都好,却是有两条桎梏着坡头村的发展。一是路,二是水。要想富,先修路,水就更加不可或缺。没有水,不能活,更别说建设美丽乡村了。进进出出走的是泥泞的田埂阡陌,三月到八月这六个月,一盆洗脸水一家从老洗到小。美丽从何谈起。只是,来坡头村扶贫的工作队跟乡里领导一样的口气:“修路难,引水更难,还是往山下搬吧。修砖房,钱补得多,搬迁木屋下山,也会适当补一点儿。要是在乡场新建的小区买房,钱就补得十分可观了。”
这就让坡头村的人们骂娘了,你们只知道叫我们往山下搬,搬下山去,能赶上坡头吗。扶贫工作队和乡领导的口径高度一致,出门走的是平坦的水泥路,自来水接到了灶头。在坡头,做梦吧。坡头村男女老少的脸上做出一种不屑,口径也是高度的一致,四个字,坚决不搬。更让领导想不明白的是,别地方的农民打工的目的,就想着把老婆孩子弄到城里去,进不了城,就往镇子上搬,做半个城里人。坡头村的人们却不,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乡场新修的小区更是懒得正眼看一看。他们攒了钱回到坡头修砖房,没有公路,砖瓦水泥靠人工挑上山去,豆腐盘成肉价钱,也在所不惜。
老林那天晚上的会开到什么时候,人们不知道,是不是最后只有周大树一个听众,也没人问起,但人们觉得老林跟过去来坡头村的扶贫干部有些不一样,那天晚上他沒有离开坡头村,第二天也没有下山去,有人发现周大树的女人还把自家的厢房打扫干净,给他开了一个铺,那样子,他是要在坡头住下来了。人们就又开始骂娘了,这是个难缠的主儿,不把大家弄下山,只怕不会善罢甘休。
只是,一天一天过去,老林再没叫大家开会,也没听他说要大家搬迁的话,更没见他拿着一摞搬迁时间安排表格,挨家挨户要大家在上面签字画押。但老林的身影却是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开始的时候,总是看见他站在周大树家门前打望,一站就老半天,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让他如此专注,周大树的女人叫他吃饭他也没有听见。后来,他就沿着村前的田埂小路往下走,小路弯弯扭扭,匍匐在层层梯田旁边,脚步虽是细碎,也能踩出泥土的芳香,氤氲在初春的空气中,荡漾出让人心醉的清新味儿。
南方的山村,基本一个样貌,房子建在半山腰,占天不占地,村前的平缓之地,一定得留出来,种苞谷红薯,或是开出梯田,插水稻。这是祖宗传下的生存法则。坡头的梯田好不壮观,一层一层,从村口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脚,有人丈量过,田间小路,蜿蜒四千八百米,老林说他却是数的梯田,从村头到山脚的公路旁边,共有一百九十五层。
当然,老林是要去看那条没有修成的简易公路和那口用水泥封起来的水池的。简易公路在梯田旁边的山岭上,隐藏在深密的杂树林里,也不知道转了多少道之字拐,到了山脚却没了,被一条深深的沟壑给掐断,从乡场修来的公路已经到了沟壑的那边,像是伸出的两只手,只能隔壑相望,却是无法亲密相握。人们进进出出,难得绕来绕去,还是走的与梯田相伴相依的泥泞田埂,简易公路上长出的杂草也就过膝了。水池修在村子后面的林子里,有屋子那么大,钢筋水泥,十分牢实,里面却没有水,像是一只干涸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渴望着蓝天。人们发现,老林在梯田旁徘徊了两天,又沿着简易公路来来回回走了两天,过后就呆呆地站在山脚的沟壑旁边,也不知道他想的什么,一站就老半天。第五天,就又站在村后面那口没水的水池旁边发呆去了。在水池旁边站了一天之后,就开始一家一家地走。人们见了他,不好关门拒客,却是做好了思想准备,他要说搬迁的话,不会给他好脸色。
让人们感到意外的是,老林进门除了问问家庭人口,生活情况,收入来源,就是和空巢老人说说白话,或是逗逗留守儿童,过后,那张清癯的脸上就流露出一种惊讶,两只眼睛还放光,说出的话也有些情不自禁:“坡头真美。”
也常有外面人来坡头看梯田,特别是五一黄金周这样的节假日,城里一些人或是骑自行车来,或是开着小车来,他们把自行车或是小车摆在山脚的公路旁边,大呼小叫地爬上山来,惊叹坡头的梯田真美,坡头的空气真新鲜,坡头的村落古朴而沧桑。过后就说,只可惜缺水,路也不通。坡头村人当然知道他们说这话的含意,好不容易爬上山来,汗流浃背,唇干舌燥腹空,却是找不到一杯茶水喝,把钱拍在桌子上,也没人愿意给他们做饭吃。
老林不说他本该要说的话,却是用这样四个字来赞美坡头,就让人们犯了嘀咕,你不是来动员我们搬迁的吗,怎么跟我们一个鼻孔出气了。没觉悟啊。
老林来坡头,的确背负着要把坡头村一百多户人家的六百多口人弄下山去的重大任务,他当然也知道坡头村的群众不会买他的账,要是愿意往山下搬,还不早就搬下山去了,留着他来啃这块硬骨头啊。
周大树什么时候离开坡头去县城打工的,老林不知道。老林来坡头村的第一天,就郑重其事地找周大树谈话:“今年不准去城里打工。当村主任,自己却去打工挣钱,像什么话,心里还有群众没有。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抛到哪里去了?”县里来的干部,跟一个每个月只拿几百块钱生活补贴的村干部谈话,还是很有点儿派头的。
周大树脑壳点得像鸡啄米,眼睛盯着老林,一脸的诚恳,一脸的卑躬,嘴里喃喃道:“领导教诲得好。不忘初心,记住乡愁。”
老林心里好笑,还记住乡愁呢,又没要你离乡背井,远走天涯。不过他还是想趁机跟周大树认真谈一谈,当然是谈往山下搬迁的大事。老林心里盘算,动员周大树带个头,把家什搬到山下就成,他叫车运到乡场的小区去,新修的砖房任他选,价钱上还有优惠,不买小区的房子也行,把木屋搬下山,公路旁边的屋场地基由他挑,费用全免。还没张嘴,仅仅才是做好了千难万难也要把他拿下的准备,周大树的孙子突然就扯起嗓子哭着找娘,声音像是嚎春的山麂,胖嘟嘟的脸上全是眼泪和鼻涕。周大树的儿子儿媳正月初三就去广州打工,把才三岁的儿子甩在家里。周大树和他女人忙着哄宝贝孙子,把他这个扶贫干部的话当作耳边风了。
夫妇俩好不容易让孙子的哭声停下来,老林就又开始了他的谈话。周大树有点烦,脸色当然就不怎么好看,说,刚才开会你说了那么多话,半夜过了,还说,不累吗?有话留着明天说吧。正月不完还是年。不急,慢慢说,慢慢消化。
那天早晨,老林又站在村口的梯田旁边打望。回来的时候,却没看见周大树,问周大树的女人,她说不知道。打他的手机,关机。老林有点恼,心想一个早晨我就站在村口的小路上,长了翅膀也飞不到哪里去。还想问周大树的女人什么的,却被周大树孙子的哭声淹没了,周大树的女人有些不耐烦地说,该说的还没说完啊?他去县城打工了。老林真的想骂娘了,居然敢在扶贫工作队的眼皮下逃跑。咬着牙说,我把坡头村百多户人家一家一家走完,再去县城找你。
转眼就到了二月,挂在天上的太阳渐渐地暖和起来,梯田里的草籽花开得热烈,卧在蜂巢过冬的蜜蜂也都忙着出来采蜜了。老林突然像是听到了春耕的脚步正款款地朝着坡头走来,不免有些着急。搬迁没有动静,春耕可不能没有动静啊。好在,全村一百九十三户他已经走了一百九十二户,就剩下一户没走了。这一户他本该第一个要走的,却是怎么都见不着人,连着去多少次了,都是铁将军把门。早晨见不着人,他就晚上去,门上还是一把锁。让老林起火的是,他第一天来坡头村召开群众大会,他也没有参加。最该到会的又是他。现在,见不着也得想办法见他了。
这个人姓刘,名叫刘新生,坡头村的村支书。来坡头之前,乡领导就对老林说了,刘新生跟共和国同龄,看那名就知道父辈对这个儿子给予了多大的希望,对新社会寄托了多少向往和憧憬。只是,刘新生的脾气有点古怪,火气还足,跟他说话得试着来,不然,你就下不了台。当然,对坡头村来说,刘新生有苦劳,也有功劳。在集体时,做了十多年生产大队长,社改乡,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着,后来年纪大了,身体还不怎么好,人前人后他就说坚决不做村干部了,谁再投他的票他就骂谁。人们就把村主任的票投给了周大树,让他的肩头少了一副担子。乡领导摇着头说:“真想让他把两副担子都交出来,许多的事情才好办,可在坡头村行不通啊,村支部选举,除了他自己不投自己的票,别的没一票旁落。”
还好,这天早晨老林终于把刘新生堵在家里了。走进屋,老林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他怎么都不会想到,刘新生的家居然是这么个样子。歪斜的木屋,破烂的家具,满地上的灰尘,灶台也是冷火悄烟。叫了一声刘支书,没人应答,却是听到房里一声轻轻的呻吟传出来。连忙走进房去,老林不由大惊:“你怎么是这么个样子了?”
从屋脊瓦楞的缝间漏下的晨曦里,老林看见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瞪着一双深眍下去的眼睛,看着屋顶漏下的光亮,满是皱纹的脸上全是焦急和忧虑。
“这个样子怎么了,不愁吃,不愁穿,日子多好。”刘新生也不看老林一眼,说出的话像是吃了生米。
老林当然会记着来坡头时乡领导交代的话,站在床前,有几分讨好地说:“来看看你。来过好多次了,你总是不在家。”
“我很好,要你看什么。”
“刚才听到你在呻吟啊,是不是病了。”老林一点都不敢气恼,脸上讨好的笑也没有褪去。
“有什么病,不过腰有点疼,不然,你别想见着我。”
“我去给你弄点药来。”
“老毛病,贴了膏药,躺两天就好了。”
老林就不再说话,动手打扫卫生,屋前屋后,屋里屋外。除了这些,还煮饭炒菜,喂鸡喂猪。刘新生眼里的那种冷漠和陌生慢慢褪去,渐渐地变得有了些温度,嘴里说:“你跟他们有些不一样。”
老林有点得意,明知故问:“哪里不一样啊?”
刘新生却是不上他的圈套,问道:“开始来坡头的那些日子,怎么老是见你站在村口,一站就老半天,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
“坡头的藍天,坡头的白云,坡头的日出,坡头的吊脚木楼,坡头的层层梯田,还有从坡头四周连绵开去的山峦溪谷,都是风景。”
刘新生心想你把坡头说得这样美,怎么还催命样要赶我们下山,嘴里说:“住在坡头,见惯了,不觉得有什么好看。我们只是知道,坡头的土地肥沃,坡头的阳光足,坡头的雨水润沛足,撒把谷种就有好收成,插棵枝条就能长成大树。”
老林没有觉出刘新生的话里有话,还在自顾自地说着:“坡头两大难,名声在外,让领导们牵肠挂肚。要是没有从山下挑水的艰难,要是解决上山下山用两脚丈量泥泞小路的困难,国家也就用不着操心费力要你们搬迁了。”
“祖祖辈辈都是这么挑,这么走,习惯了,按你们城里人的说法,锻炼身体。”刘新生过后愤愤地说,“帮不了,扶不了,也没人怪罪你们,为什么硬要把我们弄下山去,真是瞎操心!”
老林的脸色很不好看,心想你们的心肝真的没得血了。小康路上不能让一个人落下,不感谢也就罢了,还说这样的话。却是不敢说出来,担心两人扛上了怎么办,说:“这些日子,一直见不着你,怎么知道我站在村口的。”
刘新生不作声,满是皱纹的脸上,居然有了一丝狡黠的笑。
二
这天吃过早饭,刘新生说:“我的腰疼好了,得做活去了,你也该走了。”
“你要我去哪里?”
“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我是来坡头扶贫的,时间一年,这才二月,你就要赶我走?”
“动员我们搬迁的话你就不要说出来。”
“你听见我说这个话了?”
刘新生的眼睛就瞪大了:“那你来坡头做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扶贫。”
刘新生眼里的狐疑没有散去,说:“各家各户都走过了,该给谁送油盐柴米,该给谁送衣服被子,去送就是了。”
“你刘支书领导有方,坡头还真没有缺吃少穿的人家。”
“那你不就可以放心地走了吗,还呆在这里啊。”
老林知道自己的话正好让老人逮着了,笑着说:“我想跟你一块去做活,你也不让?”
“你那个样子,会做活?”
“看你做活啊。”
“挡路,耽搁我做活。”脸上刚刚才有的松动不见了,说出的话又变得冷冰冰的。
老林却是不恼,也不走,一张笑脸迎着他。刘新生站了一阵,从火坑里又拿了两个烧红薯,放进提着的塑料袋子里,前面走了。
老林这是第几次看到坡头的日出,不记得了,他只是记得来坡头的第二天清早,他就看到了坡头的日出,郁结在心里的忧愁和恼怒,居然消散殆尽,变得心旷神怡起来。
正月初八,也就是老林来坡头的第一天晚上召开的群众大会,让他的颜面扫地。按坡头村人们的说法,那是给他的一个下马威。开始的时候,会场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的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瓜子壳花生壳满天飞,是谁还在炭火上烤着糍粑,一屋子的芳香,透着浓浓的年味儿。不曾料到,他的话说完,坐在下面的,除了村主任周大树,只剩下三个老人。问他们多大年纪了,他们说,一个九十二岁,两个九十六岁。除了恼怒,他又有点感动,有点歉疚,要不是三个耄耋老人陪着,他的听众,就只有周大树一个人。
老林一个晚上没有睡着,他自己都不知道想的什么,耳畔却是回响着来时乡里领导对他说的那话,坡头的群众愿意走蜿蜒崎岖的泥泞小路,愿意下山挑水喝,也决不肯搬下山来。这次就看你的了。来坡头才一天,对坡头的印象,除了气恼,还有点杂乱,自己曾经的信心满满也似乎有些动摇。第二天清早,老林就起床了,心事重重地在梯田间的阡陌徘徊,冥思苦想着下一步该怎么走,肩头的重任该怎么完成,年底该带着怎样满意的答卷跟坡头告别。突然,他就停下了脚步。他是被一幅画面惊呆了。
那是一轮初升的太阳。开始的时候,从远方天际的那一线山影里探出了半边脸儿,像是母亲分娩,殷红四溅,让人心悸。后来,红日跃出整个身子,又像是天公的眼睛,要把世间的万事万物看个明白。老林惊叹坡头的日出居然跟城里大不一样,在城里,也就看到灰不溜秋的一团红色,像是烤过了火的烧饼,哪像坡头的日出这般纯净,这般亮丽,这般轰轰烈烈。更惊叹坡头在这般景象里的样貌,层层梯田,静静地摆在蓝天之下,大小不一,形状不一,摆得也没有规则,却是那样壮观,那样气势磅礴。梯田的两边,山峦起伏,层层叠叠,宛如大海的波浪,与远方的天际相连。梯田的上面,是藏在果树林里的高高矮矮的吊脚木屋,虽旧,却是用桐油油过,有一种漆一般的光亮。当然,中间还能见着几栋砖房,红砖青瓦,朱檐廊角,有几分时尚,有几分潮流。谁家早起,炊烟在晨曦中袅袅升起,沐浴着朝晖,轻吻着晨风,那般的温柔,那般的缠绵。时有鸡鸣狗叫,又平添了几分热闹。思来想去,老林还是只有一个字来形容:美。昨晚积聚在胸口的愤懑和不快早就烟消云散,整个身心全都浸润在坡头早晨的风景里了。
不管是第几次见着坡头的日出,老林都觉得眼角有些雾雾淖淖,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情不自禁,他只是想起刘新生说的那个话,坡头的泥土,抓一把都能捏出油来。到了丰硕的秋天,坡头的日出又该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老林的心里突然生出一种震颤,坡头的人们决绝地不肯搬下山去,只怕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抬起头来,刘新生已经走远,老林紧了紧脚步,他想跟刘新生说句什么的,可是,话没有说出来,刘新生已经绕过村后的水池,闪身钻进旁边的林子去了。
老林不知道他这么绕来绕去,要去哪里,去做什么,要说做活,一件工具都没带,要说不是做活,为什么还带着中午饭,看样子中午是不回来的。
穿过那边岭上的林子,摆在老林眼前的,又是另一种景象,脚下是一道刀砍斧劈般的悬崖峭壁,像一堵墙,一直从山谷长上山腰,谷底泉水落崖的声响,在崖壁上碰撞,变得空蒙而悠远。崖壁的那边,几座相连的大山,林莽森森,云雾缠绕,时有山鸟从林子里飞出,铁弹子一样,射向了更远的山影里。
刘新生说:“叫你别来,你却要跟着,甩也甩不掉。鷹嘴崖过不去,你还是回去吧。”
老林终于看见,悬崖峭壁的中间,有一道突起的崖嘴,像是老鹰的喙。没有路,只有一些藤萝从上面的林子里匍匐下来,悬挂在崖壁上。
“你能走,我也能走。”老林思忖,这是要去哪里做活啊。
“你是县里来的干部,掉下去我的老命可赔不起。”刘新生站着不动,那样子是要赶他回去。
老林终于问出口:“你要去那边做什么活?”
“你管我啊。快回去,看你的风景去。”皱纹密布的脸上,看不出是愠怒,还是不满,说话的口气,也听不出是冷漠,还是讥讽或调侃。
“不。”老林回答得坚决。
刘新生不再说话,站一阵,攀着藤萝前面走了。
老林跟在他的后面,一步一步小心地往前爬去。
“不要朝下面看。”
“知道。”可是,老林还是朝下面看了一眼,头有点发晕,心也提上嗓子眼了。
刘新生回过头来说:“要不是这几天你一直闭着嘴,我决不会让你跟着我来这里的。”
老林却是不敢说话,猴子一样慢慢往前爬行。真要掉下悬崖,只有一个词形容是十分的恰当,粉身碎骨。
过了鹰嘴崖,一道更加陡峭的绝壁横亘在眼前,崖壁中间却有一条开凿出来的小道,一直延伸到绝壁尽头的山林里。老林觉得十分奇怪,要说去那边大山里,从上面岭上或是从下面山谷都是可走的,为什么要在这悬崖峭壁中间开凿这么一条小路,图的捷径,又能少走几步呢,付出的代价,有多少意义?问道:“那条小路是你开凿出来的?”
“不是我,是我们。”
“还有谁?”
“一会儿他们就来了。”刘新生说,“现在可以回去了吧,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
“我要看看你们是怎么开凿那条小路的。”
“玩命,有什么好看。”刘新生不耐烦地说,原本板着的脸,变得更加僵硬。
“春耕大忙的季节眼见着就到了,还不做春耕的准备啊,跑到这里来修什么路。”
刘新生脸上流露出一种不屑:“做阳春,赶季节,莫非还要你来教我?”
这话呛得老林好一阵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在这时,从上面林子里钻出三个老人,都是一脸的沧桑,腰还有点驼,但他们也跟刘新生一样,在绝壁上行走,手脚敏捷,身形矫健,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难。
三个老人看见老林,全都缄口不语,眼睛盯着刘新生。
“像个尾巴,甩都甩不掉。”刘新生再一次下了逐客令,“快回去,我们要做活了。”
老林却问:“离鹰嘴崖还有几十米吧,还得凿多久啊?”
“这也是你打听的吗?悬崖峭壁,人多了手脚使不开,少说也得一年两年。”
“我也帮帮忙吧。”
“不行。”
“你们行,我为什么不行?”
刘新生还是说的那句话:“掉下去,我们担待不起。”
“你们没掉下去,我就掉下去了?”
刘新生瞪了他一眼,还是把一根绳子抛给了他。照着他们的样子,老林把绳子缚在自己的腰间,慢慢向那边崖壁爬去。
好不容易站在了那条逼仄的小道上,老林再不敢往下看了。真的,他的尿水都快吓出来了。
刘新生和三个老人从旁边的崖壁缝中取出铁锤和钢钎,叮叮当当凿起来。这时,老林才发现沿着这条小道,隐隐约约有一条用白漆绘出的直线,匍匐着一直向突起的鹰嘴崖延伸过去。
“这条小道开凿多久了啊?”
“连同那边山腰的两段崖壁,七年了。”
老林心里不由一沉,说的还是那句刚才说过的话:“为什么要在绝壁上开凿这么一条小道,从山顶或是山谷不都能去那边山里吗?”
“眼睛没问题吧,好好看看是不是路。”一个老人冷冷地说。
老林看了许久,心像是被什么狠狠地揪了一把。惊诧,激动,好像还不够。他是看出了蹊跷,这小道外面高,里面低,分明是水渠么。大声道:“给我钢钎,我也要帮着修水渠。”
“站在这里别掉下去就大吉了,还帮着修水渠呢,抓得稳铁锤钢钎吗?”
“还别说,我爷爷是石匠,我父亲是石匠,我要不从农村走出来,肯定也是石匠了。”
刘新生脸上的厌烦和不屑变成了一种惊讶之色,从崖壁缝里取出一根钢钎,一把铁锤,递给老林说:“记住,一定不能让腰上的绳子脱落,不然,真的要出人命。”过后兀自喃喃起来,“怪不得跟先前来的那些扶贫干部不一样,肚子里的苞谷屎还没屙完呢。”
老林却不再说话,叮叮当当凿起来。匍匐在崖壁上凿石的四个老人开始还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后来,就都只管做活去了。
“新凿出的这一段水渠太浅,水怎么过?”老林一边做活,一边这样问。
“我们也想啊,要是鹰嘴崖这三百米崖壁全都开凿出水渠,多好,一劳永逸了。可是,没有办法,你们搞的车轮战法,一年换一个,不是扶贫工作队来,就是乡里的干部来,不把坡头的人们弄下山去決不罢休,这里只有先开凿出一条能摆放水管的小道,尽快把水接过去,才好堵了你们的嘴。”
“什么时候坡头村才能喝上那边大山里的山泉水?”
“接水管当然要快得多,大半年吧。”
“为什么不叫年轻人来,就你们几个老人。”
“村里哪有年轻人。”
“周大树常年在外面打工,村里的事情就不管了?”老林对周大树居然在自己眼皮下偷偷跑去城里打工一直耿耿于怀。
“他能呆在家里么,耳朵还不被你弄出茧子来。”
老林想说句什么,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心想他当的村主任,却是长年在外面打工挣钱,村里的工作不闻不问,你还护着他呀。
叮叮当当的凿石声,在半空中回响,几只山鸟时而从林子里飞起,在身旁盘旋,更远处,传来几声野兽的鸣叫,跟凿崖的叮当声应和,组成了一曲别样的乐章。
太阳当顶,几个人蹲在崖壁上吃了几个烧红薯,就算是中午饭了。直到太阳落下山去,黄昏的脚步从远处的林子里悄悄走来,他们才放下手里的活,扯着绳子,攀上崖壁。
三
这天晚上,老林对周大树的女人说,往后他不住这里,也不在这里吃饭了。周大树的女人被孙子的哭闹弄得晕头转向,眼里闪过一缕光亮,问他是不是要回去了:“你原本就不该住在这里的。住在乡政府多好,十天半月来这里看看不就是了。”
老林没有吭声,背着帆布袋子匆匆走了。
刘新生正在吃晚饭,头没抬。老林也不说话,盛了一碗饭大口吃起来。他已经饿得肚皮贴后心了。
一碗饭落肚,刘新生终于开口说话:“住我家可以,但不能说那个话。”
老林知道他说的那个话是什么话,说:“这个话你对我说过几次了。记着的,不说。”
“也不能说修水渠的事。”
老林心想修水渠是好事,怎么不能说。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不说就是了。”
吃过饭,刘新生给老林倒了半盆水,要他快洗,他去给他开铺:“凿了一天石头,还不累?”
老林说:“二月,夜里气温还低呢,又没有空调,还是睡一块吧,暖和。”顿了顿,又说道,“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恋母情结。我却是有恋父情结。不论是小时跟父亲学石匠外出做上门活,还是后来读中学读大学,寒暑假跟着父亲走村串寨做石匠挣学费,夜里都是跟父亲一块睡,即便是现在回老家,夜里还是要跟父亲睡一张床的。”
抬手要把洗过的半盆水倒掉,却被刘新生接住了:“我还没洗。”
一个晚上,老林和刘新生都没有睡着,开始的时候,刘新生是想睡觉的,禁不住老林刨根究底地问这问那,想睡也没法睡了。
“我来的时候,乡里领导说,坡头村的六百多口人,从三月到八月,全都要下山挑水喝,村头的水渠清水长流,也没人瞅一眼。这些日子,我还真的见证了,二月就开始下山挑水了,可下山挑水再苦再累,也没人偷偷从水渠里舀水。觉悟啊。”
“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二月备耕,田里开始赶水,一直到八月稻子黄熟,谁都不能用村后山间引来的泉水,那水仅仅只能够着水田不旱。没劳力挑水的老人,全村人轮着给他们送水,一家两天一担水。九月到第二年的二月初,水田不用管水,大家就不愁没水喝了。偷水饮用,只有你想得出来。”
“搬下山去,多好。梯田改成果园,改成中药材基地,收入比插禾强多少倍,还不用这么劳累。”这是老林来坡头之前乡里领导对他说的话。乡里领导说,他们早就给坡头规划好了,整个村子搬迁下山,水田和山地改成果园和药材基地,想一想,那是一种多么气壮山河的壮举,三五年之后,坡头又是一幅多么让人激动和欣慰的景象。
刘新生不知道是生气,还是无意,伸了伸脚,正好踢在老林的下巴上。刚刚张嘴还要说什么的,牙却是狠狠地咬着了舌头,疼得老林倒抽一口冷气,说,“我说的你不喜欢听,可不能踢我。”
刘新生说:“我没踢你,是你的下巴撞着我的脚了。”过后冷冷道,“不说那话,嘴里就长蛾子了?”
“你是坡头村的一把手,怎么说,上面的话,还得听吧?”
刘新生又要踢他。老林学乖了,脸面一扭,刘新生的脚踢着了后脑勺。
“即便是水渠修通,解决了吃水的问题,还有路呢。你可以对我耍横,我敢对他们耍横吗?二者少一,我这一年的工作重心还是要动员你们搬迁的。”
刘新生一下坐了起来,愤愤地说:“你们整天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要我们搬迁,摸着胸口想一想,难道仅仅只是为了我们?”
老林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道:“不为你们,还为谁?”
刘新生却不跟他说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喃喃道:“十年前,乡领导从县里请来了专家,准备把那边山谷的泉水引过来,还勘测过水渠怎么修,没看见鹰嘴崖的石壁上有一条白线吗,就是那时专家勘测的时候留下的。他们计算过,把那边山谷的泉水引过来,得修十公里长的水渠,还要在三段悬崖峭壁上劈出一条过水沟,又不能打眼放炮,全得人工手凿。没有三百万拿不下。修路的专家也勘测过,从梯田中间修公路上山,不过占一点良田,修路的资金却是大大地节省了,我不同意,那样,路修好了,六百多口人却少了两个月的口粮。得不偿失。真要修路,就从旁边的荒山坡上修上来。他们也不同意,从旁边的山坡上修路,不占田地,却是增加了修路的难度,还要在山脚架一座百米长的桥梁,少说也得五百万。算来算去,还是搬迁划算。把一百多户人家搬下山,不过二百万。我也理解,全乡几个偏远村寨瞪着眼等着上面拨钱呢,或是修路架桥,或是异地搬迁,不可能把钱全给了我们坡头村。要我们搬下山去,我们当然也不会干的。族谱记载,八百年前,我们的祖先跟着从江西填湖南的人群往湘西腹地迁徙,从这里经过时,迁徙的队伍走了,我们的祖宗却是停下了脚步。一代又一代,才有了今天的坡头。抓一把泥土,能嗅出先人流下的汗水味儿。”刘新生突然就骂起娘来,“亏他们想得出来,多好的田地不插禾了,栽果树,办中药材基地。这才吃了几顿饱饭,就忘记了。水果能当得饭,吃药能当得饭?”
老林也坐了起来,想说什么,却没有說出口,把刘新生按进了被子里:“二月的三更,外面寒风料峭,冻出病来,我又得侍候你。”
“我没那么金贵。”刘新生还是躺进了被子里,“问你一个话,你们城里的八十老人在做什么?”
老林不知道他问这话什么意思,答道:“身体好的,早晚就在外面走一走,在公园散散步,去商场买买菜,一般基本就呆在家里看看电视吧。”
“我们坡头的八十老人能在腰上缚根绳子攀上悬崖峭壁劈石头。能比吗?”
“谁八十多岁了还上山劈石头啊?”
“那三个凿石修水渠的老人,一个八十三岁,一个八十五岁,一个八十九岁了。”
老林惊诧道:“我还以为跟你差不多,六十多岁,都这么大年纪了啊。长年累月腰上缚根绳子攀上悬崖峭壁修水渠,他们的儿孙就放得心?”
“坡头的七百多亩梯田,从犁田到插禾,到收割,都是这些七老八十的老人做的,年年大丰收,有什么不放心。在绝壁上修水渠,可不能遍地开花,错了半分,水就没法过,只得把老人们分成若干小组,三个人一轮,轮一次去修两天水渠,一个月还轮不到一次,后天又是另外的三个人了。当然,我是不轮的。除了四月把六分水田的禾苗插下去,我就陪着他们去修水渠。”刘新生有点激动起来,“要感谢我们的祖先选的这安身立命的地方啊。你来坡头,挂在嘴边的话是坡头真美,我们世世代代住在坡头,却是知道坡头这地方养人,村里的老人大都活到九十多岁,活到一百岁的老人也不少。”
老林啊了一声,他当然会想起那天晚上陪着他开会到半夜的三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耳聪目明,精神矍铄。过了一阵,老林试探着问:“还没问你呢,你就一个人?”
刘新生一声长叹:“我对不起我的女儿,对不起我的女人啊。”
原来,刘新生是有老婆孩子的,女儿三岁的时候感冒发高烧,女人要他把女儿送到医院去看看,他却带着人们到村后山岭上挖葛根去了。
中午的时候,村里一个老女人慌慌张张去山里叫他。原来他女人背着女儿去医院的时候,走得急了,在山脚的坡坎摔了一跤,一只脚被摔断,孩子也被摔到崖坎下面去了。
刘新生抱着女儿往医院跑,可是,已经迟了,手背上插着针管,女儿却没气了。女人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整日以泪洗面。刘新生没去山里挖葛,村里群众不让他去,要他在家陪陪女人。女人能下床了,说是要出去走走,刘新生没有在意,以为她心里还想着死去的女儿呢,散散心也好。不曾想,女人走了就再没有回来。
“没去找她?”
“找了,没找着。”
“没有再找个老伴?”老林的后脑壳又被踢了一脚,连忙缄口不问了。
“乡里领导关心我,办了低保,村支书还有一份工资,粮不用买,肉和油都不用买,钱怎么都用不完的。”
刘新生还说了些什么,老林没有听清楚,只觉得心里有一种隐隐的疼痛,眼睛也有些发湿。过了一阵,他问:“不可能家家户户都有老人啊,修水渠的工怎么分摊?”
“家里没老人,出钱。买水管要钱,修水池买钢筋水泥也要钱。”
“怎么说周大树也不该去打工的,该他带着大家修水渠才是。”
“他每年把打工挣得的钱拿出一多半给村里存着,日后修桥用。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都跟着学,每年也拿出一些钱交村里。叫集资也好,叫捐献也行。我当然也是要表示表示的,村支书每个月的工资从来就没有领过。村里已经存得八十多万了,再坚持几年不被你们弄下山去,山脚的水泥桥就可以动工了。”
现在,老林的胸口就不是隐隐的疼痛,像是被什么重重地撞击了一下,嘴里还啊了一声,但他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只觉得眼里的泪水更加的多了。
四
转眼,老林来坡头两个多月了,三月初,乡里召开春耕生产动员大会。下村去的扶贫工作队员和各村的主要领导都得去参加会议。
“去坡头就不知道回来了。”扶贫工作队长劈头就是这样一句话。
老林听不出领导是在责备自己,还是在表扬自己,说:“抽不脱身。”
“你女人打电话来,你父亲病了,要你回一趟老家,你也没有回去?”
“一辈子做石匠,吃的石头灰多了,出气不赢,到了春天就加重,我回去有什么用,又不能替老爷子喘喘气。”
“坡头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说了,七百亩水田,不会抛荒一丘,二百多亩旱地,也不会长一棵狗尾巴草。”
“我是问坡头搬迁的准备情况。”
“正在做群众的工作。”老林沿着自己刚才说的话往下说个不停,“你想想吧,春风荡漾,阳光明媚,蓝天白云之下,层层梯田,犁田耙地全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该是一幅怎样不同一般的春耕图。”但他决不会说还有八十多岁的老人腰间缚根绳子挂在悬崖峭壁上凿石头修水渠的话。与他去坡头的重任背道而驰,讨骂是吧。
“我说的那个话你可要记牢了。坡头的搬迁,还不仅仅是要解决那六百多口人的生存环境,让他们从此跟没水喝、路难走的两难告别,过上幸福的日子,当然也是书记乡长的政绩工程,到时候,我们扶贫工作队也才好光光彩彩回去啊。”扶贫工作队长的思路也没有被老林那富有诗意的坡头春耕图所感染,说出的话严肃又认真,还有点语重心长。
“放心,都说好了的,年底,就陆续往山下搬迁。”
“不,秋收之后。”
“那就秋收之后吧。”
这天散会之后,扶贫工作队的领导要老林留下来,改善一下伙食:“去坡头两个多月了,肚子里的油水早没了吧?”
“还好。”老林没有留下来吃领导专门为他办的好饭菜,跟着刘新生回坡头去了。
“你对他们那么说,就不担心日后挨骂?”
老林笑说:“那些话不是你常对我说的吗。”
回到坡头,刘新生再没有带着人去鹰嘴崖修水渠,开了个会,坡头的春耕图居然比老林想象的还要壮观得多,锦绣得多,热闹得多。梯田里,到处是牛的哞叫,人的吆喝,小型拖拉机的轰鸣,开得正艳的紫红的草籽花,没些日子就变成了水汪汪一片,似明镜一般,一层一层,从山脚一直嵌镶到半山腰,春风荡漾,绿肥在泥土里沤出的芬芳味兒让人心醉。
老林还是看出了坡头村的人们做田跟别地方的不一样,多做一道犁耙,田埂也做得高。
刘新生说:“关水。经旱。”
老林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说:“领导打电话来,从上面弄了些大米和油呀衣服之类的来,村里得开个会,看看还有没有春荒过不去的人家,尽快报个数字上去。”
不曾料到,刘新生一下发起脾气来:“该帮的不帮,该扶的不扶,弄些米呀,油呀,旧衣服呀献殷勤,没人会感谢他们的。”
听到这话,老林真的就生气了,声音也提高了八度:“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刘新生也觉得自己说的这话有些不妥,连忙改口说:“扶贫的政策好啊,那些遭受天灾人祸的人家,那些久病不愈的人,解决低保,或是给点钱,送点大米和油盐,让他们渡过了难关,重新振作起来,跟上小康路上的步伐。我们坡头有三户困难人家,就是这样给扶起来的。”
老林过了一阵才说:“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抱怨。把你们往山下搬迁,不也是扶和帮的一种吗?”
“这种帮扶,我们不要。”
“所以,我不再说这话了啊。”
刘新生板着的脸又变得慈祥起来:“所以,坡头的人们也才会说,只有你老林才跟我们贴心呢。”
每天三更刚过,刘新生就起床去山脚挑水,老林也跟着去,他挑着两个小塑料桶,跟在刘新生的后面,高一脚低一脚往山下走,塑料桶碰撞得哐当作响。
其实,挑水也是一道风景。老人居多,当然也有女人和孩子,长长的队伍,踩着三更的雾露,走完梯田间的崎岖小路,到了山脚,再转一道弯儿,那边山谷有淙淙的山泉跳崖。刘新生说,他们在鹰嘴崖开凿出的那条水渠,就是要在十公里之外的源头拦住这一眼山泉水,到时候,它就会乖乖地流进各家各户的灶台。
梯田的旁边,有一条水渠,从村子后面的山里引来的山泉水,清流荡漾,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过水口,过水口里摆放着一个用木头做成的分水道,是几条平行的小缺口,引来的山泉水,均匀地分给各家的水田。水渠一直通往最下面的梯田,当然,水渠里面的水也就分流殆尽。
无论老人还是孩子,男人还是女人,踩着细窄而滑溜的田間小路,挑着沉沉的水桶,艰难地往山腰爬去,却对水渠里流淌的泉水视而不见。
天亮的时候,曲曲弯弯的田间阡陌才安静下来,梯田里又有了吆牛的声音,拖拉机的轰鸣。是谁第一个开犁拉开了坡头村春耕的序曲,老林不知道,但他的胸口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愫鼓荡,他突然想,要是城里人看到这样一幅美妙的春耕图,会做何感想,那些最爱咋咋呼呼的女孩,那些最爱整出几句长短句的文青,还不扯开嗓子叫喊:坡头是他们的远方,也是他们的诗啊。
五
春播春插,前后只用了一个月。刘新生家只有六分水田,三分旱地,把禾苗插下,把旱地种上苞谷,也没用上十天时间,但他还是没去鹰嘴崖修水渠,他要挨家挨户看一看,走一走,有时,干脆就把柴棚里的手扶拖拉机开出来,帮帮那些家里少了劳力的人家。他说:“坡头不抛荒一分田地,不是担心挨领导的骂,也不是担心狗尾巴草在禾苗中间张张扬扬有多扎眼。抛荒一分田地,就要少收一分田地的粮。粮是宝贝中的宝贝。可别忘了那时没饭吃饿肚子的年月啊。”
老林心里又是好一阵感动。站在坡头,看着梯田从一片水汪汪到一片青翠,再到一片沉甸甸的黄熟,该是一种怎样的美妙和满足。
大半年来,老林尽情地享受着坡头的田园风光,明媚山色,也目睹了坡头人的勤劳和纯朴。除了去乡里开会,他就呆在坡头,五一长假,端午中秋,也没有回县城去。当然,除了去各家各户走走,站在村口看日出日落,看风云变幻,看梯田里的禾苗滋滋拔节生长,大多时间还是跟着刘新生去鹰嘴崖修水渠,安水管。中秋节的前几天,鹰嘴崖那边的山泉水终于被引了过来,汩汩地流进村子后面的水池。
刘新生召开群众大会,只对大家说了两句话:水池没灌满之前,都不要拧开自家灶台的水龙头。还要记着去山下挑水的艰难,节约用水。
人们就大呼小叫,水池的水满了,大家也是不会首先用水的,要举行一个仪式,请他老人家第一个拧开水龙头。
老林清楚地记得,第三天的清早,水池的水终于灌满,人们都往刘新生家涌来,要看着刘新生拧开自来水龙头的那一刻。
快七十岁的老人,居然也有孩童般的天真与烂漫,也有孩童般的顽劣与恶作剧。看着刘新生把长满老茧的手伸向灶台上的水龙头了,突然,呀的一声,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饱经沧桑的脸上做出惊恐状,可把大家吓得不轻,眼睁睁地看着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时,他却是把水龙头拧开了,哗啦啦,清亮的透着山花芬芳的泉水流淌出来,人们欢呼雀跃,有人还伸手捧了水往嘴里灌。刘新生站在一旁,满脸的皱纹全被开心的笑填得满满的了。
老林紧紧地抓着刘新生的手,想对他说句什么的,却没有说出来,只有眼泪簌簌地淌落。
水的问题解决了,修桥就提上了议事日程。那天,老林跟刘新生站在山脚的沟壑旁,商量什么时候动工修桥。提早动工修桥是刘新生提出来的,他说:“钱不够,慢慢凑。眼看着就开镰秋收了,搬迁却没有动静,你没法交代。”
老林心想也是,吃水不成问题了,桥动工修了,也就没必要动员大家往山下搬了。
就在这时,老林的手机唱起歌来,是扶贫工作队长要他和刘支书赶紧去乡里,有重要事情交代。
刘新生有些不愿意,老林说:“你不去,他们就会来坡头的。”
这话有效果,刘新生觉得不去还真的不行。
是县政府办公室打来电话,说领导明天要来田坪乡看看,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想了许久,也没想好要带领导去哪里看一看,看什么,后来,还是决定让领导去看坡头村的搬迁准备工作吧:“坡头搬迁,在县里是挂上号的,搬迁经费也拨下来了,不让领导去现场看一看,不放心的啊。”
老林说:“都在积极做搬迁的准备,也没什么好看的。”
乡长说:“怎么没看的呢。比如,一些群众搬下山来高兴啊,早早就把自家的家具物件打包成捆,只等着秋收完毕,就往山下搬。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思想准备,比如,人们对搬迁的认识,对领导的心怀感激,对新的生活环境的向往和憧憬。”
老林还是说的那句话:“准备就准备嘛,的确没有什么好看的。”
扶贫工作队长就有些生气了:“什么意思嘛,你自己承诺的,秋收过后就动手搬迁,现在什么时候了?快回去,照着书记乡长说的认真准备一下,迎接领导的检查。”扶贫工作队长对老林还是比较放心的,单位的骨干力量,带他下来的时候又对他交了底,要把他放在条件最苦,工作难度最大的村里去,做出成绩,一年之后回单位就让他往前走一步。快五十岁了啊,还不抓着机会解决个级别,更待何时。果然,每次去坡头看望老林,村里的群众对老林的赞扬之声不绝于耳,让他这个扶贫队长的脸上也很有光彩。
一旁的刘新生也想说点什么的,却被乡党委书记和乡长给堵了回去。书记乡长心里也有美好的愿望,把一个有八百年历史的村子搬下山来,让几百号人口异地新生,多伟大的工程,多光彩的政绩,县领导表扬他们的时候,趁着再向领导诉诉苦,说说困难,多给坡头一点搬迁经费,坡头的群众还不更多的心怀感激吗。双赢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做得更漂亮一点,更光鲜一点。
回来的路上,刘新生默不作声,那样子像是在想什么问题,老林更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后来,他像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把自己的想法对刘新生说了。刘新生拧着的眉头散开,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担心你不敢。”
“还说敢不敢啊。不这样,再没别的办法了。”顿了顿,又说,“我一直没有想明白,你为什么要把修水渠的事情对外面保密。八年啊,外面居然没一个人知道。”
“他们要知道一群老人长年累月腰上缚根绳子,挂在悬崖峭壁上修水渠,还不跳脚吗?能让我们拖延一年又一年,不早就把我们弄下山去了?”
坡头的群众全都忙碌起来,一个晚上,也是灯火通明。第二天吃过早饭,老林又匆匆去了乡里。上午十点钟,几辆小车相跟着从山外开来,一溜儿停在山脚的公路旁边。
让领导们惊讶的,梯田那边的山脚,有许多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披荊斩棘,一副忙碌的样子,看见县领导从小车下来,就一齐高喊:“欢迎县领导来坡头指导工作。”
老林把刘新生推到县领导面前说:“这是坡头村党支部书记刘新生。”
“听说坡头村的搬迁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啊。”县领导握着刘新生的手直摇晃,“坡头村的两难可是远近闻名呀。搬下山来,就永远地跟没水喝、路难走告别了。”
刘新生说:“请领导上山去看看吧。”
一旁的乡长说:“刚才领导还说路难走呢。不上山,在这里说说就是了。”
刘新生不作声,眼睛却是朝上面的梯田张望。县领导也被他的目光牵引着,对着上面的梯田看去。秋风乍起,耀眼的金黄一直延伸到白云生处,不解地问:“别地方的秋收已经完结,坡头怎么还没开镰?”
刘新生说:“坡头的稻米养人,除了土地肥沃,阳光充足,更重要的原因,生长期比别地方长。”
老林一旁道:“吃了坡头的稻米,能延年益寿。”随手把一个老人推到领导的面前,“九十多岁了,爬山还如履平地。”
县领导眼睛盯着老人就不松开,脸上除了欣慰的笑,就全是惊诧了:“真的吗?”
“甲子年冬月初二生的。”
“真的九十多岁了啊,走,到你家看看去。”
沿着梯田中间的田埂小路,才走不多远,县领导居然生出了感叹:“我去过龙脊,那里的梯田也不过如此。”
刘新生说:“我们的老祖宗从开垦第一丘梯田至今,经历了八百多年,最后的几丘梯田,直到我爷爷他们那一辈才插上禾。流下的汗水,也是能长出一季稻子的。”后面说的什么话,人们没有听清楚,只见他的嘴唇在不停地颤抖,深眍下去的眼坑里有泪水晃动。
县领导已经气喘吁吁,可他的眼睛有些发亮,时而远眺,时而又勾头看着梯田里金黄的稻浪,过后,眼睛盯着梯田上面的村子就不松开:“吊脚木楼掩映在果树林里,再有几栋砖房点缀其中,还有屋顶上那一排的电视天锅,古村落就又透出了时代的脚步。”县领导满是汗水的脸上早就绽出了激动之色,要不是上了年纪,只怕还能整出几句长短句来的。
“去家里看看吧,他们的日子过得比城里人不差的。”
老林一边这样说,一边就近往一栋新修的砖房走去。砖房外面被一堵爬满蔷薇的矮墙围着,里面却别有洞天。几丛菊花开得正艳,一个老人正在禾场旁边的水池洗菜,两个小孩膝前泼水嬉闹。一根洁白的水管从围墙外面钻进来,他们争着拧水龙头,清亮的泉水时而被关在水管里,时而又哗哗地流淌出来,老人却是勾着头忙活,也不管水池里的水四溢开去。
县领导说:“坡头滴水贵如油啊。这水从哪里来的?怎么能这样浪费掉。”
乡党委书记和乡长的眼里虽是流露出惊讶和困惑,可他们还是提醒老林和刘新生:“上山来,主要看看村里搬迁的准备工作。”
刘新生却是只管说他的:“现在吃水不难了,家家户户都安了自来水,每家有两个水龙头,灶头还有一个水龙头呢。”顿了顿,又说道,“过两年领导再来坡头村,就不用两脚丈量崎岖的田间小路,小车可以开到各家的门前。”
县领导回头看了乡党委书记和乡长一眼,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对刘新生道:“去看看自来水从哪里来。”
刘新生和老林相视一笑,领着人们出了院子,往村子后面的水池走去。
扶贫工作队长扯了扯老林的衣角,轻轻问:“什么情况,我来过坡头几次,大家都是挑水喝。”
乡领导早就把不快挂在了脸上:“不说搬迁的准备工作,把领导往山上引,要参观那口瞪着眼看天的干水池吗?”
偌大的水池却是波光盈盈,一根碗口粗的水管把清亮的泉水注入水池,水池满了,从四周溢出来,外面修有一条小水沟,溢出的水在水沟聚成清流,汩汩流进了下面的田里。县领导的眼里除了惊喜,就是狐疑,沿着水管走了过去。
刘新生说:“您想看看这水的源头吗,也不远,转过那边的山垭,就能看见水的源头了。”
林子里有一条小路,和水管并排前行。县领导不说话,高一脚低一脚往前走,刘新生想去扶他,却被他拒绝了:“让六十多岁的老人扶我,折寿啊。”
刘新生转过身,去扶乡长,乡长的身子有些胖,早就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但他也不好意思让刘新生搀扶,脸色却是变得更加难看。
站在鹰嘴崖,他们就看见了那条水渠,从那边的崖壁蜿蜒而来,水渠里的水在鹰嘴崖就兴高采烈地流进那条洁白的水管里了。
老林对着远处的山腰指了指,说:“那里还有两段比这更加陡峭的绝壁,不过不是接的水管,而是开凿出来的水渠。刘支书说,这边的一段要是全都开凿出水渠,不用接水管,就一劳永逸了。”
县领导的眼角有些湿润:“这么陡峭的崖壁,你们怎么就开出一条水渠了啊。”
“腰上缚一根绳子,四个老人一班,前前后后用了八年时间。几天前,那边山谷的泉水终于被引了过来,从山下挑水喝就成了坡头村人用以回忆的历史了。”老林抢着这样说。
刘新生摆了摆手,不以为然地道:“没什么可评功摆好的。想想我们的先人,开荒拓地,一代又一代,才有了今天的坡头。我们苦点累点,跟我们的祖先比,又算得了什么。还得感谢领导带来的专家啊,勘测多么精准,绕过五道山垭,又从三段崖壁上开凿出一条八百米长的沟渠,居然不差分毫,泉水哗哗地流过来了。我爷爷健在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我们的祖先也曾想把那边山里的泉水引过来,水渠才绕过两座山垭,就错了方位,不是高了,就是低了。”
县领导紧紧地抓着刘新生的手,眼里的雾雾淖淖在渐渐地聚拢,问跟在身后的乡党委书记:“这些,你知道吗?”
乡党委书记的脸有些发白,张了张嘴,话没说出来,却被刘新生抢了过去:“知道,都知道。他们说了,要把坡头村当作新农村的试点建设好,却是担心以前向县里打了报告的,坡头村的搬迁成了田坪乡工作的重中之重,只得让领导亲自来这里看一看,领导放心了,才好把送上去的搬迁报告取回来。”
“水解决了,还有路呢?”
“剛才上山的时候,不是看见有许多人在那里做修桥的准备吗。秋收之后就动工修桥。其实,上山的公路几年前就修好了,从那边山头修上来的,却是没钱修山脚那座桥,就停了下来,人们上山下山,还是只有走村前这条小路。”
老林一旁说:“这么多年了,周大树每年打工挣的钱都会给村里一半,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就都跟着学,每年也要给村里一些钱,还有刘支书每月的工资,全给村里存着的,已经有几十万了,村里决定,秋收之后,就动工修桥。钱不够,慢慢凑。”
“县里拿点钱,帮你们一把。”县领导把刘新生的手掌翻开,轻轻地抚摸着,两滴眼泪啪哒一声掉在掌心厚厚的老茧上,“桥修好,我要来剪彩,以后退休了,还要常来这里的,这里山好,水好,人好,养身,养心。”
送走县领导,老林没有跟着刘新生一块回坡头,被扶贫工作队长拽进了小车。刘新生赶过去想说句什么的,小车却已经开走老远了。
一个晚上,刘新生在床上辗转难眠,第二天清早,他就站在村口张望着,看见老林从山下走来,老远就着急地问:“挨骂了吧?”
“肯定啊。不过值。”老林一副笑嘻嘻的样子,“县领导说了,放下来的搬迁费,全都划拨过来给你们修桥。那可是二百万啊。”
刘新生那张忧郁的脸就笑成一朵大菊花了:“有那二百万,把桥修结实一点,上山的公路再修宽一点,还要铺上水泥。”顿了顿,又说道,“昨天晚上,全村的群众都来我家就不肯离去。大家说,年底你走的时候,要给你送行,还要在村口给你立碑。”
“桥没修好,我不会走。当然,我也不要你们立碑。大家把日子过好,我就高兴。”老林的眉头拧了拧,瞬即又散开了。
刘新生再没有作声,只是用力抓着他的手,摇了又摇,深眍下去的眼坑里又有泪水在晃动。
六
老林在坡头呆了三年,满头的黑发已经长出了银丝,腰也有些驼,走路还有点跛,是在修桥时帮着抬石头被砸的。离开坡头的时候,坡头村的群众又把要给他立碑的事提了出来,他还是不同意,自己却掏钱立了一块碑,就立在山脚的桥头,上面只有三个字:新生碑。人们说,那是他给刘新生老人立的。
大桥修好,县领导果然没有食言,来给通车典礼剪彩。县领导说,除了他自己,再要两个人跟他一块剪彩,一个是老林,一个是刘新生。两个在家带孩子的年轻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牵着彩带站在大桥头,乡里的干部一字排开站在一旁,再后面,是坡头村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都等着剪彩仪式完了,小车要开上山,开到村里去呢。只是,刘新生却一直没有来。
打电话,没人接,老林只得心急火燎地去家里叫。老人躺在床上,眼睛闭着,饱经沧桑的脸上却带着笑,老林以为他在做梦,说:“梦到什么开心的事了啊。快起来,等着你去陪县领导剪彩呢。”过后喃喃道,“我去乡政府接县里的领导,你就学会睡懒觉了。三年,从没见你这个时候还睡着啊。”
老人没有醒,脸上的笑意依旧。去推他,身子已经硬了,脸上的笑凝固成永远。医生说,老人劳累过度,死于心力衰竭。
老林离开坡头那天,乡政府的小车来接他,他却不愿意上车,背着三年前来坡头时背的帆布袋子,沿着刚刚铺好的水泥公路往山下走去。来到桥头,他就蹲了下来,把脸贴在石碑上,久久不肯离去。成群结队为他送行的群众远远地站着。不知是谁先哭出声来,后来,哭声一片。
还是周大树说了句:“老林,常来坡头走走啊。”
人们就都大声地叫喊起来:“老林,常来坡头走走啊!”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