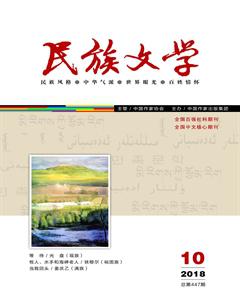海爸爸(小说)
周雨墨
趴在奶奶家的炕上,三个脑袋挤在一起,瞪大眼睛看动画片《机器猫》。那年我七岁,尽管逝去二十几年,我依然记忆犹新,毕竟那段日子,我是和别的孩子一块分享“哆啦A梦”。
七岁,还不懂性别,我就有了女朋友,就是天天和我的脑袋挤在一起的佳静。另一个脑袋,是我的玩伴,高雄。动画片让我们三人有了新名字,他们叫我康夫,小胖墩高雄自然是大雄了,佳静是女孩子,叫小静天经地义。我虽然不愿意,但也没办法,他们俩天然的偶合,我不当康夫,谁当?
看完动画片,奶奶的教鞭——鸡毛掸子,往炕沿上一拍,喊了声,写作业。我们乖乖地爬回小饭桌前,咬着铅笔,写课文,脑袋不时地往一块儿挤,学《机器猫》里的情景,作怪态。
奶奶的鸡毛掸子又敲响了炕沿。
奶奶是渔村小学的老师,当了一辈子孩子王,刚刚退休,父母便把我从姥姥家接来,送给了奶奶。于是,我就有了两个老师,学校的老师,还有家里的老师。左右两家邻居,看到奶奶天天带我学习,就把他们家的孩子也送来。奶奶说,一只羊是放,两只羊也是放,一块儿送来吧。
敢情奶奶把我们当成羊了,怪不得总抽鸡毛掸子。
另外的两只“羊”,就是高雄和佳静,我们上学下学,都是同学。
鸡毛掸子打炕沿,是警告,再不听话,就打屁股。奶奶不会打他俩的屁股,人家是客人,挨打的肯定是我,于是,我摇头晃脑地背早已烂熟的诗,心里却打着逃学的主意。没多久,我便喊,我渴了,我饿了,我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
奶奶听得懂,我要喝饮料,吃小食品,顺便让我的小伙伴也借光。奶奶递给我的,既不是饭,也不是水,是一个干巴巴的馒头。我心里不高兴,奶奶又把鸡毛掸子敲在炕沿上,警告我不要贪心。
我猜测,奶奶是小抠,不想让小伙伴分享。我不知道奶奶做过营养分析,怕我小食品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我很无奈,谁让我是小孩儿呢,逢事都要大人做主。我嘟嘟囔囔地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笔下歪七扭八地写。趁着奶奶不注意,我掰下一块馒头,狠狠地扔出去,期盼来只猫或狗,把馒头叼走。
奶奶真生气了,骂我败家,白背了锄禾日当午,你爸妈赚多少钱才能养活你,鸡毛掸子不再敲炕沿,真的挥向我的屁股。
我正担心小屁股会痛得受不了,救星来了,佳静的爸爸推门而入。那是个魁梧的大汉,装满整个门框,见到奶奶怒火万丈,愣了下神,发现是馒头惹的祸,俯下身,捡起来,大手扑棱扑棱尘土,一口塞进嘴里,嚼巴嚼巴,咽了。
这是奶奶没有想到的,掸子扬在半空,停下了,回过头,惭愧地说,孩子不懂事儿。
佳静的爸爸,我们最喜欢,出海回来,不进家门,也要来奶奶家接闺女。我没记住佳静爸爸的名字,只知道有个海字,索性叫他海爸爸。海爸爸出海回来,从不空手,网兜里装着螃蟹、皮皮虾、八爪鱼、海螺,有时还有对虾、塌板鱼。
我们特别喜欢海爸爸,都盼着他来,见到他,比见到小食品亲,我这个小吃货喜欢海鲜。
欢呼声替代了学习的沉默,奶奶的鸡毛掸子都挡不住。佳静展开胳膊,像一只海鸥,飞跃而起,蹦到海爸爸的怀里,蛇盘树一般黏了一会儿,才从海爸爸充满鱼腥味的身上滑下来。我们三个人,小毛驴一样,撒欢跑到院里抱柴火,要大煮一次海鲜。
每逢这时,奶奶十分过意不去,只是顺便带了人家的孩子,全家人跟着蹭海鲜。我不仅为解馋高兴,更高兴的是海爸爸的到来,中断了鸡毛掸子的落下,让鸡毛掸子成为吓唬人的摆设。我手舞足蹈,高唱国歌,像是中华民族熬过了最危险的时候。
海爸爸回村,就像潮讯的消息传来,半条街的女人都兴奋不已。
那时,没有手机,海爸爸骑着摩托车,呼啸进村,留下一道浓浓的海腥味,人们就知道,他们家的渔船靠近渔港了,四轮拖拉机马上拉着满网的海货,开进村里。每家每户的大门轴都转了,女人们头上扎着厚头巾,走出家门,一个个都成了惠安女,她们来到村里最宽敞的大街,顺着墙根站着,叽叽喳喳。
渔村的日头虽比不上码头毒,但也没逊色太多,她们怕晒黑了脸。
果然,没多久,几辆四轮车“突突突”地驶进村,载着还蹦着鱼虾的网。女人们围上来,卸网择鱼,赚取工钱。海爸爸的海货,养着半条街的妇女。小贩们像闻到腥味的猫,骑着摩托车追来,小贩一般蹲在网前,等择下来的鱼虾够了分量,再上秤量,批发而去。
当然,闻着味儿来的,还有税务所的。海爸爸是有名的渔老大,同样在海里撒网,别人捞上的是海草,他捞的却是鱼虾。税务所没有几个人,看住了海爸爸,就等于看住了他们几个月的奖金。有时,县城里的城管,也来凑热闹,认为他们占了大街,硬是收费,吵嚷了几回,人家是官家人,嘴大,还等着网出海呢,没收了,得不偿失,纠缠不过人家,让人家拿走几条大鱼,就算了。
喜欢腥味的,不仅仅是人,还有猫,趁人不备,偷走一条鱼就跑。海里的海鸥也不示弱,不像它们的羽毛那样洁白高贵,飞过三里外的山梁,滑翔进渔村,讨饭鬼一般,在空中“呕嘔”地叫,若是不扔出烂鱼头,破了肚子的鱼,就往择网人的头上丢臭烘烘的东西。
所幸的是,海鸥不像我这样挑食,没有鱼虾喂它们,面包屑和馒头渣也可以。这些活儿就交给我们孩子们了,我们三个人把我不爱吃的馒头,掰成豆粒状,往天上扔。海鸥们聪明着呢,它们在空中玩杂技,空中掠食,一接一个准。没接住的,它们绝不会低贱地落地上,去捡食,这便宜了溜达鸡们。
择网是很急的活儿,海货不能在网上挂久了。海鲜海鲜,抢的就是时间,沦为臭鱼烂虾,就不值钱了,况且,海爸爸还急着赶下一潮,潮水不等人。择网练的就是双手麻利,不能让网纠缠住。
过意不去的奶奶,总算有了回报的机会,也凑过去,不收工钱,给海爸爸家帮忙。只要海爸爸在场,肯定阻止奶奶,奶奶是教书的,手嫩,禁不住虾枪鱼刺螃蟹夹,总会弄得满手是血,闹得爷爷过不了几天就得买一次创可贴。
别看我们饱餐了一顿海鲜,小孩子消化快,馋虫又被勾出来了。高雄鬼点子多,装成追我,把我追到网上,我假装摔倒,他趁机偷走几条鱼。就这样循环往复,偷出的鱼越积越多。佳静呢,她比我们理直气壮,那是她们家的船打上来的,就从装鱼的筐里往出拿。择网的人不干了,她们是按分量算钱的,佳静拿走的可是她们的工钱。
柳条棍甩在她的手上,佳静哭了,委屈地找我们。我们藏在墙头后,喊佳静过来。谁都哄不好的佳静,听到我们喊她,立刻止住哭声,抹了把眼泪,顺着声音过来了。我们仨一块儿跑到壕沟,用石头垒起灶台,用树枝穿上鱼,一块吃烤鱼。偷来的鱼,刺激,虽说有贼腥味儿,不妨碍好吃。佳静“哏哏”地笑着,声音好听得像春天的柳莺。
好听的笑声,吸引来了我们同班的学生,他们也想吃烤鱼,高雄挥起了机器猫里大雄般的拳头,把他们全打哭了。他们边往回走,边威胁我们,上学后告诉老师,你们是小偷。佳静喊着,我们家船打的鱼,不是小偷。
没有人打扰了,我们吃得更嗨,直到吃得我们脸都黑了,嗓子渴得直冒烟儿,才心满意足地往沟口走。
没走出几步,我们都愣了,奶奶早就守在那儿了。我们忘了奶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校外的老师,家长授权,雞毛掸子是教鞭。奶奶没有训斥我们,让我们立成一排,站好。然后,变戏法一般,从地上拎起个水壶,让我们先喝足了水,省得过一会儿哭坏嗓子。
我本以为奶奶会原谅我们,大螃蟹大对虾都吃了,偷吃几条小油扣、小牙片、小花手绢和小青皮子,不算个啥。没想到奶奶的惩罚逐渐升级,先是罚站,然后才问我们,是哪只手偷的,哪只手偷,就打哪只手。
奶奶让我们做了充分准备才开始惩罚,这一次可不是高举轻落,实实在在地用鸡毛掸子抽我的手心儿,长这么大,我这是第二次挨奶奶打,第一次是从大姑家的柜子上拿了一块钱,那时我才三岁,那一次奶奶是拿手心打我的手心,没有这次疼。
高雄的手心也挨了抽,抽他的手心有两个理由,除了偷鱼,还加上了欺负同学。
佳静没挨着打,奶奶把她也说哭了,让她把偷吃的吐出来。佳静自己吐不出来,奶奶就让她往自己的手心吐唾沫,以示自我惩罚。
奶奶正在教育我们,海爸爸来了。海爸爸每次出海前,总是要亲一下闺女,才肯安心地走,网择完了,装进了四轮车,马上就赶往码头了,还不见他的闺女,就这样四处打听,追到了沟口。
海爸爸满不在乎地对奶奶说,小孩子,贪玩,自己家的,咋能算偷呢。
总算有人替我们说话了,我们正在窃喜,奶奶却生真气了,她反对教育孩子的时候,有人唱反调,给我们撑腰,那样会把孩子惯坏,小时偷针,长大偷金,绝不轻饶。说着,奶奶还要惩罚海爸爸,用鸡毛掸子抽海爸爸的手心。
我们看到,奶奶用十足的力量打向海爸爸,比抽我们的手心还狠,看得我们直眨眼睛,没想到,海爸爸不但没哭,还笑了,不住地向奶奶赔罪。奶奶这才原谅了他。
佳静张开海鸥一般的双臂,扑进海爸爸的怀里,海爸爸把她的脸亲红了。那时候,我也想爸爸了,爸爸在城里上班,说赚钱给我买好房子住,没时间亲我。
夜里,我的手肿了,疼得直痒痒,我听见爷爷小声说,真下得了手。奶奶说,小孩子做错事儿,第一次必须管住,让他心有戒律,等到养成坏习惯,就晚了。
在爷爷奶奶的悄悄话中,我睡着了。我梦见了海爸爸的手,肿成了气吹鼓了的河豚鱼,佳静用舌头舔海爸爸的手掌,她的唾沫像机器猫的百宝囊一样神奇,海爸爸的手掌好了,又去出海给我们捞鱼虾。
梦醒了,困惑又回来了,海爸爸挨了打,为什么不嫌疼,还笑呢,我想了很久,没想明白。直到有一天,我摸到了海爸爸的手,粗糙得像砂轮,满手的茧子比大钱还厚。我这才明白,即使奶奶拿出浑身的力气,用力抽海爸爸的手掌,也和假打没什么区别,那双饱经网纲磨砺的手,已经刀枪不入。
那时,电视里天天嚷,要和国际接轨,实行双休日,实际上限在口头上,除了星期天,我们还得天天上学。佳静她妈,每天除了择网,织网,补网,还要种地,种园子,喂鸡养鸭,天天累得腰酸腿疼,早晨就没好好给佳静做过饭。很多时候,佳静自己给自己热口饭,头不梳脸不洗,背起书包上学去。
佳静不照镜子,不知道自己脏,佳静天天在鱼腥味里,不知道自己臭,她的后衣襟,经常招上一两条没晒干的大头宝鱼,有时挂着一道一道的海皮草,走起路来,一飘一摆,像跳草裙舞。
同学们都嫌佳静身上有味儿,捂着鼻子,不和她玩。只有我和高雄这样的馋猫,专找腥味闻的孩子,才不会嫌弃她。佳静对谁好,是有选择的,她嫌高雄粗鲁,常和我勾肩搭背地走,除非有人欺负她,她才搭理高雄,让高雄替她报仇。
我父母都是要强的人,非要干出一番事业,尤其是妈妈,也是当老师的,还是市一级的骨干,动不动就在电视里晃上几眼,每逢这时,我恨不得钻进电视里去,投进妈妈的怀抱。爷爷和奶奶是外来户,因为喜欢大海,才定居在渔村。祖辈与父辈,都是研究文化的,家庭的背景,决定着我必须与众不同,他们把我打扮成小少爷,与渔村里的孩子们格格不入。
可同学们对我的格格不入,不是因为我穿得和他们不一样,是因为我和臭不可闻的佳静形影不离。于是,他们就喊,我和佳静搞对象了。我不知道搞对象是啥意思,但机器猫里已经告诉我,那是让人脸红的事情。
我伤心地哭了,恰巧赶上高雄的妈妈来学校,高雄的妈妈是从我老家那儿嫁过来的,当过奶奶的学生,对我也格外高看一眼。目睹这一幕,她忙哄着我说,你才不和佳静搞对象呢,她老农业户。
那时,城镇户和农业户,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城镇户吃供应粮,国家养着,工作国家包分配,最次是当工人。农业户没人管,得土里刨食,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面向咸水背晒蓝天,是天底下最苦的人。学习若不能出类拔萃地好,下一代逃不过继续爬垄沟,或者当满身腥臭的海榔头。
所以,城镇户有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所以,佳静与高雄的父母不遗余力地让奶奶教他们,长大了好跳出苦海。
优越感让我找到充足的理由,同学再说我,我就挺着胸脯告诉他们,佳静是农业户,我才不和她搞对象呢。
听我说得这么坚决,佳静哭了,好像我不再和她好了,不和她玩了,她就没有资格到奶奶家学习了,沦落成没人要了。
那一天,佳静是哭着去的奶奶家,向奶奶告状,说你孙子不和我搞对象了,嫌我是农业户,身上臭,不和我一块儿学习了。
奶奶听后,哈哈大笑,小屁孩懂得啥叫搞对象,都让日本动画片给教坏了,还没脚丫子高呢,就教谈恋爱。奶奶哄着佳静,告诉她,谁不要她,奶奶都要。奶奶还说,姑娘家家的,要干净。说着,奶奶张罗给佳静洗澡,洗衣服,让我们俩野小子,滚远点儿。
梳洗过后的佳静,果然俊俏了许多,奶奶还给她打了有香味的香皂,佳静再也不是臭丫头了。奶奶说,小姑娘是打扮出来的,以后,谁也不许歧视佳静,谁想和她搞对象,佳静得挑挑拣拣呢。
高雄举起了右手,向奶奶报告,我想和佳静搞对象。我瞅着高雄,不知怎么,心里有那么点儿不舒服,后来,我才懂得,那种滋味叫吃醋。
奶奶抽出了鸡毛掸子,敲着炕沿,好好学习,你们还小呢,今后谁也不许提搞对象的事儿。
三個脑袋顶在一起,默不作声地写作业。
这段日子,佳静的状态很不好,动不动就走神。奶奶看出来了,问她,有啥心事?佳静告诉奶奶,爸妈老吵架,原因是海爸爸出一次海,赔一次钱,快把家底赔光了。
奶奶很疑惑,每次出海,打的鱼还可以呀,螃蟹对虾一网兜接一网兜地往我们家拿,怎么会次次赔呢?奶奶让我们陪着,去了渔港码头,探个究竟。奶奶数学特别好,常替村里人算账,大到盖房子,小到买米买菜,有时还替人算风向,算航速,算海里,算归来的时间。在渔村这么多年,只要知道船啥时候出的海,在哪个区域作业,奶奶就能掐算出啥时回码头,上下不超过十几分钟。
翻过一道山岗,就是渔码头,我们是提前闻到的,海腥味儿,臭鱼味儿,夹杂着桐油味儿,腻子膏味,五味杂陈,势不可当地奔袭过来。难怪所有的渔村都远离渔港,这股呛人的味道,实在让人受不了,好在这味道里夹着我爱闻的海鲜味儿,否则,我也会被熏得呆不下去了。
渔港里的船一艘挨着一艘,随着海浪,上下涌动,大多数渔船的驾驶舱和网舱,空空如也。潮水快涨满了,本该是归航的时刻,码头里,渔船却密密匝匝地泊在港湾里,空闲下来的泊位寥寥无几。望向大海,只有稀稀落落的渔船,突破了海平线,三三两两地归来。
渔船刚刚靠港,船老大便迫不及待地将网摊在码头上,择网的女人蜂拥而至,双手机器一般翻飞在网上,择下的鱼还在蹦跳,就被搬进了冷库的冷藏车,没等税务局的人来扯票,渔船或“突突突”地又驶进海里,或干脆偃旗息鼓地泊在码头,人走船空。
扫过几眼,奶奶就明白了,海爸爸还是传统的老渔民,顾及乡里乡亲的方便,不让择网的女人被怪味呛着,被海边毒辣的太阳晒黑。顾及多年商贩的情感,让他们多赚几个,不卖给出价高的冷库。如此下来,又是雇车,又是搬网,多出了这么多成本,他根本不去算,只知道捏到手里的钱,越来越薄,剩下的,给船加满柴油都不够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虽说渤海没有穷成现在这个样子,只剩下咸水了,却也是日渐枯竭,本是捕捞旺季,许多渔船泊在码头,一动不动,只等着海蜇汛期的到来,捞着了,就赚了,捞不着,平时不出海,也赔不了多少。
没过多久,海爸爸的船“突突突”地靠上了码头。这一次,奶奶耍起了老师的权威,让海爸爸就地择网,马上卖给冷库的冷藏车,她亲自点现金,给海爸爸做了一次成本核算。
终了,海爸爸没有赔钱,但赚得也不多。海爸爸挠着脑袋,对奶奶说,这么做,对不起乡邻,也对不起多年买我海货的商贩。
奶奶给他算了一笔更大的账,你就没想想,天天赔钱,对得起小佳静吗?她将来要上好大学,要花很多钱,学习上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钱做基础,除非你放弃了孩子的未来,任她留在渔村,做个渔婆子。
海爸爸沉思了好久,他在想两全其美的法子,他说,下次出海,我要带足柴油,带足冰块,远航,出渤海,去黄海。
奶奶说,钱不够,我借你。
海爸爸捏着奶奶替他管回来的钱,不好意思地说,够买柴油了。
跟着奶奶到码头去一趟,我才知道,当渔民,真不容易,奶奶因为粒粒皆辛苦,就要打我屁股,想一想,我天天吃海爸爸熬着心血打来的海鲜,是多么没心没肺。我想起了妈妈教给我的另一首诗: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有些时候,诗不是背的,而是品的。从此以后,只要吃到海鲜,我的脑袋里就涌现出海爸爸那张黑红的脸庞,那双粗大的手,还有满身的海腥味儿,我连一根鱼刺都舍不得扔,直到嚼透,咽下。
那天晚上,看完《机器猫》,我们三个的脑袋又挤在了一起,开始学习前,我对他俩讲着我的胡思乱想,我说,我想发明一个机器,把一根管子插进海里,鱼虾蟹顺着管子往船上跳,海爸爸也不必那么辛苦了。
佳静很感动,就差亲我的脸了。
我害怕奶奶听到,悄声说,我不嫌你臭,同意和你搞对象。高雄扯着嗓子喊,我也和佳静搞对象。
奶奶用鸡毛掸子敲炕沿,安静,学习。
以前,海爸爸出海,出门走路一样,随随便便,海里生浪里长的,船上也如履平地。这一次不同了,出远海,要走许多天,佳静妈给海爸爸准备了好多吃的,带足了淡水。压舱石改成了压舱冰,柴油也多备了一大桶。这一次,海爸爸专门雇了个船员。
到码头送行时,佳静像条小水蛇,黏在海爸爸身上,海爸爸的硬胡茬扎疼了佳静的脸,可佳静还是“咯咯”地笑。潮水涨满了,海爸爸的渔船拖着一股浓烟,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中。
从前,海爸爸出海,都是赶着潮走,早出晚归,或者是晚出早归,不会超过两个潮。这一次,一走就是半个月,杳无消息。佳静的妈妈牵着佳静的手,跑到码头,天天向海里望,望成了一座望夫石。
噩耗是海爸爸雇来的船员带来的,他是被海警的船送上岸,接到村部的。船员说,在黄海遇到了龙吸水,大浪滔天,风裹着渔船乱转,海爸爸把他绑在船上,自己驾船和恶浪搏斗,终究被大浪卷走。船坏了,失去了动力,他在海里漂泊了三天三夜,才被海警发现,把他从绳索上解救了出来。
佳静她妈疯了般往码头跑,船被海警的船拖了回来,安静地泊在渔港,她跳上甲板,船舱、机器舱、驾驶舱,疯狂地找,哪怕一个船缝都不放过,好像海爸爸能变成蚂蚁,藏起来。末了,她双手拍着船舷,放声大哭,痛骂自己,财迷心窍,害你跑到了外海。
找不到遗体,也得举办葬礼,脑袋用一只葫芦顶替,身子就是海爸爸平时穿的衣服,塞在寿衣里,像个完整的人。奶奶请来了学校教画画的老师,按照海爸爸生前的照片,画了一张闭着眼睛的人,还涂了油彩。
给葫芦脑袋的海爸爸蒙遮脸布的时候,佳静和她妈妈一块扑上来,哭得个悲天恸地,把葫芦头拍得“啪啪”山响,好像能把魂拍回来。
葬礼过后,我形影不离地陪着佳静,才七岁,就没有了爸,怪可怜的。佳静总是往海边跑,不过不是码头,而是兴海湾,那里是旅游区,有一座三礁揽胜,由三座桥连着,伸向大海里。最后的礁石上,有个三层高的亭子,爬上亭子,能望得很远很远。
佳静站在那里,忧郁的眼神望着远方,一直望过了海平线,那里能把更多的渔船拓展进她的视野,当然,也藏着她永远也见不到的爸爸。风掠过她的头发,摇来摆去,像掠起了一团干枯的草。没有了海爸爸,她身上的海味也渐渐消失,再也没人说她臭了,也没人嫌她有鱼腥味了,可她没有了爸爸。
在风中,她的眼泪突然间失控了,“唰唰”地流下来,被汹涌的海浪接住,拍碎,转瞬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海就是这样残酷,不同情眼泪。
佳静突然从亭子上跑下来,沿着海岸线,一路狂奔,泪飞如雨,她大声呼喊着:爸爸——,爸爸——
我也随着佳静一块儿跑,也跟着他呼喊,爸爸——,爸爸——
海涛阵阵,无视我们的呼喊,更无视曾经和它们亲密无间的海爸爸。
跑累了,我们跌坐在海滩上,大海里,游人如织,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欢乐而又畅快地游戏着海水,消暑度假,享受美好生活。海鸥们展开洁白的翅膀,无忧无虑地飞。没有了海爸爸,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唯有佳静,结满蛎子皮的礁石一般,满心伤痕。
佳静在海滩上挖了个心形的坑,海浪追逐过来,埋掉了她的心,把海滩抚得平平展展,仿佛没留下任何痕迹。她接着在海滩上挖心形的坑,又被海浪给摩挲平了。她倔强地挖着自己的心,哪怕無数次被掩埋。直至大海退潮了,海浪再想够也够不着她心爱的心了。
她自己把心用沙子埋上了,埋出个丘包,仿佛是一座小坟墓,她冲着小丘包,令人心碎地叫了声,爸爸。
我也陪着她,向小丘包磕头,跟随着叫,爸爸。
海爸爸的突然遇难,佳静再也不到我家来了。奶奶伤心了很久,毕竟奶奶鼓励过海爸爸去外海打鱼。后来,我们家便搬出了渔村,我回到了父母身边,到城里小学念书,与佳静和高雄彻底地失去了联系。
二十年后,我在城里的海鲜市场见到了一个人,特别像高雄,我怕认错,尝试着叫了声,他居然答应了。现在,他从小胖墩变成了大胖子,却不是臃肿的胖,而是壮,二百多斤的鱼篓子,他抱玩具一般,抱进了摊床下。
这时,我听见一个似曾相识的叫声,爸爸。
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跳上摊床,展开海鸥一样的双臂,投入进高雄的怀里。
这一幕,多么地熟悉,我突然想到了佳静,这孩子,和小时候的佳静,好像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
时间把高雄刻成了海爸爸的样子,穿着浸满海腥味的棉大衣,胡子潦草,脸色黑红。果然,他猜到了我心中所想,坦率地告诉我,你幼年的女朋友佳静,现在是我媳妇。
他一手抓起一只海飞蟹,每只都有一斤多重,硬往我手里塞。我知道,两只野生的海飞蟹,就是四五百块钱,我承受不起这么厚重的礼物。
我说了句只有我们才懂的话,我妈没退休呢。他知道,我妈也是老师。
他讪然一笑,海飞蟹在他的双手上张牙舞爪,我知道,他没有舍不得,和当年的海爸爸一样慷慨、真诚。
我转身走了,我觉得,留下拒绝,也是虚伪,一走了之,最为恰当。走了很远,才回头望了几眼,那背影,多像海爸爸呀,难怪佳静会选择他。我感慨,为什么一代一代的生命会如此地重复?
海爸爸,我心里念叨一句,眼睛潮湿了。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