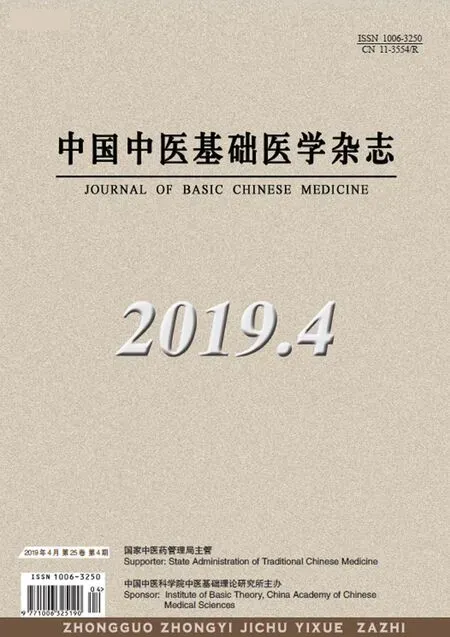从《寓意草》看喻嘉言的窠囊思想
孔令旗,孔军辉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喻嘉言(1585-1664),名昌,字嘉言,晚号西昌老人,江西新建(即今江西南昌)人,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早年致力于儒学,仕途受挫加之明清鼎革,遂隐于禅学,后又出禅攻医,游历江南。其治学思想敏锐,每在前人的论点上有所发挥[1]。《寓意草》写于喻嘉言晚年,是其代表作之一。本文试从《寓意草》中若干涉及窠囊的医案,分析和总结其窠囊思想及其对临床辨证思维的启发。
1 病机
喻嘉言在《详胡太封翁疝证治法并及运会之理剿寇之事》一案中,详细地论述了窠囊的病机,认为窠囊是“始于痰聚胃口,呕时数动胃气,胃气动则半从上出于喉,半从内入于络。胃之络,贯膈者也,其气奔入之急,则冲透膈膜,而痰得以居之,痰入既久,则阻碍气道,而气之奔入者复结一囊。[2]”脾运无力,水湿停聚,经胃火煎灼而为痰饮,积于胃口,或可随咳吐而出,或可因“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3],冲透膈膜进入肺中,肺中多气多孔,痰饮便“如蜂子之营穴”[2],更加积聚,久而久之形成窠囊。病机总以脾虚湿盛,痰饮不化,上传于肺,因而笔者认为窠囊是“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在喻嘉言的具体发挥。
2 病理特点
2.1 窠囊专积于肺
喻嘉言论窠囊有明显的病位特点,窠囊之痰因于脾,生于胃,后冲透膈膜进入肺中,久而形成窠囊,即窠囊总是形成于肺,从而导致咳喘痰饮。但在《详胡太封翁疝证治法并及运会之理剿寇之事》一案,喻嘉言论病时讲到“庶几坚者削而窠囊可尽空也”[2],在这里窠囊仅指疝病病灶,并不指由痰饮所致形成的肺部窠囊。另喻嘉言还有一“膜囊”,此是“肝火冲入,透开胃膜,故所聚之水暗从木化变酸,久久渐满”[2]而成,其病位在胃。
2.2 阻碍气机运行
痰饮始于脾胃,积于肺中而成窠囊。痰饮尚在胃时,便易呕吐而出,此一则加快痰饮冲透胸膈入肺,一则扰动气机上逆,胃气不降反升,牵连肺气不降反升而致咳喘,待窠囊形成则更加干扰肺之气机。在“论浦君艺喘病证治之法”一文中,他论及“窒塞关隘,不容呼吸。而呼吸之正气,转触其痰,鼾齁有声,头重耳响,胸背骨间有如刀刺,涎涕交作,鼻頞酸辛,若伤风状,正如《黄帝内经》所谓心肺有病而呼吸为之不利也……乃至寒之亦发,热之亦发,伤酒伤食亦发,动怒动气亦发”[2]。窠囊因为是积于肺中的有形产物,“痰入既久,则阻碍气道,而气之奔入者复结一囊”[2]阻塞气道,影响气机,导致出现如呼吸困难、声粗、头重耳响、胸部刺痛、流涕等一系列的肺系症状。“膻中之气因呕而伤矣”[2],如此也会耗伤正常的膻中之气。
2.3 病情绵延难愈
窠囊的形成时间日久,与肺结合紧密,“如蜂子之穴于房中,如莲子之嵌于蓬内,生长则易,剥落则难,由其外窄中宽,任行驱导涤涌之药,徒伤他脏,此实闭拒而不纳耳”[2],此则体现了窠囊的特殊形态和其绵延难愈的特点。
2.4 窠囊出路二则
窠囊之痰从胃而来肺,但并不是一直停留在肺中,也能再回到胃中。《详胡太封翁疝证治法并及运会之理剿寇之事》一案中说:“安得不出。但出之曲耳。盖膻中之气,四布于十二经。布于手足六阳经,则其气从喉吻而上出;布于手足六阴经,则其气从前后二阴而下出。然从下出者无碍,从上出者亦必先下注阳明,始得上越,是以难也”[2]74。喻嘉言认为窠囊的痰因经络联系,下可以从二便而出,也可以再次注入胃中,然后从胃中向上吐出,但非常困难。
3 窠囊论治
喻嘉言在《详胡太封翁疝证治法并及运会之理剿寇之事》中写道,窠囊“生长则易,剥落则难,由其外窄中宽,任行驱导涤涌之药,徒伤他脏,此实闭拒而不纳耳”[2]。故治疗时视病情从多方面下手,辨证论治。他论及治法,总结为治痰、健脾、治气三法,但未论及方药,我们在临床上应结合具体症状辨证论治。
3.1 治痰
痰饮是窠囊的直接原因,为本病之标,若咳呕上气等标证严重是痰积聚肺中情况较为严重,当先治痰。“痰消则气自顺,是必以治痰为急……无痰则不呕,不呕则气不乱,气不乱则自返于氤氲矣”[2],“必先去胃中之痰而不呕不触,俾胃经之气不急奔于络,转虚其胃,以听络中之气返还于胃,逐渐以药开导其囊而涤去其痰。则自愈矣”[2]。其他医家涤荡痰饮之法可资参考,如《医学正传》载滚痰丸(即今礞石滚痰丸) “治湿热、食积,成窠囊、老痰。[4]”
3.2 健脾
“肺中之浊痰亦以脾中之湿为母”[2],“必以健脾为先。脾健则新痰不生”[2],健脾是治痰的治本之法,脾运有力,新痰不生,旧痰亦能缓缓除去。
3.3 治气
“痰饮结于胸膈,小有窠囊,缘其气之壮盛,随聚随呕,是以痰饮不致为害,而膻中之气,因呕而伤矣”[2]。在痰饮上呕的过程中,伤气乱气,故治疗窠囊必治气,补气理气。喻嘉言在《详胡太封翁疝证治法并及运会之理剿寇之事》一案中认为:“治气之源有三:一曰肺气,肺气清则周身之气肃然下行……一曰胃气,胃气和,则胸中之气亦易下行……一曰膀胱之气。膀胱之气旺,则能吸引胸中之气下行”[2],肺和胃之气均以降为和顺。而膀胱之气也是以降为和顺,这是喻嘉言的发明之处,治膀胱之气在于治肾,“膀胱之气化,则空洞善容,而膻中之气,得以下运。若膀胱不化,则腹已先胀……然欲膀胱之气化,其权尤在于葆肾。肾以膀胱为腑者也。肾气动,必先注于膀胱……肾气不动,则收藏愈固,膀胱得以清静无为,而膻中之气,注之不盈矣。膻中之气,下走既捷,则不为牵引所乱,而胸中旷若太空”[2]。肺胃膀胱(肾)三者之气和降,气不上逆则胸中平和,痰饮不会上涌,咳呕亦会减轻。这也是喻嘉言“大气论”[1]学说的体现。
4 学术源流
喻嘉言的窠囊思想,笔者认为是来自于宋代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因其在《论吴圣符单腹胀治法》一案后,选录了许叔微《普济本事方》的一段文字,并命名为“窠囊证据”[2],作为自己窠囊思想的佐证。许叔微在其《普济本事方》中自述生平有二疾,一则脏腑下血,二则膈中停饮。许叔微膈中停饮一症即与痰饮有关,起病于“年少时夜坐为文,左向伏几案,是以饮食多坠向左边,中夜以后稍困乏,必饮两三杯,既卧就枕,又向左边侧睡”[5],因为自己左向伏案、左向卧、夜酒,导致酒食积于左边,三五年后出现了“觉酒止从左边下,漉漉有声,胁痛,饮食殊减,十数日必呕数升酸苦水,暑月只是右边身有汗,漐漐常润,左边病处绝燥”[5]的症状,众医无效。许叔微自己揣度,十数日一呕酸水是“已成癖囊,如潦水之有科臼,不盈科不行,水盈科而行也,清者可行,浊者依然停,盖下无路以决之也,是以积之五七日必呕而去,稍宽数日复作”[5]。许叔微认为这种有形病理产物的蓄积,是因为脾运无力,且痰热积聚,法当燥脾胜湿,最终“一味服苍术,三月而疾除”[5]。
许叔微的癖囊思想与喻嘉言的窠囊思想非常相近,病机都是由脾虚湿盛、痰饮不化引起的,治以苍术燥脾胜湿,这也与喻嘉言健脾治痰的思想相近,但病位不同,许叔微之癖囊是在胃,喻嘉言的窠囊而在肺。
最早窠囊一词被用于解释病机,首见于朱丹溪学派的《丹溪心法》:“许学士用苍术治痰成窠囊一边行极妙,痰挟瘀血,遂成窠囊。[6]”我们可以看出,朱丹溪的窠囊思想也是从许叔微“癖囊”一案中悟出,但是朱丹溪认为窠囊的病机是痰挟瘀血,这与喻嘉言的思想不同。喻嘉言的窠囊思想也影响了后世许多医家的学术观点和临床辨证治疗。
《杏轩医案》中的“福方伯哮喘”一案中,患者“胸满喘促,呼吸欠利,夜卧不堪着枕。药投温通苦降,闭开喘定,吐出稠痰而后即安”[7]。程杏轩以“思病之频发膈间,必有窠囊,痰饮日聚其中,盈科后进……痰气上逆,阻肺之降,是以喘闭不通。务将所聚之痰,倾囊吐出。膈间空旷,始得安堵。无如窠囊之痰,如蜂子之穴于房中,莲子之嵌于蓬内,生长则易,剥落则难。[7]”如此论述正是程杏轩对喻嘉言窠囊思想的总结,采用的治法为:“早服肾气丸温通肾阳,使饮邪不致上泛。晚用六君,变汤为散,默健坤元,冀其土能生金,兼可制水。夫痰即津液所化,使脾肾得强,则日入之饮食,但生津液而不生痰。痰既不生,疾自不作,上工治病,须求其本[7]”,采用的治法也是喻嘉言健脾和治气之法。在《答鲍北山翁询伊芳郎饮证治始末并商善后之策》一案中,程杏轩更是直言:“窠囊之说,许叔微论之于前,喻嘉言详之于后。师古而非杜撰。前番势轻,病后只须治脾。此番势重,病后务须治肾”[8]。程杏轩也认为喻嘉言的窠囊思想与许叔微的思想一脉相承。《一得集》的“痰证随宜施治论”中说:“年久老痰,窠囊锢结,当遵喻氏法以运出之,又须继以补脾,而为填空之计”[9]。又《回春录新诠》也说:“而痰饮者,本水谷之悍气,缘肝升太过,胃降无权,另辟窠囊,据为山险”[10]。由此可见,喻嘉言的窠囊思想确实对后世医家多有影响。
5 结语
喻嘉言受到许叔微《本事方》的影响,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发展创新了窠囊的病机思想,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前人的窠囊论治体系,影响了后世的医家,是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