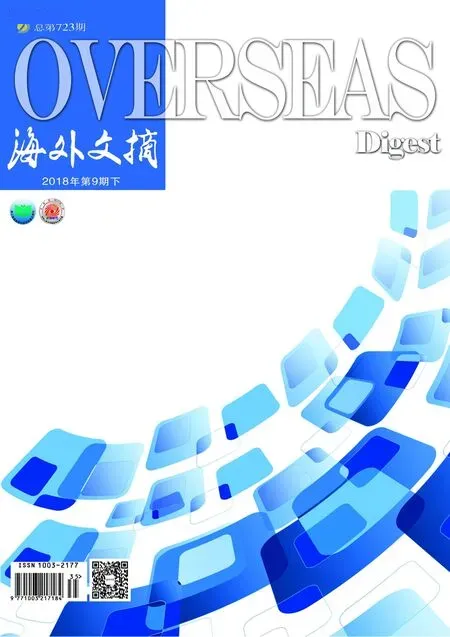阎真笔下女性书写的男性化色彩
——以《沧浪之水》、《因为女人》为例
马巧仪
(广西大学,广西南宁 530000)
1 何谓“女性书写”
在70年代中,法国女性学者埃莱娜·西苏开始提出“女性书写”的概念,是从她在1975年所写的文章《美杜莎之笑》中提出的,她肯定两性之间存在差异,但并不认同将女性放置在一个“他者”的位置,寄希望于通过女性书写来打破男女之间的二分局面,以此来区分男女的特质。西苏在《美杜莎之笑》开篇写道:“我将提出女性书写,有关她的可能性。女性一定要写她自己的故事、其他女性的故事,把女性带入写作之中”,鼓励女性运用自己满带感性的、诗性的语言来诉说自身的故事,表达自身的欲望(这里的欲望不单指身体欲望,还包括物质欲望),积极引发两性对话,打破两性对立的状况。
西苏的女性书写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主要有四种:一是“女性写作”,最早见于韩敏中翻译、由伊莱恩·肖沃尔特所作《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载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和由林建法、赵拓翻译、陶丽·莫伊所著《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二是“妇女写作”,最早见于黄晓红译、西苏所作《美杜莎的笑声》,载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三是“阴性写作”,在宋素凤所著的《法国女性主义对书写理论的探索》(载《文史哲》1999年第五期)中有所体现;四是“女性书写”,借鉴了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界对德里达维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提出上的书写理论的汉译,似从“对于女性的书写”简化而来,多见于同时期国内学界对“五四”之后女作家以及当代女作家对女性经验的书写所做的研究。而国内学术界常用的是“女性写作”和“女性书写”,以此来对应西苏所提出的女性书写理论。对于“女性书写”这个理论内涵的理解,必须清醒认识到作品性别与作者性别之间的区分,“女性书写”并不限定书写主体的性别,署上女性名字的作品并不一定具有女性特征,也可能是男性写作,而署上男性名字的作品也不排除包含女性特征。要谨慎看待“女性书写”,很多女性形象其实是男性书写,而“女性书写”也未必都由女性创作,一些男性创作的作品也可以是“女性书写”。凡是能够传达女性生命体验、反映女性主体特征的写作风格、文本属性等,都可以视为是“女性书写”。
作家阎真,他的文学创作始于1996年,1998年创作了长篇小说《曾在天涯》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对小说技巧的把握以及文章行云流水的书写成功引起文坛注意;接着,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于2001年问世,2007年又创作《因为女人》。后两部作品以更纯熟的小说技巧和女性意识体现(《沧浪之水》乍看虽为男性主题,但背后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体验不容忽略)揭示了现今社会女性所面临的情感和生存困境。文章试图借“女性书写”这一视角来剖析阎真在创作《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两部小说背后所蕴含的男性化色彩。
2 阎真笔下女性书写的体现
2.1 《沧浪之水》
小说《沧浪之水》塑造了池大为这样一个从无职无权、空怀壮志到时来运转、大展宏图的男性形象,小说的脉络以人物池大为贯穿始终,从这点看来,这部小说是明显书写男性角色人生起伏的。文学评论家白烨曾说:“这部小说从池大为的人生经历,写出了时运转移中的人生百态与人情翻覆,官场之波诡云谲、反腐之惊心动魄,都从他的升降沉浮中充分而深刻地展现出来,实为当下现实题材的难得力作”,又有学者孟繁华评论道:“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历来就是一个矛盾的群体,在传统文化被不断重构、整合的今天,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仍然是一个问题。我们不是池大为,但池大为的心路历程和行为方式有极大的典型性”,类似的文学评论还有不少,评论的主体对象几乎放在了池大为这个男性形象的身上,但仔细阅读可知,阎真于行文中还花了不少笔墨去塑造池大为妻子董柳这个女性形象。
小说第二篇开始,董柳是以池大为妻子的身份登场的,夫妻两人是在市卫生系统的联欢会上认识的,阎真对早期董柳的性格刻画是“安安静静的”、“淳朴的”、“没有丝毫自恋性骄傲的”、“毫不做作的”,也正因如此,两人结为夫妻。此时的董柳安于现状,守着柴米油盐过活,对身体欲望和物质欲望没有过多追求,生活圈子基本以丈夫池大为为中心,完全一心一意扮演好妻子的角色。但儿子一波的出生,改变了董柳,她想给儿子世界上最好的一切,而这一切都建立金钱与权力的基础之上,“我就是爱钱,我一波动一动都要用钱,我爱我一波我就非爱钱不可,有了钱我一波少受点委屈,他受一点委屈我这心里就有钢丝扯着疼”,董柳已经完全从妻子的角色转变成母亲的角色了。一波上幼儿园事件及被开水烫伤事件的发生都刺激着董柳性格的转变,两人的对话也透露出,一个家庭的崛起必须有权力和金钱的支撑。董柳对现阶段自己的所要所想是十分明确的,她一反早前无欲无求、安于现状的态度,开始学会用女性的武器——眼泪、性冷暴力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要求丈夫为人处事圆滑些,多去领导家里走动,争取早日升个一官半职。字里行间体现出董柳不再一味顺从丈夫言语,她即将拼尽全力争取自己和儿子生活幸福的权利,她要摆脱家庭生存的困境,此阶段阎真对董柳女性意识和女性特征的书写是十分到位的。
转机的出现,是马厅长孙女渺渺的病重,素有“董一针”称号的董柳被请到医院亲自为渺渺打针,由于董柳个人职业水平的出色,身为董柳丈夫的池大为逐渐受到马厅长的提拔和重用,直至小说结尾坐上了厅长的位置。除了池大为个人能力突出外,最不可忽略的原因是董柳在其中发挥的助推作用。阎真这个情节的设计完全改变了小说人物的命运走向,男性仕途的沉浮起落以及女性主体地位的升降等,都昭示着个体的精神成长过程,小说中传统文化语境下男性对女性的命运拯救并不明显,相反,明显的是女性意识觉醒(董柳中、后期的性格意识发展)对男性走向成功(池大为登顶权力中心)的重要性体现,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或影响男性的选择了,她们的家庭话语权并没有完全消失。
2.2 《因为女人》
小说《因为女人》是阎真继《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力作,小说通过讲述女大学生柳依依的成长故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爱情和婚姻的现实问题,正如阎真所说:“这是一部必须要写的小说。我看了太多、听了太多、想了太多,不写出来难以心安”,作者为柳依依的每一步都长吁短叹,也为世上的男人和女人忧虑不已。小说《因为女人》与《沧浪之水》的描写对象侧重不同,前者通过塑造柳依依这个主要女性形象来反映问题,而后者的女性形象董柳则是次要人物的描写体现,这可看出作家阎真写作技巧更加纯熟,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更加深入、全面,就连学者周昌义也评论说:“男性作家中,能把纯情女生终成旷世怨妇的女性悲剧演绎得如此精致细腻的,恐怕只有阎真教授了”。
纵观小说,阎真对柳依依的女性书写色彩是十分浓厚的。小说中柳依依是以清纯的女大学生身份出现的,她的舍友苗小惠在穿着打扮、思想方式、性心理等方面都给柳依依以指导,言语当中更加以柳依依岁月催人老的紧迫感和压力感。在柳依依这个女性形象的成长过程中,先后出现了薛经理、夏伟凯、郭志明、阿裴、秦一星、宋旭升这几个男性,起初柳依依在面对校园爱情肉欲化、人生游戏化的现实境况下,仍保持自己对爱情的忠贞信仰并将爱情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但初恋夏伟凯的背叛摧毁了她赖以生存的情感圣殿,而“女人的美好是要男人来品味的,青春有价”这些观念逐渐渗入她的内心。此时柳依依对现实爱情的肉欲化和物欲化已有了认识,她是现代知识女性与旧式传统女子的矛盾结合体,虽将爱情视为人生的信仰,但认识到现实的残酷后又不肯向现实妥协。往后,在她作为已婚成功男士秦一星情人的日子里,成熟男人的情爱技巧和物质关怀使柳依依沦陷,她的身体欲望和物质欲望虽得到满足,但却永远得不到情感的保障。这阶段的柳依依已经完全不是曾经那个清纯无邪、心思单纯、对忠贞爱情充满憧憬和向往的女大学生了,她已经成长为一个有欲有求的女人,在各类男性和女性(苗小惠、阿雨)有意无意的指引下,对女性现实生活的生存体验认识得更加透彻,家庭的压力、现实的困境以及情感圣殿的崩塌使柳依依迫切需要一个安稳的港湾,即使她是一个有工作有能力的知识女性。
年龄的压力以及情人秦一星的劝诫使柳依依与当时家庭条件、个人条件不佳的宋旭升结婚,两人在发生婚后关系的第一夜便产生了隔阂,宋旭升吐出“是松的”这几个字深深刺激了柳依依,但此时柳依依在家中是有一定话语权的,毕竟她的工作地位、工资收入都在宋旭升之上,家庭内部也离不开既是妻子又是母亲的柳依依。但宋旭升经济收入好转后,便在外面养了情人,即使柳依依花精力和金钱打扮自己、武装自己,与残酷的岁月做斗争也无果,夫妻两人彻底陷入怀疑与防备的境地,她的情感无从寄托,也无法在生活中获得完满。阎真在小说结尾部分对柳依依的女性形象书写极具悲剧性的,“柳依依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又能够怎么办。自由吗?自由。但自由对自己没有意义。欲望优先,这是一个世纪性的错误,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错误。男人失去了爱情,收获了欲望;女人失去了爱情,收获的是寂寞。女人必然是输家,因为青春不会长久”,这种认知让柳依依“在脑海的黑暗深处留下了一个清晰的亮点,灼得她隐隐地痛”。而她为了不让女儿重蹈自己的悲剧,更是“要趁她还没有成长起来,就要把她那种天然的信仰萌芽摧毁,摧毁了她才不会被悲剧性的宿命所摧毁。因为,她也会成为一个女人”,可见,现实给柳依依带来的心理上、情感上的创伤是巨大的,爱情和亲情已经不是最后的归宿。
3 女性书写背后的男性化色彩
3.1 男性的主导地位依旧
从小说《沧浪之水》、《因为女人》的整体把握来看,男性在女性的主体成长过程中依旧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男性形象在两性的交往活动中基本处于主动地位,都积极或消极地引导着女性的成长,男性是作为家庭中心而存在的,而女性则围绕着这个中心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沧浪之水》中的女性形象董柳虽不是研究生学历,但知识水平也不低,作为卫生院的一名护士也有着较好的业务水平。起初“董柳专注于自己的日子,对其他事情没有兴趣,她不下棋不打牌,不串门不聚会,在家里就是呆得住。结婚以后,我(池大为)就成了她关注的焦点。她早出晚归,每天早早起来,把早餐做好”,这阶段的董柳在家庭中扮演着妻子的角色,尽职尽责,完全是围绕着丈夫池大为而活;有了儿子一波之后,她又转换成一个母亲的角色,凡事亲力亲为,对儿子一波百般宠溺,“发胖就算了,有些人为保持身材不给孩子喂奶,我真的不理解,还是做母亲的人?我要那么好的身材干什么,只要我一波身体好就好”。可见,在董柳主体成长过程中始终有两个男人占据生活的主导地位,她走不出家庭,也无法摆脱男性对自身的主导作用。而小说《因为女人》中女性形象柳依依的主体成长过程却与董柳有些不同,她的生活世界先后出现了初恋夏伟凯、情人秦一星和丈夫宋旭升这三个主要男性,初恋夏伟凯摧毁了她的爱情圣殿,情人秦一星将她作为婚外的新鲜剂并给予她情感和生活上的建议,而丈夫宋旭升婚后的出轨让她对婚姻和家庭失去希望。这几个男性给柳依依的成长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几乎主导了柳依依的整个成长过程。在这里,我不禁提出反思,为何董柳、柳依依这两个有知识、有工作、有能力的女性在感受到家庭生活不完满时不选择离婚呢?难道凭借她们的工作能力和薪资水平还养活不了自己吗?在《因为女人》的扉页中阎真针对波伏娃“女人是后天逐渐形成的”论断提出了“生理事实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文化和心理状态,而不是相反。把女性的性别气质和心理特征仅仅描述为文明的成果,就无法理解她们生存的真实状态”,阎真是认识到当下女性的生存困境而创作的,但是书写的背后还是沿承着几千年来传统男权社会给女性的人生定位,仅将女性定位在“女人”的位置,一生只懂扮演好妻子和母亲这两个角色,这完全忽略了女性本身,将女性放置在了“他者”的位置,丧失了家庭、生活、情感上的主动权,最后也只能在男性的主导地位作用下走向悲剧。
阎真在《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这两部小说中都未曾有关于女性走出家庭的书写,甚至是一点伏笔也没有留下,虽极尽笔墨揭示了欲望化社会给女性带来的生存困境,但从其女性书写的背后仍有阎真本人男性化色彩的体现。
3.2 女性的宿命悲剧仍存
关于女性宿命悲剧的体现,小说《因为女人》比《沧浪之水》来得更为深刻,前者是自始自终将女性形象柳依依作为书写的中心刻画得淋漓尽致,阎真将她如何一步步走向命运悲剧进行了入人骨髓的书写;而后者中的女性形象董柳的悲剧性是从侧面体现的,命运的悲剧性意味需要读者在小说之外体会,这里主要以《因为女人》中的柳依依为主要分析对象。
《因为女人》的结尾部分是这样写的,“她说服自己这是宿命,悲剧性是天然的,与生俱来。既然如此,反抗又有什么意义?在这个欲望的世界上,如果她已经不再年轻漂亮,她又有什么理由什么权利要求男人爱她,疼她,忠于她?欲望的时代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她们在人道的旗帜下默默地承受着不人道的命运。有人说过,母系社会的解体是女性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也许,欲望化社会的出现是女性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吧!柳依依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越是怀疑就越是抑郁,越是抑郁就越是怀疑。她沉默了许多,在公司,在家里。沉默啊,沉默啊,也许,会永远沉默下去,直到时间的深处。在那里,一切都化为乌有,并获得最后的公平”。这段话可以说是阎真在小说结尾对柳依依命运悲剧的一个反思和总结,同时也是他个人主观色彩的体现, 他将这悲剧归结为女性一生无法逃避的宿命:生为女人,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这种悲剧与生俱来,无法避免。柳依依身处恋爱或婚姻中时尽力说服自己屈从于“女人”的客体位置,这也是导致其自身命运悲剧的一个方面。阎真以柳依依爱情理想梦的破灭来揭示女性的生存处境,看似为女性的弱势地位抱不平,但实则传达的是对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的无条件认同和潜在的大男子主义。阎真的女性书写看似是在为女性代言,在女性的立场上鸣不平,但从小说最后的结尾部分,还是可以看出阎真作为男性在看待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和悲剧时所夹带的男性化色彩的,阎真笔下的女性有着自己想象中女性的幻影。
4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阎真的两部小说《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我们无可否认其具有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阎真凭借其敏锐的现实洞察力和纯熟的小说技巧,以女性书写的笔法明暗结合地揭示了现下女性在欲望化社会所面临的家庭困境、情感困境和事业困境,她们在困境中没有找到出路,爱情和亲情也不是她们最终的归宿。但是阎真在小说的女性书写背后,还是暗含不可忽略的男性化色彩的,男性主导地位的体现以及女性宿命悲剧的存在,都体现出阎真作为男性作家在书写女性生命体验和性格特征时所附带的男性化色彩,这是我们在阅读、分析这两部作品时所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