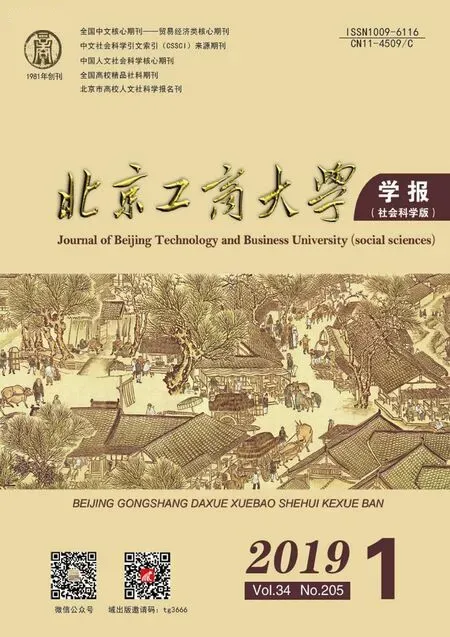并购重组中内幕交易为何如此频繁?
——基于社会关系视角的经验研究
曹 宁, 李善民
(1.香港中文大学 法律学院, 香港 999077; 2.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资本市场中的内幕交易,尤其是并购重组期间的内幕交易情况非常严重。岳宝宏、王化成[1]指出,大部分超额收益发生在首次公告之前,上市公司被并购事件的内幕交易效应超过50%。朱宝宪[2]通过对比不同市场的数据,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的内幕交易行为比成熟市场要严重许多,尤其在并购事件中。为何并购重组中的内幕交易会如此严重?传统的研究多是从公司治理角度进行分析,而较少有从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角度进行的研究。
国外关于内幕交易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合法取得内幕信息的内部人自身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发达国家的法律严格禁止公司高管和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以及利用内幕信息交易获利,因此国外学者很少研究公司高管通过社会关系非法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即较少研究高管的社会背景、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内幕交易的影响。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关系在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社会关系对个体及组织的经济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内幕信息泄露引起的非法交易行为非常严重。内幕信息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公司高管有动机将其泄露给他人,以巩固自己的社会关系,增强自己的社会资本。因社会关系引致的内幕信息泄露及由此产生的非法交易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严重损害已是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但是缺少较为严谨的经验研究来证明。本文拟从上市公司高管的社会关系入手,基于上市公司高管的个体性质进行研究。高管的社会关系类型代表了不同的内幕信息泄露渠道,不同渠道泄露内幕信息获得的潜在收益、泄露行为被发现的难易程度都是不同的,所以对内幕信息泄露严重程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上市公司高管与监管机构的关系可能会使得上市公司内部人拥有更强的遵纪守法意识,从而降低内幕信息泄露的程度。本文从这些关系入手,研究其影响内幕信息泄露程度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综述
1.内幕交易及其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对于内幕交易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丰富。经济学、财务学领域的学者对于哪种类型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生内幕交易行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Shleifer & Vishny[3]以及Denis & McConnell[4]等研究认为,公司治理是影响上市公司内幕交易的关键性因素。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公司代理问题较弱,外部股东利益可以得到有效保护。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内部人获利的机会更多,更有机会进行内幕交易。Laporta et al.[5]研究指出股权集中度越高,越有可能导致内幕交易的发生。大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获得信息优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幕交易。Noe[6]通过建立理论模型研究了薪酬机制与内幕交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内幕交易可以看作薪酬激励的替代品,会对经理人产生激励作用。在该情形下,如果公司股东默许经理人进行内幕交易,股东也会采取低一些的薪酬水平。Cruces & Kawamura[7]利用ITP指标对拉丁美洲各国资本市场进行研究,发现流动性越强的公司发生内幕交易的概率越小;与此同时,在投资者保护制度比较好、公司治理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内幕交易发生的概率较小。Anand & Beny[8]对加拿大的资本市场进行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地位越强、公司规模越大的公司越容易发生内幕交易,并且内幕交易监管的有效性会降低。Cziraki & Xu[9]研究了股权制衡度和内幕交易之间的关系,发现股权制衡度越高,内幕交易发生的概率越低。唐齐鸣、张云[10]研究指出,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和内幕交易严重程度之间具有显著的关系。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基于公司股票的内幕交易越少。姜华东、乔晓楠[11]研究了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内幕交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内幕交易严重程度和股权集中度呈倒“U”型。凌玲、方军雄[12]研究也发现,公司治理因素是影响内幕交易的重要因素;董事会的独立性越强、规模越大,内幕交易发生概率反而越大。何贤杰等[13]研究了独立董事制度对于内幕交易的影响,发现在中国本应该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独立董事却与内幕交易的产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除了公司治理方面的因素,国内外学者还从信息披露、企业类型及特征、机构投资者持股等方面对内幕交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Fidrmuc et al.[14]对比分析了美国和英国的信息披露制度,发现英国对于内幕信息披露要求更加严格,要求披露的时间也更短,所以英国的内幕交易发生概率比美国要低。Jayaraman[15]指出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越低,内幕交易的发生概率越大,好的信息披露制度是遏制内幕交易发生最有效的方式。张丹等[16]对因为信息披露违规而被处理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ST公司的内幕交易严重程度显著高于非ST公司。李捷瑜、王美今[17]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之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薪酬激励以及两职分离可以减少内幕交易的发生。岳宝宏、孙健[18]对2001—2009年中国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控制权转移支付方式、公司规模大小、盈利能力以及公司治理水平等都会影响内幕人的收益。沈冰等[19]对2009年进行重组、高转送、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公司的治理结构、信息不对称性以及法律环境是影响内幕交易的主要因素。
2.社会资本对内幕交易的影响
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等在定义社会资本的过程中注重社会系统的整体层面,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或团体所拥有的社会连带的加总,要想获得社会资本,需要靠这些社会连带的建立与维持[20]。社会资本真正在经济学、管理学中的应用要追溯到Nahapiet & Ghoshal[21],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由人际连带网络发展出来的,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而为个体带来资源。Lin[22]指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网络中所达到的资源,每个个体的社会资本都是通过社会连带而得到的。且在社会资本理论中,一般用社会连带的概念来代替社会关系。
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并且社会关系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关键因素。而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呈现出的社会关系形态也不一样。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更注重社会关系的国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23]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根据关系亲疏远近的不同而形成一层又一层由内而外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层次的关系适用于不同的互动规则。后来,黄光国又对费孝通的思想进行了延伸,指出中国人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网络主要有三层,分别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以及混合了前两者的混合型关系[24]。这三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大致可以对应于家人、熟人以及生人,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规范,分别是需求法则、人情法则和公平法则。罗家德[25]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家人之间的互动是基于保证关系与情感关系,熟人之间是基于社会交换与情感关系,而生人之间是基于信任关系,而这种信任关系是带有互相为利的成分的。中国人的人脉就是一个由信任延伸开的网络。透过这样一圈又一圈的信任关系,个体可以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
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关于关系对经济行为影响的研究也是比较多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研究一个团队(比如企业)的社会关系对团队(企业)的经营、发展、创新能力、社会资本等的影响。第二类是研究个体的社会关系对于职业发展、创新能力以及其他方面的成就的影响。如Florin et al.[26]探讨了企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企业上市的影响。边燕杰、丘海雄[27]研究发现,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关系会对产值有显著影响。李善民等[28]研究了社会网络带来的信息优势与企业并购行为之间的关系。
而关于社会关系对内幕交易的研究,虽然学术界和实务界一直都认为非常显著,但是具体的研究却很少。为何中国市场中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如此频繁?这与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关系。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网络主要有三层,分别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以及混合了前两者的混合型关系。在本文中,主要关注熟人层面的内幕信息泄露行为。合法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如上市公司高管)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将内幕信息传播出去,根据人情法则,他可以在未来获得好处。泄露内幕信息可以看作是公司高管基于自身信息优势的一种投资行为。在以往的内幕交易研究中,较少考察这部分因素,所以本文创新性地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切入,对内幕信息泄露行为进行研究。
(二)研究假设
在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高管在证券交易中需要遵循的规则,重要信息的敏感时期内,公司高管进行的股票交易是被严格控制的,而且每一笔交易都会被实时监控,公司高管等内部人自身进行内幕交易的机会就变得非常少。虽然上市公司高管自身不能进行证券交易,但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获利。一种有效的方式便是基于自身的信息优势对社会关系进行投资,最直接的投资方式便是将内幕信息泄露给其他个体,内幕信息被第二层、第三层以及更多层的交易者获取并被用来进行证券交易获利。当内幕信息获取者获利之后,按照中国社会礼尚往来以及人情不可欠的人情法则,他们会在未来给泄露人一定好处,比如其他有价值的信息、更好的发展机会等等。这些对于公司内部人来说就是对社会关系的投资带来的收益。这些收益因为较为隐蔽,很难准确度量,但确实是有价值的资产,会给内幕信息泄露人带来个人财富的增长或社会地位的提高。相比于公司内部人自身进行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更难以监控和调查,所以泄露行为频繁发生。
对于上市公司高管的社会关系,本文参考史欣向[29]从社会资本视角对IPO定价效率的研究,从五个角度进行衡量,这五个角度都和高管的任职经历有关系,分别是政府任职经历、金融机构任职经历、兼任情况、工作经验以及监管机构任职经历。当公司高管的社会关系更丰富时,他便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进行社会关系投资(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并且投资回报会更高(泄露行为带来的潜在收益更高)。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上市公司高管的社会关系越强,泄露内幕信息的动机就越强,基于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泄露行为就越严重。
在中国,由于所有制特征以及监管的特殊性,政府对经济的参与较多,政府公务人员也会参与到公司的许多决策中,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所以,在政府任职经历可以反映高管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在政府任过职的高管人脉更广,倾向于拥有更强的社会关系。由此得出第1个假设。
假设1:上市公司高管在政府的任职经历越丰富,社会关系越强,基于上市公司股票的内幕信息泄露行为越严重。
金融机构对于资本市场的参与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股价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所以,在金融机构任职经历也可以反映出高管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并且由于金融机构身份的特殊性,这种社会关系可能更会对内幕信息泄露产生显著的影响。当一个高管持有内幕信息,他将该信息泄露给以前在金融机构的同事,那么该同事可能会利用其在金融机构工作的便利进行更频繁、更大量的内幕交易。由此得出第2个假设。
假设2:上市公司高管在金融机构的任职经历越丰富,社会关系越强,基于上市公司股票的内幕信息泄露行为越严重。
兼任情况也是反映高管社会关系的一个维度。如果高管同时在其他公司任职,那么他平时能够接触的人会更多,人脉也会更广,社会关系也会更强。而这种社会关系也可能会对内幕信息泄露行为产生影响。由此得出第3个假设。
假设3:上市公司高管兼任情况越多,社会关系越强,基于上市公司股票的内幕信息泄露行为越严重。
第4个指标“工作经验”也是反映高管社会关系的一个指标。前3个指标主要是从高管在其他地方的任职经历进行考察,而这个指标则是单纯从高管的工作经验来进行考察。工作经验越丰富的高管,能够拓展的社会关系也就越多。而这种社会关系也可能会对内幕信息泄露行为产生影响。由此得出第4个假设。
假设4:上市公司高管工作经验越丰富,社会关系越强,基于上市公司股票的内幕信息泄露行为越严重。
还有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关系,即上市公司可能有曾经在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这样的监管机构工作过的人员。这些前任执法者对应的社会关系可能会和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产生不一样的影响。在国内,对这一类型的社会关系少有研究,本文将分析这些前任执法者的存在是否会遏制上市公司内幕信息泄露情况的发生。本文认为,在监管机构工作过的人员进入上市公司工作,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尤其可以提升公司内部法制思想的普及,使得上市公司的内部人员都具有更高的遵纪守法意识。所以不同于前4个角度的社会关系,“监管机构任职经历”可能会遏制上市公司内幕信息泄露的发生。由此得出第5个假设。
假设5:上市公司高管在监管机构的任职经历越丰富,内幕信息泄露程度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内幕信息涉及上市公司发展的各个方面。截至目前,证监会查处的内幕交易案例仍然较少,涉及的金额也都偏低,所以很难通过监管数据进行有效的大样本实证分析。在这些内幕交易中,关系到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事件的内幕信息是被使用最多的。并购重组一直是内幕交易重灾区。本文选取股权分置改革之后,2007—2016年实际发生了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在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事件公告之前内幕信息泄露程度的大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在样本选择过程中进行了一些筛选,筛选的原则是:(1)剔除了一年内重复发生控制权转移的样本;(2)剔除了连续两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公司;(3)剔除了在公告日之前停牌超过一个星期的样本;(4)剔除了控制权转移未成功的样本;(5)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经过这样的筛选,一共得到218个观测值。
实证研究所需的数据来源于两个途径。股价及财务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高管关系数据则基于手工收集及整理。作者收集了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的全体高管简历,对每一份简历进行检阅,判断出其在政府、金融机构、证券监管机构(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交易所)的任职经历以及兼任情况,记录下来后再加以整理,形成研究所需的数据。
(二) 变量的选择
正如前文所述,社会关系是较难度量的,只能就一些可获得的数据中从侧面进行分析。本文将分别从三个层面来对上市公司高管社会关系的影响进行研究,分别是董事长总经理层面、董事会层面、全体高管层面。
自变量的选择如表1。第一个指标“政府关系”是考察高管在政府的任职情况。对于每个高管来说,如果曾经在政府任职过,那么则用1来表示,如果没有在政府任职过,则用0来表示。第二个指标“金融机构关系”是考察高管在金融机构的任职情况。对于每个高管来说,如果曾经在金融机构任职过,那么用1来表示,如果没有在金融机构任职过,则用0来表示。第三个指标“兼任关系”指的是当前高管在其他公司的兼任情况。对于每个高管来说,如果在样本期内也有在其他公司兼任,那么则标记为1,如果没有兼任,则记作0。第四个指标“工作经验”也是反映高管社会关系的一个指标。在本文中,选取“高管年龄”作为工作经验的代理变量。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人脉也越广,社会关系也就越强。对于第五个指标“监管机构任职经历”,本文考察上市公司高管在一会两所等监管机构工作过的情况。对于每个高管来说,如果在样本期内也有在其他公司兼任,那么则标记为1,如果没有兼任,则记作0。其中,政府关系、金融机构关系、兼任关系、工作经验都是选取的控制权转移事件前一年的数据,监管机构任职经历选取的是控制权转移事件前三年的数据。之所以该数据选取的时间跨度较长是因为公司治理水平的变化、法制思想的普及以及提升都是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体现出来的,只考虑前一年内在上市公司工作的前任执法者不够全面。
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可能会对内幕信息泄露的严重程度产生影响,在本文中,将这些因素设置为控制变量。本文选取“公司业绩”“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金融机构持股”“独立董事占比”和“高管薪酬”等7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表1 变量定义表
(三)模型设计
1.内幕信息泄露行为严重程度的测算
国内外对于内幕交易的识别主要有两种方法,分别是PIN值模型(知情交易概率模型)、基于事件研究法的CAR值模型。其中,前者更多应用于非基于具体事件的研究。Aktas et al.[30]对于并购事件进行研究并指出,利用PIN值来衡量并购事件发生前后内幕交易的严重程度不够严谨。至少当对应的事件是并购事件时,PIN值模型的可信度存在问题。于是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选取一个事件窗口期(t0,1)。公告效应是控制权转移公告当天到披露后一天的累积超额收益率CAR(0,1)。则公告效应是:
(1)
在本文中,选取与公告效应对应的指标来衡量内幕信息泄露行为的严重程度,并且命名为runup。其计算公式为:
(2)
该指标反映了对控制权转移事件引起的市场反应有多少在公告前就已经表现出来了。runup越高,说明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性越高,内幕信息提前泄露情况越明显,内幕信息泄露程度越深。runup越低,说明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性越低,内幕信息提前泄露情况越少,内幕信息泄露程度越低。
对于runup的计算,本文采用市场模型(market model),并且选取市场调整模型(market-adjusted return model)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市场模型是指,在清洁期内证券收益率和市场收益率满足:
Rit=αi+βiRmt+εit
(3)
而市场调整模型是将市场收益率作为个股的正常收益率,即在市场模型中令:
αi=0,βi=1
(4)
在市场模型不适用的情况下,市场调整模型是较好的替代。
2.回归模型设定
本文建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runupi=β0+β1governi+β2financei+
β3concurreni+β4experiencei+β5regulator+
β6roei+β7sizei+β8shrcr1i+β9shrzi+
β10rundratioi+β11outsideri+β12salaryi+ε
i=1,…,n
(5)
其中,runup是衡量内幕信息泄露程度的指标。本文分别从董事长和总经理、董事会、全体高管三个层面进行研究。每个层面都会考察该层面高管人员的社会关系的程度。特别地,对于“监管机构任职经历”,因为本文主要想考察其对于遏制内幕信息泄露的影响,并且认为监管机构的任职经历会影响到整个上市公司内部的遵纪守法意识,故该指标不根据讨论层面的不同而改变,均为根据全体高管信息而计算出的指标。
(四)描述性统计
回归涉及的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和表3(被解释变量的计算因为也涉及实证分析,所以放在了后一部分)。不同层面的研究样本,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也有较大差别。特别的,“高管薪酬”变量也分别根据研究层面的不同而变化,分别为董事长和总经理层面的薪酬、董事会层面的薪酬、全体高管层面的薪酬,单位为百万元。在实证结论展示过程中,每个层面的研究,薪酬均用salary来表示。

表2 社会关系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3 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研究
(一)并购重组中内幕信息泄露行为的严重程度
本文采用市场模型来对控制权转移事件公告前的内幕信息泄露程度进行定量衡量。分别令t0=-5,t0=-10,t0=-20,t0=-30,选择4个不同的事件窗口期对内幕信息泄露程度进行测算,分别记作runup1、runup2、runup3、runup4。runup的描述性统计在表4中呈现。

表4 内幕信息泄露程度的描述性统计
可以看出,窗口期(-5,1)、(-10,1)、(-20,1)、(-30,1)计算出的内幕信息泄露程度runup的均值都大于0,并且T检验表明这四个窗口期对应的runup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异于0。这表明,在控制权转移事件公告前,内幕信息泄露是显著存在的,并且程度较深。从整个样本来看,在窗口期(-5,1)内,内幕信息泄露造成的市场反应占了事件整体市场反应的67.14%;在窗口期(-10,1)内,内幕信息泄露造成的市场反应占了事件整体市场反应的75.88%;在窗口期(-20,1)内,内幕信息泄露造成的市场反应占了事件整体市场反应的79.48%;在窗口期(-30,1)内,内幕信息泄露造成的市场反应占了事件整体市场反应的88.69%。由此可以发现,随着窗口期选择范围的扩大,runup均值也在升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资本市场内幕信息泄露的时间较早,以至于当考察的时间区间越宽时,测量出的内幕信息泄露的程度越高。当把区间扩大至(-30, 1)时,内幕信息泄露所引起的市场反应已经非常接近于事件引起的整体市场反应。
(二)高管社会关系对内幕信息泄露程度的影响
本文首先从董事长总经理层面研究高管社会关系对内幕信息泄露程度的影响。表5中前4列分别使用runup1、runup2、runup3、runup4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采用稳健回归。结果显示,董事长总经理层面的研究,只有政府任职经历对内幕信息泄露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假设1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变量regulator在两个回归中都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第4个回归中接近显著。这说明,上市公司拥有在监管机构工作过的高管越多,内幕信息泄露程度越低。假设5得到了验证。
表5中5~8列对董事会层面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采用稳健回归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董事会层面的研究,政府任职经历以及金融机构任职经历对内幕信息泄露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对于4种窗口期的选择,政府任职经历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金融机构任职经历分别在3个回归中具有显著性,在另外一个回归中接近显著。另一方面,和董事长总经理层面的研究类似,变量regulator在表5的4个回归中都具有显著性,其中在两个回归中在1%的水平上显著。整体而言,对于董事会层面的研究,假设1、假设2、假设5得到了验证,假设3和假设4没有通过检验。
全体高管层面的回归结果和董事会层面的回归结果比较接近,政府任职经历以及金融机构任职经历对内幕信息泄露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对于4种窗口期的选择,政府任职经历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金融机构任职经历在3个回归中具有显著性,另1个接近显著。变量regulator在表5的4个回归中都显著为负。整体而言,全体高管层面的研究,假设1、假设2、假设5得到了验证,假设3和假设4没有通过检验。
综合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全体高管3个层面的研究可以发现,社会关系的几个维度中,在政府任职经历以及金融机构任职经历对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泄露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和假设不同的是,兼任情况和工作经验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兼任往往发生在关联企业之间,而关联企业本身联系就非常紧密,信息交流也频繁,内部兼任对于关系的影响就非常小了,所以导致兼任这一变量并不显著。工作经验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年龄作为工作经验的代理变量并不非常合适。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拥有在监管机构工作过的高管,降低了内幕信息泄露的程度。这表明证券监管机构执法者进入业界工作有利于证券市场秩序的提升,有利于上市公司内部人遵纪守法意识的提升。
(三)其他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
从表5的回归结果来看,控制变量中具有显著性的其他因素主要是公司规模变量以及独立董事占比变量。

表5 高管社会关系对内幕信息泄露影响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T统计量;*、**、***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均保留小数点后三位有效数字。
公司规模变量在大部分模型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现为显著为正。虽然规模越大的上市公司越容易成为市场焦点,受到的监管也倾向于越多,但这并没有降低内幕信息泄露的发生。这暗示,规模越大的公司,能够接触到内幕信息的人就更多,内幕信息泄露的途径也就更多,这些都可能导致内幕信息泄露行为更加频繁。
独立董事占比变量也在大部分模型中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现为显著为正。一般认为,独立董事占比越高,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效率也越高,公司治理水平越高。但是在中国,独立董事模式的发展并不是非常良性。那些和董事长、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管关系比较密切的人更容易获得独立董事的位置,因此在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中,独立董事也就很难起到积极有效的监管作用。在本文中也证实了,独立董事对于从公司治理角度遏制内幕信息泄露行为并未起到良好的作用,反而起到了反向作用。独立董事所占比重越高,内幕信息泄露的程度也越高。
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高管薪酬、金融机构持股等控制变量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因素并没有对内幕信息泄露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不支持国内已有的一些实证研究结果。尤其是金融机构持股指标,虽然相对于普通证券交易者,金融机构属于信息优势的一方,
也是内幕交易的重要参与者,但这并没有通过金融机构的持股行为反映出来。反观解释变量中的“金融机构关系”则是显著的。这说明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主要是通过和上市公司内部人的社会关系而获得的,而非单纯通过资本投资获得的。
(四) 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利用事件研究法计算内幕信息泄露程度的过程中使用市场调整模型替代市场模型,回归结果见表6。

表6 高管社会关系对内幕信息泄露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T统计量;*、**、***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均保留小数点后三位有效数字。
虽然和表5的结果并非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对前面的实证结论持肯定意见。 “政府任职经历”、“金融机构任职经历”都是显著的,即在政府任职经历以及金融机构任职经历对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泄露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监管机构任职经历指标,也在大部分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以下结论依然是成立的,即上市公司拥有在监管机构工作过的高管越多,越能降低了内幕信息泄露的程度。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较少有从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的角度对内幕交易进行的实证研究。本文从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切入,认为内幕信息是一种有价值的资产,知情人可以通过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来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这对于知情人来说,是一种有价值的投资。尤其是当内部人自身证券交易被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将内幕信息泄露给和自己有社会关系的人便是很好的投资方式。而社会关系越强,泄露内幕信息的机会和渠道也就越多。
本文从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全体高管3个层面对社会关系和内幕信息泄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根据本文的研究,上市公司高管的社会关系会对内幕信息泄露程度产生影响,高管和政府的社会关系以及高管和金融机构的社会关系均是泄露的途径。董事会层面和全体高管层面的研究均验证了,上市公司高管在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的任职经历越丰富,内幕信息泄露行为就越严重。另一方面,在监管机构工作过的人员进入到上市公司工作可以降低内幕信息泄露的程度,即高管和监管机构的社会关系对于内幕信息泄露起到遏制作用。
近年以来,监管部门在打击市场违规、内幕交易行为方面,力度逐年加大。然而,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规行为依然不断出现,这反映了当前内幕交易违规惩处制度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监管机构应做出更多努力,以更好地维护股市的稳定、繁荣,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中国资本市场中的内幕信息泄露行为非常普遍,监管机构应加大执法力度。不仅要重点关注内幕信息知情人自身的证券交易行为,还应当仔细排查知情人是否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了其他个体。对于后者,监管机构应加大惩罚力度,以示警诫。第二,在执法过程中,应重点排查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社会关系。其中,知情人在职业生涯中拓展的社会关系应当作为重点关注对象。第三,实证表明,有执法经验的人员进入上市公司工作,对于遏制内幕信息泄露具有正面效果。应当发挥在监管机构工作过的又进入上市公司工作的高管的作用,推动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