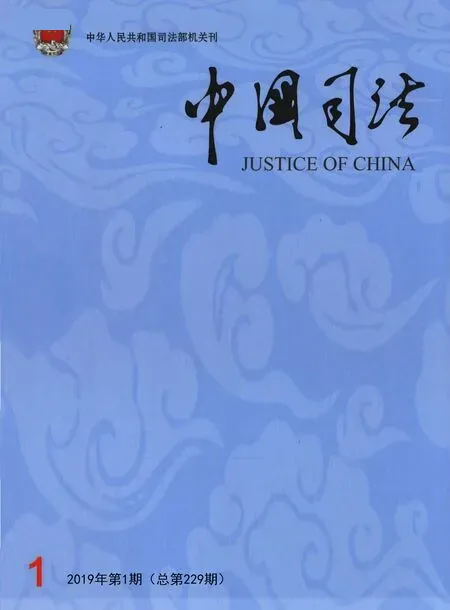关于我国假释制度的几点思考
崔星璐 吴占英(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
我国有关假释制度的规定散见于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监狱法》之中。研读我国相关法律之中有关假释制度的一些规定,我们发现其中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和斟酌。现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关于假释适用条件规定的思考
我国《刑法》第81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第二款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第三款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笔者认为,上述第一款规定中的“可以假释”值得商榷。众所周知,“可以”一词在法律中的涵义为:也可以,也不可以。就符合假释条件的犯罪分子而言,即使其符合法律规定的“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条件(排除有第二款情形且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无实质性负面影响),也不一定获得假释。这条规定值得进一步研究。一个在押犯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那么,对其继续羁押就纯属多余,这既会造成刑罚过剩,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也不符合假释制度设置的初衷。由于长期受羁押拘禁,罪犯一直过着单调的生活,适应社会正常生活的能力下降,而假释制度为在押罪犯设定了一个从监狱到正常社会的过渡阶段,假释的考验期便是使其适应正常社会的过渡期。试想:一个服刑者如果符合假释的实质条件却不能获得假释,这怎么能实现假释的初衷呢?所以,笔者认为,如果一个在押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那就应当被假释,故而,法条规定的“可以假释”也就应当修改为“应当假释”。修改为“应当假释”无疑是落实我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精神的质的飞跃。当然,把“可以假释”修改为“应当假释”,并不意味着对罪犯可以滥施假释,司法机关对于假释的适用一定要严格条件,绝不能把不符合假释条件者予以假释。
谈及假释的适用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只是该条对假释适用条件是与减刑的适用条件混杂在一起的。这种混杂的规定难免带来一些问题,一是它给人一种印象:假释的适用对象为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但事实上假释的适用对象并不包括被判处管制、拘役的罪犯;二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是假释适用的实质要件,而事实上在执行期间确有立功表现并不是立法规定的假释适用的实质要件。形成这种印象的原因是立法技术造成的。为避免这种现象,建议对此进行如下修改:“对于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罪犯的减刑、假释,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在假释的适用条件方面,我国《刑法》第81条第二款对假释的适用对象进行了限制:“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我们认为,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其人身危险性比较大,在假释的适用上对其予以严格限制,立法的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上述对象采取一律不得假释的做法则过于绝对。对罪犯适用假释是有效激励罪犯积极改造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对上述对象采取一律不得假释的做法则不利于罪犯积极改造。笔者认为,对上述对象也应当给予假释的机会,但鉴于其人身危险性较大,应当对其执行刑期的长度予以适当延长,这便于考察其是否达到了假释的实质要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可谓利于实现刑罚报应与预防之功能。同时,基于对其人身危险性较大的慎重考虑,对符合假释实质要件的上述对象的假释考验期也要适当延长。这样做一方面也可以体现刑罚对他们的报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考察他们是否满足了假释所要求的“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根本要求。
二、关于假释程序立法方面的思考
对假释的程序,我国《刑法》第82条进行了简单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程序进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假释。”笔者认为,对于假释的程序问题在实体法中规定显得不尽合理。程序问题应当由程序法解决。即对于假释的程序方面的问题应当统一在程序法——《刑事诉讼法》中进行规定。况且,即使从实然的视角看,《刑法》第82条的规定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按照《刑法》第82条的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程序进行”,而第79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据此,假释的程序应当是:对于犯罪分子的假释,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假释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事实的,裁定予以假释。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假释。“对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事实的,裁定予以假释”这句话的理解,应当是:只要罪犯有“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事实”,就必须裁定予以假释,因为“对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事实的,裁定予以假释”这句话中,“裁定予以假释”用语之前并没有“可以”一词。没有“可以”一词,那就应当将“对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事实的,裁定予以假释”这句话理解为只要罪犯有“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事实”,就必须裁定予以假释。但是,前文已述,我国《刑法》第81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易言之,我国《刑法》第81条第一款规定说的是罪犯“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而第82条有关假释程序的规定中说“对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事实的”,“应当”予以假释。这在逻辑上显然出现了矛盾。前文已述,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在押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那就应当被假释,故而,《刑法》第81条规定的“可以假释”应当修改为“应当假释”。
在假释的程序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笔者认为,执行机关将假释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是正确的,因为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有权对执行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所以有权就假释建议方面的问题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问题是,人民检察院就假释建议方面的问题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后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何种反应,立法并没有规定。我们认为,这样的立法规定显然是不周延的。如果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就假释建议方面的问题向其提出书面意见无动于衷,那么人民检察的监督作用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所以,应当对立法进行修改:人民检察院就假释建议方面的问题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后,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答复。
就假释裁定的时限问题,我国《监狱法》第32条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符合法律规定的假释条件的,由监狱根据考核结果向人民法院提出假释建议,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假释建议书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审核裁定;案情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一个月。假释裁定的副本应当抄送人民检察院。”笔者认为,《监狱法》就假释裁定的时限作出限定是合理的,这样可以防止人民法院对罪犯的假释裁定久拖不决。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就假释裁定的时限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立法的不协调必然给司法适用带来麻烦。立法存在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立法的修改加以解决。笔者认为,我国《监狱法》第32条就假释裁定的时限问题作出的规定是合理的,《刑事诉讼法》应当作出适时修改吸纳这一合理规定。
三、关于撤销假释规定的思考
关于假释的撤销及其处理,我国《刑法》第86分三款针对不同的情形做出了规定。第一款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第二款规定:“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第三款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
上述法律规定针对的是: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以及“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三种情形下应当撤销假释的问题。然而,立法疏漏了下列情形: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是否应当撤销假释?笔者认为,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即发现漏罪都要撤销假释,而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情形属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犯新罪的情形,这当然更应当撤销假释,并按照《刑法》第71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为此,笔者建议在立法中增加上述情形,增设内容可以表述为:“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关于假释的撤销及其处理,我国《监狱法》第33条也进行了规定:“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假释的建议,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撤销假释建议书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审核裁定。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假释的,由公安机关将罪犯送交监狱收监。”笔者认为,我国《监狱法》第33条仅对假释撤销及其处理的一种情形进行规定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对一个罪犯假释的撤销,总共涉及四种情形,即我国《刑法》第86条规定的三种情形以及应当增加的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情形。既然一个罪犯假释出狱后可能因为四种情形被撤销假释,那么,《监狱法》作为调整监狱与罪犯之间法律关系的法律,应当对这几种假释的撤销的情形均应当有所涉及,况且,这么做也可以使《监狱法》与《刑法》规定之间协调一致。
立法就假释撤销裁定的时限作出规定是应当的。由于因犯新罪、发现漏罪而撤销假释的时限涉及所犯新罪、发现的漏罪的审理时限问题,所以这类假释撤销的情形的裁定时限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对所犯新罪、发现的漏罪的审理时限为限。而对于因“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情形撤销假释的裁定时限,则应当专门作出规定,以防对此类案件的裁定过于迟延。应当说,我国《监狱法》第33条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根本未就此种类型假释撤销的程序及其裁定的时限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这是不应该的。《刑事诉讼法》作为一种程序性立法,理所当然应当就假释撤销的程序及其裁定的期限做出明确规定,否则就是不完备的,而不完备的立法自然会给司法机关的适用造成困难。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建议吸纳我国《监狱法》第33条规定的合理规定,对《刑事诉讼法》作出适当修改,就假释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情形撤销假释的程序及其裁定时限作出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