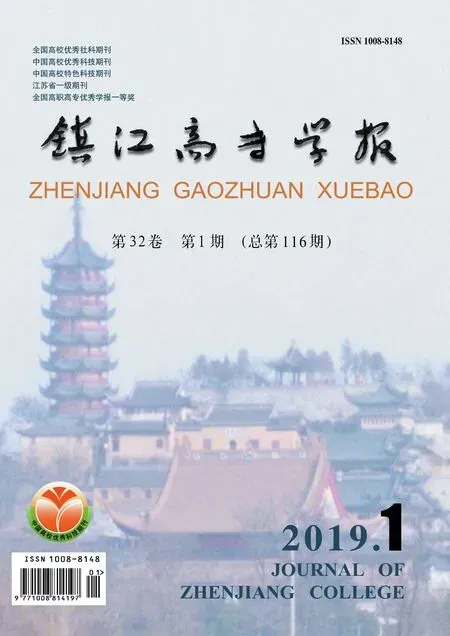“写得最精彩”不止于“亲眼目睹”
——《大地》灾荒书写的文学渊源和贡献
张正欣
(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江苏 镇江 212004)
彼德·康曾在《赛珍珠传》中指出,赛珍珠《大地》中对饥荒的描写是小说中“写得最精彩的部分”[1]141,传记中还数处明示赛珍珠一生中多次“亲眼目睹”灾荒[1]45,142,151,这种经历对于作家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对于《大地》中的灾荒书写,目前研究成果有所涉及,但专门及系统的考察,似未多见。研究赛珍珠灾荒书写的文学渊源,探索赛珍珠承继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可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关于赛珍珠的学术研究。
1 灾荒书写·“亲眼目睹”
在小说开篇,主人公对丰收有着美好的展望,“大地就要结果实了”[2] 3。但随后的灾荒画面令人印象深刻,是全书“写得最精彩的部分”。这里的灾荒书写是核心情节,也是故事的高潮。小说这样处理比较冒险,但写得好却具有独特效果。这场旱灾对于主人公及全家而言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大转折。
“他现在买的这块地看起来根本算不得什么”[2]45,此谓干旱前娶妻生子、种地买地的预见性。“他的孩子快要饿死了,吃的是地里的泥土。他们来到这里,趁他危急的时候要夺去他的土地。”[2]68这里是说干旱时杀牲卖地的背井离乡。“他紧紧抱着那些还有别人身上余温的金子,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明天,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2]110这里写的是逃荒乞讨的日子即将过去,动乱中意外发财终于回乡。由贫穷经勤劳而稍有结余、又旱灾逃荒骤富后回乡,情节跌宕起伏。
灼热日光下的干旱饥荒,是小说最精彩的描写;有预兆、来势猛且时间长的水灾,同样是引人瞩目的书写。“为修复堤岸筹集资金”,“人们把募捐到的钱都交托给刚上任的县官” ,“县官因为没能实践修复堤岸的诺言”,“当他看到自己会被人打死时,便跑了出来,跳河自尽了”[2]217,这里揭示的是吏治腐败的社会政治背景。因意外之财一夜成暴发户的王龙被诱惑而堕落,“他和他的爱妾吃着,喝着,尽情地享受着,他感到满足了”[2]159。结果,惩罚似的蝗灾连着长时间的水灾,造成庄稼房屋田地被破坏,生活生产许久不能恢复。这也正应了西方哲学所言:“无食裹腹、无衣蔽体是真正的灾难,而财富则是相对的灾难。”[3]61灾荒也是主人公王龙由爱土地勤劳作的“好”向嫌发妻宠小妾的“坏”的人生节点的大转折。
小说中除了描写旱灾、饥荒、蝗灾和洪水的自然灾害,还描写了无以防备的社会兵匪之患。暴富后的王龙更有脾气个性,但对好吃懒做且有歹心的叔叔一忍再让,小说告诉我们答案。“他叔叔解开上衣,让他看了看上衣衬里上的东西”,“王龙直僵僵地站住了”,“他颤抖着,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2]183。原来,他叔叔是匪盗红毛集团的二当家。联系小说前面描写的县长名为治水实敛财的情节,小说在这里将灾荒的社会背景引向更为广阔的朽腐政治背景和复杂危险人际关系方面,王龙性格的丰富性得到进一步展示且更有说服力,因为“一个拦路强盗挥舞着手枪从树丛中跳出,索要我的金钱,我只能被迫交出。但是,他的强力并不证明他的行为是公正的,我的软弱也不会使我的勉强付出受到责备”[4]567。
赛珍珠人生经历中多次“亲眼目睹”各种灾荒,作家自幼具有的用心观察对其精彩的灾荒描写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大地》中,筋疲力尽的王龙无力赶走那只饥肠辘辘把阿兰刚生下来的女婴尸体吃掉的狗,“这样的事赛珍珠小时候曾经亲眼目睹过”[1]142。童年时候的赛珍珠常在坟茔中看到死去孩童的尸骨被狗刨出地面,赛珍珠就会掘坑再将这些尸骨埋葬。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斯波林在酝酿赛珍珠的传记时,即以“埋骨”写进书名(《埋骨:赛珍珠在中国》),可见此等情形的“亲眼目睹”对于赛珍珠后来创作的重要影响。
在1905年,家庭教师孔先生过世一年多后,赛珍珠焦虑激增,因为她“亲眼目睹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带来的灾难”。她与母亲亲历了令人难忘的救助江北难民的活动。“赛珍珠一辈子都会记着大群大群饥民在风雨中的呻吟”[1]45-6。她像风雨中看苦难流民的李尔王一样要呼喊:“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都应让安享荣华的人们“睁开眼睛来,替这些不幸的人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5]233-234
“1931年的洪水算得上20世纪最具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之一”,“赛珍珠亲眼目睹了这场大水及其受害者,通过观察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小说,把抽象的数据转换成便于想象的个人悲剧。这些小说主题简单:中国农民原本就过着朝不保夕的艰难生活,洪水更使他们一贫如洗、苦不堪言”[1]151。
赛珍珠的这些小说与30年代中国作家们对乡村灾难的书写(丁玲的《水》、匡庐的《水灾》、欧阳山的《崩决》等)结合起来,有力印证了灾荒形成的原因,即:“虽然饥荒总是包含着饥饿的严重蔓延,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影响到遭受饥荒国家中的所有阶层”[6]58。
赛珍珠将多次的亲眼目睹和仔细观察、每一次的“新的痛苦和极度的怜悯”[7]140带入《大地》等作品的创作中:既描写了中国农民在灾荒岁月里的受苦受难和苦苦抗争,又展示了中国北方农村真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风俗;既印刻了作家在中国成长生活岁月里对农民的同情怜悯和难忘记忆,更昭示出作家思想灵魂深处的面对艰难时世人类须具有的共命运信念。
2 圣经文体·文学渊源
对圣经稍有阅读的读者在阅读《大地》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二者语言叙述及文体风格有极其相似的感觉。同样,也会对《大地》中满目灾荒的书写中呈现出的穷人之苦难,给予人道主义的同情,对权富之贪欲给予谴责。这正是可考《大地》的文学渊源的两个视点,即风格与思想。
《大地》体现出庄重朴素的叙述风格,正与《圣经》文体风格吻合。彼德·康指出小说受美国读者欢迎的原因:“小说用正式文体叙述,风格和《圣经》近似,为故事赋予了一层庄严的色彩。许多读者对书的风格极为推崇,说它有助于升华故事情节,使之产生广泛意义。”[1]149
试以《大地》和圣经两个文本的数例语句作一比较:
1) “我们从土地上来的……我们还必须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们守得住土地,你们就能活下去……谁也不能把你们的土地抢走。”[2]287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8]86
2) 断粮的日子终于到了,既无剩米也无剩面,只有一点点豆子和一点少得可怜的玉米,牛也饿得低下了头。这时老人说:“接下来我们要吃这牛了。”[2]57
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籴些粮来。”[8] 110
3) 天空昏暗起来,空中到处都是蝗虫翅膀互相摩擦产生的低沉的嗡嗡声。蝗虫扑向地面,飞过一块地落到了另一块地里,头一块地的庄稼一动未动,后一块地却被蝗虫吃得像冬天的荒野一样186[2]。
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的一切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156[8]。
上述每组单数例句子来自《大地》,双数例句子来自《圣经》。这数例仅是两书中无数类似个例的大致所示,而二者的全篇叙述风格大体如斯。因此,我们可以明了熟悉《圣经》的读者为何感到亲切以至推崇《大地》的原因了。
《大地》有《圣经》的庄严之风:文体正式端庄、叙述平稳从容、语词朴素简练。《大地》之所以让我们产生既熟悉又陌生之感(熟悉的是表层看到的故事情节类的题材,陌生的是其中蕴藏着的作家对于题材处理的态度倾向),就是因为小说再现了自古而今决定人类延续最必须的“民以食为天”的基本生存问题(庄稼食物、土地水源),表达了作家和读者对这一问题具有共识的正义(契约)、慈善(同情)和人道(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情感和信念。由此可见,《大地》庄严精炼朴素的语言叙事风格的外表下,其深层表达的是基督教和人道主义一些广为我们这个星球各种世俗社会的文化所推崇的共同价值观。
譬如:对土地的热爱眷念、执着守护的不变情结;对劳动的肯定赞美、光荣自豪的价值观念;视生活俭朴为品行美德的操守根本;正视生活苦难的坚忍的意志力。美国文学同时代的一系列作品(如《飘》《烟草之路》《愤怒的葡萄》等)反映的也是相同的题材,这也是美国文学的一贯主题及风格。
再如对于贫穷和财富、善恶有报等故事情节的处理倾向:即使在外乞讨以求活命,王龙也不忘不偷不盗是道德底线,对拿了肉回来要下锅煮着吃的小儿子竟狠心大打出手;但自己“一旦发大财”,便嫌贫爱富、厌妻纳妾,“在道义上就迷失了方向”[7]149。
文艺复兴以来,直至19世纪,进步的作家们以人性论、人道主义思想反映了与《圣经》基督教相类似的价值观。如关于行善和平等:“我所要做的事,不能只是让一千个人有吃有穿,像是喂养和赶着一千头羊那样,而是要对这些人行善。这一千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和我一样,也有同样的过去,同样的欲望、诱惑、谬误,同样的思想,同样的问题,是同样的人。”[9]599关于慈善和爱:“施舍吧!为了使你们能得到上帝的抚爱,/为了使恶人也称道你们,向你们致敬,/为了你们家庭的和睦与安宁。”[10]84关于富人和穷人、平等和人性:“富人在本能地呼喊:‘让咱们大吃大喝吧,反正我们将来总有一死。’穷人则本能地哀号:‘得等多久?主啊,得等多久?’”[11]20,“在你们中间的穷人,是我的托付,请照顾他们,勿仅致力于你自己的逸乐。如你遇着穷人,请勿轻视他。想一想,你从何而生,你们同出于苦恼之源。”[12]1316
赛珍珠创作方法的文学渊源可溯至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虽然很多学者包括赛珍珠自己,都认为受中国小说影响颇大,但笔者认为,作家受自幼就诵读多遍的狄更斯作品影响更大。因为,创作题材的来源和取舍、主人公形象的确定和描写、小说叙事的基本结构和脉络线索、人物形象的烘托刻画塑造(例如心理描写),及上述基督教道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资源,都不是传统中国小说所能提供的。狄更斯的巨大影响让赛珍珠始终感到有欠导师一笔债之感。她感谢狄更斯把洞察现实生活的激情、人间万物的欢乐给了自己,让其“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和蔼可亲的英国人的上帝,一个类似父亲的上帝,一个性情纯朴的穷苦人乐于求助的上帝”[13]。“狄更斯小说世界里的人物已经成为她生活里的一部分”,“那几乎就是她的整个生活”[14]43。
赛珍珠的《大地》不仅继承了19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还展示了人道主义思想财富的积极价值,真实描写了社会底层农民生活的不幸遭遇。“我们人的脆弱而悲惨的处境的天然贫乏性,我们人的处境可怜到了极点。”[11]30《大地》揭示了灾荒带给人民的深重苦难,灾荒中甚至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现象,干旱饥荒中“村子里有人在吃人肉了”[2]63,“低等动物为了自己的生存,虐杀、捕食其他的同类,是无关紧要的。可是,人却是没有此必要的”[12]1316。
《大地》表达了作家对于受灾受难农民的真诚深切的同情。赛珍珠不止于在中国亲眼目睹灾荒,她在印度乃至美国也亲眼目睹许多受苦累受压迫的穷人,她悲伤心痛甚至曾上前阻止以强凌弱的欺压行为。人道主义精神植根于赛珍珠心灵深处,无论何种肤色、无论哪个民族、无论贫富与否,对于同类,赛珍珠执守平等信念和美善愿望。“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难存在”,“但至少要留下一线光明,至少留下一点希望的闪光,以促使人类中较高尚的部分,怀着希望,不停地奋斗,以减轻这种苦难”[12]1319。因为,“根据未来的最高精神来证明,/人道是我们永久的目标”[15]350。19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史的一个高峰;赛珍珠继承了欧美现实主义的传统,并在新世纪实现再攀登;现实主义的《大地》问世近百年,早已是并仍将是“现代经典作品”。
3 艺术形象·文学贡献
赛珍珠的《大地》为20世纪中国文学灾害书写填补了艺术形象和人物谱系的空白。
首先,学界对民国时期的灾害文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这无疑加深和丰富了我们对民国历史和文学的理解[17]30。成果取得共识的一点是:20世纪中国文学灾害书写的艺术形象尚显不足。作家阎连科曾表示,面对苦难的民众,“确实没有充满作家个人伤痛的深刻思考民族历史和更为疼痛的个人化的写作,没有写出过与这些20世纪苦难相匹配的作品来”[18]。赛珍珠的中国灾荒题材书写正好作出了有特别意义的增补。这种意义体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茅盾、沈从文为代表的中国作家笔下的乡土中国,分别呈现的是“解剖”“病态”社会的病人(阿Q等)、表现社会剧变中蚕农(老通宝等)的悲惨命运、寄希望于新一代觉醒出走、描写虽有“隐伏的悲痛”但仍是令人向往远离尘嚣的梦中边城——湘西沅水。赛珍珠展示的是传统乡土中国风俗风景,表现的是地道乡土中国原貌原态,希望的是新一代回归土地的感性理性,这些独特主题恰与中国作家的书写形成相应观照。
其次,《大地》围绕着灾荒题材的书写,为20世纪中国文学灾荒书写中的人物谱系作出了有价值的填补。20世纪中国社会经历历史重大巨变,但此时鲁迅时代开始的对国民对农民的本质性的书写停滞了,赛珍珠的中国农村农民灾荒题材的书写,恰是从另一角度对鲁迅式书写的继承和深化。闰土们的后代水生们在革命文学那里参加革命去了,而赛珍珠的书写中有像王源一样学成归来,在祖先的土地上用新知识来种好自己的庄稼(如伏尔泰的“老实人”)。艺术形象画廊里有王龙、阿兰、老秦、王龙父亲等勤劳、质朴、坚忍、勤俭、守土的中国传统正面农民群像,也有像黄姓地主、王龙叔叔、荷花等这样颓靡、潦倒、匪气、油滑的反面农民形象。这些群体系列的农民形象无疑增加了中外读者对现代中国乡村农民社会生活面貌乃至本质性的认知。
再次,《大地》灾荒书写中的艺术形象或人物谱系,可从文学人类学、文化学研究角度(如原型批评),上升至文学意象和寓意寓言的高度进行研究。如关于王龙和阿兰形象的评论和关于大地、土地、洪水意象的深入研究。
关于王龙这一人物形象,一般评论将其概括为具有勤劳本分传统美德,虽有蜕变但最终回归大地的传统正面农民形象,有研究者将王龙和古希腊神话中英雄安泰进行比较,认为两者有共同点,他们力量的有无与强弱、品性的好坏,都与大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关于阿兰形象,有研究者运用原型批评理论进行分析,将其比作原始时期人类的全能而神圣的大母神形象。阿兰兼备善恶两种属性:周身透着一种永恒的母性光辉(忠实能干、危急关头有主见),又凭借其足以压倒一切的破坏力(毫不犹豫的溺婴、仇恨多年前的对手并使其蒙羞)威慑着茫茫众生[19]。王龙与阿兰这两个形象展示了中国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原始的韧性生命意识。
有关土地、大地形象的描写,其艺术效果或已上升至意象乃至寓意寓言的高度。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将主人公与大地的关系写得如此浑然一体的;在中国现代作品中,很难发现有作品将土地对于农民的现实生产生活意义和农民的原始生命生存欲望,写得如此细节真实、心理丰富、朴实庄重的;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很少有从乡村农民题材本体出发,有如《大地》史诗般再现农民主体应有的社会身份、自信心理和人格尊严的。诚然,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似没有惊天伟业壮举,与灾荒的相缠困斗,似也没有传统文学描写的悲剧英雄本质的因素。但笔者认为,“凡诸水之泛滥,皆从山水来,山水之爆发,皆从霪雨来”,“仓促不能归海,则泛滥田间而为大害”[20]810,当农民面临干旱、洪水、蝗灾、匪患这些令人惊恐不安的灾难时,征服这些灾难就是壮举。朝出暮归、勤劳耕作的农民群体中,同样存在“两种属于悲剧英雄本质的因素”:一是“使他毁灭的不幸属于那种必须与之斗争的不幸”;二是“确实与使他毁灭的不幸进行了斗争”。“我们发现人们用一切自由力量抵制灾难,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与灾难斗争,同时又感到灾难的袭来是‘必然的’——正是人们用如此巨大的能量与灾难斗争,并且念念不忘这种斗争时,我们感到灾难是一种特殊的崇高的必然性。”[21]301在《大地》的灾荒书写中,具有平民意识的作家赛珍珠帮助我们进行了理性思维的拓展,这无疑是一份意外的收获。
综上所述,赛珍珠撰写的《大地》“是一部深刻的、得到了中国‘真相’的伟大作品”[22]188,赛珍珠以她不同于中国其他灾荒书写的作家创作的本位角度,丰富和拓展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乡土中国的表现领域,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作出了独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