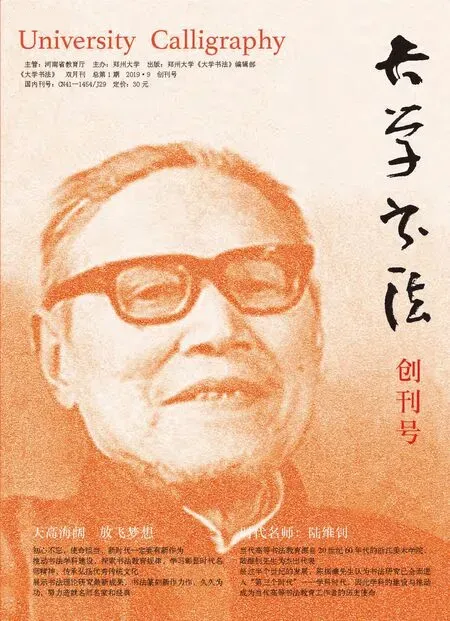沈曾植与民国章草复兴
——兼论民国章草“马鞍形”发展之成因
⊙ 王谦
梳理章草发展史,会明显看到章草发展的三次高峰。自秦汉之际萌芽、汉代成熟运用之后,元代、民国为章草的两大复兴期。如将这两次复兴的情况作一对比,会发现许多有意味的内容。如果说元代章草复兴在较大程度上是出于书体的怀旧与纯艺术追求的相互掺合,章草在民国初年受到重视,动因远不是如此纯粹,而与当时的文字改革也有一定关联。在民国初年的文人视野,书法各种书体中,章草被一些学者认作最简易的书体,因其字体结构远较今草、大草规范,加之历来相沿形成的字字独立的章法布局,于是将其视为汉字改革可以参照的理想字体,希冀借以改造楷书繁体字在现代文化及交际应用中的低效率。这种主要出于实用层面的努力,终究昙花一现。
在书法艺术领域,晚清学术通人、书家沈曾植以其晚年对章草的强势吸收,在达到一生书法高峰的同时,也以取法路径和经验对当时的章草复兴发挥着引领之功,沈氏也成为“民国章草复兴”的早期高峰。通常而言,一个时期某一书体的发展成就主要是通过最高成就和代表性书家群体来呈现的。在民国章草发展中,沈曾植除了先导、引领之功,其个人所成就高度同样非常重要。倘大略考察民国章草历程,可见沈曾植、王蘧常为前后两端高峰突起,而中间阶段较为平缓的主要趋势。研究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对当代及今后的书法研究与创作均有现实意义。
一、先导与垂范:在章草之内与章草之外
章草成为沈曾植晚年取法的主要来源之一,起码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学者型书家的潜意识里,或许章草并非仅是一种书体,同时还表达着一种趋于高古的格调和情怀;其二,作为书体,章草有一显而易见的特点,即它具有“兼容性”或称“兼容能力”,发生在它之前的书体如秦隶、汉分以及之后的今草、楷书、行书,均可依书家各自的审美眼光、兴趣而有所择取。余德泉、孟成英在《章草大典·前言》中归纳的章草七种类型中除原始型、标准型之外,还有简章型、章今型、今章型、正章型、章篆型五种[1],也证实了这一“兼容性”的存在。
相比而言,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文人甚至专家“专利”的甲骨文书法之所以难以“复兴”,即便在少数人一生致力下(如罗振玉、董作宾等)也难将其推到书法创作的较高境界,主要原因便在于它从根本上缺乏这种“兼容性”。
清晚期及民国简牍的出土,除历史文献考古的学术意义之外,在书法领域亦具有多层面的意义。首先,简牍的出现,在帮助学者、书家借以研究书法史上楷书、草书等书体的产生,以及研究书法史上重要的隶变现象的同时,更让书家凭着艺术直觉而与相隔两千年之遥的汉代章草发生对接,成为触发近现代章草复兴的一大因缘。其次,融合碑帖以及历代优良书法因子而形成的沈氏晚年书风,更让民国书家以最近的距离感受到章草的生命力和魅力。
《流沙坠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为20世纪出土的三大代表性汉简。其中,前两者为20世纪前半期的发现。
《流沙坠简》经罗振玉、王国维整理,于1914年在日本出版;《居延汉简》于1930年出土,但当时学术界发表文章多是对汉简内容的研究,墨迹资料只有极少数学者、书家见到,即便于右任亦是多年后才看到,此由其诗中可以见出:“此生得见居延简,相待于今二十年。为谢殷勤护持者,乱离兵火得安全。”[2]按,《居延汉简》墨迹的图版迟至出土29年后方获正式出版,1959年出版《居延汉简甲编》,1980年出版《居延汉简甲乙编》。可见,对民国章草复兴之推助,罗、王之《流沙坠简》实功莫大焉。刘延涛著《章草考》,对简牍书法有如此评价:“右列诸简,或雄浑,或遒丽,不可企及。然此犹边塞之无名作家也,吾人于此,可以想象刘、杜、崔、张之美艺矣。”[3]
沈曾植作为最早一批接触到汉简,又最早将其书法成分用于研究和创作的书家,在初接触到汉简时,即在所作王珣《伯远帖》跋语中写道:“内府收王珣《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特南渡名家,韵度自异耳。[4]”他认为《伯远帖》之“隶笔分情”与所见简牍的隶笔相通,所异之处在于从王珣笔迹可见出南渡书家笔下与西北汉简之间韵味的不同。
学者称简牍墨迹中有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此不过笼统而言,其实大多墨迹难以明确各书体之间的分野。究其原因,一是其发生时代在书体已经形成规范和定式的晋代之前,在文字与书法史的轴线上大体处于所有书体发生期的末期,各种书体的样式已临近却又未全部达到最终定型,其墨迹的书体之间界线往往难以明确;二是简牍的书写者大多并非专门研究书法之士,而其书写是为应用而非为艺术,大抵以能够记录、交流为目的,很少将字体结构的准确性、艺术性考虑在内;三是戍边群体的构成虽非来自“五湖四海”,但也是五方杂处,受教育程度各异的人带来不同地域、形态各异的书风,其背后是书法教育背景的不纯粹,结果是自然地在西北边陲形成特定时期的“混搭”书风。
简牍墨迹中,为近现代书家所乐于取用并借以成家者,多是隶书;其中章草的取用,以沈曾植为第一位。沈曾植慧眼独识,又以过人的功力与艺术的想象力,将简牍章书作为焊接、融合碑学与帖学的书体,使碑与帖之精华在他腕下被同时激活。这样的成功,绝非寻常书家所敢为、所能为。
简牍楷书、隶书、行书中大多掺杂着多种书体之元素,呈现多种渐变性的状态,这种面目恰与沈曾植的追求暗合,所以他对简牍的兴趣虽以章草为主,对其他书体亦未必没有取法之用心。简单地说,沈曾植对简牍墨迹的选择策略是这样的:选择章草,又不止步于章草。对章草的重视与临习、创作,是那一代文人书家的一大群体性倾向。沈曾植之同时代,即有受其影响而肄习章草者,郑孝胥即为其中之一。郑、沈两位初识于1886年,交谊直至1922年沈曾植去世,长达37年。郑孝胥的隶书已有楷化倾向,这一追求趣向与沈曾植所谓“隶参楷势而姿生”为同调。他对草书较少临习,到中晚年才正式习草,曾直接向沈曾植请教。《郑孝胥日记》1914年11月11日记载:“以近日来所作草字示子培,子培曰:‘薛道祖欲为此体而未成就,宋高宗意亦在此,亦不能佳。知此径途不易觅也。’余曰:‘子敬尝叹章草宏逸,余又恶草书纵笔有俗气,故欲以皇象、索靖为归耳。’”[5]郑氏拿给沈曾植看的“近日所作草字”应即是章草书体。此时郑孝胥决意取法章草,以两人交谊与艺文观点之彼此影响看,应与沈曾植对章草的深厚兴趣和致力密切相关。肖文飞推断,以沈曾植为首领,形成了一个围绕《流沙坠简》而引发的临写章草的小团体。[6]
纵观章草的第一次高峰时期遗留下来的作品,以及被学者称为第二次章草高峰的元代章草作品,除最初的个别章草帖(如《月仪帖》)之外,都呈现为十分平稳、均衡的结体和约定俗成的字势特点。在明代绝大部分时段,章草颇为沉寂,到明末清初,王铎、傅山、八大山人等书家偶一为之,并未作为主要追求,而多数是与行、草书杂合书之,因此很少受到章草规范的束缚,而表现为随意自如甚至纵肆。只有到了民国初期,章草成为一些书家有意识的追求,他们用心推究根源,研出新意,并向帖学之外的碑刻取法,赋予作品厚重及欹侧、跌宕之势。这既有书家个体的有明确意识的追求,也有时代审美趋向的因素。
在清末民初取法章草(包括以章草为主攻方向)的书家中,多以向碑刻的取法作为书家探求古源、获取古法的渠道。在向章草之外碑帖的取法上,沈曾植亦有引导之功。最鲜明的一例,便是对《爨宝子碑》的倾心与临写,这是沈曾植之后许多章草书家的共同特点,王世镗、郑诵先、王蘧常三家传世作品中都有突出呈现。
二、高峰与高原:沈曾植与民国众家成就之比较
民国时期擅长章草的书家,主要有罗复堪、王世镗、卓定谋、王薳(王秋湄)、余绍宋、林志钧、刘延涛等。在章草创作和章草理论研究两方面均有建树者,以王世镗、卓定谋、郑诵先等为代表。
王世镗(1868—1933)的章草著作,有《稿诀集字》《论草书章今之故》《叶刻急就章考正》。《稿诀集字》既排列出诸多字的结体、部首规则,及若干相近字之区别,也包括王世镗对草书的一些观点,如“穷源在西汉,史游《急就章》。粗书解隶体,稗效广《凡将》。特从篆隶造,那可行楷方”,即是认为西汉史游《急就章》衍生自隶书,字形与篆隶相通,不可用行、楷书结体、笔法去写;又如“分布率平正,迅速愈谨详”,是指出章草字字、布局以平正为要,既用草书的速度去写,又不可失去“谨详”之法度。于右任《挽积铁子王鲁生先生四首》有“三百年来笔一枝,不为索靖即张芝”[7]之高度赞誉。刘延涛(1908—2001)认为:“近人王世镗书,殆复返于汉者也。”[8]
王世镗书法以章草为主,除直接取法皇象、索靖传世章草外,亦取法于《爨宝子碑》及北朝碑刻。他年轻时即接触龙门石刻,后来到汉南,游观褒斜,抚临摩崖,尤其致力于《爨宝子碑》,并曾集《爨宝子联语》八百余副。其晚年章草书风亦融汇章草法帖及简牍、《爨宝子碑》味道,1933年(癸酉)所书联“百宝在渊有龙守,九天之乐如鸾鸣”的题款写道:“癸酉以集《爨宝子碑》文,用流沙坠简中笔意书之。”“癸酉初夏,以集《爨宝子碑》之联语,用西陲竹木简笔法书之,时赁庑梅溪山庄,盛暑挥毫,殊不计工拙也。”[9]可见,王世镗与沈曾植同样是将《爨宝子碑》与汉简相融合入书。
卓定谋(1886—1967)早年毕业于日本高等商业学校,曾任中国实业银行经理、全国农商银行讲习所教务长,后为北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前夕赴台湾。他一生有志于章草资料整理与传播,在1930年出版《章草考》,并将清代李滨所著《急就章偏旁歌》加以考证补订,出版《补订急就章偏旁歌》。
卓定谋成为民国早期整理、研究及推行章草最力的学者。他以其个人收藏即“自青榭藏章草”之名,出版多种章草法帖,包括《章草草诀歌》(此帖印行后,发生对王世镗侵权之争议)、《明章草大家宋仲温急就章真迹》《明章草大家宋仲温书用笔十法真迹》,以及其本人章草作品《卓君庸真草缩印》《卓君庸章草墨本》《卓君庸章草拓片》等书,并发表《用笔九法是用科学方法写汉字》《用笔九法与章草》《章草之研究》《章草与中国字体之改革》等文章。
郑诵先(1892—1976)先由帖学入手,后受罗复堪影响,转而习碑,于汉隶《张迁碑》《石门颂》及“二爨”用功甚多,形成自家的章草书风。他对“二爨”用功之深,至老未辍,弟子谷溪回忆说:“直到晚年,仍将两碑置于案头,偶尔临之。[10]”启功说郑氏“尤其喜爱汉碑和‘二爨’的字,他常想把那些字的特点融合到章草中去”[11],并曾评述其临习特点:“曾见当年所临《张迁碑》、‘二爨’诸碑,不作圭角怒张之态,而笔力圆融,中涵古朴之致,虽至晚年,弥臻醇厚。”[12]
王世镗、卓君庸、郑诵先等人与沈曾植书法成就的差距,容或存在于多个方面,沈曾植学养深博与翰墨取法广泛两方面因素应是其他书家未及之处。仅由翰墨取法层面看,王、郑二家,《爨宝子碑》在其成熟章草书风中占了绝对主要的成分,少见其他来源的取法;沈氏晚年虽然可见明显“爨味”,但同时来自其他源流的成分亦极鲜明,加之沈曾植所擅之用笔法(如铺毫运笔)、结字法(如结字造险、笔势造险),遂使晚年书法超凡入圣,远胜过诸家之上。虽然王世镗、卓君庸、郑诵先也曾由帖学入手,但即便比较帖学修养,二家也明显逊于沈曾植。
沈曾植不论从年纪而言均早于王世镗之后诸家—沈氏早于王世镗近一代人(沈氏生于1850年,王世镗生于1868年),早于卓君庸、郑诵先等人则更多—还是中年时期所处京师文化、书法圈往往能得书学风气之先的客观优势环境,都决定了他接触《爨宝子碑》要早于王世镗等人。
当代学者认为沈曾植引领“民国章草热”,颇有笼统下结论之嫌。如欲对沈曾植所起作用得出真切的结论,应从如下几个层面进行分析,方可作出独立而客观的判断。
第一,虽然沈曾植为晚清、民初学术界至尊,依其在书坛的影响,对“民国章草热”的引领之功应是以润物无声的形态发生,而未达到类似于“旗手”的一呼百应的程度。
第二,对章草的关注,是彼时一部分文人书家的不约而同的兴趣倾向,沈曾植作为成功实践碑帖融合的通人书家,又以章草融入晚年书风,应会对这一群体发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后起章草书家的书体追求。
第三,与沈曾植时代相近的章草书家,如王世镗由于年龄的差距,其发生兴趣的时间未必早于沈曾植,更主要的是王世镗较长时段偏居陕西,在社会、文化圈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其对书坛影响甚微,以至发生大学教授卓定谋指《章草草诀歌》为明代无名书家所书,王氏窃为己有之讼事。王氏广为书坛和部分社会人群所知,则是在1930年前后受知于于右任之后的事情。至于是否存在当代诸多学者所说的王世镗章草受沈曾植启发和影响,尚无直接证据。
第四,沈曾植书法的影响,包括对民国章草热的影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由微至显的。
综合如上方面,可见王世镗之后的数位章草书家对碑帖整合之取径,与寐叟晚年书法实践及成功之间应不乏内在关联。
民国章草自沈曾植为先导,其后如王世镗、卓君庸、郑诵先等以章草名世的书家就各自所达到的水平来看,与沈曾植相比,均有明显逊色。回顾民国阶段的章草状况,可谓沈曾植巍然耸立于前,成为高峰,而在较大程度上经他引导而涌现的一众章草名家不啻是组成了那一时期的高原。民国时期即致力于章草的书家中幸有王蘧常,尽其一生努力,终为民国章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双峰相映:沈曾植与王蘧常之衣钵承传
民国时期的章草复兴之发生,与沈曾植晚年以碑帖融合入章草的成功实践密切相关,然而民国早期专门从事章草的书家,无论创作水平还是理解高度,皆与沈曾植有很大差距。[13]在真正的书法文化意义上接续沈曾植而成就辉煌的书家,是比王世镗、卓定谋时代更晚一些的王蘧常(1900—1989)。
沈曾植为开启王蘧常章草的一大关节。1919年夏,王蘧常在上海哈同花园拜沈曾植为师。师生之间并非仅为书法传授,而是从治学门径入手,教以“读书分类札记之法”,同时接受师教,学习章草。王蘧常日后多次撰文回忆这段经历,其《自传》载:“年十九,见沈曾植师于上海,师以为骨骼已树,可肄北碑,求纵恣。以旧拓《郑羲》《敬使君》两碑见赐,并指授用笔用墨之法。”[14]由此两碑开始,王蘧常开始临习北碑,《张猛龙》《龙门造像》《云峰山摩崖》《爨龙颜碑》《爨宝子》《瘗鹤铭》等碑皆在临习之列。与此同时,他开始章草的学习,这同样是出于沈曾植的启发。沈曾植得知弟子此前一直在临习王羲之《十七帖》,便直言相告王羲之书法系远承章草而来,但王羲之之前的章草传本已不复得见,而今世章草传帖,“疆域褊小,特殊难光大”,指点他“融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于周鼎彝”,以“开前人未有之境”。[15]这是王蘧常以碑为主、兼攻章草的起步阶段。沈曾植“小子勉之”之语,更是伴随终生,王蘧常二十八九岁时为诸生所作《书法答问》即写道:“近岁以来,奔走衣食,旧业已废。唯不忘金丈及寐师遗教,欲作草,必自章草始,偶偷闲学之。欲仿《月仪》及《出师颂》,后得松江本《急就章》,日必习一二纸,然卒不能致力,觉腕下有鬼,无以发奇蕴,每自讼曰:‘负吾师矣,负吾师矣!’”[16]
沈曾植与王蘧常缔结师生名实后不久,沈氏即辞世,但他对后者的一生治学、治书影响甚为深远。王蘧常晚年又将篆书、隶书、章草、今草及汉简、制书、陶文以己意而融会贯通,铸成圆浑凝重、古意婆娑的章草,亦即“蘧草”,更有学者将蘧草称为书法史上章草书法的第三个高峰。[17]弟子成就尚且如此受到尊重,作为直接的老师,又以晚年独具面目的书法开近现代章草新风的沈曾植,其书法成就自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章草学习过程中,王蘧常亦有客观实效的方法,可为当代习书者之学习途径。他为马国权所作《章草字典序》中回忆中年时期与好友共同学习章草的情形:“武进蒋石渠(即蒋庭曜,1898—1979)中岁,亦肄章草勤,旅沪日,见必谈章草,或任取古籍一文,以章草对录,合草法之多少为胜负。予之遍摹章草草法,自此始。”[18]
王蘧常进入花甲之岁后,渐渐形成个人风格,其借鉴周彝鼎、陶砖瓦,三代吉金篆籀等古文字的结字方法,使其晚年章草面目更多古朴、奇奥的审美内涵和文字学价值。蘧草笔画富寓篆籀气息,运笔匀速平稳,比古代章草传帖中的结字、用笔更具古意。蘧草书风与沈氏书风相比,用笔含蓄而凝练,以篆籀之遒劲圆转极大地消解了乃师取自碑派的侧笔劲折、多出方角之态,而加以浓郁浑穆之古意。
王蘧常的社会身份是古代哲学史、思想史教授,对书法的态度与沈曾植相似,极少有专门论书之作,今可见者,只有《明两庐题跋劫余录》所收14则题跋,《答问八法》《自述篇》《综合篇》以及用章草书写的《章草字典序》《居延汉简跋》《武威汉简跋》《宋仲温书急就章跋》《草书赵孟頫急就章跋》等,总计不足万字。他晚年自述治学及学书情状,每不忘将先师教诲传给后学,可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古风之现代演绎。沈曾植原稿多取章草写法,令文稿整理者不易辨认,其身后整理出版的《海日楼题跋》文字所偶见纰误即由此而生。王蘧常文稿亦多用章草写法,唯结字更古、更难识读。但王氏能在章草取法方面超出沈曾植之上,一则受乃师引导,青年时期即致力于章草研习,二则由其能在取法与创作方面更多出以己意,成就之高度亦不为乃师所限。
谢稚柳这样评价“蘧草”:“千年以来一人而已。”[19]沈曾植是直接启发并推助王蘧常章草高峰之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有沈氏导夫先路,厥有王蘧常树立自古迄今之章草艺术最高峰的卓越成就。
王蘧常对书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沈曾植学问、书法之整理与阐扬。他在沈曾植去世后撰《嘉兴沈乙庵先生学案小识》发表于《史学杂志》,1928年撰《嘉兴沈曾植先生年谱初稿》,后又撰《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谱》。王蘧常中年、晚年分别受社会环境、身体精力所限,发表书法专论文章极少,其中有关沈曾植的内容占了相当重要的部分。其二,王蘧常于章草研究、创新用力尤巨,其晚岁形成的“蘧草”为沈曾植之后章草最高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蘧草的成功也代表着寐叟的成功,两者实是相得益彰、互为补益之关系。
作为沈曾植衣钵之继承人,具体到书法技术层面,王蘧常自称在“三王二爨”之间取法,对《爨宝子碑》亦多有取法,此由其传世作品中的临写墨迹可见用功之深,而其创作中则表现为“以圆化方”,以圆浑笔法化解了爨碑的方笔。
沈曾植晚年书法与王蘧常的章草相比,各自存在如下特点。
(一)结字。沈氏吸收章草用笔特点,字的结体以今草、行书为主;王氏章草字法更为地道,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古文字写法,以章草诞生之前的古字来丰富章草结字,并且部分字的结体形成了蘧老所独有的范式,笔法特点亦与字法作出同步趋古的变化。
(二)笔法。沈氏用笔方圆相济,以方为主,作品极富起伏变化,折射出运笔之迅捷;王氏弃方就圆,不求起伏变化,如香象渡河,沉浑如一。沈氏跌宕、纵放,用隶书及北碑笔势,多见侧锋,如奔雷走石,临深据槁;王氏线条粗细变化极小,而在往复穿插中得趣,是用篆籀笔法,一味中锋用笔,如屋漏痕,如虫蚀木。
(三)布局。沈氏起伏变化大,王氏起伏变化小。郑逸梅所称“沈曾植用指力,他(王蘧常)用腕力”[20],盖即指此。
结语
沈曾植的章草成熟诚然主要出现于民国肇立之后,王蘧常的章草成熟则主要凸显于新中国成立后,但却是他在民国阶段取法与努力的自然成果,其成就应视为民国章草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考察、研究一位书法家的成就,绝不能够截然割裂其中年与晚年的书法实际,更何况放眼中国书法全局,同样起步于民国时期的卓君庸以及成就更大、有“当代草圣”之称的于右任同样定位为民国书法家。从书法史的延续特点看,王蘧常进入成熟期之后的章草,按理应可归为民国书法的概念之内。
沈曾植与王蘧常可谓位于民国章草史前后两端的高峰。正因为有这两位大家的存在,民国期间的章草书坛方不至于平庸:沈曾植为民国章草确立了起点极高的开端,王蘧常则在为民国章草复兴画上一高亮句号的同时,也为书法史贡献出新的章草范式—“蘧草”。处于沈氏、王氏之间的诸家所代表的章草书法的高原,则在这段“马鞍式”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各尽所能进行创作与研究的过渡作用,使复兴、发展的节奏不至于中歇。
注释:
[1]余德泉,孟成英.章草大典[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前言.
[2]于右任.喜见居延汉简出版[G]//刘正成,王睿.现代书家书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8.
[3]慕黄.章草考[J].草书月刊·复刊,(1)2:16慕黄为刘延涛的字。
[4]沈曾植.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M].钱仲联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10.
[5]郑孝胥.郑孝胥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6:1538.薛道祖,即薛绍彭,字道祖,宋代书法家,与米芾齐名,时人并称“米薛”。
[6]肖文飞.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从沈曾植看清末民初书法的丕变[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08:62.
[7]陈振濂.中国现代书法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85.
[8]刘延涛.章草考[J].草书月刊,1948(56):12.
[9]陕西省汉中市博物馆.王世镗先生遗墨[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5.
[10]谷溪.神融笔畅章草薪传—郑诵先书法艺术述略[J].书法,2000(5):47.
[11]启功.郑诵先书法选序[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1.
[12]启功.郑诵先先生法书遗墨汇编跋[J].中华书画家,2013(1).
[13]谢凤孙似为一例外。他作为沈曾植弟子,有较深的学养基础,但书法是随乃师而亦步亦趋,未跳出寐叟晚年书风范围。其书风应是介于章草与行书之间,或未可直接定位为章草书家.
[14]王蘧常.王蘧常自传[G]//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7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38-163.
[15]王蘧常.王蘧常书法集自序[G]//王蘧常书法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
[16]王蘧常.王蘧常自传[G]//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7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38-163.
[17]杨吉平.二十世纪草书四家评述[J].中国书法.2000(10):69.
[18]王蘧常.章草字典序[G]//王蘧常书法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50-151.
[19]范敬宜.近代书坛一巨星[G]//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王蘧常.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前言.
[20]郑逸梅.王蘧常章草选·后记[G]//王蘧常章草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