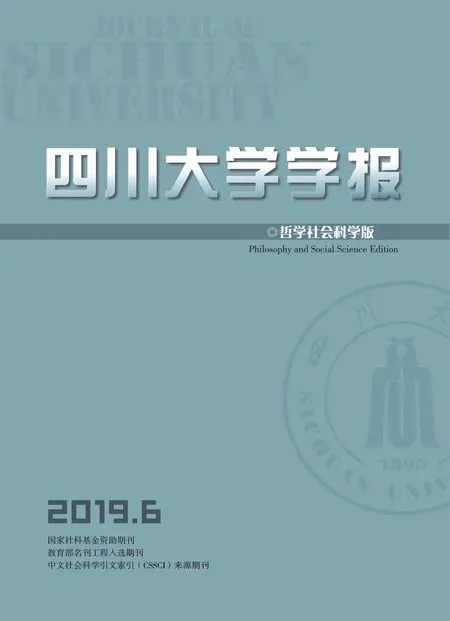“宗教的秘密”与人的“救赎”
——《神圣家族》对一个普通女人命运的思考和透视
长期以来,马克思被诠释为一个无神论者乃至反宗教的斗士,特别是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表达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的看法,被视为其思想与宗教决裂乃至绝缘的依据。然而,如果将马克思的思想还原到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的土壤之中就会发现,他与宗教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中文语境中所理解的作为毒品的“鸦片”与马克思视宗教为“安妥”人的灵魂的麻醉剂和镇静剂的内涵之间有着很大差异;另一方面,曾经浸润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中的马克思又感到,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宗教救赎之路其实是虚妄的,人的境遇的变革和人性的“救赎”只有通过实践之路才能完成。比如,在被列宁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前夜”的作品《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对当时流行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中人物的分析,把“宗教的秘密”与人性的现实联系起来,致使他的讨论既与宗教关联,又不囿于宗教,而是突破和超越了宗教的视界,同时又达到了新的现实高度。这是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最深刻的体现。在过去的研究中这方面的细节甄别和思路梳理极其缺乏,本文拟对此作出探究。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所剖析的是一个叫做玛丽花的妓女,她是《巴黎的秘密》里的主要人物之一。法国小说家欧仁·苏创作的这部小说以德国盖罗尔施坦公国的大公鲁道夫公爵微服出访巴黎、赏善罚恶为线索,通过对各种人物命运的描写,展示了这个繁华的世界大都市中贵族、下层贫民、罪犯三类人物的生活内幕和生存“秘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特别是妓女、越狱犯等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和痛苦,也对上流社会贵族阶层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等情形作了深刻的揭示。马克思把《巴黎的秘密》看作是现实主义的作品,认为其情节可能是虚构的,但反映的现象和状况却是真实的。充满人性特征和美好幻想的“雏菊”玛丽花迫于生活际遇和压力沦落为妓女,受人“拯救”走向了宗教,但最后已成为修女的她却惨死在修道院里。宗教是她短暂一生的向往和依托,但宗教到底带给了她什么呢?马克思根据玛丽花的遭际透析了宗教的实质与现实人性的关系。
一、充满人性的“雏菊”玛丽花
在《巴黎的秘密》中,欧仁·苏通过四个情景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充满人性的玛丽花的形象——一朵美丽善良、蕴藏着丰富生命力、含苞待放的“雏菊”。起初,她是巴黎许多坏人藏身、碰头的塔皮弗朗小酒吧老板娘的奴隶,“前额洁白纯净,天使般完美的椭圆脸蛋”“喉音温柔、颤巍、调和,实在迷人”“仿若在杀人的战场上开放着一朵美丽的百合花”,因此,人们叫她“唱歌的小妞儿”。“玛丽花”也有“童贞女圣母”的意涵。(2)欧仁·苏:《巴黎的秘密》上册,成钰亭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14页。不幸的命运让她遭遇极端的悲惨,虽沦为卖淫女,但仍然保持高尚的心灵、性格上的落拓不羁和人性中的优美,在非人的境遇中合乎人性地成长着。马克思通过几个典型的情节点出这一点。
情景一:在小酒馆里,当一个号称“操刀鬼”的地头蛇要挟她为其买单的时候,玛丽花严词拒绝,而后“操刀鬼”打了她一拳,她便拿起剪刀朝“操刀鬼”的肋骨猛刺了一下,并且坚强地说,“你别过来,否则我用剪刀挖掉你的眼睛,”“我没有惹你,你干嘛打人?”在这一场境中,外形纤弱的玛丽花表现出朝气蓬勃、精力充沛、生性灵活的品质,显现的是一个不屈服于暴力、善于捍卫自己权利的坚强女性的形象,而不是一只没有防御能力、任人宰割的“羔羊”。
情景二:在费维街罪犯们聚集的酒吧里,她向鲁道夫叙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她从小被父母遗弃,不得不和一个叫“猫头鹰”的单眼瞎的老太婆一起生活,每天乞讨、挨打,最后还被拔掉了一只牙。忍无可忍之下,她逃了出来,不幸又被当作小偷关进感化院,一直待到16岁。从感化院出来后,她本想做一个勤劳的、自食其力的人,但处境艰难、尴尬,又很少能得到机会和帮助,所以她没有去找工作,而是把从感化院后赚得的300法郎统统花在游逛和装饰上,后来她虽然后悔了,可还是为自己辩解:“但是没有人劝告我呀”。她想做一个纯洁的人,但在无奈的生活际遇下被卖身于酒吧的老板娘,不得不在灾难中悲伤地过活;她想做个诚实的人,“真的,我想起过去就伤心……做个诚实的人想必是很好的”,但是,她又感觉到,在那样的环境中,她要做个诚实的人太难了,“诚实,我的天!你说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诚实!”她想做个坚强的人,“我决不哭鼻子”,但她的生活充满悲苦,“是很不愉快的”;她想忏悔自己的过去,但根本没有渠道,只能不了了之,无奈地提出一条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式的人性原则:“到头来,做过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3)欧仁·苏:《巴黎的秘密》上册,第216页。讲述自己悲惨经历的玛丽花是诚实的、内心坦荡的,又是一心向往纯洁与善意的,即使对于自己的过往没有自觉的反省,有的只是身不由己的无奈!
情景三:当鲁道夫和玛丽花在郊外第一次散步的时候,鲁道夫问她:“不幸的孩子!意识到你如此可怜的处境,你应该经常想到……”,“想到死,对不对,鲁道夫先生?”玛丽花打断了他的话,“是的!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透过河岸的栏杆凝视着塞纳河……可是,过后我又转过来看着花,看着太阳……并且自言自语地说:河始终会在这里,可是我还没有满十七岁呵……谁会知道呢?”“希望遇到一个好人,给我活做,让我能够摆脱奥格雷斯……这样一希望,仿佛就能使我得到安慰……我对自己说:‘我的苦是受够了,但是至少我从来没有害过什么人……假使有人劝告过我,我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这样一想,就减少了难过……虽然自从我的小月季花死了以后,我难过得更多了。”(4)欧仁·苏:《巴黎的秘密》上册,第75页。这无疑是一个天性乐观、虽饱受生活的磨难仍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小女孩。当鲁道夫帮助她离开自己以前无力摆脱的恶劣环境,来到大自然怀抱中的时候,她便自发地表露出固有的天性,显现出小姑娘蓬勃的生趣、丰富的感受以及对大自然之美如此合乎人性的欣喜若狂。
情景四:鲁道夫许诺玛丽花,要带她到若尔日夫人的布克伐尔农场上去,那里将会有鸽房、马厩、牛奶、乳酪、水果等。这对于从来都“没有出过巴黎”、成天生活在“那间又脏又臭的小屋里”、自从到了“奥格雷斯家以后”“就没有进过教堂”的玛丽花来说,就有一种渴望解放和临近解放时的“痛快”之感。当鲁道夫为她描绘了一个空中楼阁的时候,她天真烂漫地以为自己不幸的命运是自作自受,“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不会节省钱的缘故”,甚至反过来规劝鲁道夫把钱存入储蓄银行。她觉得鲁道夫带她到若尔日夫人日常帮忙打理的农场去,是上天给她的恩赐。她没有对过往的生活进行反思,也没有直接对当下的生活进行思考,而只是幻想着愉快、光明的生活,也只有在这种幻想的比照下,她才想起了自己过去境遇的极端可怕。
这便是欧仁·苏展现给我们的生活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黎社会的“雏菊”玛丽花的形象。《巴黎的秘密》之所以轰动一时,成为当时法国社会中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其原因就在于这部小说较为详尽、真实地描写了受苦难人民的生活,反映了他们贫困不堪的处境,叙述了他们一向被“上等人”所蔑视和践踏的苦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部小说“以鲜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等阶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5)恩格斯:《大陆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94页。
二、“救世主”的“赎救”之道
对于命运多舛仍然充满着鲜活人性的玛丽花,小说作者欧仁·苏并没有找到拯救她于悲惨生活的现实途径,而是满怀憧憬地把她交到了鲁道夫这个所谓“拥有”超乎寻常智谋的“救世主”手上,把鲁道夫当做玛丽花能且仅能抓住的“稻草”,把鲁道夫所谓的“仁慈”看作了使玛丽花获得幸福的途径。然而,不幸的是,似乎可以洞察巴黎社会一切秘密的、具有着过人的胆识和气力的、又是玛丽花的亲生父亲的鲁道夫,却选择了让玛丽花皈依上帝,在信仰中幻想着命运的改变,最终使玛丽花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小说《巴黎的秘密》的情节还在延续。鲁道夫把玛丽花从罪犯云集的费维街小酒馆里带出来,又想办法把她送到布克伐尔农场,将其交给两个人照看,一个是照顾她日常起居的若尔日夫人,另一个是布克伐尔教堂中的牧师拉波特神甫。若尔日夫人患有忧郁病、常感到不幸,且对宗教十分虔诚,她用非常动听的话——“上帝保佑那些又爱他又怕他的人、那些曾经不幸并已经悔悟的人”——打动了玛丽花这个从来就没感受到爱、也没有爱过的人,因此她事实上成了玛丽花的教母。而牧师拉波特则用教义来改造玛丽花,当他看到玛丽花因生活境遇翻天覆地的变化流露出忧郁的神情,而不是感到幸福快乐的时候,便给玛丽花以“持续不断的关心,使她能够光彩地生活”。
于是,刚刚脱离悲惨生活环境的玛丽花,欢欢喜喜、坦率天真、毫无设防地在农场开始了新的生活,但她对过去种种痛苦和屈辱的经历仍然忌讳莫深,对过去生活中的污点感到羞愧和恐惧。特别是当她在农场里遇见佃户杜布勒伊太太的女儿克拉腊小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憔悴的腮帮一感触到克拉腊娇嫩的小脸……我的脸羞得像火烫一样……我感到疚心……想起了自己……我!”她没有想到是,这样自然的、感性的情感却正好为老教士拉波特和她的教母若尔日夫人的宗教关怀留下了充足的空间。拉波特趁机给她以道德的启发,让她“领悟到”自己过去的卑贱处境,“与其说是不幸,还不如说是有罪……”(6)欧仁·苏:《巴黎的秘密》上册,第349页。而这样的表白又正中拉波特的下怀,他口气坚决地回应玛丽花:“这实在没有办法!”“就是品性最高尚的人,只要他在你被救出的污泥中呆过一天,出来后也会在额上留下一个洗不掉的污点……”至此,可怜的玛丽花只能伤心地说:“那末,您看出我是命定该绝望的罗!”
这是拉波特对玛丽花宗教改造的第一步。他毫不留情地撕开了玛丽花过往的伤疤,然后决绝地宣布这个伤疤将会永久地留在她的额头上,因此,无论她做何等的努力,她都会是一个罪人。而且,她还必须有原罪的意识,痛苦与忏悔必定伴随着她的一生。其实,对玛丽花来说,这样的痛苦远远大于她仍旧沦落在过去的火坑里的痛苦,因为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的话,“也许贫困和毒打很快就断送了我的性命,而对于这种无论我怎样渴望也得不到的纯洁,我至少是可以毫不知道便了此一生的”。(7)欧仁·苏:《巴黎的秘密》上册,第352页。至此,从小受尽人世间种种痛苦和磨难的玛丽花在教母若尔日夫人和牧师拉波特的宗教关怀下变成了一个终身悔悟的罪女。
接下来,对于这个注定只能纠结于过去的不堪经历而倍感绝望的小女孩,拉波特教士在宣布她不可能完全撕掉过去可悲的印记的同时,又为她指明了唯一的出路,那就是期望全能的上帝以无限仁慈来帮助她,经过尘世的眼泪、忏悔、赎罪,得到赦免和永恒的福佑的天堂。“上帝的仁慈是无穷尽的,我的亲爱的孩子!在你受苦受难的时候上帝都没有弃绝你,这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救你于绝境的这位宽大为怀的人实现了圣经上的话:人有呼主之名者,主将庇佑之;人有呼主者,主将成就其心愿;主将闻听其呻吟并拯救之……主将完成自己的事业。”(8)塞利加·维什努:《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18页。
这样,在唯一济度世人的教堂里、“在开始忏悔和赎罪的地方”,自然的、感性的、充满着人性的玛丽花不得不放弃了作为人本应有的羞惭,接受了拉波特对希望超凡出世的解释以及人间万事万物必须受上帝摆布的观念,拜倒在上帝的绝对权威之下。然而,这一切对天真烂漫、对尘世还怀着深深眷恋的玛丽花来说,又都是被迫的。她被拉波特教士唤起了“自己有罪”的意识,又被告知上帝会拯救她于罪孽的煎熬之中,但在她的意识里,上帝是虚无缥缈的,她所能想到的还是人世间她的“救星”鲁道夫,那个“对我仁慈并使我回到了上帝那里去的人”。
但是,有着基督教式的粗暴的拉波特教士,哪里肯让玛丽花轻易地摆脱罪孽感呢!他立即打破了玛丽花有违神道的幻想,说道:“很快,你很快就会得到赦免,赦免你那深重的罪孽……主保佑一切行将堕落的人。”(9)塞利加·维什努:《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9页。他用虚幻的许诺来逼迫玛丽花在追寻上帝的路上更进一步。
事实上,表面上显示出对玛丽花极大的同情和关怀、又信誓旦旦劝慰玛丽花只要诚心赎罪,终会得到上帝护佑,但实际上他们对玛丽花过往的经历是不能释怀的,他们早就在心中给玛丽定了罪。俩人在私下谈话就提及,玛丽花是不能“嫁人”的了,因为没有一个男人有勇气从内心上接纳她那被玷污了的青春经历。更根本的是,他们认为,“如果她有道德感的话,她是不会堕落的”,所以她根本不可能在此生赎补这么大的罪恶。她避免不了被社会唾弃的命运,就像那些直到半夜还在最热闹的街头叫卖火柴的七八岁的小女孩,最终逃脱不了被饿死、冻死的命运一样。可见,玛丽花的原罪是世俗观念来界定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宗教使命的观念形式与人的救赎的现实问题的有效结合,居然会仅仅依托于宗教伪善的“循循善诱”。玛丽花无可逃脱的残酷命运本应归因于她所处的现实社会境遇,也有着如若尔日夫人和拉波特教士之流观念影响的现实因素。她内心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意识到今生今世永远摆脱不了良心的谴责和过去的罪衍,另一方面又觉得即使对上帝坦诚布公也不可能赎罪或者获得谅解,这使她深感自己“好苦啊!”其实,玛丽花如此的现状和对这种状况的思考是完全符合人性的、也是合乎逻辑的。但拉波特却对她说道:“恰巧相反,这是你的幸福,玛丽,是你的幸福!主使你受到良心的谴责,这种谴责虽然充满了痛苦,但却是与人为善的。它证明你的灵魂有宗教的感受性!……你所受到的每一点苦难都会在天上得到补偿。相信我的话,天主一时把你放在邪路上,是为了以后让你得到忏悔的荣誉和赎罪所应有的永恒的奖励!所以,孩子,你要拿出勇气来!……支持、依靠、指导,你什么也不缺……”(10)欧仁·苏:《巴黎的秘密》上册,第354页。这就是宗教的伪善推导出的逻辑!
归根结底,宗教的逻辑无非就是激起人的宗教情感——一种非感性的、非自然的情感,而这种情感的对象却是莫须有的、无形的。拉波特巧妙地利用了玛丽花对大自然美的纯真喜爱。在傍晚玛丽花送他回家的路上,拉波特指着黄昏之时一望无涯的天际,说它“几乎能使我们产生一种永恒的观念……”并把玛丽花热爱大自然的秉性说成是“易于感受自然之美”,而这又被视为宗教崇拜,“看到这造物之美在你心中,在你那长久丧失宗教感情的心中激起了宗教崇拜,我常常是深为感动的”。(11)塞利加·维什努:《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20页。
在拉波特的启发下,玛丽花彻底否定了自己以往对有形的自然之物产生的感觉,为自己曾经对自然现象的欣喜若狂感到万分惭愧,更进一步地,她为自己没有能够体味到晶莹清澈的太空与永恒的观念之间的联系而感到沮丧。她终于意识到,自己一切人性的表现都背弃了宗教,违背了真正的神恩,因此是离经叛道的、亵渎神灵的。她自感“罪孽深重”,急迫地想要对拉波特教士“告白”,她亟需赎罪。
除了否定自己对自然之物的感性,玛丽花还否定了自己对现实人的感觉,从而把自己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彻底隔绝了。玛丽花原本对鲁道夫心存感激,因为是鲁道夫帮助她离开巴黎肮脏的小酒馆、离开非人的罪恶的生活,送她到农场、过上新的生活,也因此,她“曾经每一分钟都在想念着鲁道夫先生”。但是,在她得到来自拉波特教士的宗教启示以后,她便对自己对于鲁道夫、对于现实的、新的、幸福的生活的渴念表示怀疑,甚至是否定了。“我时常抬头望着天,但不是在那里找上帝,而是找鲁道夫先生,好向他道谢。是的,我在这一点上责备了我自己,我的神甫;过去我想念他比想念上帝为多;因为他为我做了唯有上帝才能做出的事情……我是幸福的,幸福得跟永远逃脱了大险的人一样。”(12)塞利加·维什努:《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21页。可以看出,对于此刻的玛丽花来讲,她又非常矛盾地幻想着鲁道夫不仅是那个拯救她于悲惨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人,而是现实版的“上帝”,或者说,在玛丽花的思想深处,鲁道夫应该与上帝合一,因为上帝才是真正的“救世主”。
这就是玛丽花在生活中对于宗教的理解和态度上的转变。如此的转变与自然、现实、感性、知识等等均无关系,它不需要玛丽花的理性思考和实在努力,甚至不需要推理和论证,也不需要通过告白以祈求上帝的宽恕。“主已经向你证明他是仁慈的”,玛丽花要做的、她能够做的仅仅是“领悟”,领悟到自己的原罪和上帝的神恩,从而去赎罪、皈依,直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那个虚无缥缈的存在。她成了修女,宗教生活完全取代了她的世俗生活。她打心眼里为自己的“觉悟”感到庆幸,她把自己过去的不幸理解为罪孽,把对世俗生活的自然态度转化为超自然的观念,把拯救她的人的恩惠体悟为上帝的仁慈,又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若日尔夫人和拉波特教士的“教诲”,因为是他们“使我懂得了我的罪孽是无限深重的”。(13)塞利加·维什努:《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21页。
三、玛丽花最终被“救赎”了吗?
对于宗教的理解和态度发生转变之后,玛丽花的生活境遇如何呢?在小说中,我们看到:
首先,她由自己的“主人”变成了宗教观念的奴隶。在遇到鲁道夫之前,玛丽花虽然生活在悲苦与不堪的现实中,但“在最不幸的环境中还知道在自己身上培养可爱的人类个性”“在外表极端屈辱的条件下还能意识到自己的人的本质是自己的真正本质”,还有能力说“我决不哭鼻子”,有勇气与自己的过去说再见并憧憬自己的未来。可以说,这时候的她自己还是自己的主人。然而,当她把过去生活的不幸看作自己的罪孽,把自己的幸福定位于摆脱世俗的、自然的、人的感觉而拥有宗教的启示,把精神上的不幸看作最大的不幸,从而开始用基督教的观点来自我谴责的时候,她便成了“自己有罪”这种意识的奴隶。
其次,成为宗教观念奴隶的她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质的生活。本来是现代社会的污浊伤害了她,使她沦落为不洁的少女,但在与拉波特教士的交往中,在宗教的不断“洗礼”下,她自觉地把社会强加给他的不幸看成了她的宿命,而且认为一切的罪过都是自己的原罪。因此,“经常不断地忧郁自责,就成了她的义务,成了上帝亲自为她预定的生活任务,成了她存在的目的本身”。(14)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23页。她作为人的感觉,包括对自然之物的感觉、对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体会、对日常生活的感知以及对未来幸福的期盼统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在自我折磨、忏悔过去中度日,并且她把忍受这种折磨视为至高无上的“美德”和“荣誉”。
再者,向往着“美德”和“荣誉”的玛丽花却还是不能完全摆脱她那健全的天性。人性在她那里还在闪烁着哪怕是最后的、微弱的光,她的心还不免困惑于尘世的事情。当她和鲁道夫的父女关系得到确认,最终成为了盖罗尔施坦郡主的时候,她向父亲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祈求上帝把我从这些迷茫中解脱出来,让充满在我心中的单只是对上帝的虔诚的爱和神圣的希望,最后,我请求上帝完全掌握着我,因为我想全心全意地皈依于他,但是我的这些祈求都落空了……他不听取我的祈祷……不用说,这是因为我对尘世的眷恋使我不配同上帝交往。”(15)塞利加·维什努:《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23页。因此,在人性和神性之间徘徊与纠结,成了发生宗教转变之后的玛丽花日常生活的“新常态”。
显然,玛丽花“既然已经领悟到使她解脱非人的境遇是神的奇迹,那末她要配得上这种奇迹,她自己就必须成为圣徒。她的人类的爱必须转化为宗教的爱,对幸福的追求必须转化为对永恒福祐的追求,世俗的满足必须转化为神圣的希望,同人的交往必须转化为同神的交往”。(16)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23页。也就是说,她必须对尘世和世俗的事情完全死心,完全皈依上帝,这是她不二的选择。只有这样,她才能够得救,而上帝的仁慈才可以得到确认。
那么,完全脱离尘世,进入了修道院,朝以继暮、旷日无间地活在悔悟当中的玛丽花得到上帝的护佑和救赎了吗?
在修道院中,鲁道夫想方设法让玛丽花得到了女修道院长的职位。起初她认为自己不够格,拒绝接受这个职位,但后来在前任女修道院长的劝说下,她同意接受了。然而,终于走到了离上帝最近的地方、终日可以与“美德”和“荣誉”相伴的玛丽花,却并不适应修道院的生活,“衰弱颓丧,脸色苍白,精神痛苦”。就在初修期满,第二天将正式发愿的前一夜,身体虚弱加之冬日天气的严寒,更有神经性的激动,玛丽花的生命终于走到尽头,寂然辞别了人世。把她送上宗教的审判庭的父亲鲁道夫这样说道:“对她来说……死,也许更幸福。”
在宗教伪善的逻辑下,人性的救赎与生命的结束竟然是捆绑在一起的!小说中美丽的、心地纯洁的、会唱歌的玛丽花以她短暂一生的曲折经历表征了一个普通的底层民众希望从宗教中获得救赎的心理。亲生父亲鲁道夫先是把她遗弃,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下又救她于悲惨的生活之中,同时,也是这个父亲,把她变为悔悟的罪女,再把她由悔悟的罪女变为修女,最后把她由修女变成一具死尸。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取代上帝来改变玛丽花的命运,而上帝怎么样呢?“基督教的信仰只能在想像中给她慰藉,或者说,她的基督教的慰藉正是她的现实生活和现实本质的消灭,即她的死。”(17)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24页。
四、玛丽花命运的“观念”解读
《巴黎的秘密》不仅在法国引起巨大轰动,影响还扩展到德国。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之一的塞利加·维什努(SzeligaVishnu)在1844年6月的《文学总汇报》第7期上发表了《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一文,对这部小说进行了评论,将其中所叙述的各种事件在观念的意义上(所谓“思辨的秘密”)予以分析,认为小说的不凡之处就在于充分揭露了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一切秘密”。曾经也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马克思,当时正处在与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进行思想剥离的过程中,为此他与恩格斯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其中设专章分析了《巴黎的秘密》以及塞利加·维什努的评论,马克思不仅对玛丽花命运做出了深入的思考,同时,更借此机会批驳了塞利加·维什努的思路,认为他的评判不过是站在思辨哲学的立场上对小说进行的“再加工”,是一种自认为“创造”性的、实质上却是歪曲的评判。
塞利加·维什努认为,现实世界是由“普遍的世界秩序”所主导的,而思辨则是现实世界的打开方式。在他看来,玛丽花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却是无限的,而这种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她“艺术地”诠释了“普遍的世界秩序”与现实的个人命运的“思辨统一”。这是超越小说《巴黎的秘密》、连作者欧仁·苏也没有揭示出来的“秘密”,是“思辨的秘密”。小说主人公鲁道夫的使命就是揭示这个秘密,而玛丽花——小说中彰显人性的“雏菊”则是这个秘密的践行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玛丽花无疑成了思辨的“雏菊”。在塞利加·维什努看来,思辨的“雏菊”是对人性的“雏菊”的一种修正,这是他对“雏菊”的思辨的设计理念。我们将看到,在这种设计中,这朵思辨的雏菊无非是“观念的体现”而已!
从玛丽花和鲁道夫的关系来看,当塞利加·维什努把玛丽花设计为“思辨的秘密”的践行者而把鲁道夫设定为秘密的揭示者的时候,二者的关系就出现了扑朔迷离的状况。玛丽花是“普遍的世界秩序”与现实的个人命运的思辨的统一,是“真正统一的整体”的体现。因此,按照塞利加·维什努的设计逻辑,她就是一切秘密的根源,是思辨的目的本身。鲁道夫作为秘密的揭示者,是手段,是以她为根据的。二者的关系是母亲与儿子的关系,即鲁道夫应该是玛丽花的儿子。而在小说里,鲁道夫不是玛丽花的儿子,却是她的父亲。显然,这里出现了塞利加·维什努设计“雏菊”的逻辑与小说中的人物设定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在塞利加·维什努看来却是《巴黎的秘密》中诞生出的一个“新秘密,即现在所孕育出的常常不是未来,而是早已衰逝的过去”。与此同时,他还为玛丽花在小说中作为女儿找到了思辨的辩解:“一个孩子如果不也成为父亲或母亲,而是保持着童贞进入坟墓……那么他本质上……是一个女儿。”(18)塞利加·维什努:《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4页。
不能不说,把女儿看作她父亲的母亲,塞利加·维什努的这种思想同黑格尔的思辨是完全一致的。“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和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也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19)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4页。这是思辨哲学固有的思维逻辑,是它把一切现实事物都视为观念的产物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从玛丽花的早年经历来看,当塞利加·维什努把玛丽花设计为“真正统一的整体”的体现者的时候,她身上的善与恶却没有办法统一起来,因而也就失去了真正的人性。她是善良的:在非人的环境中生活,但她不曾害过任何人;她有着像太阳和花一样纯洁无瑕的天性;她很年轻,因此对未来和人生充满希望和朝气。这是她的本能、她作为人的愿望使然。但对于自己的生活境遇,她不认为是自己自由创造的结果,也不是她自己身上拥有的恶的本性的表露,而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别人强加给她的。这是她对社会、对人性的无知使然。玛丽花相信自己是善良的,又无法理解自己人性中恶的部分,因此就没有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避恶趋善,这是她之所以最后拜倒在上帝面前的原因。塞利加·维什努却将她出于本能和人的愿望的善良看作是善的抽象观念,同样将她悲惨的生活经历看作是恶的观念所致,认为在“批判的”“雏菊”玛丽花身上,“时代的普遍罪过、秘密本身的罪过”又构成了“罪过的秘密”。因此,她在本质上成了观念的代名词,一定会被思辨玩弄于股掌之中,如此的她,在现实中当然只有死路一条。
从玛丽花遇到鲁道夫开始直到最后惨死的过程来看,当塞利加·维什努把玛丽花设计为“普遍的世界秩序”与现实的个人命运的思辨统一的时候,实际上是把现实的个人命运统一到“普遍的世界秩序”这个思辨哲学的抽象而虚幻的概念中去了。作为现实的个人的最后死亡,恰好衬托出抽象的“普遍的世界秩序”的最后“胜利”。鲁道夫拯救玛丽花于水深火热的罪犯穴巢之中,让她从此摆脱了因贫贱的物质生活而产生的痛苦,同时也开启了她更加痛苦的精神之旅:她“欢欢喜喜、坦率天真地”与拉波特教士接近,但拉波特貌似超凡出世,却有着“险恶的用意”。他在心中已经给玛丽花定了罪,所以他是笃定“要玛丽花赎罪”而去与玛丽花接触的。玛丽花按照拉波特的规劝变成了一个“痛改前非”的罪人;为了把玛丽花的错误变成背弃上帝的罪行,使她认识到自己的罪孽,从而进行忏悔和赎罪,拉波特教士仅用言语就成功地摧毁了她心中对大自然真诚的喜爱,把这种爱变成了一种宗教上的惊叹,使现实的人同宗教的关系在玛丽花身上真切地表现了出来:就人与宗教而言,绝不是一切自然的、可以用理性所把握的关系,而是人类的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关系,处在彼岸世界的上帝对人来讲是无限的、超自然的、超人类的。人祈求宽恕与上帝的仁慈之间绝不存在因果关系,表面上是人在请求宽恕,但实际上上帝的仁慈是先在的。意识到自己有罪的玛丽花只需观念一转,便一定会由衷地“感到自惭形秽”,摧毁自己自然的素质和力量,以便接受超自然的东西和基督教的恩赐。如果说,玛丽花在幼年和童年的苦难经历中还依然保持着晶莹清澈的人性的话,那么,此时沉浸在自由和痛快之中的她,显然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感受与思考,被贬为适合神意的、基督教化的自然。她充满活力的、栩栩如生的自然的和精神的力量以及各种自然的天赋都化为灰烬,成为永恒性的观念,剩下的只有乖乖地接受上帝的洗礼。这便是宗教的伪善作祟的结果,“把人身上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与人相左的东西,而把人身上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人的真正的所有”。(20)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21页。
最后,在塞利加·维什努看来,支配玛丽花的已经不是人的自我意识,而是基督教的宗教意识。她唯一拥有的只是用基督教的观念来谴责自己。当她将自己感觉自己卑下这样一种合乎人情的意识变成了感觉自己永远不可挽救这样一种基督教的、因而也是难以忍受的意识的时候,她的心灵就被罪孽深重的感觉所支配,这意味着她必将变成忏悔和赎罪的牺牲品。她穷途末路,唯有去到上帝跟前,请求上帝把她在尘世间受到的每一点苦难,都以“忏悔的荣誉和赎罪所应有的永恒的奖励”的方式补偿她。她的人类之爱转化成为宗教之爱,对尘世幸福的追求转化成对永恒福祐的追求,世俗的满足转化成对神圣的希望,同人的关系转化成同神的交往。总之,她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上帝,只有彻底脱离尘世,进入修道院,在那里慢慢地枯萎和死去,她才有可能摆脱自己有罪的意识。这便是鲁道夫为玛丽花找到的唯一的得救之路。塞利加·维什努把玛丽花的生命称为“无辜的”存在、“短暂的”存在:她确实是无辜的,只是由于论证“普遍的世界秩序”的存在的需要,她的命运才被关注;她的生命过程也一定是短暂的,因为“普遍的世界秩序”必将永存,就像在宗教意识里“罪恶”是永存的一样。
从马克思的视角看,在小说《巴黎的秘密》中,欧仁·苏把玛丽花的命运归咎于鲁道夫善良而周全的“意志”,而没有深入到这样一个16岁的少女沦落为妓女的悲惨命运之中探究罪恶的社会根源,这反映了他同情弱者、拯救人性的愿望的虚幻性。而塞利加·维什努根据这些素材和情节,却把玛丽花的形象做了思辨的处理,使她的命运变成思辨的“批判”的产物,变成纯粹的观念的产物。这是他思考世界的方式导致的结果。在塞利加·维什努看来,“普遍的世界秩序”和现实世界的发展要结合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整体”,“就必须使两种因素——这个混沌世界的秘密同鲁道夫借以洞察和揭露秘密的明确、坦率和信心——在一个人身上互相冲突……雏菊也就执行着这个任务”。(21)塞利加·维什努:《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2页。这是塞利加·维什努在赋予鲁道夫以思辨秘密的揭示者的使命之后,又必然要诠释出的玛丽花人生经历中的思辨因素。虽然塞利加·维什努也称玛丽花为Marienblume,(22)这个德文词的含义是“雏菊”。但其真实用意却是要她执行将“普遍的世界秩序”与现实世界具体地、思辨地统一起来的形而上学的使命,以证明思辨哲学所谓的“真正统一的整体”的存在与合理性。因此,玛丽花的人生经历、她身上所隐藏的世俗世界的秘密,在塞利加·维什努那里不过只是为了能证明一点:个人力量的发展必然诉诸“普遍的世界秩序”。不仅如此,塞利加·维什努还用神学的逻辑对玛丽花进行了世俗的评价,“而她本人还是没有什么需要宽恕的”“她怀着人所罕有的内心纯洁而与世长辞了”。我们看到,他放在玛丽花墓上的是一束教会辞令的枯萎、干瘪的花朵!在活生生的生命面前,“批判”的神学显得多么地无力和丑恶!
一部小说、一个普通女人的命运,引发不同的评论者之间不同思路的评论,这当然是正常的、常见的,但不意味着这些不同的评论者、不同的思路之间没有客观和主观、真实和虚幻、到位和偏差、深刻和肤浅等程度上的差别。《神圣家族》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理论合作、他们在世时定稿和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是引起研究者高度关注和具有广泛影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本文的解读表明,它既是一部对论敌展开严苛的批判、对其观点和体系给予彻底解构的著述,更是一部建构之作,即通过玛丽花命运的揭示,马克思揭示了“以纯观念、精神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和“以现实、历史和实践视角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新哲学”在宗教本质和人的“救赎”方面的差异和逻辑,这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及其丰富内涵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