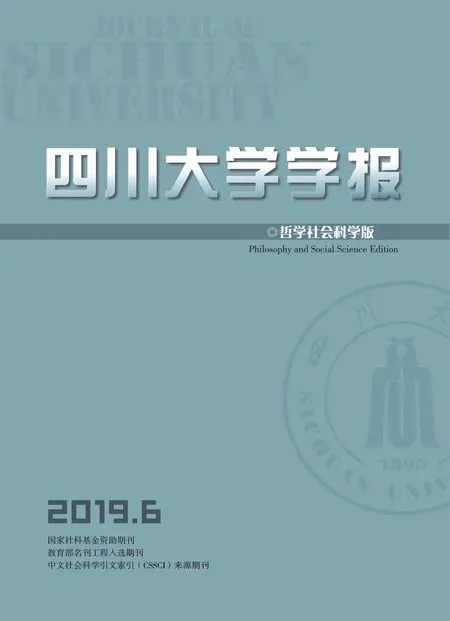吴经熊法学思想中的西方与东方
一、前 言
在近代中国留洋归来、“学贯中西”的法学家中,吴经熊(John C.H. Wu)可能是最为西方人所知也最有魅力的一位,堪称“法学界的林语堂”。(1)在耶鲁大学取得法学学位的王宠惠的政治生涯比吴经熊要显赫得多,也有英译《德国民法典》的美谈;但是王宠惠谈不上著作等身,也没能如吴经熊一般得到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庞德(Roscoe Pound)、魏格莫(John Henry Wigmore)、卡多佐(B.N.Cardozo)、斯塔姆勒(Stammler)等众多西方法学巨擘的青睐。吴经熊(1899—1986)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科,后赴美留学、获密歇根大学法律博士,他与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W.Holmes)是忘年之交。作为近代中国法律人的代表,吴经熊的经历非常丰富,他曾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兼法律系主任,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研究员,夏威夷大学教授,又历任上海特区法院法官、院长,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立法院外事委员会主席,立法院宪法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民国宪法起草人,驻外公使。其间,他还成功开办过律师事务所。他是著名的法学教授、重要的立法者、成功的律师、出色的法官,还是文学家和哲人。与林语堂所谓“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自我评价类似,吴经熊将其英文自传命名为《超越东西方》(Beyond East and West),这不仅是其自我定位,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期许。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吴经熊其人其学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2)笔者以吴经熊为主题检索中国知网,相关的期刊论文有77篇、硕博士论文有20篇,未收录的研究成果应该还有不少(最后检索时间为2019年6月15日)。本文仅仅是对前人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小小的注脚。
二、吴经熊其人其学的“全盘西化”
与近代中国留学欧美归国的大部分法界精英(如王宠惠、王世杰、钱端升)相较,吴经熊似乎更加“西化”;作为一个坚持个人主义的天主教徒,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大时代,他显得特立独行,甚至有些“玩世不恭”。他一结婚,便提出与一直照顾、支持他的哥哥分家,理由是“先小人,后君子”,免得妯娌不和,影响兄弟感情。在工作方面他尽职尽责,但常常凭兴趣换工作,绝对谈不上鞠躬尽瘁。他的婚姻是包办的,他的太太甚至不识字,他先是以花天酒地的方式来逃避不幸的婚姻,继而又皈依天主、找到了精神的寄托。(3)参见吴经熊:《超越东西方》,周伟驰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少年得志”的吴经熊一生的机遇实在是令人羡慕,他也任意挥霍自己的机遇,对任何重要职务都不十分眷恋。他留学归国即任教于东吴法学院,是“整个国家薪水最高的教授”,满心要通过法学教育来推动中国法的变革。他四处募集资金、计划设立一个名为霍姆斯法律研究院(Holmes Law Institute)的国际化的法学教育研究机构,虽然他的宏大计划很快遭遇挫折,但他的兴趣也就此转移。(4)William P. Alford and Yuanyuan Shen, “‘Law is My Idol’: John C.H. Wu and the Role of Legality and Spiritualty in the Effort to ‘Modernise’ China,” Essays in Honour of Wang Tieya, edited by R. St. J. Macdonald, Berlin: Springer, 1993, p.49.1927年,他出任上海特区法院的法官,很快出类拔萃,年方三十即担任临时法院院长。一家美国报纸甚至称赞其为“法官席上的所罗门王”,中文报纸则呼其为“吴青天”。可是吴经熊很快对法官工作厌倦了,并且不顾忘年之交霍姆斯的反对,于1929年“重回美国深造,加强自我修养”。(5)参见吴经熊:《超越东西方》,第129-136页。霍姆斯借用普林尼的事例讽喻吴经熊应当在职业法律人的长跑中持之以恒:“致力于为公众服务”,“解释法律,执行正义,这乃是哲学的一部分且是最高尚的部分,这就是将教师所教的理论实践出来。”1930年回国后,他先后以律师、立法委员(宪法草拟者)为主要职业,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他还受蒋介石私人聘请(每月津贴一万元)翻译《圣咏集》和《新约》,来补贴家用。1946年,曾任立法院外事委员主席之高位的吴经熊欣然“低就”,赴罗马就任国民政府驻梵蒂冈公使;尽管梵蒂冈只是一个微型国家,但对于天主教徒吴经熊来说,其意义则异乎寻常。1949年,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之中,吴经熊被老友——行政院长孙科召回,同意“临危受命”,加入孙科组建的内阁、担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并提出司法独立、提高法官薪金、帮助教育囚犯等条件。可他未及就任,孙科内阁就垮台了,对此吴经熊也不以为意,“既不高兴也不难过”,“凭借着上主的恩典我已获得了道德上的胜利,这就是一切啊。我告诉朋友们:‘你看看,做为一个大方的人就有好报!’他们都笑了。”(6)吴经熊:《超越东西方》,第387-392页。很快他便接受夏威夷大学的邀请赴美讲学。
吴经熊早年生长于近代中国开埠较早的通商口岸宁波,在出国留学前历经教会学校与美国循道会在上海所建的“中国比较法学院”(东吴法学院前身)的教育。尽管幼年在私塾就读时读过一些儒家经典,但在吴经熊幼年所处的教育环境中,“英语已经是所有学校的第二语言”,他本人“从9岁上小学既已开始学习英语”。他甚至在英文自传中要特别辩白一句:“当然了,我未忘掉自己的母语。我用英文思想,却用中文感觉,这便是我只写汉诗的原因。”(7)吴经熊:《超越东西方》,第46、48页。吴经熊早年(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有多种中、西文法学著作问世,其英文作品得到多位西方法学名家的引用与好评;可到中、晚年时,他几乎忘了自己是一个法学家,转而研究东西方宗教与哲学。与同时代的其他法学大师们相比,吴经熊的法学思想更加超脱、空灵,能超然于众人之上做“逍遥游”,甚至超越中西。吴经熊这样描述他这种空灵的法学研究:“作为一个受过古典精神熏陶的人,我怎样从事法律研究,大概是可笑的。我承认我对法律女神的激情似乎过于离谱的浪漫。我只能以永恒的眼光来审视法律问题。除开法学大师,我还求助于老子、莎士比亚、斯宾诺沙、歌德、惠特曼、威廉·詹姆士等人,以及其他许多的外行人,如孔子、康德和杜威。不知什么原因,我在法律和音乐这如此不同的东西之间竟发现了许多的相似之处,这一定与我分析能力的欠缺有关才对!对于生命奥迹的意识,象幽灵一样不断伴随着我,即使在判决一个很不重要的案子时,亦是如此。我的小宇宙沐浴在充满了宇宙感的柔光之中。”(8)转引自王健:《超越东西方:法学家吴经熊》,《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2期,第218-219页。
吴经熊为人为学是如此“西化”,他与西方法学界的交流也十分通畅:其用英文写就的法学文集得到不少欧美法学大家的引用与推介,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通过阅读吴氏青年时期的中英文法学论著,学者或可得出如下结论:吴经熊的人格特质与学术范式基本上是西方的,他对于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更接近于海外汉学的外部视角。
三、争讼与非讼、自由与保守
如前所述,吴经熊的法学思想从整体上看可以说是相当西化的;可是我们考察吴氏在具体法律问题上的观点,就会发现他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全盘西化”。甚至在吴经熊早期的法学论著中,便已展现出东方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持续对话。吴氏在争讼与非讼、自由与权威等关键问题上的论述相当“变通”,或者说其思想存在前后不一致乃至根本的“断裂”,至少他三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个绝对的西方主义者。
在吴经熊的作品中,有两篇大约发表在同一时期的文章,其观点南辕北辙,甚至可以说是自相矛盾。其中一篇批判儒家“非讼”与法律道德化的思想,鼓吹“为权利而斗争”,将诉讼作为实现真正的社会和平的必由之路;另一篇则高度称赞中国传统的社会和谐观念,并引用《易经》所谓“讼则终凶”。有趣的是,这两篇都被收入吴氏1933年出版的《法律哲学研究》一书之中。
在“中国旧法制底哲学基础”一文中,吴经熊对中国传统的“非讼”思想进行了辛辣批评,认为“非讼”造成了民族心理的压抑与社会矛盾的最终激化,而唯有争讼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平:“道德家固然用不着奖励争讼,……但是将争讼的本身当作不道德的勾当,那是一桩非常危险的事情。……法学的昌盛,法治精神的发达,都是以争讼为基础的。没有争讼,就不会有真理,也不会有公道。法律以争讼为发源地,以公道为依归处。”“将不能拔除的自然现象当作根本上不道德的,并且讳莫如深的事情,其流弊不一而足”:其一,“民族容易落于‘心理压迫’的状态。心理虽有冤屈,因为礼教的缘故,不敢直说,恐怕动辄得咎,所以还是忍耐为妙。但是人心总非草木可比,忍耐到相当程度,不能再忍了,于是怒不可抑地大发雷霆起来了。压迫的程度愈高,反响亦愈厉害,甚至一发难收,简直不顾三七二十一地作村妇地谩骂了。如此说来,谩骂就是那种禁止争讼的道德的私生子!天下事往往因理想太高其结果适得其反。……我们如果想铲除谩骂的习惯,非将争讼变作一种艺术和科学不可。法律就是争讼的艺术和科学哩。”其二,“民族容易学得一种假冒为善的脾气。实在心里很不平,还要咬紧牙齿装作大量,……最高尚的道德是要我们对于不满的事情尽管爽快的说,而对方也用不着见气,因为要知道‘人心之不同正如其面’,世间没有两个人思想是一样的。真正和平,是从争讼里寻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吴经熊对于“非讼”文化做了极其彻底地否定,用“危险”“压迫”“伪善”等等严厉的字眼来形容“非讼”,将其视为法律现代化的大敌。吴氏甚至大胆断言,整个中国传统法制的哲学基础——包括天人交感的宇宙观、道德化的法律思想与息事宁人的人生观——与现代法制是根本不相容的:“孔子和儒家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刘姥姥”,“在这种心理空气之下,自然也谈不到私人的物权或债权了,更谈不到独立存在的民法了”。(9)吴经熊:《中国旧法制底哲学基础》,《法律哲学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4-65、59、63页。
可是,在其“三民主义和法律”一文中,吴经熊关于中国传统诉讼观的看法则几乎完全是正面的,他引用中国古代兄弟争田,审判官员以兄弟之情晓以大义,最终使兄弟和解、撤诉并重归于好的例子,高度赞扬中国古代官员融情入法、调解息讼的传统。吴氏高度赞赏国民政府通过现代立法复兴传统民事调解制度,称之为“民族精神的产品”:“究竟什么是我们民族最好的特性呢?我的答案便是:‘中和之道’。‘中’就是不偏的意思;我们民族不喜欢走极端的,不容易变成过激的。‘和’就是不高兴争讼的意思;我们相信和衷共济,讼则终凶。所以专打官司的人,我们名之为‘讼棍’。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在中国法律史上,这种至诚开导的例子不可胜计。即就现在的法律而论,也常有中和的表现。比方新近立法院颁布民事调解法规定,民事初级案件和人事,如婚姻等类,都要经过调解,不得即行诉讼。各法院都设有民事调解处;法官们用他们的苦口婆心谆谆善诱。”(10)吴经熊:《三民主义和法律》,《法律哲学研究》,第97页。
为什么吴经熊在同一本书中一方面鼓吹“为权利而诉讼”,另一方面宣传“为和谐而息讼”?笔者尝试从两篇论文写作的时间轨迹上探寻吴经熊在争讼与非讼问题上观点的变化,可原书并没有标明两篇文章写作的时间顺序。通过检索发现,在《法律哲学研究》结集出版之前,这两篇论文并没有公开发表于报刊,所以也无法由此判定其写作的具体时间。(11)参见田默迪:《东西方之间的法律哲学:吴经熊早期法律哲学思想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2页。该书所附田默迪编“吴经熊著作表”也认为这两篇文章在结集之前尚未出版过。似乎唯一的线索便是在《法律哲学研究》一书中,“中国旧法制底哲学基础”排序在前,“三民主义和法律”排序在后。不过从两篇文章所提及的写作背景看,“中国旧法制底哲学基础”的基本思想形成于吴经熊1929—1930年在美国讲学之时;(12)“最近我在美国演讲,有几位对比较法学有兴趣的同事向我提出许多疑难杂题”,“我现在要把答复他们外国学者的话略微说给读者诸君听听”。吴经熊:《中国旧法制底哲学基础》,《法律哲学研究》,第56-57页。)“三民主义和法律”则是写于1930年12月民法典完成之后。(13)文中提到了1930年《民事调解法》与新《民法》的先后颁布。看起来这两篇论文的写作时间前后相差至多不过是一两年,“碰巧”在这段时间里吴经熊完成了从“在野”到“在朝”的转变。1931年吴氏就任立法委员,并且与孙科、宋美龄等国民党要人保持了长期的友谊。
与同样留学英美的自由派学人胡适、罗隆基等人相较,我们很少看到吴经熊对国民政府发出批评的声音。反倒是在吴氏的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到他鼓吹“国父”的“三民主义”,宣讲立法院长胡汉民所提倡的中国传统“王道精神”。在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保障问题上,吴经熊的见解甚至与同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张知本相较,也显得更为保守。(14)张知本早年留学日本习法政,是同盟会元老,在国民党内属于西山会议派;如果说吴经熊从政只是“玩票”的话,张知本则是典型的政治人物。在五五宪草的起草过程中,张知本、章友江等朝野人士均主张废弃宪法基本权利条文中的“法律限制”字眼、采宪法直接保障主义;但吴经熊则反驳说对人民基本权利采宪法保障主义并不现实,规定宪法基本权利受法律限制并无大碍:“二十世纪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已经离开纯粹的自由很远了”;更何况,人民权利的被侵害,主要不是因为“‘依法’限制的缘故,实在是行政官吏未能依法办理所致”。(15)参见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3-127页。
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国难”的现实与“救亡”的压力,有一批留学欧美、曾经服膺自由民主思想的法政学人转而鼓吹“开明专制”:例如“蒋廷黻在自由民主的力量和臆想中的专制的功用之间被撕扯着,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最后还是决定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通过考察德国和意大利的崛起,他们“发现专制政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曾留学哈佛的政治学家钱端升“是这种世界潮流观念的代表人物”,他“设想的制度是‘一种智识阶级及资产阶级的联合独裁,但独裁的目的则在发展民族的经济’,在意识形态上,这和三民主义是吻合的。他同意孙中山提出的‘一盘散沙’理论,认为中国人需要组织起来”。(16)参见冯兆基:《寻求中国民主》,刘悦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5-111页。吴经熊法学思想中自由与保守、西方与东方的相互拉扯,在他那一代学人中并非特例,甚至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符合“大时代的潮流”。
笔者并不打算将吴经熊法学思想的重大转变简单归因为其从政的经历,事实上吴经熊对于政治的兴趣并不是特别浓厚。与先后做过民国北京政府总理、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法学家王宠惠相较,他只是政坛中的“票友”和“技术官僚”。1924年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吴经熊年方25岁,到1933年起草宪法时也不过34岁。吴经熊从校园走向社会甚至参与政治,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其法学思想中的东方与西方的平衡可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四、吴经熊法学思想中的“西学中体”
在经历了短暂的“全盘西化”之后,吴经熊在而立之年便已转向“中西会通”。吴经熊对于将东、西方法律传统截然对立的二分法逐渐不以为然,他认识到欧美法律体系并非铁板一块、英美德法的法律哲学也可能大相径庭,中国法律与法学现代化的途径乃是在纷繁复杂的西方各国立法经验与法学思潮中择善而从。而所谓“善”的标准,就是移植的西方法律与思想是否与中国固有的民族性相容。
1930年代国民政府民法典颁布,有人将其条文与德国、瑞士等国法典逐条对校,发现“倒有百分之九十五是有来历的,不是照账誊录,便是改头换面”,这是否意味着民国的立法工作毫无价值呢?对此,曾任民法典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立法委员吴经熊解释说:“世界法制,浩如烟海;即就其荦荦大者,已有大陆和英美两派,大陆法系复分法、意、德、瑞四个支派。我们于许多派别当中,当然要费一番选择工夫,方始达到具体结果。选择得当就是创作,一切创作也无非是选择。”“立法本可不必问渊源之所自,只要问是否适合我们的民族性。俗言说的好,无巧不成事,刚好泰西最新的法律思想和立法趋势,和中国原有的民族心理适相吻合,简直是天衣无缝!”(17)吴经熊:《新民法和民族主义》,《法律哲学研究》,第172、173页。欧美各国法制有所差异、西方法学流派众多,根据中国的实际对于西方制度有所选择,基于自身的文化背景对于西方法学中的某一或某几流派“择善而从”,这或许也是“中体西用”的表现。吴经熊这么一个看似“全盘西化”、秉持“个人主义”的人物,其法学思想依然是融汇中西。吴经熊本人的法学思想深受霍姆斯和庞德的影响。而这两位法学家在当时美国法学界都可谓特立独行之辈,霍姆斯被称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中“伟大的异议者”,庞德与当时美国主流的形式主义法学也是格格不入。不过霍姆斯和庞德所代表的“泰西最新的法律思想”,倒是与中国传统法哲学思想有“会通”之处。
霍姆斯的名言是“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其所代表的法律实用主义拒绝建立一个哲学系统,因为任何系统都不能持久;把握其法学思想必须从具体的生活中、只言片语中抽丝剥茧出来,以便从片断的洞察与透视中建立起他精神世界的整体。(18)参见田默迪:《东西方之间的法律哲学:吴经熊早期法律哲学思想比较研究》,第161-185页。吴经熊本人在其自传中也认为他与霍姆斯相比,后者更加“东方化”。在霍姆斯看来,“系统思想是贫乏空洞的,洞见才是有价值的,而洞见易受系统的扼杀”。(19)吴经熊:《超越东西方》,第104-105页。霍姆斯充满“禅意”的法学观,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可以说是十分接近。(20)尽管试图调和霍姆斯和斯塔姆勒(旧译斯丹木拉)的法学思想,但吴氏首先还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清华大学贺麟先生在民国时期写了一本书叫《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对于近代中国的哲学学人有一些非常辛辣的评语,他说有一些人表面上接受西方思想,然而其实不明白西方思想的根底;他们所接受的并非真正的西方思想,而仍然回到旧的“窠臼”;但这些人喜欢用他们自己也不完全懂的新名词、新口号,喜欢做翻案文章,抬出一些他们尚未消化的西方某些学派的学说来攻击古人;他们学习西方哲学的经过,仍然是先从外表、边缘、实用着手,功利主义、实验主义、维也纳学派等,五花八门都已经应有尽有;“然而代表西方哲学最高潮的、需要高度的精神努力才可以把握住的哲学,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从康德到黑格尔两时期的哲学,却仍寂然少人问津”。(21)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38页。贺麟先生对于当时中国哲学界的评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印证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包括实用主义法学)在中国的流行,一方面是源于胡适、吴经熊等留美精英的鼓吹;另一方面也是源于其与传统中国哲学有“会通”之处,易于中国学人理解和接受。吴经熊所谓霍姆斯在思想上比自己更像东方人,并非无因。(22)参见吴经熊:《超越东西方》,第148页。
庞德作为现代社会法学派的领军人物,提出“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强调法律的社会目的、效果与作用。他发展了耶林的功利主义法学,提出“社会利益保障说”,强调司法中应对社会利益加以衡量、实现社会利益,而不是机械地依照法律实现所谓“正义”。吴经熊先后在美国学习、讲学的时代(1920—1930),法律形式主义(类似于今天所谓的“法教义学”)仍然在美国大行其道。尽管吴经熊先后做过法官、律师,可他本人对于技术化的形式主义法学毫无兴趣甚至心怀抵触,1930年他再次来到哈佛访学而大失所望:“我在那里不是很快活,因为庞德离开了那儿”,“我与约瑟夫·比尔相处得很好,但他对我助益不大,因为他更算一个法律技术员而非法哲学家。我的精神不振,我的心灵一片空白,我多少有点觉得离开中国是个错误……”(23)吴经熊:《超越东西方》,第140页。吴经熊已经认识到现代法律并非万能(“法律只能革面,不能洗心”);他把以庞德为代表的西方法律社会化思潮与传统中国的“王道”“大同”思想相类比,用庞德的思想来“打倒”机械化的形式主义法学,“拥护主张实际公道的法学”,并在立法中贯彻这一思想。(24)参见吴经熊:《六十年来西洋法学的花花絮絮》,《法律哲学研究》,第223-226页。与欧美近代资本主义崇尚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的理念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财富观与“大同”的理想。吴经熊对于20世纪以来西方法律社会化的潮流“心有戚戚”,认为:“泰西的法律思想,已从刻薄寡恩的个人主义立场上头,一变而为同舟共济、休戚相关的连带主义化了。换言之,他们的法制与我国固有的人生哲学一天接近似一天!我们采取他们的法典碰巧同时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文艺复兴中重要的一幕,也就是发挥我们的民族性!胡汉民先生曾说过新《民法》为我们民族性中根深蒂固的王道精神的表现。”(25)吴经熊:《新民法和民族主义》,《法律哲学研究》,第176页。
五、结 语
吴经熊在步入不惑之年后似乎与法学与法律职业渐行渐远,从“将法律作为神明”转而虔信天主,并将研究重心转向宗教与哲学。有学者考其缘由,将其归因于吴氏在参与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的过程中遭遇了重大挫折,故而远离了法律职业、放弃了法学研究。关于吴经熊中年职业、学术兴趣与信仰的转向,安守廉教授与沈远远教授的观点与上述看法略有不同:他们不赞成将吴经熊的为人为学前后截然两分的观点,尽管不少学者甚至吴经熊本人的自传都认为其前后段泾渭分明。但也许正是在移植欧美制度与思想、推动中国法律彻底西方化的过程中遭遇挫折,才让吴经熊认识到现代法制建设的本土资源问题。(26)Alford and Shen, “‘Law is My Idol’: John C.H. Wu and the Role of Legality and Spiritualty in the Effort to ‘Modernise’ China,” p.52.
其实,从吴经熊作品的发表时段来看,也不能得出吴经熊早年在法学以外心无旁骛,中年之后则放弃了法学研究的结论。吴经熊在1930年代即有不少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学的作品问世,例如后来结集为《唐诗四季》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成果,便在1938—1939年用英文发表于《天下》杂志。(27)参见吴经熊:《唐诗四季》,徐诚斌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事实上,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吴氏仍有多篇法政论文问世。(28)吴经熊的著作年表参见田默迪:《东西方之间的法律哲学:吴经熊早期法律哲学思想比较研究》,第208-223页。吴经熊在1955年还出版了大部头的英文法学专著《正义的源泉:自然法研究》,他在书中特别强调:“法律,乃是为了人所创制,而非人徒以法为目的。所以就终极言之,法之目的,不可或缺对人之终极或人之目的之关照。”(29)吴经熊:《正义之源泉:自然法研究》,张薇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11页。吴氏虽然自述其观点乃是受到圣托马斯的影响,但这也与中国传统的法观念符合若节。
如前所述,即使在吴氏早期的法学思想中,仍然包含着“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些特征”,“无论吴氏对西方文化保持多么开放的态度,他总没有断绝自己文化的根。虽然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在他身上,从表面上看,暂时还不很明显,但在深处却继续存在着,而且逐渐影响他思考的努力”。(30)田默迪:《东西方之间的法律哲学:吴经熊早期法律哲学思想比较研究》,第68页。从25岁留学归国到50岁离开祖国,吴经熊担任了法学教授、法官、律师、立法者、制宪者、外交使节等多个职位,很少人有机会从这么多个角度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法律问题。作为法理学的研究者,他在人生的后半段并没有远离法律与法学;他自觉不自觉地致力于东西方宗教与哲学的研究,或许正是为了从头做起、真正“超越东西方”,最终实现中国法律的“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