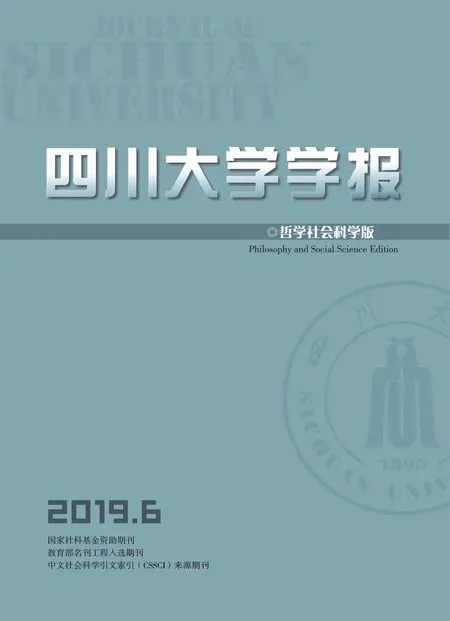中国当代文学文献的特殊困境及解决方向
刘福春
中国当代文学文献相对于中国古典文献而言,自然是特殊的,即便是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它仍具有独特性。虽然切近当下,似乎得之甚易,实则由于特殊性和复杂性,当代文学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有不可轻忽的难度,更有其不可轻忽的必要性,或许应当提到建立学科的高度,予以重视。
如:根据不同地质类型进行砂、石取样,以上、中、下三层为主进行等量分层样品,合并后作为试样,避免仅以下层或某一层为试样,导致实验室样本缺乏代表性,增加检验结果与真实情况的差异。
一、时空延展:当代文学文献整理的困境
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始于1949年,至今已经70年整,并不算短,却远不能与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相比。然而作为发展和成长中的文学形态,当代文学与封闭的古代文学不同,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70年来,当代文学已经遗留下丰富的文献,并且以加速度增之未已。因此当代文学文献不仅有过去时,还有现在时和将来时。作为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并将继续发展下去的当代文学,其文献整理工作不仅要发掘和打捞渐渐远去甚至湮灭的历史,还要与当下的文学生产和相关文献保持同步并持续跟踪。这是一列现在还无法知道终点的列车。文献加速度膨胀,搜集整理工作也相应加速度递增,对学者的视野、精力和判断力形成愈来愈高不可及的期待。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开始编写《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稍后所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1)》收录了文艺理论、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概况,还重点记录了1980年的创作情况、重要会议等,收有《1980年文学纪事》《1980年中篇小说篇目》和有关重要文献等。(1)《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这项与当代文学同步的文献整理工作至今已经持续了近40年。另外,从1999年起,白烨开始选编《中国年度文坛纪事》,(2)白桦选编:《中国年度文坛纪事·99卷》,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栏目有《热点扫描》《文案寻踪》《作品档案》等,至今也坚持了20年。
这些文献整理工作既是同步整理,也是持续的追踪。我编撰《中国新诗书刊总目》,(3)刘福春编撰:《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原本只是收集已经成为历史或被历史淹没的文本,结果也变成了没有终点的旅行。最早我是整理现代新诗集,也就是1949年10月前出版的新诗集,这一部分基本完成后又开始当代新诗集的搜集。当时以为当代部分要比现代部分容易,但着手之后才发现更难,几乎是一个永远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我曾打算把这工作截止到20世纪末,但是文献汹涌而来,搜集整理工作难以遽停。2006年《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出版后也没能收束作结,而是修订并补充了大量新出版的书刊。我决定将这一工作截止于2019年12月,相距第一本新诗集出版于1920年1月,正好是中国新诗集出版100年。然而人为的“截流”毕竟是研究者和整理者迫不得已的“别无选择”,反衬的正是层出不穷的当代文学文献对研究者和整理者的生命有限性和学术连续性的挑战。
不只是作为总体的中国当代文学文献整理得不完整,具体到有些作家文献的整理也是难以齐全。像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等一批从大陆到台湾的诗人和作家,相关文献地处两岸,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搜集起来都会有一部分缺失。如台湾文学馆出版的《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纪弦》(4)《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纪弦》,须文蔚编,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1年。中的《文学年表》,1949年以前的部分仅3页半,只是收录了纪弦先生所出版的诗集和所编的诗刊,而之后的部分则有19页,除了作品集之外,还记录了大量单篇发表的作品。
在时间的难度之外,更有空间的难度。中国当代文学地域涵盖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由于政治等多种因素和多年相互的隔绝,造成了大陆与台湾、香港和澳门各地区文学的差异性和相对的独立性;而随着诗人、作家的全球流散和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日益关注,当代文学的边界又不断向海外延伸,几乎扩大到了全世界。从字面意义上看,“中国当代文学”与不包括港澳台的海外华文文学实为不同的概念,然而它们之间却有交叉性和连续性,譬如严歌苓、严力、高行健、高尔泰等人的写作,既是“中国当代文学”,也是“海外华文文学”,去国前后难以截然两分。由此,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在时间上是有始无终,在空间上是无远弗届。这就给当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使得所出版的很多相关文献专书显得很不完整。如前面提到的《中国文学研究年鉴》和《中国年度文坛纪事》都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的文学。《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倒是全包括了,但是缺失很多。而且台湾部分主要是使用了张默先生主编的《台湾现代诗编目》,如果没有张默先生的这部著作及其授权使用,遗漏就更多了。这样的问题并不只是在大陆存在,台湾的此类出版物也有类似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出版物分为正式出版物和非正式出版物。一般地讲,正式出版物是由正式出版机构出版,非正式出版物也称内部资料,仅在行业内部交流,不公开发行。其实在这两种出版物之间还有一些特别的出版物,比如用香港和海外书号出版的出版物、不规范的“正式”出版物等。文学领域的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各种不规范的“正式”出版物数量庞大,质量参差,导致文献搜集整理工作所面临的是复杂甚至混乱的文海书山。在此仅以新诗的“非正式出版物”为例,讨论当代文学文献搜集整理的另一重难度。
二、搜集难题:当代文学出版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总之,由于时间的不断绵延和空间的不断拓展,如何全面地整理不同时空中的文学文献已成为一个难题。而中国当代文学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也已然不再是一个或者几个学者之事,甚至也不是一代或几代学者之事,这一工作召唤学科的成立、学界的协同和学术的传承。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大批新诗写作者,特别是年青写作者,自印了大量诗集、诗刊和诗报等新诗“非正式出版物”,譬如《今天》《非非》《他们》等刊物和北岛的《陌生的海滩》、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海子的《小站》等诗集。这些新诗文献,一是数量大,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到底有多少这种文献,至今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初步估计至少应在万种以上;二是种类多,有诗刊、诗报,还有自印的诗集,从印刷方式分有油印本、复印本、铅印本等;三是产生地域广,从首都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学校到工厂,都有这类出版物,尤其高校居多;四是印数少,特别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油印的出版物,受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大多印量很小,多则几百册,少则几十册;五是发行范围窄,此类出版物为非卖品,多以自行交换或赠送方式发行,范围不是很广;六是图书馆少收藏,受收藏制度限制,此类出版物图书馆基本不收藏。数量大、印数少、发行范围小、图书馆又不收藏,这是研究界对此类新诗缺乏研究的主要困扰,也给文献整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2008年7月10日国家图书馆发出《关于“非正式出版文献”的征集函》,称“近年来,‘非正式出版文献(内部资料)’的价值越来越被社会所重视和认可,但由于其形式多样、发行范围小、传播不广且易流失等特点,给此类文献的收集、保存和利用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使此类文献中一些学术性与资料性较强的文献得到妥善保存与利用,国家图书馆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非正式出版文献(内部资料)’”。(5)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非正式出版文献征集》,http:∥www.nlc.cn/ /dsb_zx/dsb_zjqs/201111/t20111115_55003.htm,2019年8月10日。国家层面的认可和呼吁,或能使图书馆的“非正式出版文献”收藏丰富起来,以利于研究和文献的整理。
虽然“智”与“勇”是内政与外交的需要,是贵有天下的君主所必需的品质,但在孟子那里,二者已经与“仁”不直接联结,而降低为一般性的德目。
如何整理和利用这些文献是个难题。目前检讨类文献已经整理出版了一些,譬如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了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其中收有1966年4月2日的《思想检查报告》、1966年7月22日的《我的交代》等。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是诗人郭小川在各政治运动中所作的各种检讨的专集。但揭发批判文献的整理和利用难度要大得多,一是这类文献除了政治批判,还包含一些对个人隐私的揭发;二是对于这些或主动或被动的写作,该如何面对成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常见的处理方式一是回避,二是修改,由此造成了“全集不全”的现象。如艾青在上世纪50年代写过《什么“芽子”!》和《把奸细消灭干净》二诗,并入选作家出版社1955年8月出版的《把奸细消灭干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讽刺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6月出版的艾青诗集《春天》中收有这两首诗,而且单独编有第六辑《把奸细消灭干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的《艾青专集》中的《艾青著译目录索引》也有这两首诗,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艾青全集》没有收入,其原因当不是没有发现而漏收。冯至1958年写有《论艾青的诗》一文,最初收入由作家出版社1963年1月出版的《诗与遗产》一书,此书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冯至全集》中被编入第6卷,并附有编者说明:“在《诗与遗产》一书中,个别篇章在写作时曾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作者事后曾为此深感歉疚,但为了尊重历史的原貌,本卷仍照原样予以收录,只是对有关当时被错误定性的人和事的提法在文字上作了少许处理。”(6)《冯至全集》第6卷,吴坤定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4页。可这少许的处理却是删去三千左右文字,其中删掉百字以上的有八处,最多一处删去一千多字。全集不全,可说是现已出版的多种作家全集的一个通病。(7)对此,我曾在《20世纪新诗史料工作述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第258页)中举例说明。
除了非正式出版物引出的文献搜集整理的复杂性难度,当代文学文献搜集整理工作还面临一些富有价值却也更加难以把握的文献,这就是进入上世纪50年代后,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为当代文学遗留下的大量特殊文献。如其中有一类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对作家揭发和批判的文献资料,与此相应地是另一类资料,即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作家所做的检讨。当时成集印制的这两类文献,有的是公开出版物,如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出版的《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等;还有的则未公开出版,如《讨论胡风文艺思想参考资料》(共五辑),以及1957年9月印制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1958年1月河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印的《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1967年9月福建省文联《批判文艺黑线》编写组编印的《蔡其矫三反罪行》和1957年9月印制的《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检讨》等。除了专集,散见于报刊的这两类文献也极为丰富,而最难见的则是档案中的相类文献。此外,作家在平时受到批评发表的检讨也颇常见。如1950年3月1日《人民文学》第1卷第5期刊出朱定的诗《我的儿子》,同年8月10日《文艺报》第2卷第10期刊出批评文章,10月25日《文艺报》第3卷第1期刊出朱定的《我的检讨与希望》。卞之琳在1951年1月10日《新观察》第2卷第1期发表诗歌《天安门四重奏》后受到批评,于是在同年4月10日《文艺报》第3卷第12期发表了《关于“天安门四重奏”的检讨》。
㉒王浦劬、赖先进:《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模式与机制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文革特殊年代也遗留下一些特殊文献,其中如红卫兵文学,出版的诗集有武汉钢二司宣传部1967年10月编印的《武汉战歌——抗暴诗选》,钢二司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钢工总新人印东方红兵团1967年10月编印的《江城壮歌》,开封市红卫兵代表大会《八二四红卫兵》《中原歌声》编辑部1968年编印的《暴风雨所诞生的——开封八二四战士诗选》,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1968年12月编印的《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等。除了这些作品文献,也有揭发批判文献,如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1968年印制的《批判毒草影片集——四十部影片毒在哪里?》、北京师大井冈红军1968年2月印制的《瞿秋白批判集》,以及原中国文联批黑线小组编、北京师范学院《文艺革命》编辑部1968年9月出版的《送瘟神——全国111个文艺黑线人物示众》等。
后期,将进一步优化路由,并扩展路由协议,使其满足更多的路由指标,如可靠、吞吐量。这是后期研究工作的重点。
无论是作品文献,还是批判文献,都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显示出复杂独特的社会、历史和文学经验。
三、展望:建立“当代文学文献学”学科方向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虽然只有70年,但文献数量却大得惊人,而且晚近的增长更呈爆炸性特征。我搜集1920年至1949年出版的新诗集,当时查阅了五十多家图书馆的相关收藏,之后又通过多种渠道继续查找,到现在见到的和知道的总计还不到两千种。而在近些年,一年出版的新诗集就应该接近或超过这一数量。当代文学文献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多,除了文字文献,还有大量的声音文献、图像文献等,尤其是网络文学的出现,如何整理这类文献更是一个有难度的新课题。
从异常成像图中可以看出成像效果比较好,中心埋深相符合,中间最大值出现在x0的左半侧,右侧出现负异常值,说明该地质体有质量亏损。在水平方向上出现负异常,说明横向分辨率比较高,整体可以分析可知,如果地质异常体分布范围比较广范,该方法的使用价值就越高。也能明显的区分正负异常值。
不仅如此,相较于古代文献,当代文献整理还面临另一个难题——版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8)《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第7页。由此,在当代文献整理方面,特别是对特殊年代遗留下的特殊文献的整理,受到版权所有人的影响或制约就在所难免。如何在“学术保存”“学术研究”层面解决“版权使用”问题,考验着我们的制度,也考验着我们的学术选择,这一问题的完满解决,将是影响文献史料能否在“公益使用”(学术使用)中发挥历史作用的关键。
中国当代文学文献的特殊性与整理的难度,越来越迫切指向一项学术要求,那就是建立“中国现代文献学”学科点,并在学科中分出一个重要的学科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学。作为一般通行的“现代”概念,自然也将所谓“当代”涵盖在内,不过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看,“当代”历史本身却有着更为繁复难解之处,对研究者的心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如此浩繁的当代文学文献,可能对“专业”和“专职”的期待,以及对团队分工协作的要求都更为迫切。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学界已有更多的研究者重视现代文学文献的建设,四川大学已筹建了中国现代文献学二级学科并获得批准。(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http:∥www.moe.gov.cn/s78/A22/A22_gggs/s8476/201907/t20190724_392053.html,2019年8月10日。学术界近年来的动向,特别是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划与决策,具有特别的积极意义,至少百年来的“现代文献”有了理直气壮的“学科”名目,而作为“现代”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的种种文献,也有了一个及时的学科归宿和工作的正当性。
现代文献学科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当代学人在学术交流的层面上深入开展校际合作,互通有无,彼此补充,从根本上扩大文献搜集的来源;同时,也能够借助“科研合作”的方式对当前的研究工作进行反省和检讨,拾遗补阙,在严肃的批评和挑剔中不断完善我们的工作方向,当然也包括当代文学文献的完整性。我相信,在当前学科建设的态势中,当代文献整理工作的某些难题终将获得解决或者部分解决,中国当代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将逐步形成自己的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中国现代文献学”不断发展壮大,为我们不断深入认识现代社会历史、更细致更准确地把握现代文学的精神脉动作出切实有力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