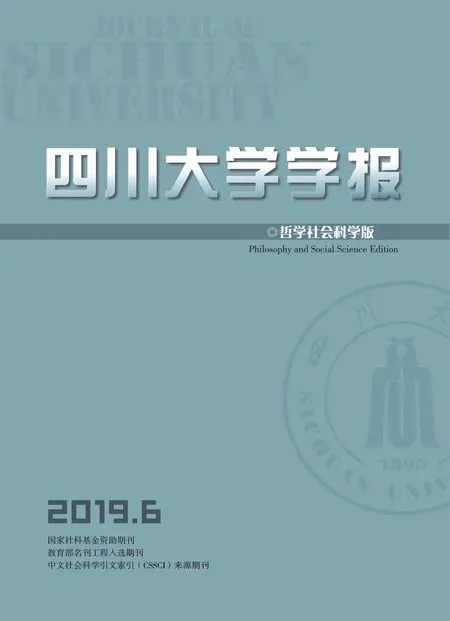陈纲案与明前期对赃官的惩治
赃官是历朝关注的重要话题,对赃官实现有效的惩治是历代司法的重要目标。明太祖朱元璋对赃官的严酷惩治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洪武末年,朱元璋明确宣布取消一切严刑酷法,规定后世子孙不许行用。(1)《明太祖实录》卷239,台北: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1962年,第3477-3478页。此后,类似“剥皮实草”的话题鲜有人提及。万历十三年(1585),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上书,以国初有剥皮之刑为例,要求对赃官进行重惩,遭到同僚弹劾。(2)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98页。
但是,洪武以后对赃官的惩治,的确是在朱元璋确定的司法祖制下展开的。(3)关于明代祖制的定义等,可参见吴智和:《明代祖制释义与功能试论》,《史学集刊》1991年第3期,第20-29页。关于祖制以及明代祖制的功能以及后代君臣对其的利用,参见郭厚安:《也谈明代的祖制问题》,《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5期,第3-10页;田澍:《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第153-159页;孙冰:《明代宫妃殉葬制度与明朝的“祖制”》,《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0年第4期,第72-74、93页;朱勇:《“祖制”的法律解读》,《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190-208页等。洪武三十年(1397),《大明律》最后成稿,刊布天下,朱元璋在卷首的《御制大明律序》中规定如下:“今后法司只依律与《大诰》议罪,……杂犯死罪并徒流迁徙笞杖等刑,悉照今定《赎罪条例》科断。”(4)《御制大明律序》,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页。其中的《大诰》则是“撮其要略”。关于附入《大明律》的《大诰》内容及其在明代司法中的影响,可参见黄彰健:《明清史研究丛稿》,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杨一凡:《洪武法律典籍考证》,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年等。这一司法祖制(5)吴智和先生在《明代祖制释义与功能试论》一文中认为,洪武祖制最核心的部分是《皇明祖训》,而这是狭义的洪武祖制,广义的洪武祖制则包括所有洪武时期确定的典章制度。洪武皇帝试图在各个领域为后代君主确立规制,因此笔者认为祖制所指为何,还是与具体的讨论和话题有关。就司法而言,朱元璋在《御制大明律序》中的规定殊为明确,可以视为这一方面的祖制。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包括了部分《大诰》条目的《大明律》与《赎罪条例》成为司法的主要依据;其二,《大明律》与《赎罪条例》的关系为依律定罪、照例发落。
清修《明史》,其中《刑法志》明确指出,洪武三十年《赎罪条例》颁行,“自是律与例互有异同”。(6)《明史》卷93《刑法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93页。即洪武司法祖制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其实存在矛盾,这一矛盾在赃官惩治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总体而言,《大明律》对犯赃官员惩治相对较重,而《赎罪条例》的行用使律条的规定得不到落实,赃官惩治出现不力的状态。
如何在祖制的格局下,解决祖制带来的问题,有效惩治赃官,成为洪武以后君臣的重要课题。特别是仁宗、宣宗以后,这一主题更为明确。这一过程一直延续至弘治十三年(1500)《问刑条例》颁行,有效的惩治以条例的形式得到固定。
成化十五年(1479),河南南阳府舞阳县陈纲案发。此案先经河南按察司分巡汝南道佥事胡恭初审;因为陈纲不服审判结果上诉,又经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戴中审理;成化皇帝将戴中的审理意见下发都察院,经都察院和刑部会议,前后历经四年,最后以成化皇帝的决断为依据结案。陈纲案对于展示成化后期朝廷对于赃官的惩治,包括其理念、程序和司法实践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审视明前期的司法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关于明代法制的既有研究,从时间上来说,多集中于明初与明代中后期。洪武以后至弘治时期的司法状况,研究相对薄弱,使得这一时期法制的建设和发展情况相对模糊。(7)吴艳红:《近三十年来明代法制史研究述评》,(日本)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史学》第22卷,京都:朋友书店,2012年,第41-53页。有关明代赃官惩治的研究也具有类似的特征,20世纪末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集中在太祖洪武时期;洪武以后,朝廷对于赃官的惩治具有怎样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深入的讨论相对缺乏。(8)参见蒋祖缘:《明初的惩贪倡廉与广东的吏治》,《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第61-65页;温晓莉:《明中后期的贪赃之风与法纪衰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7-11页;王世华:《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质疑》,《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56-159页;程志强:《张居正的惩贪思想及其实践》,《安徽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第375-379页;卿文峰、李交发:《明初低俸与重点惩贪及其历史启迪》,《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92-96、127页;徐晓光、路保均:《中国古代反腐惩贪法律制度述要》,《现代法学》1998年第4期,第115-120页;高春平:《顾佐惩贪与仁宣之治》,《晋阳学刊》1998年第6期,第87-89页;岳金西:《高拱的惩贪方略及其代价》,《古代文明》2011年第1期,第98-111页;Jiang Yonglin,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the Great Ming Cod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pp.160-164等。此外,柏桦、葛荃《公罪与私罪——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4期,第149-155页),许颖、曹铂《明清两代的公罪与私罪制度》(《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第223-226页)等文章也可参考。
本文讨论陈纲案,具体展示不同群体和个人在这一案件中的诉求和表达,以此考察这一时期赃官惩治中的几个核心问题:洪武祖制如何得到利用与调整,《大明律》与条例关系如何被理解与落实,以及赃官惩治中的不同目标如何得到调和。本文以陈纲案为中心对以上核心问题进行考察,希望能够厘清明前期赃官惩治和司法发展的具体样貌。
一、陈纲案始末
陈纲,河南南阳府舞阳县县丞。成化十五年七月,舞阳县县民张贤、何斌同时谋充收丝大户。其中张贤央请老人张景原引见县丞陈纲,许诺陈纲白银三两,请陈纲相助。陈纲听允,准令张贤收丝。之后张贤备足银两,准备呈送陈纲。其间何斌得知此事,扬言告状,陈纲因此惧怕,并未接受银两。但是何斌仍将陈纲听许张贤一事状告至河南巡抚李都御史处。所谓的“陈纲案”案发。
李都御史接受词状后,将案件批发河南按察司分巡汝南道佥事胡恭进行初审。胡佥事问拟陈纲“听许财物,减等杖九十,徒二年半,系听许赃官行止有亏人数,纳米完日为民”。(9)以下对案件的描述,均出自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41,《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5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74-675页,不再单独出注。即以《大明律·刑律》“官吏听许财物”一条对陈纲进行定罪,援引《大诰》减等的惯例,(10)所谓“减等”,即“有《大诰》减一等”,是明初以来的司法惯例。参见吴艳红、姜永琳:《明朝法律》,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年,第57-58页。以“杖九十,徒二年半”对陈纲之罪进行惩治。这一惩治的身体刑和徒刑并不具体落实,而通过“纳米”赎免。陈纲所犯罪行虽然得到赎免,但是因为属于赃官,所以被革职为民。
陈纲对此处断不服,令其子陈谦抱奏冤枉,要求比照之前直隶保定府庆都县知县白壁事例处理,将“革职为民”改为“还职”。陈纲提到的白壁事例发生在天顺五年(1461),知县白壁所犯同样为“听许财物”之罪,法司起先定拟“革职为民”,白壁不服,累诉冤枉,最后经都察院题准改拟“还职”。陈纲案因此转发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戴中处复审。戴中同意初审胡佥事的处断,判定陈纲“仍发为民”。
陈纲再令其弟陈荣抱诉。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戴中对此案再行审理,并将审理结果和理由直接上奏皇帝。戴中在奏疏中提出以下几点核心意见:第一,直隶保定府庆都县知县白壁事例发生在天顺五年,天顺八年成化皇帝即位,有诏书明确规定将之前条例悉数革去不用,所以白壁的事例不能作为司法依据;第二,河南布政司、按察司送到的所属官员的“贤否揭帖”表明,陈纲“素乏清誉,惠不及民”,所犯又是“听许财物”,因此陈纲属于“素行不谨之官”;第三,祖宗立法,官吏凡犯贪淫,俱罢职役不叙。就淫而言,犯奸调戏,虽未成奸,官员也在革职之列,陈纲听许财物,“贪污已着”;第四,现行事例,官员经吏部、都察院节次考察,清誉不闻,素行不谨者,俱冠带闲住。为此,戴中建议按照现行事例,将陈纲改拟冠带闲住,即保留身份,但是发回原籍,不在朝廷任职。
皇帝收到戴中的处理意见之后,下旨司法衙门商议。成化十九年二月,都察院、刑部等衙门会议之后上奏如下:“居官以清慎为本,用人以素履为先,听属而欺公,本心已失;居官而图利,素行有亏。”指出陈纲听许财物,则其道德有失,品行有亏。法司官员回顾了《大明律》“官吏听许财物”一条的规定、天顺年间白壁的案例、官员冠带闲住的现行事例,以及巡按监察御史戴中的建议,认为陈纲“财物虽未入己,贪污则已显然”;如果按照白壁事例令其还职,则“诚恐贪污得志,无以惩戒将来”。因此,他们同意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戴中的处理意见,驳回陈纲还职的诉求,建议将陈纲追纳赎米完日,“发回原籍,冠带闲住”。并建议通行内外衙门,将此作为定例:“今后遇有此听许财物之徒,问罪明白纳赎完日,发回原籍,冠带闲住。”
成化皇帝收到中央法司的处断意见,并不同意。圣旨批复:“若令冠带闲住,未足以为贪墨者之戒,必仍发为民,如律意为是。”并嘱“法司其遵行之”。按照成化皇帝的意见,陈纲被革职为民。这是陈纲案的大概情况。
署名戴金编次的《皇明条法事类纂》收录了陈纲案的审理经过。戴金,正德九年(1514)进士,嘉靖初年曾经任广西、四川等地巡按监察御史。有学者曾对戴金编辑《皇明条法事类纂》及其成书时间存在怀疑,目前的考证成果认为,戴金在其四川巡按监察御史任上编撰《皇明条法事类纂》,而其编撰的主要依据是《条例全文》一书。《条例全文》修订于弘治初年,是为弘治十三年修订《问刑条例》和之后修订《大明会典》作准备,其中收录了相对完整的明英宗至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前的诏书、案例等。目前所存《条例全文》仅为残本,因此依据《条例全文》修成的《皇明条法事类纂》成为收集正统,尤其是成化、弘治时期司法档案的重要资料汇编。(11)关于戴金及其《皇明条法事类纂》的编撰,可参见刘笃才:《破解〈皇明条法事类纂〉之谜》,《北方法学》2017年第5期,第150-160页等;关于《皇明条法事类纂》与《条例全文》的关系,可参见张伯元:《〈皇明条法事类纂〉与〈条例全文〉的比较考述》,《法律史论集》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520-540页等;关于《皇明条法事类纂》的价值,可参见杨一凡、齐钧:《皇明条法事类纂点校说明》,《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第4页等。
此外,《明宪宗实录》以及明代后期何乔远私撰史书《名山藏》等对陈纲案也有记录,不过其记载中并未出现陈纲以及舞阳县等人名和地名,而集中于中央司法部门与成化皇帝之间的交流,重点突出的是成化皇帝对此案的坚决态度。比如《明宪宗实录》记载如下:
都察院奏,文职官有犯听许财物问发为民者,其人援有复职例奏辩。按律,官吏凡犯贪淫,俱罢职役不叙。今其人犯赃虽未入己,贪污已着,概拟复职,亦非政体所宜。宜如考核素行不谨者,令冠带闲住。奏入。上曰:居官以廉洁为本,一犯赃污,清议所弃,况能逃于国法乎?彼听许财物与受而入己者虽若不同,然既心许之矣,不必论其迹也。概使复职,固失之纵,若令冠带闲住,亦未足以为贪墨者之戒,必仍发为民,如律意为是,法司其遵行之。(12)《明宪宗实录》卷237,台北: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1962年,第4026-4027页。
《名山藏》将此案收录在专门记录皇帝行迹的《典谟记》中,对此案的描述多依据《实录》,只是相对更为简略。(13)该记载云:“都察院奏,文职官有犯听许财物问发为民,此律文也。今有援例奏辩求复者。夫其人赃虽未入己,已见贪矣。按官吏凡犯贪淫,俱罢职役不叙,此亦律文。请加考焉,如素行不谨,令其冠带闲住。上曰:居官本廉,听许与受虽若有间,心膻之矣,如律为是。”参见何乔远:《名山藏》卷17,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第969-970页。可见陈纲案及其处理,在当时和以后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
陈纲案中,陈纲本人、司法官员以及成化皇帝各方,对于以《大明律·刑律》“官吏听许财物”条议罪,处以“杖九十,徒二年半”,并以“纳米”赎免并无异议。各方提出的不同意见,其核心在于对陈纲的发落,即陈纲在其罪行赎免之后该如何处置:陈纲的诉求是“还职”;成化皇帝的处理与初审胡佥事相同,均将陈纲“罢职为民”,但是胡佥事依据的是“行止有亏”条例,而成化皇帝强调的是《大明律》律意;巡按监察御史戴中以及都察院和刑部的官员态度谨慎,他们既不同意陈纲“还职”的诉求,同时也不同意将陈纲“罢职为民”,而是建议以“冠带闲住”发落陈纲。
陈纲案发落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意见与因此而起的讨论,展示了明前期朝廷在惩治赃官时具有怎样的理念、司法依据以及司法实践?这对于理解洪武以后直至弘治十三年以前的司法发展过程具有怎样的意义?
二、“还职”:从洪武祖制说起
洪武末年,太祖朱元璋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子孙后代以《大明律》和《赎罪条例》为司法的主要依据。对赃官的惩治自然也在这一格局之内。
《大明律》历洪武一代完成,精益求精。太祖明令子孙后代不能擅自改变其内容:“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14)《明史》卷93,第2279页。与前代律法相比,《大明律》对赃罪的规定在分类、刑等上更为简约,量刑更重,而且“更加突出了官吏赃罪”。(15)程天全:《从唐六赃到明六赃》,《复旦学报》1984年第6期,第93、94页。
就文职官员犯赃而言,《大明律》专门设置了“受赃”一卷,包括11条涉及官吏及其家人犯赃的条目。该卷第一条为“官吏受财”,该条规定“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官员在此基本原则下,按照受财“枉法”与“不枉法”,受财者为“有禄人”还是“无禄人”,(16)《大明律》律条文内注解“有禄人”为“月俸至一石以上者”,而“无禄人”为“月俸不及一石者”。参见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23,第815、818页。规定计赃科断的等则。受赃数量不同,则有相应的不同的惩治。比如“有禄人枉法赃”,犯赃一贯以下杖七十,满贯八十贯则为绞罪。“官吏受财”确定的量刑等则成为惩治其他受赃形式的标准。比如该卷最末一条为“官吏听许财物”,该律条规定:“凡官吏听许财物,虽未接受,事若枉者,准枉法论;事不枉者,准不枉法论,各减一等。所枉重者,各从重论。”(17)参见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23,第833-834页。所谓“事若枉者,准枉法论;事不枉者,准不枉法论”,是指“准”“官吏受财”条的规定;各减一等,也是在“官吏受财”条确定的量刑等则下减去一等。
《大明律》还明确规定了对赃官惩治之后的发落。上文提到,《大明律》规定,官吏犯赃,死罪之外,一律罢去职役,不得继续为官,即“官追夺除名,吏罢役,俱不叙”。(18)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23,第814页。所谓“追夺”,是“追夺其原领诰敕,除去其官籍之名”。(19)高举:《大明律集解附例》卷23,台北:学生书局,1970年,第1751页。因此“追夺”而“除名”,是彻底的罢职为民,明代律家专门指出,这一类的罢职官员与普通民众无别,需要承担赋税徭役。(20)《大明律例据会细注》卷1,明刻本,第10页。
为了保证以上律条的有效性,《大明律》规定,官吏犯赃,其罪不可赎,也不可赦。《大明律》规定的可以赎免的罪行,即后代所谓“律赎”范围有限,在可赎免罪犯的身份与可赎免罪行的轻重方面,均有严格的限制。官员犯罪而可以律赎的,主要是公罪,且限制在笞这一等,(21)关于明代律赎的具体规定,及其与之后的例赎的关系,可参见《明史》卷93《刑法一》,第2293页;王新举:《明代赎刑制度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吴艳红、姜永琳:《明朝法律》,第179-181页等。犯赃官员不在律赎范围之内。而在《大明律》的《名例律》部分,则设有“常赦所不原”一条,规定“虽会赦并不原宥”的所谓“一应真犯”中,明确包括了“枉法不枉法赃”。所谓“一应真犯”,按照律条内注解,为“皆有心故犯”,与“过误犯罪”“因人连累致罪”以及“官吏有犯公罪”相区别,后者都属于“无心误犯”,因此都在大赦可以原宥的范围之内。(22)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1,第172-173页。而“枉法不枉法赃”属于“有心故犯”,罪在不赦。因为赃罪既不可赎,也不可赦,所以对赃官的惩治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对律法严明的保证。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起码在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官吏受赃过满”这一死刑,已经被列入杂犯死罪,在《诸司职掌》和《大明会典》中均有相关的记录。(23)《诸司职掌》之《刑部》将“官吏受赃过满”列为杂犯死罪,即死罪中可以赎免的罪行。参见《皇明制书》卷5,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大明会典》记录,洪武三十年确定,把“官吏受赃过满”归入“工役终身”。参见《大明会典》卷173,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第2399页。“官吏受赃过满”成为杂犯死罪,则这一官吏犯赃的最重罪行,成为可以赎免的罪行;“枉法不枉法赃”也得以进入常赦所赦免的范围。这样的司法实践,在洪武末年得到了法律的确认。一方面,洪武三十年最后修订的《大明律》,在律文460条之外,附录《钦定律诰》147条,分“不准赎死罪”与“准赎死罪”,条列来自《大明律》和部分《大诰》的死罪条目。其中“准赎死罪”类下明确列入“官吏受赃过满”。(24)黄彰健:《大明律诰考》,《明清史研究丛稿》卷2,第164页。另一方面,洪武三十年,太祖命六部、都察院等官议定赎罪事例,具体落实官吏百姓的赎罪方式。《实录》记载,最后议定的《赎罪条例》规定:“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纪过,徒流、迁徙者以俸赎之,三犯罪之如律。杂犯死罪者自备车牛运米输边,本身就彼为军。民有犯徒流、迁徙者,发充递运水夫。”(25)《明太祖实录》卷253,第3647页。其中虽然没有将赃官单独列出,但是官吏犯赃既为杂犯死罪,则其赎免的方式当为输米为军。英宗正统年间,司法官员提到,洪武时期,枉法犯赃至一百二十贯,按照《大明律》规定,本为死罪,但是司法实践中则以“免绞充军”处置。(26)《明英宗实录》卷73,台北: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1966年,第1418页。可以为一证明。洪武三十年,太祖朱元璋在《御制大明律序》中强调新颁布的《大明律》的司法地位,同时,将《赎罪条例》与《大明律》并列,明确规定法司断罪,依《大明律》(包括《大明律诰》)议罪,同时,“悉照今定《赎罪条例》科断”。(27)《御制大明律序》,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第2-3页。黄彰健先生认为,这里提到的《赎罪条例》应该是指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中所附录的《钦定律诰》,《钦定律诰》以条例的形式存在,而且以准赎死罪和不准赎死罪为主要内容。但是《钦定律诰》基本不涉及“徒流迁徙笞杖等刑”,并不能成为科断这些刑罚的依据。从这一角度来看,《御制大明律序》提到的《赎罪条例》更可能是指洪武三十年《赎罪条例》。可参见黄彰健:《大明律诰考》,《明清史研究丛稿》卷2。由此,官员犯赃,从《大明律》规定的最轻一等杖七十到满贯的死罪均可以赎免,得到了法律的确认。
洪武以后即位的新主,在即位诏中,均会对以上祖制进行重申,以表达不予更张、遵守祖宗成法的政治决心。以陈纲案发生的成化时期为例,天顺八年正月成化皇帝即位诏就规定:“凡问囚犯,今后一依《大明律》科断,照例运砖、做工、纳米等项发落。所有条例,并宜革去。”(28)《明宪宗实录》卷1,第21页。从永乐朝开始,直至陈纲案发生的成化朝,各新帝即位诏中,均有类似的表述。参见《皇明诏令》,《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第105、193、217、281、357、393、446页。这一诏令与洪武皇帝在《御制大明律序》中对《大明律》与《赎罪条例》及其关系的表达是一致的。
《赎罪条例》的规定显然与《大明律》的律条存在矛盾。《大明律》对赃官惩治严格,涉赃官员均需罢职;赃官之罪不得赎免,也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但是赎罪条例的行用,使得官吏犯赃,包括其中最严重的罪行,即官吏受赃满数罪在绞的罪行,均可以赎;遇大赦,则均可得赦免。因为《赎罪条例》成为科断的依据,而《大明律》律条只是议罪的依据,《大明律》律条所规定的对赃官的惩治不能落实。
赃官还职,是赃官之罪可以赎免、赦免的自然结果,换言之,是洪武祖制格局的自然延伸。仁宗洪熙元年(1425)六月,明宣宗即位,大赦天下,其中赃官也得大赦。浙江布政司参议王和、袁昱及陕西按察司佥事韩善等“坐赃罪遇赦”,吏部按例“奏拟还职”。宣德四年(1429),监察御史上言指出,因为“营建宫殿”,官吏犯罪,不问轻重,不分是否犯赃,一律运砖赎罪,之后“复其职役”。这里提到的监察御史,不确定是否为之前曾经上书言及此事的监察御史王翱。王翱曾在此前上书,其中明确提到,朝廷因“运砖之利”,遂“不问轻重罪名”,也不分犯赃与其他犯罪,“工满皆还职役”。(29)《明宣宗实录》,台北: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1962年,卷2,第11、38页;卷53,第1316-1317、1279-1280页。
另一方面,赃官还职,显然也有朝廷表达矜恤、收拢人心等实用目的。明仁宗、明宣宗之后,赃官还职虽然逐渐减少,但不同的时期,仍有规模性的实施。比如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景泰皇帝临危即位,即位诏中规定,“文武官吏、军民、匠作人等,有为事做工及运砖、运炭、运粮等项,悉宥其罪。官吏各还职役”。其中并未对赃官进行区别,则赃官也在赦免还职之列。之后,正统十四年十二月,景泰帝颁布尊立后妃诏,犯赃官员和其他犯罪官员一样,可以免罪还职。同样,天顺元年正月,英宗皇帝发动南宫之变,再次即位,即位诏中也明确规定,“文武官吏、军民人等,有犯罪运砖、运灰、做工、炒铁、煎盐、摆站、瞭哨、立功等项,悉皆放免,各还职役,随住宁家”。(30)以上参见《皇明诏令》,《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第355-383、392-393页。则犯赃官员和其他官员一样,均在赦免并还职之列。《明史·刑法志》指出,明代赎法的行用对象为“凡朝廷有所矜恤,限于律而不得伸者”,“以济法之太重”;同时“国家得时藉其入,以佐缓急”。(31)《明史》卷93,第2292页。也说明赃官还职不仅与祖制有关,也与这一司法实践所具有的政治性和实用性有关。
陈纲案中,陈纲以天顺五年直隶保定府庆都县知县白壁的案例为依据提出“还职”的诉求。白壁所犯也是“听许财物”,起初也被发落“为民”,经过不断的伸冤,最后都察院奏准改为“还职”。但是从以上的讨论来看,陈纲提出“还职”的诉求其实具有更深厚的背景。陈纲案中,司法官员可以直接简单地否定白壁案这一先例的适用性,但是对于“还职”所反映的司法格局与实践,即祖制的框架和“还职”行用的实用性,则需要更为审慎、用心的处理。
三、“为民”:《大明律》与“行止有亏”条例
官吏犯赃,可以赎免,可以入赦,《大明律》律条得不到落实,显然影响了对赃官的惩治力度。赃官还职,对于司法与吏治的负面影响则更为直接与深入。
宣德三年,皇帝与当朝重臣杨士奇、杨荣等有如下对话。宣德皇帝问:“祖宗时朝臣无贪者,年来贪浊之风满朝,何也?”杨士奇回答:“贪风永乐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3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8,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6页。杨士奇等官员将此归咎于永乐皇帝因疾怠政以及官员缺乏自律。但是从这一时期君臣的讨论来看,朝廷可能已经认识到赃官还职与贪风盛行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一时期的讨论中,赃官“污丧廉耻矣,虽经赦宥,岂可复居民上”;赃官还职,则“贪黩有财者幸免,廉洁无私者获罪,欲以劝惩,盖无分别”,是“明启贪污之路,谁复为善”,(33)《明宣宗实录》卷2,第52页;卷53,第1279-1280、1316-1317页。这样的言论比较常见,朝廷做出明确反对赃官还职的姿态。
与这样的言论相对应,在司法实践中,从仁、宣经英宗到陈纲案发生的宪宗成化中期,将赃官罢职为民的做法开始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落实。其中有就事论事临时的处置,比如上文提到,仁宗洪熙元年六月,浙江布政司参议王和、袁昱及陕西按察司佥事韩善等坐赃罪遇赦,吏部奏拟还职,新即位的宣德皇帝指出“士大夫当务廉耻”,三位贪污,“岂可复任方面”,为此将这三位官员罢职为民。(34)《明宣宗实录》卷2,第38页。或者以诏令的形式使这样的做法更具有规范性和规模性,如仁宗以后的一些大赦诏书中会专门注明,将赃官排除在赦免之后还职的范围之外。比如仁宗洪熙元年《郊恩诏》规定:“文职官员,自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以前,有犯罪作办事官及发充吏役、承差者,并送吏部授职。但犯赃罪者,不在此例。”这一诏书还对洪武年间曾经实施一时的绑缚有罪官员陈告一事进行了重新规定,明令各地百姓对于害军害民的官吏,不得擅自绑缚,以免“有伤大体”,但是对于“受赃及造反谋逆及逃叛者,听绑缚前来,不拘此例”。(35)《皇明诏令》,《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第198-199页。把受赃与造反谋逆、逃叛等相提并论,显示了对于官吏受赃这一犯罪的重视。从仁宗即位至成化十五年陈纲案发生之前,朝廷颁布大赦诏总计27次,(36)分别为仁宗2次,宣宗3次,英宗10次(正统6次、天顺4次),景帝5次,宪宗成化十五年之前7次,可参见《皇明诏令》卷6至卷15,《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其中有19份诏书包含了类似上述《郊恩诏》中的规定,即其他犯罪的官员可以赦罪还职,文职犯赃官员不在赦罪还职之列,占全部诏书的70%。
天顺初年,福建按察司佥事赵访上奏,指出正统年间例,官吏坐赃枉法死罪者,充军;徒流而下皆赎罪为民。景泰七年(1456),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年富在上言中也提及,“文职犯赃,轻者为民,重者充军”。(37)《明英宗实录》卷280,第5991页;卷269,第5696-5697页。可见,在逐渐推广行用的过程中,将赃官罢职为民的做法已经比较确定且相对规范。
成化十五年,陈纲案初审,胡佥事以“行止有亏”将陈纲定拟罢职为民,也正是以上司法实践的反映。需要指出的是,胡佥事以“行止有亏”这一条例而不是《大明律》作为将陈纲发落为民的依据,说明这一时期行用的“为民”不是对《大明律》律条将赃官“追夺除名”的落实,而是新的调整,是对赃官的加重惩治。这从“行止有亏”条例的逐步形成中可以看出端倪。
“行止”一词在明代的行用,与官员考察密切相关。明代官吏考满,需要将任内的各类行迹上报吏部,作为官员升官降职的依据,是为“给由”。《大明律》规定,官吏给由到达吏部之后,吏部考功司限五日移付各司,查勘该官员之“脚色行止等项”,是为“付勘”,作为选官之依据。付勘的内容包括“过名、行止、日月、出身等项”。如果考功司吏典“漏附(官员)行止”,则有罪。(38)高举:《大明律集解附例》卷2,第446页。因此“行止”可看做是官员的履历。嘉靖年间应槚著《大明律释义》,认为官员“行止”即“出仕之来历”,包括“月日、地方、出身、过名”,(39)应槚:《大明律释义》卷2,《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页。则“行止”一词包含内容更多。
这样,“行止有亏”一词就具有对官员职役的道德作负面评判的特征。宣德三年四月,吏部尚书蹇义上奏,其中提及,仁宗时期,内外官员中有“不能守己奉公,故违法律”之人,犯罪之后以罚役的形式赎罪,又想办法逃避罚役,得遇大赦免罪,竟然还职。蹇义提到他当年就曾上言,“若此之徒,行止有亏,难以任用”,仁宗皇帝也认同这样的评判。为此,这些“行止有亏”的官员虽然得以还职,朝廷仍予特殊处理,或将这些人改拟其他职位,或发往交趾任职,或者命其到南京历事一年再予选用。这些人数量不小,到蹇义于宣德初年上奏之时,“其中有挨取年久至今未到者,有到部听候未发落者,亦有先送南京历事已满授职者”。蹇义认为这样的官员“处心不臧,不知廉耻。虽授之职,无益于用”,因此向宣宗皇帝建议“俱宜罢黜,以励将来”,奏准。(40)《明宣宗实录》卷41,第998-999页。从这样的行用来看,这一时期“行止有亏”以道德谴责为主要特征,与“行止不端”“素行有亏”“素行不谨”等词可以并用,作为法律专门名词的特征还不明显。
大致在天顺时期,“行止有亏”似开始逐渐具有法律专有名词的特点。天顺五年七月,明英宗为平曹吉祥等乱大赦天下,诏书明确规定:“有赃官吏监生知印承差并行止有亏者,原籍为民。”(41)《明英宗实录》卷330,第6787-6788页。“行止有亏”似乎已经用于指代一类特殊的犯罪人员。同时,“行止有亏者”与赃官并举,则似乎赃官还未进入“行止有亏者”之列。天顺五年以后的诏书,行文又有变化。比如成化元年十一月的《承天门告成宽恤诏》,其中一条提及,“文职官吏有犯贪淫罪者”,“俱发原籍为民”。(42)《皇明诏令》,《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第464页。两相比较来看,则之前天顺年间诏书中的“行止有亏”似主要指官员犯奸淫者,与犯赃者并列,均以革职为民处置。天顺末年,锦衣卫奏报南京兵部郎中金亮与员外郎严端奸淫乐妇,都察院定拟赎杖为民,英宗皇帝称“亮等行止既不端不可处以常刑。其发威远卫充军”。(43)《明英宗实录》卷355,第7098-7099页。一方面可以印证“行止有亏”与官员罪犯奸淫有关,同时也说明这一时期,“行止有亏”的行用并不确定,其相应的惩治也不固定在罢职为民。
可能正是在成化的前期,“行止有亏”一词在泛指官员行为不当、道德有失的同时,逐渐成为一个法律的专用名词,就文职官员而言,行止有亏之人主要包括犯赃和犯奸的官员。将犯赃官员从法律上确定为“行止有亏”之人,以“行止有亏”条例专门惩治犯赃和犯奸官员,彰显的是这两类犯罪的道德性。将这两类犯罪从其他犯罪行为中划分出来,作为特殊犯罪进行特殊处置,具有对这些犯罪官员进行道德谴责的特征。而从司法上来看,“行止有亏”则是以条例的形式,对官员的这两类特殊犯罪进行加重处置。换言之,“行止有亏”条例规定文职官员犯赃、犯奸,一律罢职为民,则是以条例的形式重申《大明律》的相关规定,重新实现对赃、奸官员的有效惩治,缓解《赎罪条例》行用带来的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陈纲案中,成化皇帝对陈纲的最后处断与胡佥事的初审结果相同,但是其依据却是《大明律》,也就是说,同样是将赃官发落“为民”,成化皇帝提出了自己的话语。这一话语将《大明律》与条例相对,赋予《大明律》更高的道德性。仁宣以后,对赃官还职的反思,将赃官罢职为民的决心,是在有关《大明律》与条例的关系这一话语背景中得到表达的。上述宣德四年,因为监察御史上言贪赃官员赎罪还职,皇帝对吏部和法司发出以下吿谕:“例者所以权一时之宜,岂可常行。若久行之,使贪污者益肆其志,廉公者无所激劝,其可乎?”为此明令,“今后文职官吏犯赃罪,俱依律”。这一告谕解释犯赃文职得以还职,以条例为依据,是临时的做法;以后在这一问题上,要以《大明律》为依据。而按照《大明律》的规定,赃官将被罢职为民。为配合以上告谕,宣德皇帝随即下令吏部、刑部、都察院:“文官久任有政绩者,给诰敕,以示奖劝。劝惩有法,则人勉于善而耻于不善。尔等其循旧例,但受诰敕之后有犯者,追夺;未受而犯者勿给。”(44)《明宣宗实录》卷55,第1317-1318页。这也是对《大明律》规定的对赃官“追夺除名”条的某种应和。
成化十九年,成化皇帝在陈纲案最后处断中对《大明律》的强调,要求司法官员遵行《大明律》,正是以上话语的继续。而在《明宪宗实录》与之后《名山藏》有关陈纲案的记载中,成化皇帝更为强调“国法”“律意”,则其遵依《大明律》的决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从司法层面来说,以《大明律》为依据将陈纲发落为民,其实很牵强。上文提及,“依律定罪、照例发落”这样的格局确定之后,《大明律》其实很难成为直接惩治赃官的依据:《大明律》中将贪赃满贯的官员按律处死的做法很难落实,(45)黄彰健《大明律诰考》(《明清史研究丛稿》卷2,第195页)中也提到这一点,其中祖宗成法是指《大明律诰》。将贪赃官员追夺除名为民的规定也很难落实。“为民”这一惩治的依据只能由条例来承担。而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将《大明律》作为祖制代表,而条例只具有临时特征,也值得商榷。洪武末年的司法祖制,既有《大明律》,也有条例,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但是,成化皇帝的以上话语显然仍有重要的意义。成化皇帝对《大明律》的强调,强调的或许是其惩治赃官的决心,是对澄清吏治的追求。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大明律》为依据将赃官发落为民,就是一种德政的表现。《明宪宗实录》与《名山藏》对陈纲案的记录,突出的恐怕也是这一主题。
四、冠带闲住:犯赃还是“素行不谨”?
在陈纲案中,以监察御史戴中和都察院、刑部的官员为代表的资深刑官,态度谨慎。他们既不同意陈纲“还职”的诉求,也不赞同将陈纲“罢职为民”。他们的犹豫主要与对陈纲案件性质的认定,以及对《大明律》“官吏听许财物”这一律条的理解有关。
《大明律》规定“官吏听许财物”“准”“官吏受财”条,即比照犯赃官员的律条量刑。但是“听许财物”并无实际收受赃物的事实。定罪量刑可以比照犯赃官员的律条,但是“听许财物”的官员到底算不算赃官?《大明律》对此并无明确的规定。而在成化以前成书刊刻的《大明律》私家注释中,也没有对这一点有明确的说明。成书较早的《律解辩疑》只对如何准罪量刑本身进行了解释,(46)何广:《律解辩疑》,明刻本,第146页下。就在成化年间得到刊行的张楷的《律条疏议》,(47)张楷的《律条疏议》成书于正统年间,在成化年间得到刊刻。参见张蓥:《〈律条疏议〉序》,张楷:《律条疏议》,明成化刊本,第2页上-第3页下。在这一律条下指出:“财虽听而未受,心已蔽而不明。秽迹虽未昭彰,临事岂无偏狥。故事若枉则以枉法加刑,事如不枉,则以不枉治罪,诛其心也。各减一等,盖恕其未得云”。(48)张楷:《律条疏议》卷23,明成化刊本,第14页下。解释的是这一条款设置的原理,也并没有解释具体的发落。
但是负责再次审理陈纲案的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戴中,对这一律条的理解却是明确的,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指出,陈纲“今犯听许财物”,虽有“贪污”之嫌疑,但是“律意”“不在除名”,换言之,“听许财物”的官员从律法上而言不算赃官,因此不应该罢职为民。都察院与刑部官员商议之后,显然同意戴中对“官吏听许财物”这一律条的解读。在他们给皇帝的建议中,要求直接确定条例,规定以后官吏听许财物,纳赎之后,发回原籍,冠带闲住。(49)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41,《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5册,第674-675页。即不罢职为民。
对“官吏听许财物”这一律条提出最为直接解释的是弘治初年任职大理寺的官员屠勋。弘治六年五月大理寺左少卿屠勋应诏陈言,明确提出,《大明律》规定“凡官吏听许财物,虽未接受,事若枉者准枉法论;事不枉者准不枉法论,谓之准者,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50)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89,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00页。在屠勋看来,“听许财物”虽然准“官吏受财”,即按照“犯赃”定罪,但是两者毕竟不同,听许财物的官员不是“赃官”,因此按照《大明律》的律意,所犯罪行为“听许财物”的文职官员,并不在除名之列,即不应该被“罢职为民”。
屠勋,成化五年进士,初任工部主事,继而进入刑部,对律法多有研究,案件“剖决如流”,刑名能力突出。(51)顾清:《故刑部尚书致仕东湖屠公勋行状》,焦竑:《国朝献征录》卷44,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1845-1846页。成化十四年十月,屠勋已经成为刑部郎中,很有可能在成化十九年讨论陈纲案时,屠勋正在刑部,并参与了讨论。屠勋对“官吏听许财物”这一律条的讨论,可能和陈纲案有点关联,但其实他在任职大理寺官期间,对“官吏给由”等律条及“奸义子妻”等现象,均有如何实现公正司法的讨论。(52)参见屠勋:《屠康僖公文集》卷5,明刻本,第4页下。而他关于“官吏听许财物”这一律条的讨论不仅针对其律意,也与当时的司法实践有关,即“行止有亏”条例的行用。屠勋指出:“今在外问刑衙门,遇有此等人犯,都拟以行止有亏,发遣为民,是与巳行接受者无异。虽以禁贪,律果如是乎?”希望皇帝敕令刑部通行两京内外问刑衙门,今后遇到“听许”这样的案件,应该按律拟断,不许引用行止有亏等项名色发落。(53)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89,第800页。
从屠勋的上书可以看到,陈纲案初审,对于“听许财物”的官员,以“行止有亏”条例将其罢职为民是这一时期普遍的做法。屠勋提出,包括“行止有亏”在内的条例是否精当,应以符合《大明律》律意为标准,即依《大明律》罪在罢职的可以定以“行止有亏”,而他认为“听许财物”的官员按照《大明律》律意就不应该罢职,因此“行止有亏”条例也就不能适用于这一犯罪群体。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什么样的罪行可以归入“行止有亏”,其实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尤其是在陈纲案发生的成化时期,正是行止有亏条例初步形成阶段,其模糊性就更为明显。与此同时,因为“行止有亏”具有的道德谴责特征,这样的模糊性很容易演化成“行止有亏”条例的泛用。
以奸淫为例,陈纲案发生之前,成化十二年山西按察司赵敔上奏提出的六个问题中,已经包含了关于“行止有亏”的行用问题。赵敔指出,《大明律》规定,官吏宿娼者,只杖六十。但是宿娼这一行为被界定为“行止有亏”,因此官员犯此罪者,“并罢职役”。与“杖六十”这样的处罚相比较,明显更重。又官员挟妓饮酒,在《大明律》中本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而当时通行的做法是引用“不应”律,(54)“不应律”是指《大明律·刑律》“不应为”条,该律条规定:“凡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参见高举:《大明律集解附例》卷26,第1891页。处以杖罪,并将此行为界定为“行止有亏”,杖罪赎免,官吏罢职为民。赵敔认为如此司法有轻重失宜之嫌疑,成化皇帝下令法司会议。(55)《明宪宗实录》卷154,第2809页。但结果不详。
陈纲案中,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戴中和都察院、刑部的官员既不同意陈纲还职,也认为以“行止有亏”条例,将陈纲罢职为民,有失公允,从而提出了以官员考察“素行不谨”为名,以“冠带闲住”发落陈纲,是司法官员在无法可依情况下的变通。
明代地方官员的朝觐考察始于洪武年间,在成化年间得到完备。(56)柳海松:《论明代的朝觐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第147-151页。从成化初年开始,在官员的考察中开始出现“素行不谨”的名目。成化二年,吏部奏黜浙江等十三布政司、按察司、南北直隶府州县来朝并在任官1708员,其中以“老疾”名目致仕的895员,以“素行不谨”名目“冠带闲住”的84员,以“贪暴”原因除名为民的16员,以“罢软无为”而“冠带闲住”的693员。(57)《明宪宗实录》卷25,第490页。老疾、罢软无为、素行不谨、贪暴已经成为官员考察的常见名目,相应的处置也已经比较确定。陈纲案中,都察院和刑部所上的奏疏中也明确提及,“文职官员素行不谨者,俱令冠带闲住”是当时的“现行事例”。(58)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41,《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5册,第675页。
比较明初,此时这些考察名目的确定显然是一种制度的完善。但是,这些名目大多内容涉虚,影响考察效果。弘治即位之初,大臣丘浚向皇帝进《大学衍义补》,(59)《明孝宗实录》卷57,台北: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1962年,第1093-1094页。其中对当时行用的考察新制,即以老疾、罢软无为、素行不谨、贪暴等名目直接将官员罢黜的做法多有批评,认为“殊非祖宗初意”,其中所谓“素行不谨”者,“尤为无谓”,因为“贪者未必暴,暴者未必贪,老疾未必老疾,罢软未必罢软,素行不谨,不知何以指名”,在丘浚看来,都是属于暗昧不明之“恶声”,是“空名”。(60)丘浚:《大学衍义补》卷11,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虽然皇帝认为《大学衍义补》一书“有补致治”,但是这一官员考察新制的行用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嘉靖年间陆粲再次批评了这一考察制度,他从丘浚的言论开始说起,指出其议论“深中近世考察之弊”,也指出老疾、罢软无为、素行不谨、贪暴等名目多“虚应故事”,认为既然有这些考察名目,就应该“寻实事以实之”,其中特别指出的就是“素行不谨”。(61)陆粲:《去积弊以振作人材疏》,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289,第3048-3049页。陈纲案中,巡按监察御史戴中以河南布政司和按察司送到的“贤明揭帖”中对陈纲的评语是“素乏清誉,惠不及民”,认为陈纲应被确定为“素行不谨”,显然也有“暗昧不明”的特征。
但是,在陈纲案中,或许正是“素行不谨”“暗昧不明”的特点,促成司法官员为司法公正而寻求变通。当然,为使这样的变通成为长远,陈纲案中,都察院和刑部官员在变通之余,明确提出将这一做法形成条例,通行内外问刑衙门,“今后遇有此听许财物之徒,问罪明白,纳赎完日,发回原籍,冠带闲住”。(62)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41,《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5册,第675页。
五、结 论
陈纲案中,针对陈纲该如何发落的问题,各方各有主张。陈纲自己认为应该“还职”,他提出的直接依据是天顺年间一个相似的案例。司法部门可以很容易地将这一先例的依据性予以否定,但是“还职”所赖以出现的洪武祖制,不同时期的赃官惩治中体现出来的实用性,以及“还职”在当时仍有实施的司法实践,则需要司法部门和皇帝审慎地对待。
仁宣以来,将“还职”说成是按照条例的处置,而将《大明律》标榜为祖制的代表,这样的话语为成化皇帝强调《大明律》律意,将陈纲发落为民,提供了依据。不仅《大明律》被赋予了高于条例的道德性,依据《大明律》将陈纲发落为民,也成为返归祖制的象征;而在这一过程中,对“为贪墨者之戒”的强调也使得这一司法行为占据了道德的高度。
而从司法部门的态度和建议中,则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有关赃官惩治的司法实践。初审胡佥事以“行止有亏”条例将陈纲发落为民,说明在当时的赃官惩治中,“为民”是新的惩治方式,虽然与《大明律》中对赃官的“追夺除名”内容相同,却是以这一时期新形成的“行止有亏”条例为依据,其出现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大明律》的以上条款得不到落实。换言之,“为民”的出现是在洪武祖制的框架下进行调整,寻求有效惩治赃官的结果。
而监察御史与都察院、刑部的官员提出的貌似调和的做法则体现出在赃官惩治中对司法公正的追求。他们对“官吏听许财物”这一律条进行了审慎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对陈纲案是否属于犯赃、陈纲是否属于赃官提出疑问,并对“行止有亏”条例在这一案例中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他们提出以“冠带闲住”这一方式发落陈纲,并试图以此为契机,将此做法确定为固定的条例,其意义超出了陈纲案,而具有阐明律意、厘清条例行用的司法意义。弘治《问刑条例》修订之后,“行止有亏”条例确定,对“官吏听许财物”和“行止有亏”条例的讨论就很少见了。
直到万历年间,海瑞还明确指出,朝廷之所以贪残之风不止,“盖起于改枉法赃八十贯绞律而从杂犯准徒许赎”。(63)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第598页。即赎罪条例的行用,导致了《大明律》律条不能落实,赃官惩治不力。赃官“还职”是这一祖制框架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最集中体现。
洪武以后,特别是仁宗、宣宗皇帝对官吏贪赃有深刻认识之后,在祖制的框架下,对赃官的惩治有所加重,其依据的主要是条例。将赃官发落“为民”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弘治十三年,《问刑条例》修订,其中涉及文职犯赃的核心条款有三条:其一,“文职官吏、监生、生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但有职役者,犯奸、犯赃并一应行止有亏,俱发为民”;其二,“文职官吏、监生、知印、承差,受财枉法至满贯绞罪者,发附近卫所充军”。此外一条主要针对王府文职,王府文职官员希图改调,故意犯赃,有碍行止等项,俱解京奏请改调边远叙用。重者从重论。(64)白昂等:弘治《问刑条例》,《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2册,第220、260、235页。最后一条的合理性很快受到质疑,并在之后重修《问刑条例》时取消。(65)司法官员认为这一条例的行用一方面使“贪官得志”,一方面“律例矛盾,人难遵守”,因此建议将王府文职与其他文职官员一并处置,其中有犯赃私入己者,行止有亏,俱拟罢职为民;无入己赃私,则可以奏请改调。这样才能“法律画一,人可遵守”。参见《大明律直引所附问刑条例和比附律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2册,第271-272页。因此针对文职官员犯赃的惩治主要是“行止有亏”与“充军”两条条例。按照这两条条例的规定,充军主要惩治的是《大明律》中犯赃至死的官员;而“行止有亏”条例处置的则是其他犯赃官员。至此,洪武以后对赃官惩治不力的问题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而且以法规的形式得到固定和确认。
陈纲案发生的成化后期,虽然充军、为民这样的惩治方式已经在赃官的惩治中得到稳定的行用,但是因为条例仍具有不确定性,条例与《大明律》的关系没有得到清楚的解释,司法实践中“还职”仍有出现,因此在赃官的惩治中仍有存在不同意见的余地。弘治《问刑条例》颁行之后,对于赃官的处置发落就相对清楚与确定,如果陈纲果真被确定为赃官,则或许再无“还职”的可能。
如果说弘治《问刑条例》为陈纲案中围绕赃官惩治的问题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答案,陈纲案本身则为《大明律》“官吏听许财物”的处理带来了更大的混乱。《皇明条法事类纂》收录成化年间条例,以陈纲案为内容,其标题为“官吏听许财物照《大明律》行”,(66)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41,《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5册,第674页。说明在陈纲案的基础上形成该条例,官吏有犯听许财物者,均照此例行,罢职为民。如果说《皇明条法事类纂》乃抄录《条例全文》而来,而《条例全文》是为弘治《问刑条例》的修订而做的资料准备,则可见《条例全文》中对于陈纲案及其始末讨论结果当也有收录。但是,尽管成化皇帝以陈纲案为例,要求司法官员将“听许财物”的官员罢职为民,并以遵行《大明律》为倡导,但在以情法适中、经久可行为原则的弘治《问刑条例》中,这一条例并没有被收入。换言之,成化皇帝将《大明律》“官吏听许财物”之官员解释为犯赃之官,并没有得到《问刑条例》的确认。
此后,不同时期的律家对于“官吏听许财物”的注解多有不同。隆庆刻本《大明律疏附例》在《刑律》“官吏听许财物”条下注解:“官追夺除名,吏罢役,俱不叙,此国常也。”(67)《大明律疏附例》卷23,明刻本,第21页上。万历年间坊刻《大明律》律注《刑台法律》,在“官吏听许财物”条下,列范例招,其中也明确提到,官吏听许财物,“俱行止有亏人数,革职役为民”。(68)《刑台法律》卷12,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16页。以上两种解释均同意将“听许财物”的官员认定为赃官,与赃官同等处置,革职为民。而差不多同一时期成书的《大明律例据会细注》则认为“听许”与受赃到底不同,犯罪“听许财物”,定罪可以准“官吏受财”条,但是犯罪官员并“不在追夺除名之限”。(69)《大明律例据会细注》卷9,第154页。这与陈纲案中监察御史、都察院和刑部的官员,以及后来大理寺屠勋的观点相同。尤为有趣的是,万历三十八年,巡抚浙江等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高举刊行《大明律集解附例》,在“官吏听许财物”条下有注释云:“考条例节要,一官吏听许财物,止照《大明律》拟罪,不问为民。此成化十九年二月十一日例,可依。”(70)高举:《大明律集解附例》卷23,第1796页。《条例节要》中记录的这一条例,时间为成化十九年二月十一日,则是以陈纲案为基础形成的条例。但是基于陈纲案而来的条例中,照《大明律》行,是将听许财物的相关官员罢职为民;而《条例节要》中记录的这一条例则是照《大明律》拟罪,不问为民,两者内容大相径庭。《大明律集解附例》的作者认为《条例节要》中的条例可依,则也是认为“听许财物”的官员不为赃官,不应罢职为民。也就是说,《大明律》“官吏听许财物”条的解释和相关犯罪官员的发落,可能终明一代都没有确定的答案和做法。对于这样的结果,成化皇帝牵强地以《大明律》为依据,将陈纲发落为民,可能应负相当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