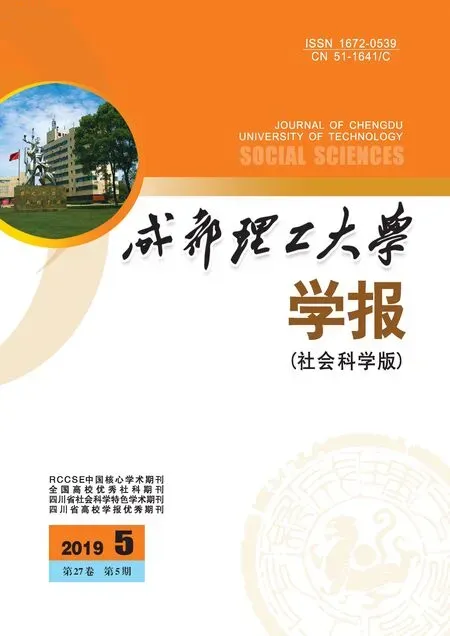科技之害与“诗意地栖居”
——论海德格尔“天地人神”对神性的召唤
黄 健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一、引言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谈到海德格尔,世人往往对那句著名的“诗意地栖居”耳熟能详,而且基本停留在浅显的“人”的角度加以理解和探微。不可否认,“诗意地栖居”一语是海德格尔思想的高度结晶,也是一个走进海德格尔思想的重要路标;但普泛层面的视阈并不能完全呈现它的真正意味,原因在于困厄于科技之难的现代人缺乏对神性意味的体悟和领会,“当现代人把自身的地位拔得很高之后,人便脱离其真正的本质世界,它不会仰望天空之辽阔,也不会静思大地之神秘,更谈不上对神秘的保存和神性的爱护了”[1]243。“神性”在海德格尔那里,主要渗透于他后期的美学思想中,但也或显或隐地呈现于其前期的思想。海德格尔的“神”“神性”的概念与欧洲传统基督教或其他宗教的神的观念都迥然相异,他的“神性”大致相当于早期希腊人所理解的自然神灵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主客对立之前的自然和人浑然不分的状态[2]198。归根结底,它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自由关联的状态、命运性的处境,具体表现为:在“天地人神”四方一体的体系世界中,“命运”之声的流淌所带来的召唤——以神性为尺度,于“诗意”中生存。
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的美学思想以对神性的探索为凝聚点,其存在论所蕴含的神性是此在的“人”生存的法则依据,而作为特殊存在者的现代人,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严重缺失神性的贫乏者,他们受到来自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迫害而迷失自己。因此,他想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系,即以“天地人神”四方一体所蕴生的“命运”神性,召唤一种更高意义上衡量“人与他者”关系的尺度,“诗意地栖居”便是他解救“人”的危难处境所寻求的道路,这样的道路是通过艺术(本质是诗歌)来聆听命运的神性之声而实现的。但海德格尔只是给出了一个预言性、模糊性的命运神性召唤,而并未具体言说“命运”的真正实质内涵,也没有针对“思”与神性的关系进行深入阐明。尽管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的归家仍然充满宗教神秘性和未知的模糊性,但这不妨碍他思想的独创性和启示价值。本文试图解读海德格尔的这一思路,通过分析神性的始基(即存在)如何构建“大地与世界的斗争”而向“人”启迪神性、“人”因缺失神性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当“人”在仰望天空和神明时那个四方一体对他意味着什么,旨在剖析海德格尔以“诗意地栖居”解救此在和召唤神性的乌托邦色彩,以及透过这些纷扰的美学思想窥视其背后对于神性的美好寄托。
二、神性的始基——海德格尔存在论
读懂“存在”是理解海德格尔哲学“神性”范畴的第一步,也是一切思考的源头。海德格尔认为,神性与存在息息相关,也与人的此在息息相关,但传统形而上学所认为的“存在”一直以来都只是存在者而非真正的存在,它们在本质上是对神性的压迫而使万物的存在(包括人的此在)未能“诗意地栖居”。因而,海德格尔重新思考存在本身,意图从存在本身出发寻找神性的始基,从而在根源上探寻万物包括人在神性未被驱逐之前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海德格尔的哲学很大一部分旨归是为了解决关于“人”的问题,他认为人是特殊的存在者,只有人才能对存在进行追问,并领会存在,并将这一层次的存在称为此在(das Dasein),“此在是存在通过人展开的场所和情景”[3]56;但同时又是它将存在者从隐蔽状态显现为无蔽状态、带入“世界”中来,“此在在它的存在中总以某种方式、某种明确性对自身有所领会……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的规定”[4]14。因此,探讨“人”的此在生存问题就不得不追溯本源,即思考“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源于颠覆巴门尼德开始的西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论,其二则源于对尼采存在论的借鉴。
在形而上学传统体系,“存在”指一种具有永恒同一性、永恒不变性、从来如此的合理秩序等状态,也指能够赋予这种状态的“终极存在者”,如柏拉图的“理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基督教的“上帝”等。这样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思想,他意识到,“我们对世界的全部真实的认识是通过我们关于世界的种种具体判断来实现的,而在这些具体判断中,系词‘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它不仅具体地将主词和谓词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具体的关于某个对象的判断,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通过它的断定功能来表明这个判断是关于某个对象的真实判断,即表明这个判断是真的。”[5]60巴门尼德抓住了一个关键的系词“是”,通过判断式的认识来界定事物的本质,这是本体论的范畴,也是存在论的范畴。因为“本体”(ontology)的“on”在古希腊语中就有“存在”的内涵,表示真实存在;同时它也是古希腊语“是”的分词形式,拥有判断的功能,这就关乎真理的判断。因而存在论就作为关于事物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判断或本质判断而现于世人视野,并通过柏拉图进一步凝练和放大而深远地影响了西方哲学此后两千多年的基本走向。究其根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论,尝试将存在界定为不变的形式法则,意图建立一个永恒的核心为“本质”,来解释充斥于心灵世界或现实世界的“现象”的形成,并因此肯定“本质”而否定“现象”,这就是本质和现象这一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基本概念形成的最直接原因。
但海德格尔并不认同这样的“存在论”,某种意义来说,他根本否定本质和现象的对立乃至它们的出现。这一思想受启发于尼采对“上帝”为首的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彻底颠倒和对立。在尼采看来,“任一事物的存在都是无限多样之关系与特征的综合,而任何概念都不可能穷尽这些关系与特征,因此,以有限的关系和特征甚至一种关系和特征来规定事物的本质所获得的概念并不能再现事物的存在[6]53。”尼采认为,形而上学所宣称的一切“存在”,包括“上帝”、统一、永恒、秩序、逻各斯、理式、主体、绝对精神等,都是人为臆造的结果。因此他将存在论建立在“非人造”的基础上,即那些一再被传统形而上学所轻视、否定的东西,即“权力意志”为核心的生命—生存形态。受此启发,海德格尔坚称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是形而上学、只思“存在者”而不思“存在”,他们说所建立的理式、上帝、逻各斯、绝对精神等“存在”依然只是存在者,并不能解释或代表真正的存在,根源在于它们预定了一个先于一切存在者而存在的超级存在者,但实际上这种预设仍然是人为的结果。与此完全不同,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和存在者的关系不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存在”是指存在者的“无蔽状态”而非某个超级存在者,它是在“成已发生”(Ereignis)的命运性关系中生成的。海德格尔认为,“作为无蔽状态(Unverborgenheit)的存在绝不是静止不动的状态,无蔽状态内含遮蔽状态(Verborgenheit),或者说,无蔽状态中充满了去蔽与隐蔽的斗争和去蔽与反去蔽的斗争”,他将去蔽与隐蔽的斗争解说为世界与大地的斗争,即被纳入世界的去蔽与被收回大地的隐蔽的斗争[6]100,是它们决定着物 (包括人)的存在方式。神性伴随着这样的斗争此起彼伏,深深影响着此在如何去把握存在。
至于世界与大地之间的斗争,海德格尔认为“世界”赋予万物以意义,使之作为有意义的存在者而显现。因而在特定的世界中意义便是光,它“照亮”着存在者,世界便是有光存在的澄明之域。“行动着的世界以‘组织’‘给以’‘意义化’的方式‘去蔽’,使某物作为有什么用的东西显现出来”,在日常世界中我们的视野只能看到那些被照亮的有用性,至于无用性却因没有被显现而受到忽视。进而他认为“大地”是“万物神秘地涌出又神秘地回归之处”,“从大地中涌现的存在者是无意义的,是世界将存在者纳入意义之域,使其作为有意义的事物而显现,但世界对存在者的意义化并不能穷尽存在者存在的秘密,归属于大地的存在者在根本上是拒绝对它的意义化的。”[6]102海德格尔常用“农鞋”作类比,那双农鞋原本当它能穿的时候我们会留意到它,但当它破烂被闲置时我们会慢慢忘记它,不再关注它,这是因为我们对农鞋的存在定义局限于有用性,表面上看是我们赋予了它存在的意义,但实质上人们并没有完整地把握它、理解它,并没有看到它真正的“存在”。“世界”使农鞋作为有意义的存在者而自“大地”显现出来,这是去蔽的过程;但“大地”却接纳被耗尽有用性而变得无意义的农鞋,使之回归、脱离世界,这是“隐蔽”的过程。而这整个的过程就凸显了“存在”和命运。而作为特殊的存在者的“人”的存在,在一种类似“有用性”的世界规则里被定制了,他的处境和结局并没有与农鞋有何区别。海德格尔正是站在这个高度上充分反思“此在”的处境,当“有用性”被世界充分照亮,那存在于暗处的更本源的神性意味便被隐藏了,此时倾向于依靠无止境的“去蔽”并不能将“隐蔽”起来的神性释放出来,这样的此在状态必定导致人类的沦陷和迷茫,因为此时的人只是作为物品而存在。
三、科技之害对神性的驱逐
作为特殊的存在着的“人”,他面临怎样的困境?为了阐明此在在现代世界中的处境,海德格尔继续沉思世界与大地的斗争,此时世界和大地的关系是敌对的,神性因受驱逐而隐退了。从西方历史语境看,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作为形而上学的对立面就已经四处蔓延,在经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的乐观主义和理性传统大受打击。而代表形而上学、理性的科学和技术自然不免也受到海德格尔质疑。他指出:“现代科学和极权国家都是技术之本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技术的随从……归根到底,这就是要把生命的本质本身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而在技术观念的统治展开来的时候,个体的个人看法和意见的领域早就被弃之不顾了。”“人本身及其事物都面临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就是变成单纯的材料以及变成对象化的功能。”[7]262,265但这一切在海德格尔看来不过是因为神性被自觉不自觉的遗忘了,缘于科学和技术的覆盖,使之隐蔽于大地。要理解这一点,就不得不涉及另一个关键的命题“命运”。
“命运”在海德格尔看来它的本质应当是“成已发生”(Ereignis),即“自行发生的相互占用中的自行显现与各成其是”,主要指一切事物“显现自己和成为自己”的方式,它包括存在、天、地、人、神、世界、物、语言、思想、艺术、诗、科学、技术等[6]107。从古希腊的世界中不难理解这样的关系,他们建立希腊神庙等于建立了一个世界,它作为人与神关联的场所将古希腊人生存所必需的各种关系和道路紧密相连、聚集为一体,“诞生与死亡、灾难与祈福、胜利与耻辱、坚忍与堕落都由此道路和关系而获得人类存在的命运形式。这种敞开的关系域之全部支配性范围就是一个历史民族的世界。”[8]42在这里,人虽然是特殊的存在者但并不凌驾于其他存在者之上,“主体”是不显现独立性和特殊性的,人只会响应命运和顺应命运,在其中体验神性的欢愉。这是一种人与他者(包括地天神、其他存在者等)之间的“自由关系”,在和谐共处中显现各得其所、各成其是的自然氛围。人通过介入去蔽和隐蔽的斗争而生存在世界和大地之间;存在(无蔽状态)则通过被人看到而成为自己,离开了人之看,存在之无蔽也就不会发生。这是一个平等共处、相互成就的过程,不存在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因而,“在海德格尔心目中,‘自身的缘发生’(Ereignis的另一种译法——引者注)不止于解决理论上的存在意义问题,而是能在‘上帝死了’之后,为人类找到并保存那最终的、当然也是最原初的神意和信仰的思想”[9]48-54。
但是被现代科学和技术塑造起来的“人”的形象,是被“普遍强制”(Gestell)的结果,而不再是“成已发生”(Ereignis)的命运。“普遍强制”指的是“将一切存在者聚集到强行摆放之中”(2)。在形而上学的“本质”论和“人类中心论”中,技术的本质是“获得和利用工具而达到某种目的的人的行为”,但根本上它不过是“命运”使存在者从隐蔽状态进入无蔽状态的“去蔽”行为。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这种“命运”行为是不同于古代技术的。“古代技术对存在者的摆放是不强制存在者一定要如何如何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或‘让其是其所是’(letting-be),在这种摆放中,存在者始终保持在本己的神秘状态之中,他作为神秘的某物而自行涌现,古代技术从不试图消除此神秘;而现代技术对存在者的摆放则是一种根据技术意志的要求而对存在者的‘强求’(challenge),在此摆放中,一切存在者都被强制性地摆放为技术所需要的状态,都被强制地作为明确可用的资源而显现。”[6]141神秘性的去除则意味着神性生存土壤的缺失,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就是现代科学和技术强制去蔽所带来的后果之一。而作为特殊的存在者,人并非如笛卡尔“主体”所宣称的是一切事物的中心、主人,它也不外如此为现代技术所“强制”,“人并不是现代技术活动中的‘主体’,在现代技术世界中,人与物一样都是‘被技术所摆放者’,即‘被技术所订购者’,不同的只是:人还被技术订购来实施对别的存在者进行订购,换言之,人只是特殊的被订购者而已。”[6]142这是非常悲哀的,也是此在在遗失神性之后所必然面临的生存困境;同样,这也是技术“强制普遍”的命运的彻底失败,是它造成人与神性的严重分离,在无休止地去蔽中,神性隐匿于大地。
海德格尔认为解决的路径是让一切存在者回归“成已发生”的命运关系中,让人与他者之间回归“自由关系”而非“主奴关系”,不是强制去蔽而是让一切存在者自我显现、各成其是,让作为命运神秘者的最高尺度的神性重新介入“天地人神”的体系中。为此,需要重新找到一种全新的“命运法则”,他标举艺术(本质是诗歌)作为更本原的被许可的去蔽形式,不仅能窥视技术对此在的迫害,也能将“人”置入那个神性弥漫的家园,使人得到拯救。而艺术的构建、神性的重现、“人”的拯救,首先需要全新的生存土壤——“天地人神”的世界体系作为基础。
四、“天地人神”对神性重生的酝酿
神性的生成和弥漫并非无根之萍,它要有自己的生长土壤。海德格尔将神性纳入“天地人神”的世界中,这里的世界并非“大地与世界的斗争”的那个“世界”,而是指更广泛意义上容纳一切并使其内部各事物各成其是的一个体系,它的含义比后者广泛得多(3)。海德格尔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谈到了日常世界、现代世界和古希腊世界,这些都是“大地与世界的斗争”的那个世界,只是不同的关系、形态造成的不同的世界。人对物的使用性关系形成日常世界,基于主奴关系和普遍强制构成现代世界,而让物自行涌现和人泰然接受产生古希腊世界。但在上述的体系中,该“世界”是“天地人神”的“四方关联体”。此四方彼此有别又共属一体,海德格尔说:“地、天、神、人(出于其本身所具有的一致而彼此一致)以四方统一的单纯方式而彼此归属在一起(belong together)。四方中的每一方都以自己的方式映照出其他三方的在场。同时,每一方又以自己的方式反照自己,进入在此四方之单纯统一中的自己……每一方都在它们的相互占用中被占用(be expropriated)而进入其自己的存在。这种被占用的占用(the expropriative appropriating)是此四方关联体的镜照游戏。”[8]179由此可见,此“世界”是天地人神相互占用并各成其所是的游戏。这样的游戏有点类似庄子的逍遥游之“游”,都是体现了一种绝对自由的状态,人、物、“神”、天地、自然等各方均彼此交融却又能自我独立,恬然自适而又归融合一。那么,这个“天地人神”的四方一体的“世界”是如何呈现神性的?它又如何定位此在的“人”?
在海德格尔思想构建的“天地人神”中,大地是万物神秘地涌出又神秘地回归之处,是去蔽的开始也是隐蔽的结束。在海德格尔看来,大地本身是隐匿的,是世界让大地呈现,世界去大地之蔽,大地性的东西在日常世界、现代世界、古希腊世界,分别以“有用者”“被订购者(客体)”和“自行涌现者”的身份出现。但是不管世界如何呈现大地,它都不能完全究极大地的所有。他以石头和色彩为例子,认为尽管二者能被科学的重量单位和波长数据所理解,但是石头的沉重和色彩的闪耀并不能从大地被揭示、显现出来,“只有当人们将大地作为本质上不可揭示的东西来理解和保护之际,亦即作为那从任何揭示中退隐而永远保持锁闭的存在时,它才作为大地本身而显现在澄明之中”[8]46-47。而作为特殊存在者的人,他在思“存在”和“天地神”的时候,并非以古代世界中作为自然、神灵的奴隶的身份登场,也不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世界标举的意义化、主体、被订购者等形象出现,而是意图挣脱、在自由的关系中还原人的生存本质。“人之为人乃是在他与存在者之存在(无蔽)、与天地神、与世界、与万物、与语言的相互占用中生成为自己的。也就是说,他的生存归属于作为‘Ereignis’的‘命运’,它的本质是在此命运的游戏中生成的,而不是现成自足的。”[6]116海德格尔引入“命运”及其所带来的“成已发生”的自由关系来营造“人”的生存。至于天空和神灵,海德格尔表述得很隐晦、神秘。他认为,与隐蔽的、孕育万物的大地形成对比,天空是敞开和高远的,大地与天空的蕴含和敞开中,为人的生存和存在提供空间,人与万物因此能以最本真的形态存在着。当人立足于大地仰望天空之时,他看到天空的辽阔高远也窥见到神的行踪,居住在天空的神则通过可见的景象暗示不可见的存在。人在聆听(思)神的启示就是在取得一种度量一切的尺度,也因此获得生存的法则。人需要测量自己在天地之间生存的尺度,他仰望天空就是在寻求神灵,离开了它们人就不能生存于天地之间;而离开了人的仰望,隐匿在天空的神也不能显现,天空不再辽阔、神性不再弥漫、作为万物生与灭之场域的大地不再神秘。
但这一切在海德格尔看来也不过是“命运”及其在“天地人神”的体系中呈现的自由关系所营造出来的神性意味。他说:“于是(在荷尔德林一首名叫《希腊》的诗中)就有四种声音在鸣响:天空、大地、人、神。在这四种声音中,命运把整个无限的关系聚集起来。但是,四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片面地自为地持立和运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就没有任何一方是有限的。若没有其他三方,任何一方都不存在。它们无限地相互保持,成为它们之所是,根据无限的关系而成为这个整体本身。”[10]210命运将“天地人神”聚集成为一体,让任何一方既能保持独立又能融入另外三方,从而形成“天地人神”(包括世界、物、存在与时间)共属一体,并让一切关系在游戏中变得自由而各成其是。神性就是在“命运”和“自由关系”的激荡中作为高渺且神秘的东西而显现出来。可以说,海德格尔以“天地人神”为根基为人的生存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模态(体系),它根本有别于传统形而上所建构的世界。在这个体系中,人被重新定位,他不再是自然、神灵的奴隶,也不再是“万物的灵长和宇宙的精华”,他只是回归作为“天地人神”中的一方的本真。正因为回归,他才能重新聆听命运之声,并窥见神性的尺度,从而体会到“人”之为人的生存本真的自适和快乐;否则,他只能在现代科学和技术中作为“被订购者”而不断被迫害、摧残、湮灭,直至最终迷失“自我”。海德格尔称那条归家之“路”,便是“艺术”!只有它能通向神性,勾连人神之秘。
五、解救此在与召唤神性——“诗意地栖居”
海德格尔构建“天地人神”的四方一体固然完美,但如何让“人”回归这样的世界、家园?他认为,只有艺术能担此拯救、引领归家的重任。海德格尔的“艺术”本质上就是对真的创建,美与真并不是并列的关系,美是由真派生出来。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他说:“真是作为某物而存在的存在者之无蔽状态(unconcealedness)。真是存在的真。美的发生并不是与真并行且脱离于真的,当真将自己置入作品之时,美便出现了。这种出现(erscheinen,appearance)——作为作品中真的存在者并作为作品——就是美,因此美的存在者属于真之成已发生。”[8]81基于此,海德格尔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将存在者呈现出来,它将存在者的无蔽状态(即“真”)“创建”(Stiftung,Founding)出来。海德格尔举古希腊神庙的建立为例子,用以说明存在者的无蔽状态是在艺术作品所建立的世界和被作品放上前来的大地的冲突中发生的。古希腊神庙是艺术作品,它的建立将人神关联、将各种关系聚集在一起,并形成一个世界;而神庙的建立,不仅是对石头、木材、色彩等物的“有用性”的运用,它还将那隐藏的“石头的厚重”“木材的坚韧”“色彩的明暗”等材料本身带上前来,而不是使之消隐[8]42,46。在希腊神庙艺术作品中,人神关系或与生存相关的其他关系都是和谐的,一切存在者都能在命运中处于无蔽状态、成其所是。这就是艺术作品创建了存在者的“真”,艺术的本质就不再是再现、表现或象征某物,而是“创建”,通过将世界与大地的斗争固定在作品中而将“存在者的无蔽状态”显示出来。同时,海德格尔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创建”[8]75,因为被后人翻译为“诗”(poetry)的“poiēsis”最初含义指将自行涌现的存在者从隐蔽状态变为无蔽状态的活动;而“诗是以语词对存在的创建”[11]281,因此他将艺术(本质是诗)对真的创建归结为诗对语词的创建,并首先让语词“成其所是”。
那么,诗如何作为“诗意地栖居”拯救作为此在的人?它如何在艺术的命运路径中现出神性?海德格尔认为,诗的语言是通过给存在者命名的方式创建存在,此时存在者显现为无蔽状态是被“诗意”的语言所给予的。“诗意”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种诗性的言说,是一种让存在者自行涌现的自由方式,也是一种充满命运“呼唤”的神性之声、神的尺度。因为诗性的言说不只是给存在者命名,它还将存在者“带上前来”让其自行涌现,并因此而成为聆听命运之声、使人自在生存于命运中的方式。具体而言,“诗意”使人“在对命运之声(语—言)的聆听中,用语词命名(人—言)一切存在者(天地人神、万物、时间、世界)之存在,从而使自己与那被命名者关联在一起,并在此关联中获得自己的存在”[6]175。海德格尔反复运用荷尔德林的诗句“诗意地栖居”阐释他的这一思想。在荷尔德林的诗歌《教堂的尖塔映衬着蓝天》——
假如生活是十足的辛劳,人可否
抬望眼,仰天而问:我甘愿这样?
当然。只要善——这纯真者
仍与他的心同在,他就乐意按照神性来测度自身。
难道神乃子虚乌有,不可证知?
抑或他显露自身,有如天穹?
我宁可相信后者。神乃人之尺度。
人建功立业,但他诗意地
栖居在大地上。如果可以,我要说,
那被称做神之形象的人,较之
夜的充满星辉的夜色,更为纯真
大地上可还有一种尺度?
绝无。[12]197
为了生存,人栖居于大地上,仰望天空并寻觅神明的踪迹,但他“看到”的神的形象也仅仅是基于自身的“看”,他仍然是以自身作为人的尺度去度量神的形象,这并不能帮助人捕捉到神启示的尺度。唯有灭绝让自身成为一切的中心的欲望,并“诗意地”聆听与思,才能把握住神性,进而体会到命运的“本原性关联”(4),最终以神性尺度作为生存法则。值得区分的是,海德格尔认为的神性的尺度并不是以神为标准的尺度,而是神向人启示所产生的尺度,这需要人神的双向沟通感应,沟通感应的结果才相应产生“神性”。因此海德格尔说:“何谓人类度量的尺度?神?天空?天空的显明?都不是。此尺度在于保持不可知的神作为神如何通过天空而显明的方式。神通过天空的显现乃在于一种揭露,它让我们看到自行遮蔽的东西。”[13]207人需要这样的神性尺度作为准则介入到“天地人神”的体系中,但现代世界将这一切摧毁了,神性尺度亦隐匿了。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世界中由于人对神的驱逐,以现代科学和技术为主导的“人的尺度”代替了“神性尺度”的地位,因而人的生存本质受到迫害,逐渐走向非神性化、世俗化。这是“贫乏的时代”,神、神性受到驱逐,那种支配“天地人神”的命运所营造的本原性的关联(即自由关系)也一并被摧毁。因此荷尔德林所谓的“无神”并非指神从来就不存在,而是指神的缺位和流离。现代世界的根本危机是“现代人远离了自己诗意的生存根基,悬于无底的深渊之中而不自知,更明确地说,现代人不再以诗意的方式聆听命运的声音,不再响应命运的召唤而进入与天地神的亲密关联之中……天地人神之间那种只有平等自由的‘中间’而无任何强制‘中心’的关系被掩盖了”[6]176。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绝对中心化,造成的结果不仅是神遭受驱逐,而且连带着神性、信仰、命运、自由也一并被排除在现代人的视野之外。因此,“诗意地栖居”是途径也是目的,凭借着神性的桥梁,诗将人与“天地人神”的四方一体勾连贯通,“诗人的任务就是反世俗化,就是祛除无神论的妄见,搜寻远离大地的诸神之踪迹,将神的暗示传达给世人,重建人与神的生存关联(即尺度性关联),为神的重临准备道路。”[14]156-171
海德格尔指出,艺术、诗的存在就是通过“诗意的言说”(5)重拾被丢弃的神性,让“天地人神”营造的神的尺度代替人的尺度,让人重新仅仅作为“四方一体”的一方回归“世界”,也让一切关系、一切事物自由地显现自身。总而言之,让特殊存在者的人、一般存在着的物都能在神性弥漫的“世界”里“诗意地栖居”,自由地成为其所思、成为其所是。
六、结语
海德格尔以“存在”为切入点,深刻剖析现代科学和技术以及日常世俗化对人本质生存的迫害,根本上是通过对神秘性、神性的驱逐和革除来实现的。在后期的美学思想中,他更多地把拯救的重任放在艺术和“道路”上,藉由它们创造“天地人神”四方一体的意境便是为了呼应命运的召唤。命运召唤神、神性尺度,它诞生于此意境。神性的贯通和弥漫,使“诗意地栖居”成为迷失的现代人回归“天地人神”的家园的“道路”。在这个层面上,海德格尔无疑找准时代的弊病、也提出富有创见性的拯救方案,这体现了他作为思想家深刻的洞察力。但他思想中的一些细微之处仍值得推敲,诸如“让言语按自己的方式言语”的背后是否在更深层次上契合神性、“思”的终点让神性是显还是隐、通往神性的“路”唯有艺术还是可以包含其他等,显露了他思想中的乌托邦色彩与宗教神秘性合力造成的局限性。关于海德格尔之“神性”的探索应当是开放式的而非唯一的,“诗意地栖居”只是他的答案。就像海德格尔所谓的“命运”(6)所具有的无限性和多样性,我们应当借鉴他的思考,把“道路”走得更宽、更远,甚至走出多条路。
注释:
(1)类似于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中所理解的Ereignis“成已发生”,表示自行发生的相互占用中的自行显现与各成其是,重点突出自由的关系。下文待论。
(2)通过摆放,存在者便作为某种状态的存在者而显现出来,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去蔽的过程。
(3)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的思想里的很多专有名词是不同于形而上学传统的,因此在探讨具体问题时所出现的相关概念,不能依常理审度。他对aletheia,physis,logos等词的阐释就是在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理解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及其整个体系就必须要转变我们的固常思维。
(4)“本原性关联”就是人与天地神、人与自然、人与存在、人与语言的最本真的关联,这是一种自由的关系体现,直接体现人的本质、生存的本质。这是与“诗意地”对应的,惟其如此才能听到神性之音并以此为尺度,度量一切。
(5)语言本身也应当归属于拥有“自由关系”的命运,让语言自己按照它本身的规则言说,但语言的言说需要人的言说的帮助,这也进一步佐证诗与语言的关系。
(6)“命运”并不是形而上学所理解的那样固定不变且有一定的终极意义,而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体系有不同的表现,古希腊世界、日常世界、现代世界的“命运”表现形式都不同,海德格尔注重的是如何让“命运”呈现自己的那种方式,这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