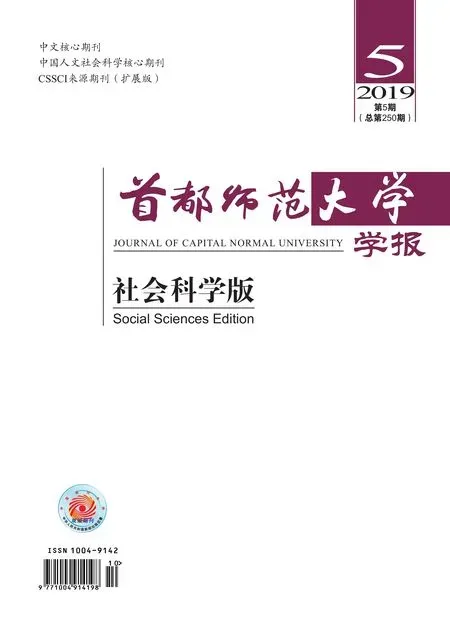从幕府到竹林:汉魏易代之际的思想转型与文学书写
王洪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而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又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长期的人文滋养,并与现实政治、社会环境相互作用,才能涵养出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处于思想转型以及文学新变的汉末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无论是建安风骨,还是竹下风流,如果我们需要选取考察源流的一个起点,这个点固然是多元性的,但汉桓帝时培养的三万余太学生,恰恰可以作为风萍之末的讨论依据。苏轼即说:“稷下之盛,胎骊山之祸。太学三万人,嘘枯吹生,亦兆党锢之冤。”(1)苏轼:《苏轼文集》,卷七十二,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98页。就党锢之祸而言,坡翁的见解是深刻的。对于易代之际的思想转型、文学转关而言,三万太学生更是积极的人文条件。太学生是作为官吏的储备力量而存在的,三万余太学生大多白首空归而委身乡野,这样就形成了从庙堂到江湖无处不在的文明承载者、文化传播者。知识群体的增加以及下移,由此开拓了汉代文化的新风尚,孕育了魏晋的魁奇风骨与“一往情深”,呈现出各具特色、各领风骚的文学镜像。
一、“游学增盛”:知识群体思想生活多元分化的内因
无论是思想的发生,还是文学的兴起,都离不开知识人的参与。作为汉代知识阶层形成的生力军,西汉博士弟子,东汉太学生,这里不包括博士、儒生的私学弟子,基本上都是以等额规模培养的官吏,即每一位博士弟子或者太学生,都会被政府选拔为各级官吏,这是极其令人羡慕和荣耀的仕进路途。而东汉和帝以后,官学制度松弛,博士私学教育繁盛,一人开门,则有徒众数百人,甚至上千人。本初元年(146)四月,梁太后颁布了两项诏令,一是郡国举荐50岁-70岁明经诣太学学习,二是大将军至六百石遣子弟赴太学受业。最关键的是考课制度的改革,即“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2)范晔:《后汉书·汉质帝纪》,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1页。这就令很多儒生看到了进入官吏队伍的希望,无疑刺激了儒学队伍的扩大。需要说明的是,郡国所举明经年龄范围扩大,明经又基本上是博士或者民间大儒的私学弟子,客观上促进了东汉末叶私学的发展。像我们熟知的,马融有弟子四百余人,升堂入室者五十余人;李膺教授弟子常千人;郑玄耕读东莱,学徒相随数百人,其他博士、大儒在籍或不在籍的私学弟子还有很多。据统计,到了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全国人口数量达到了五千六百多万人,按太学生三万人计,太学生所占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万分之五。实际上,这一比例还要高得多,因为其中并不包括博士或者大儒的私学弟子。如果加上这些私学弟子以及各级儒官、文吏,估计此时东汉的知识人将占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这不仅在两汉历史上,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无须考察梁太后颁布就学诏令的初衷,客观上已经刺激了汉代儒学的大规模传播,无形中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民智开启的新时代。春秋末期的大规模的私学授受是我国古代社会民智开启的发端,它造就了稷下学派以及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传播了学术,更重要的是传播了思想,使中国的思想、哲学汇入到了世界历史的大潮中,我们与世界古代多国共同进入了哲学突破的时代,这在中国思想史上、世界哲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桓帝以降,儒学培养出来的社会精英,大量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他们求学的初衷,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心系政权,关注家国、民生。民智开启,知识下移,不治而议论的复古风气勃然而行,其行为表现在以私意左右上层官吏的意识,甚至是直接上书以达天听,客观上造成了干预朝政的后果,在各方面权力斗争中,最终导致党锢之祸的发生,汉末儒生成为皇权政治的牺牲品。袁宏总结汉代士风的变化时说:“高祖之兴,草创大伦,解赭衣而为将相,舍介胄而居庙堂,皆风云豪杰,崛起壮夫,非有师友渊源可得而观,徒以气勇武功彰于天下,而任侠之风盛矣。逮乎元成明章之间,尊师稽古,宾礼儒术,故人重其学,各自是其业,徒守一家之说,以争异同之辨,而守文之风甚矣。自兹以降,主失其权,阉竖当朝,佞邪在位,忠义之士发愤忘难,以明邪正之道,而肆直之风盛矣。”(3)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二,《两汉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33页。皇权对于婞直士风的无情打击,引起了知识阶层的对于致君尧舜理想、修齐治平行为的自我反思,从而开启了儒学内部的自我批判,直接导致了儒家知识分子思想行为的分化。桓帝延熹二年(159)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等上疏推荐大儒徐穉、姜肱、袁闳、韦著、李昙,诸人皆辞疾不就。中平五年(188),灵帝征拜申屠蟠、荀爽、郑玄、韩融、陈纪等十四人为博士,无一人赴任。汉代儒生的荣耀——被朝廷拔擢,遭遇了两次党锢之祸的残酷杀戮,被有识之士清醒地摈弃,一部分士人走上了与汉代政治分道扬镳的路途。更有甚者,并不仅仅是抛弃主权政治那么简单,开始反思处士横议以及婞直士风带来的政治危害,甚至预判出汉代政权的走向。其中,申屠蟠认为:“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4)范晔:《后汉书·申屠蟠传》,卷五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52页。徐穉驰书告诫士人领袖郭太:“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5)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二,《两汉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20页。在他的影响下,郭太也对朋友说过同样的话:“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6)范晔:《后汉书·郭太传》,卷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25页。陈蕃、窦武之死,郭太忍不住叹息:“‘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7)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三,《两汉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49页。至此,大一统政治格局下形成的角色意识,在知识精英的思想世界里,“学而优则仕”的信念,治平天下、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逐渐淡漠、退化,最终流于无形。罗宗强先生认为名士风流与凄凉血泪交织的心绪,“对于士这个阶层来说,这种悲哀甚至悲凉的心绪,正是他们和大一统政权在内心上疏离的最后一丝眷恋。这种悲哀心绪,和对于腐败朝政的疾视与批评(抗争与横议),伴随着他们从忠心耿耿维护大一统政权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走向自我。这一转变是巨大的。没有这个转变,就不会有后来玄学的产生”(8)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诚然,一部分儒家士人,不仅家国责任淡化,甚至消失,个体的道德操守也在发生着变化。大儒马融为人任性,不拘儒者之节,绛帐授学,班列女乐。其人生信条是:“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9)范晔:《后汉书·马融传》,卷六十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53页。至汉桓帝时,马融已经仕为南郡太守,因触忤外戚大将军梁冀,被免官剃发,流放到朔方郡。赦还后,竟为梁冀飞章诬陷李固,大将军长史吴祐怒对马融说:“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即诛,卿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10)范晔:《后汉书·吴佑传》,卷六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02页。马融又作《大将军西第颂》,歌其功颂其德,以此为正直士人所讥笑。马融侄女婿赵岐就曾嘲讽说:“马季长虽有名当世,而不持士节,三辅高士未曾以衣裾襒其门也。”(11)范晔:《后汉书·赵岐传》,卷六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21页。范晔为马融作传,也批评说:“羞曲士之节,惜不赀之躯,终以奢乐恣性,党附成讥。”(12)范晔:《后汉书·马融传》,卷六十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72页。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坚守道义,马融固然传播儒学而有功于当世,但其行为对于儒家教义的破坏是致命的。就此,余英时论曰:“此种‘生贵于天下’之个人主义人生观,正是士大夫具内心自觉之显证。”(13)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页。实际上,这并不是人生观的自觉,而是汉代传统士人精神的变异,是儒家知识分子内部个体的精神乃至人格的裂变。只是这种改变,在东汉末叶的历史以及思想大潮中显得尤为突出罢了。
温润如玉的儒家君子人格,被充满个性的张扬不羁所替代;精神上的疏离,个性自我的释放,成为汉末士林潜滋暗长的流波。一些志存高远的士人,坚守着儒家的理想和道德,与宦官、外戚做着考验精神和意志力的殊死争斗,为了皇权却得不到皇帝的谅解,鲜血淋漓的杀戮几乎终结了汉代士人的群体精神。而一部分士人,在任情逍遥、激扬个性方面,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张升任情不羁,赵壹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排摒。前者侈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有知我,虽胡越可亲,苟不相识,从物何益?”(14)范晔:《后汉书·文苑传下》,卷八十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27页。后者作《刺世疾邪赋》,以舒其怨愤。二人被范晔写入《文苑列传》,虽然背离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风流,怨而刺的文学风格还是使汉末的文学出现了一抹亮色。离经叛道,狷介狂傲,在《文苑列传》最后一个传主祢衡身上表现得更为鲜明。更有甚者,时人谓之狂生的向栩,名自己的弟子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又或“或骑驴入市,乞丐于人。或悉邀诸乞儿俱归止宿,为设酒食”(15)范晔:《后汉书·独行传》,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93页。,狂放不羁,性情怪异,在汉末已经肇端。当然,一部分儒家士人不隐不仕,开启了中国士人的新的生活方式,奠定了文人生活隐逸基调和生命华章。
汉代知识人走了一条儒生、文士到文人激情蜕变的道路,也是汉代政治思想转型的必然结果。深受儒家教义影响的儒生,将人格内塑而达至温柔敦厚作为个体理想和追求目标,究心典籍就变成儒生的道义追求。与此相对照,优游诗酒,醉心诗赋成为文人的特质,尤其是竹下文人的生命追求。文士介于二者之间,既有着儒家的人格追求、道义精神,同时,赋诗唱和成为这一群体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汉末,这样的文士更多的是集中在幕府之中,而不是朝堂之上。
二、幕府掾署:驰骋文辞的栖息地与精神家园
东汉士人有着进入幕府供职的文化传统,也是士人曲折实现从政理想的一种变通方式,即展现才能得到幕主的赏识,通过幕主的荐举达到干谒世主的目的,从而实现跻身官僚体制之内的理想。东汉幕府,无外乎是将军幕府、州郡幕府。首开幕府的是东平王刘苍,依次是章帝建初三年(78) 马防开府、永元元年 (89)窦宪开府,由此掀起了东汉幕府文学的一次高潮。汉明帝、章帝父子喜好文章,又是东汉鼎盛时期,游走于幕府和庙堂之间的士人有着超乎前代的国家荣誉感,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向心力,这时幕府文章以歌颂国家文治武功或者幕主的军功伟业为主,文学幕僚的歌颂造就了东汉文学的辉煌。所以,范晔说:“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16)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卷八十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13页。之后,东汉外戚权臣相继拜为大将军,基本都建立了自己的幕府,如汉安帝时邓骘、阎显,汉顺帝时梁商,汉桓帝时梁冀,汉灵帝时窦武、何进等。安帝之后,汉代政治进入皇帝、宦官、外戚、儒官相互倾轧的统治时期,外戚生存的政治环境异常险恶,当然也与外戚本身权势熏天、嚣张跋扈、为所欲为有关。幕府之中的士人,往往也处在惊恐不安中。即便这样,逃遁山林、游走巉岩的士人依然很少。永元四年(92),汉和帝逮捕窦宪等人,收缴其大将军印绶,“宪、笃、景到国,皆迫令自杀,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17)范晔:《后汉书·窦融列传》,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20页。。汉桓帝与单超等五中常侍诛杀大将军梁冀,“其它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18)范晔:《后汉书·梁统列传》,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6页。。由于朝廷内部各势力集团政治斗争的激烈以及皇位迁移所造成的政治冲击,东汉末叶的文士游幕出现了重大的政治风险。而两次党锢之祸后,外戚何进被诛,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了。朝廷权力控制的软弱以至于松弛,各地强势军阀相继建立了幕府,于是文人从朝廷、外戚幕府转而投奔了各地军阀,相继发挥他们的作用,呈现他们的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汉献帝时期,建立幕府或曰霸府的有袁绍、袁术、刘表、曹操、孙策、刘备等。投身于幕府中的士人,对于汉代皇权的忠诚程度严重分化,其中不乏有像荀彧、荀攸叔侄以“兴复汉室”为己任、韩嵩欲“成天子之臣”、臧洪“投命于君亲”者,然而有这样思想的士人已经如凤毛麟角一样稀少,大多数士人进入了士无定主自由选择的状态。作为讨伐董卓之关东联军盟主,袁绍首先建立了自己的幕府,文士有田丰、沮授、许攸、郭图、逢纪、审配、辛评、辛毗、陈琳、崔琰以及荀彧等。建安二年(197)袁术称帝,建立的小朝廷,文士杨弘、阎象、李丰、袁胤、袁涣等参与政事。初平三年(192),荆州刘表开府,幕僚有韩嵩、王粲、傅巽、伊籍、蒯越等。在汉末动荡不安中,袁绍、袁术、刘表幕中的文士,审时度势,最后大多选择归顺了曹操,如许攸、辛毗、陈琳、崔琰、荀彧、袁涣、王粲、韩嵩、蒯越、傅巽等。当时,较为稳定的是江东孙策、孙权兄弟幕府,有张昭、张弘、周瑜、鲁肃、陆逊、诸葛瑾、步骘、虞翻等;荆州刘备幕府有孙乾、简雍、麋竺、诸葛亮、庞统等,分别成为建立吴、蜀二国的文士精英。当然,在汉末人才济济的幕府,唯曹操而已。曹操麾下除了上述归顺的文士外,还有郭嘉、荀攸、程昱、王朗、司马懿、刘廙、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繁钦、路粹、丁仪、丁廙、司马朗等一百余人。战乱频仍,士人的流动性非常大,如贾诩先从董卓,再归张绣,三奔曹操,而曾经隶属于曹操阵营的陈宫,又选择了投奔吕布。
政治的分裂预示着权力的分裂,地域的分裂必然出现思想的分裂以及精神上的变异。军阀割据势力的出现,幕府士人有意或者无意地入幕选择,恰恰是汉末士人思想分裂最初的表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为其主的思想成为士人的主导思想,汉代四百年来培养的家国精神、皇权意识已经成为一种高度,却是在一段时间内被逐渐抛弃的思想,而士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私欲与皇权努力铸就的家国意识与主权精神所造成的矛盾,即自由个体与皇权意志的对抗,造成了血淋淋的杀戮。这样的政治史也是士人的血泪史,又持续了四百年之久,至隋唐统一才稳定下来。汉末魏晋南朝时期的政治就是皇权与个体之间合作与对抗的矛盾,虽然士人以血淋淋的代价确立了个体自我自由生存的人生范式,但魏晋时期让人铭记的自由精神之人性辉光永远让人向往,成为一种永恒。
汉末曹魏易代之际士人主体精神意识的自我改变,令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建安五年(200),鲁肃为孙权密谋了“鼎足江东”的计策;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给刘备描绘了三分天下的蓝图;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上书曹操,俯首称臣,言说天命,陈群、桓阶劝进。就在这些士人汲汲乎另一种功名的时候,建安五年(200),应玚参与了官渡之战,而陈琳作《为袁绍檄豫州文》,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建安九年(204),刘桢从曹操征邺。次年(205),陈琳被俘。《魏书》云:“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19)陈寿:《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传》,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0页。我们在《献帝春秋》中看到陈琳如此作答:“矢在弦上,不得不发也。”(20)虞世南:《北堂书钞·艺文部》,卷一百三,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版,第395页。不得已而为之的窘态昭然若揭。但《长短经》却有这样的记载:“陈琳典袁绍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谢曰:‘楚汉未分,蒯通进策于韩信。乾时之战,管仲肆力于子纠。唯欲效计其主,助福一时,故跖之客,可以刺由,桀之狗,可以吠尧也。’”(21)赵蕤:《长短经·诡顺》,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也就是说,在袁言袁,在曹言曹,各效其主,幕府文士思想意识与精神境界在此有了极其鲜活的表现。曹操爱陈琳之才而不咎其事,署为司空军谋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阮瑀受业于蔡邕,有文名于当时,是被曹操强迫入幕的。《文士传》载:“太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22)陈寿:《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传》,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0页。建安十二年(207),徐幹来归,被曹操辟为司空军谋祭酒。建安十三年(208),寄身于荆州刘表的王粲,和刘表之子刘琮降曹,被任命为丞相掾。是年,孔融被曹操诛杀。以上七人,被曹丕称为建安七子,也是那个时代最为优秀的文人。曹丕、陈琳、阮瑀、徐幹、刘桢、王粲、应玚等参与了赤壁之战,大军还至襄阳,陈琳、王粲、应玚同作《神女赋》。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留守邺中,曹丕、曹植兄弟与除孔融外的六子以及吴质等游宴赋诗,同题述作。若干年后,曹丕记忆犹新:“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23)曹丕:《与朝哥令吴质书》,萧统:《文选》,卷四十二,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90-591页。又曰:“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24)曹丕:《与吴质书》,萧统:《文选》,卷四十二,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91页。建安二十二年(217),爆发大疫。王粲、陈琳、应玚、刘桢染疫而亡。四十八岁的徐幹在“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厉疾,大命殒颓”(25)《中论序》,程荣辑:《汉魏丛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页。。次年(219),曹操病殁,建安文人走过了辉煌的生命进程,人生以悲壮的死亡而落幕。曹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26)曹丕:《与吴质书》,萧统:《文选》,卷四十二,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91页。建安幕府士人的落幕,恰恰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开端,带着野心和文心的曹丕建立了曹魏政权,不拘细行的文人脱离了幕府,逃避了魏阙,走入林下,酣畅淋漓地纵歌,肆无忌惮地喝酒,飘飘欲仙地吃药,进入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逍遥境界。恰如宗白华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7)宗白华:《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三、竹林风流:人生逆旅的精神反抗与价值追寻
我们知道,秦始皇任用李斯等人,采取了法家思想作为治国方策。而法家对于人的个性和个体生命的蔑视,决定了它无力承担起凝聚思想、稳定社会的重任;刘邦建汉,意识形态采取了黄老道家思想,这是一种无奈的被动的无为,对于社会现实采取的是放任的姿态,客观上表现得无所作为,这与儒家积极进取的教义和命世精神扞格不入。从汉初到景帝末,国家承平日久,“儒家的理想主义终于向现实主义靠拢,而儒者的思想学说也终于向政治意识形态倾斜”(2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页。。年轻的欲有所作为的汉武帝即位,谋求新秩序的建立,采取了儒家的治国方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此后汉代的统治思想。由此可知,汉代儒学的政治事功最初是强制性的,强迫得久了就变成了无法逾越的规则,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自觉。四百年的仄仄独行,走过了宣、元时期的辉煌,有过洋洋乎永平的盛世气象,由于缺少其他思想派别的挑战与砥砺,虽然经过各种调适和补充,儒家经学并没有被怀疑,也没有遭到反抗,独尊的儒学最终走向了衰败。在民智再次开启的桓、灵时代,对于儒家思想、儒学精神的质疑,首先来自经学培养出的社会精英们,表现出个体自我价值的危机,也是儒学发展的危机。
历史是螺旋式前行的,思想的发展也是曲曲折折的。春秋中后期私学的兴盛,使历史进入民智开启的时代,从而迎来了百家的思想争鸣。桓灵帝时期太学的空前发展,再一次大规模地传播了知识,开启了民智;儒家学术的传承者,也是思想者,甚至是那个时代的反叛者,在特定的时代,遇到合适的土壤,再一次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必然到来。也就是说,知识人聚集的地方,就是产生思想的地方,而理念与个性使然,必然发生思想的对抗,导致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生。汉末文士、文人游走于诸侯军阀之间,思想运动的先声已经开始发生。就在儒学自我否定、儒家士人自我怀疑的东汉末期,道家学说再次进入了儒家士人的思想意识,而思想者们这次选择的是对于被儒家伦理深自束缚的人性进行反拨的老庄之学,并且快速地在士人中弥漫开来。
就在马融以道家的行为准则,行儒家之功的时候,本应该是儒家人文理念坚定维护者、支持者的汉代统治阶层内部也发生了思想行为的变异。延熹八年(165)正月、十一月汉桓帝连续两次派人到苦县祭祀老子。九年(166),祠黄老于濯龙宫。故而《西域传记》说:“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29)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22页。此后,襄楷上疏谏汉桓帝有言:“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浮屠。”(30)范晔:《后汉书·襄楷传》,卷三十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2页。儒生的警告没有奏效,而在这一年发生了党锢之祸。显然,汉桓帝并没有变儒入道,对于“党人”的残酷杀戮证实了这一点。熹平二年(173),陈愍王刘宠与前国相魏愔“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31)范晔:《后汉书·襄楷传》,卷三十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69页。,可以给我们解开汉桓帝崇信黄老以及佛教的原因:此前的汉冲帝、汉质帝年命不永,至延熹八年(165),34岁的汉桓帝尚无子嗣,两年后薨逝。崇尚黄老、浮屠有祈求长生之命意。道家养生说,始于《道德经》第六章“谷神不死”、《庄子·在宥》“黄帝见广成子”;由于皇帝信好,逐渐形成了风气。《后汉书·逸民传》的传主基本上是桓、灵帝时期人,以此可见一斑。同时,出现了道教经典著作《太平清领书》(《太平经》)《老子想尔注》,道家已经向道教发展。龚鹏程从《太平经》中解读出了“不舍世而超脱”的人生型态:“所谓不舍世而超脱,指它虽提倡长生、虽讲成仙,但并不否拒此世之道德行为规范及社会组织结构。它反对捐妻子、入山林;其守一存神,宗旨乃在在世而度世。治身与治国,在其理论中有奇妙的统合关系。”(32)龚鹏程:《汉代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78页。诚然,道教出现之后一时段,儒家士人的生存状态和理想追求就在于此。而更确切地说,这样的人生型态,主要是受道家哲学的影响,而不是道教。
儒生对于老子的研究,非隐逸之士单纯追求的玄虚,而是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在东汉中晚期,马融比较早地为《老子》作注,马融弟子郑玄也注了《老子》。“郑玄不仅为《易》注输入大量理性因素,指出了由象数到义理的发展方向”(33)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7年版,第642页。,王弼的《老子注》直接承袭了郑玄援道入儒的注经方式,建立起系统的玄学理论体系,直接开魏晋玄学风气之先。《世说新语·文学》载:“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3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34页。正是在何晏、王弼的推动下,正始玄学扭转了汉代四百年的儒家思想,使士人们抛弃礼法,由内塑转而外放,追求精神上的卓越。如果说司马氏发动的高平陵之变,是一场政治阴谋,不如说是儒家政治势力对于新兴起的哲学新思想(一种异端)的毁灭性打击。但是,虽然天下名士为之减半,玄学的趋势已经形成,思想却不会因为领袖人物的逝去而失去,“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追求和精神释放,使竹林诸贤不失时机地出现在魏晋的历史舞台上。而士人对道家的关注点,从《道德经》转向了更加注重个体逍遥精神的《庄子》。
在魏晋易代之际残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安顿生命、栖息心灵是竹林士人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道家思想的接受和实践是一种自然的选择。阮籍以深醉而佯狂避祸,嵇康以服食追求养生,刘伶裸形于屋中,种种行迹,追求的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旨趣。林下诸贤寻找一种超然的生命安放方式,即选择了庄子的任达逍遥,不过是以一种行为方式对抗另一种行为方式,其中不免有矫饰伪作的成分。阮籍率意独驾,途穷而痛哭;嵇康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向秀大畅玄风,又著《思旧赋》,无不说明他们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无奈,所以,竹林诸贤的行为中有诸多不可解之处。阮籍不让其子模仿父兄的行为,嵇康临终将其子托付给山涛,除了刘伶病殁外,其余诸贤都有出仕的人生经历。这从侧面说明,林下诸贤畅言老庄是一种精神趋向,是理想的人生状态的一种追寻,是别样的人生境界。李泽厚以为,魏晋之际,旧的规范制度和社会秩序已经崩溃,士人开始对于外在权威进行否定和怀疑,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自省和追求,“人(我)的自觉成为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而对人格本体构建,正是魏晋玄学的主要成就”(35)李泽厚:《庄玄禅宗漫述》,《中国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元代历史学家郝经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评魏晋时代的玄学宗尚,说:“汉魏之季,何晏、王弼始好老庄,尚清谈,谓之玄学。学士大夫翕然景向,流风波荡,不可防制。于是嵇康、阮籍、籍兄子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皆一时名流,跌宕太行之阿,号竹林七贤,蔑弃礼法,褫裂衣冠,糠粃爵禄,污秽朝廷,婆娑偃蹇,遗落世故,颠颠痴痴,心死病狂。乃敢非薄汤武,至于败俗伤化,大害名教。或临丧而剧饮,或途穷而恸哭,或箕踞而为锻,或荷锸以自埋,解弛乐浪,旷然以为高。”(36)郝经:《续后汉书》,卷七十三上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显然,缺少了对于魏晋时代个体生命价值与生命精神的关照,以及魏晋人风神对于中国士人人格形成中的重要价值的理解,具有时代的思想局限性。
四、易代之际文学书写的主题变迁与情感表达
历史学家贺昌群先生以为:“若历史家承认有所谓时代精神(the spirit of a time),为支配其时代心理之绝大势力,其他一时发生之现象,虽若非其时代精神所可产生者,而其实亦受时代精神之支配。”(37)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9页。迥然有别于两汉的魏晋,时代精神滋养了一代士人的生活历程和人生体验。司马迁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3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547页。在汉末魏晋易代之际,诗文并不是儒之余事那么简单,高者上升至“经国之大业”,沉入现实生活,又成为文人的乐趣、抒发心迹的雅事。当文士蜕变成文人,诗赋文章之事也由被动变成自觉地主动,文学的特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造就了汉魏晋易代之际文学特殊的时代性。
1.从“爰颂其德”到“游心自娱”
东汉明帝之后,汉代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对于胸怀致君尧舜而使天下化之理想的儒家士人也是一种鼓舞,为了表达对君主、朝廷的颂扬之意,上疏达意,诗赋显志,便成为儒家士人表达心志的手段。“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文心雕龙·颂赞》)。歌颂社会,称扬汉代君主的德行治功已经成为文人的共识,王充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39)王充:《论衡·须颂篇》,卷二十,黄晖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47页。鸿笔之臣润色帝王德业,这是儒生士人的传统使命。特别是在汉代,除了西汉初的几代君主,后世的汉代君主几乎都是按照儒家理想打造出来的人格模式,治国方略虽有异,却是大同的,那么汉代君主取得的政治成绩,就是儒家士人可以炫耀的资本,同时,宣传国家的盛世太平,歌颂帝王的文治武功,都成了儒家士人以及文人政治议题和文学想象中不约而同的主题。
《论衡·颂圣篇》屡次强调:“晓主德而颂其美,识国奇而恢其功”,“虞氏天下太平,歌舜德;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是故《周颂》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凡颂四十篇,诗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当颂明矣”。(40)王充:《论衡·须颂篇》,卷二十,黄晖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48-849页。王充毕竟处在东汉社会的繁荣富庶期,国家和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儒生以及文人的思想依然处于经学恢复而一展身手的亢奋状态,对于国家的褒美之情溢于言表,发乎心,显乎情,寓于文。所以像王充这样,思考儒生使命,着力进行思想建设以及抱着文学期待的儒生璀璨如星云。文学本身就是儒生之余事,也就是说儒生本身的学术以及文化积淀为文学创作活动的展开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又有用文学进行讽谏的传统,所以不待王充的大声疾呼,歌功颂德一直存在于朝堂之上,这是永远无法忽视的事实。歌颂大汉之德成为汉代士人歌咏的主题之一。身居魏阙的士人如此,幕府文人依然有如此浓烈的情怀。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北征匈奴,班固为中护军随行,为记窦宪伐匈奴之功而作《封燕然山铭(并序)》以及《窦将军北征颂》,傅毅作《北征颂》《窦将军北征赋》,崔骃作《北征颂》《大将军西征赋(并序)》,颂扬窦宪的北伐之功。史岑为邓骘作《出师颂》,马融为梁商作《梁大将军西第颂》,皆为颂美功德。当然,此时的美圣德,是在歌颂大汉国威军威的情况下,对于幕主的称扬伐美。
曹操幕府中文士延续了用赋颂的方式称扬幕主武功征伐的勋绩,如王粲《征思赋》《浮淮赋》,徐幹《西征赋》《序征赋》《从征赋》,陈琳《神武赋》《武军赋》,应玚《撰征赋》《西征赋》,阮瑀《纪征赋》,曹植《车征赋》等,讴歌了曹操北伐南征的功勋。最值得称道的是,建安十三年(208),赤壁战败后回师行军至江陵,有感于宋玉《神女赋》,王粲、陈琳、应玚同时具作《神女赋》,骋才言情,讽谏的意味已经消失,成为个体才华和情思的表征。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建安诸子游宴赋诗,阅景抒怀,诗赋由庙堂走向生活,成为文人抒发性情的手段,情感依托的载体。刘桢《赠五官中郎将》:“明月照缇幕,华灯散炎辉。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为且极欢情,不醉其无归。”曹植《公燕诗》:“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公燕诗》又曰:“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此时,宾主之间是欢愉的,文学创作是兴之所至的情感抒发的结果。《文心雕龙·时序》曰:“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袵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文学褪去了讽谏的政治光环,成为樽前宴后抒发情感的工具。其中不免歌功颂德成分,但都出自真诚,是富于个体真诚情感的书写,这样的文人风流与情感书写,成就了建安文学独特的文人气质,流风以远,衍变成文学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2.从“反情合志”到“以情纬文”
随着汉末儒学教育体制的崩溃,文士开始追求个体的生命意义以及闲适的人生旨趣,易代之际的诗歌突破了儒家伦理教化的价值和意义,《诗》之温柔敦厚,赋之讽谏,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政治语境以及思想文化土壤。传统意义上的儒林已经不能涵盖所有的士人,范晔不得不正视汉末出现的文学现象,将一类人归入《文苑传》。范氏的概括和总结是“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41)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卷八十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58页。,情感恣肆,语言华美,蔚为大观,志趣相同者甚至同题同作,展现新的文学风貌。不可否认的是,受汉代四百年经学教育的影响,诗赋讽谏的价值没有也不会完全消失。正因为诗赋的意义在于政治的功用,诗歌情感的表现含蓄而内敛,这是符合温柔敦厚的儒家文化教育宗旨的。《诗》《骚》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发展源头,也是两种不同的审美范式。前者在诗之为《诗》的本原状态,是抒情的诗歌,感情奔放而热烈。诗一旦上升为经,就变成了饱含政治意味的诗三百,汉人经学诠释的着眼点全在于礼乐教化,强调的是美刺讽谏,最后达到儒家士人共同的致君尧舜的政治目的。《礼记·乐记》曰:“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又曰:“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因为,诗歌是政治的,接受的对象是君主,所以,诗歌表现出温柔敦厚的中道和平气象。在经学教育的体制内,培养的是比德如玉的温润君子,深受这样教育影响的汉代士人,创作出的诗赋表现出了反情和志的创作风格。东汉中后期经学教育体制崩溃,经学对于人的思想,尤其是人性的控制力度减弱,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诗,建安诸子的诗赋,基本挣脱了经学思想控制以及情感的束缚,或缠绵哀怨,或低回婉转,或高亢浏亮,非常注重个体自我情感的淋漓表达。所以,汉末魏晋易代之际文学情感的发抒,突破了汉代经学的禁锢,书写个体的情感体验,感物缘情是这一时期诗赋的显著特点。
中国诗歌历来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划分,也就是《诗》《骚》的文学传统。前者是写实的,后者是浪漫的,抒情的。作为荆楚文化代表的《楚辞》,成为浪漫主义的文学的先声。《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42)黄伯思:《东观余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是楚文化孕育出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传统,而世代相传的楚人的文化、思想、性情孕育着楚人的文学感悟以及文学精神。太康十年(289),楚文化的杰出代表,钟灵毓秀的陆机、陆云兄弟来到了洛阳,引起了洛阳文人的极大关注。不仅因为江左陆氏是曾经的豪门,也是因为二者的才华。太常张华曰:“伐吴之得,利获二俊。”(43)陈寿:《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卷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60页。西晋士风浮华,追求诗歌的技巧与形式,呈现出绮丽与繁缛的文风,刘勰批评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4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然而,从个体的创作动机与审美取向上来说,陆机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主张。实际上,缘情说是对于荆楚文化孕育出的浪漫主义的骚赋文学以及汉末文人诗歌、汉乐府创作经验的总结,是中古诗学理论和诗歌观念的创新。“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45)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卷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8页。。沈约在为谢灵运作传时,总结了前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以情纬文”的观点,道出了建安魏晋文学的总体特点。明代的胡应麟又作如是观:“《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六朝之诗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46)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46页。显然,胡氏认为诗缘情诗学理论的提出是汉晋抒情文学的转关。詹福瑞先生阐释得尤为详细,他说“陆机及其后的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47)詹福瑞:《“诗缘情”辨义》,《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触及到了魏晋文学发展变化的实质。
3.从“梗概多气”到“境玄思澹”
东汉末期,由于战争以及地震、水旱灾害频发,又伴随着全国性大规模的疾疫,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就是人口急速大量减少。据《文献通考》(48)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7页。记载:桓帝永寿二年(156),东汉人口达到了极盛,计50066856人。遭逢黄巾之乱、董卓之难,军阀之间混战,又汉末大疾疫,至三国鼎立时初期,魏国人口443万人,蜀国人口90万人,吴国人口230万人,三国人口总计760多万人。不足百年间,人口几乎是以十倍的速度下降,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重的哀伤气氛。《搜神记》载:“汉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自灵帝崩后,京师坏灭,户有兼尸虫而相食者。魁、挽歌,斯之效乎?”(49)干宝:《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页。干宝的说法,范晔《后汉书》亦有相应的记载。永和六年(141)三月上巳,大将军梁商大会宾客于洛水之滨,“宴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50)范晔:《后汉书·周举传》,卷六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28页。。武人尚且如此之悲伤,文人自然不免。《古诗十九首》就是汉末文人悲歌的具体表现。《诗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51)孔颖达:《毛诗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0页。怨怒、哀思恰恰是汉末文人诗歌的共有特征,刘勰论述建安时期诗歌特点时就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5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3-674页。实际上,哀怨的极致呈现方式恰恰是悲愤,嵇康《声无哀乐论》有言:“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哀切之言。”(53)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46页。这一点在曹操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薤露》《蒿里行》本来是汉末流行的挽歌,曹操用其题而反其意,直接写成抒情诗,哀婉中有悲凉感慨,冲淡了哀歌的情感色彩。如“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薤露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悲伤中不乏武人的豪迈、慷慨。流行最广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更是体现了凄苦悲凉之中含有不羁的风格。对于汉末的其他文人来说,与曹操相比,气格卑弱,难有曹操那样的慨而慷,即便是号称建安七子之冠冕的曹植,虽然也长于军中,《诗品》称其诗“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美则美矣,与“幽燕老将”之“气韵沉雄”相比,还是偏于柔弱。繁钦《与太子笺》所言,几乎是那个时代诸子诗文风格的侧写:“暨其清激悲吟,杂以怨慕,咏北狄之遐征,奏胡马之长思,凄入肝脾,哀感顽艳。是时日在西隅,凉风拂祍,背山临溪,流泉东逝,同坐仰叹,观者俯听,莫不泫泣殒涕,悲怀慷慨。”(54)繁钦:《与魏文帝笺》,萧统:《文选》,卷四十二,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65页。
在死亡和政治迫害面前,文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不断被挖掘,甚至逐步走向超越。在正始玄学的启蒙和引领下,阮籍将老庄之道视为自己的人生哲学,虚构了超世绝俗的“大人先生”作为自己的人生标的,体验并实践着玄学人格的美学意味以及形而上的人生况味。也就是说,如果不去隐遁山林,脱离恐惧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于现实生活的逃避。这种逃避造成了思想上的玄远,行动上的趋利避害,就像《庄子》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丑陋的大树,不用才能全身而免被刀锯之祸,所以,汉末以来道家思想混入了士人的精神意志,甚至影响了士人群体中主流的价值取向,《庄子》逍遥自得境界成为汉末之后魏晋人的思想旨趣以及人生镜像。《文心雕龙·隐秀》谓阮籍诗“境玄思澹,而独得乎优闲”,这是这个时代玄学影响下的文学自然的反映。魏晋文人自纵放达的逍遥的人生体验,超越世俗生活的迁绊,将目光投向山水自然、日常生活,用审美的眼光仔细审视天地之间的大美,谛听自然的生动韵律,完成了精神家园与世俗世界的契合统一。在缥缈的游仙以及言之玄远的诗歌之外,山水不仅是生活的视界,也是文学颂达的主题。《世说新语·言语》曰:“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5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0页。又曰:“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浄,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5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8页。在东晋风流倜傥名士眼中,星云、山水、花鸟、草木无不暗含玄意,由精神世界的遨游走入静明山水的徜徉,诗歌从玄言派生出了山水,中国文学进入了另一种境界,既是人生的,也是文学的静谧和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