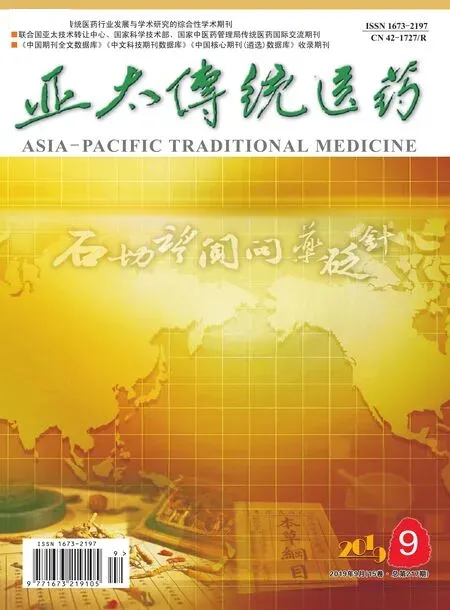中医与阿育吠陀的“生命观”互鉴研究
李希颖,秦 霞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昆明650500)
中医,主要指中国汉族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而创造并实践的传统医学,因此也称为“汉医学”,其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影响,形成了多学科互相渗透交融的综合性医学科学知识体系。来自印度的阿育吠陀(Ayurveda)以哲学层面的文化内涵为主体,涵盖生活层面的常理知识,并被赋予了“远古神圣启示”的宗教意识。其中,阿育(Ayus)指“生命”,包含了肉体、心智、感官和灵魂;吠陀(Veda)是“知识和智慧”之意,因此阿育吠陀有时候也会被成为“生命吠陀”。中医和阿育吠陀都肩负着促进人类健康、消除疾病的使命,经过数千年的传承、积淀和发展,其完善了诊疗手段和防治措施,丰富了健康知识和养生方法,对两国甚至全世界医疗事业发展影响深远。
1 生命存在观
生命观,也可以理解为“观生命”,是人类观察并认知生命的过程,包括人类看待自身生命和自然界生命体的态度,从人类历史发展整体看,生命观也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认知程度以及社会的文明程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因此,首先需要确认的,就是“现实的个人”以及这些个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远古到现代,哲学家们对世界本原的思索从来不乏争论,唯物和唯心两大阵营的对立使生命存在变得丰富多彩,神仙鬼怪的臆想、宗教意识的产生、圣贤先人的崇拜、唯物辩证的发展等,无一不是我们对生命的认知过程。而无论何方论辩占据主导,两者的终极话题却始终围绕着尊重生命、保护生态、物意平衡、和谐发展的理念。
1.1 生命神话观
远古先人对生命的存在和意义曾发出过多元思考,在无法辨识自然现象、生理现象和意识显现的初期,他们用创世神话来对宇宙世界进行解释,以求“虚无中创生万有”的答案。
1.1.1 中国神话传说 中国先民将不能做出解释的自然、社会及人的生理、心理现象付诸于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拜,认为在万物生生不息地衍化变迁的背后,有创世神灵幻化了世间一切。“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2],是对盘古在天地尚未形成之前就已经诞生的描述;继而,盘古垂死化生自然界和人类,“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3]另有“女娲造人”之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4]女娲以陶土仿照自己捏制人身,土制泥人拥有了生命力之后将女娲奉为创世之母,而女娲所造之人也产生了富贵贫贱之分,喻示着人类进入等级社会。“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刚柔相成,万物乃形”[5],此文则描述了伏羲、女娲二神阴阳交合,创生万物。
1.1.2 印度神话传说 印度“正统”哲学流派信奉之神——原人(Purusha),被认为是人类之始祖。据《梨俱吠陀》第10卷《原人歌》记载:“原人之神,微妙现象;千头千眼,又具千足……唯此原人,是诸一切;既属过去,亦为未来;唯此原人,不死之主;享受牺牲,升华物外。”[6]印度远古的吠陀仙人、神学家和哲学家猜测、设想宇宙万有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个永恒不灭的超验存在,仙人作者那罗延把“原人”神格化为一个有相的自然神。原人的带超验性的神相,超然物外,既不受宇宙客观规律的支配,也不受经验世界因果关系的约束[6]。此神不但主宰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还创造了情世间(人与种姓)和器世间(物质世界),原人的口、双臂、双腿、双足分别化生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原人胸脯、眼睛化生出月亮、太阳等,阐述了化身原人创造具体的人类(及其四大种姓的划分)和物质世界(宇宙天、空、地三界)的形成,为原人塑造了一个具体的创世主形象。1.1.3 中印神话传说的互鉴 “在原始人看来,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的,花草树木也不例外,它们跟人一样拥有灵魂。”[7]中国和印度的神话传说亦是如此,创世者不单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与人类和谐共生的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以及众生灵赖以安身立命的宇宙环境与自然现象。因中印神话传说的相似性,以至于牟复礼先生在《Mote》杂志中就盘古神话在中国的文献中出现时间相对较晚而发出质疑:“盘古神话直到公元二世纪前才被人记述。此时,中国人自己独特的宇宙观已经非常成熟,显然这个神话中的宇宙观和中国的宇宙观是异源的。它很可能是来源于印度,那里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创世故事。”[8]但细究中印神话的不同之处,可见中国神话无论是盘古还是伏羲、女娲,都描绘了一个由混沌到有序的宇宙变化,由惟像无形衍生出阴阳二性,再有阴阳二性之交合化生万物……它们创造了自然并于死后回归于自然,其故事梗概与中国道家思想同归一理。印度神话虽然也是由创世主造就了人类和物质世界的诞生,但印度人民始终相信此创世主是永恒不灭的,它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自然规律的制约,主宰着世间万物。
1.2 生命物质观
唯物论在看待生命起源的问题上,坚持认为生命是由非生命物质渐进性地发展进化而来,是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自我繁衍是生命发展的根本规律。生命之所以有感知,是因为客观世界带给生命意识的反映和复写,生命意识是生命个体间相互区分的依据。客观世界包含着生命,而又独立于生命意识以外。
1.2.1 中医之“气”与阿育吠陀之“Prana” 中医之“气”是指一切无形的、不断运动着的物质,其充塞于无垠的空间,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基本的物质形态。气一元论,是古人认识和阐释物质世界的构成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宇宙观,《庄子·知北游》提出:“通天下一气耳”;《关尹子·六匕篇》则有“以一气生万物”的记述。中医认为气是生命的体现,“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并认为人体内有多种气的形式,如禀赋于父母的先天之气、出生后获得的后天之气、循行于体表的卫气、流通于肺中的宗气、贯行与脉管的营气、封藏于肾内的精气、串连于经络的经络之气等,对人体起到防御、推动、温煦、固摄等作用,同时,气也象征了一种道德和精神,如孟子所言的“浩然正气”。
阿育吠陀认为“Prana”无处不在,其不是具体的物质,但我们能感觉到,并可以从空气、阳光、食物和水中获得。瑜伽行法则认为,生命能量的控制(Pranayama)主要体现于呼吸法,其可以使身体洁净,有助于唤醒内在的精神能量。Prana在人体胸部以上时,它是生命的赋予者,被称之为“生命之气”;Prana聚集在人体咽喉至肚脐时,它总管发音、语言、精神、记忆,被称为“上升之气”;Prana活动于胃肠道促进消化吸收时,被称为“脐部之气”;Prana维系大肠排泄与骨盆内脏器功能时被称为“下降之气”;Prana汇聚心脏调节心血管及全身循环功能时,被称之为“全身之气”[9]。
“气”和“Prana”相关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决定生命活力和生命能量的基础物质,其所表现出来的多种形式都是大自然和人体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两者不同点在于,中医之“气”除了表示物质之外,还体现为一种人文精神,而阿育吠陀的“Prana”被认为在新鲜食物中含量最高,随着食物放置时间变长,Prana也会逐渐丢失。
1.2.2 中医之“阴阳”与阿育吠陀之“三性”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宇宙中相互关联事物或现象对立属性的概括,中医学运用阴阳之间的关系认识生命,解释世界的本原。其中,自然界以天、日、上、火、温热、动、无形等划分阳性,以地、月、下、水、寒冷、静、有形等划分阴性;人体以亢奋、明亮、温热、体表、气、背部等划分阳性,以抑制、晦暗、寒冷、体内、血、腹部等划分阴性。人体内阴阳二性的相互依存和消长平衡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基本条件,阴阳失调会引起疾病,阴阳离绝则喻示死亡。印度数论派哲学认为,宇宙是由悦性(Sattva)、激性(Rajas)、惰性(Tamas)三大自然原动力交互作用衍生而成,即“三性”或“三德”(Gunas)。激性代表移动和变化,为感觉与运动器官的移动提供能量,表现为活力、运动、兴奋、紧张等;惰性代表阴暗、无知、沉重,负责深度睡眠,带来停滞、困惑、迷惘、迟钝、冷漠、昏沉等;悦性代表稳定、纯净、清明、本质,衍生出心智、5种感觉器官和5种行动器官,是平衡、协调、纯净、智慧、觉悟、亲切的象征。阿育吠陀认为人与万物相应,可视为微缩的小宇宙,一样具有不同程度的三种特质,在特定的时间、环境和饮食的影响下此消彼长。对比“阴阳”和“三性”,两者都蕴含着事物既对立又统一和彼此消长的属性,在阿育吠陀中主要表现在激性与惰性的相反关系,而阿育吠陀的悦性则类似于中医的“阴阳”平衡状态。
1.2.3 中医之“五行”与阿育吠陀之“五大元素”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5种基本物质属性的运动变化,中医用上述5种物质的特性及其生克制化规律来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探求宇宙规律,是各种事物普遍联系的法则,其可以对应自然界的五味、五色、五气、五方、五季,也可以对应人体的脏腑、五官、形体、情志等,通过这5种属性的相互作用,使整体获得动态平衡,从而维持事物的生存和发展。“五大元素”是阿育吠陀核心的理论基础,其分别代表了某一类功能属性,并非是确切的物质。五大元素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单位,根据各元素组成比例的不同,显现出不同的能量、体质、感官、性格、心理特征等,例如,人体需要“空”才能生存、成长和沟通,生理之“空”包括呼吸道和消化道,心理之“空”,带来自由、平和,也会带来空虚、不安的感觉;风是移动的法则,生理之“风”统管运动功能,心理之“风”赋予人们清新、快乐和兴奋,也会与“空”合力,表现为焦虑、不安、恐惧和神经质;生命之“火”用以调节体温、消化和新陈代谢,心理上既反映关注、领悟、辨识,也负责愤怒、批判和竞争;水元素在体内以液体形式存在,润滑、洁净,富于营养,水的盈亏会引发水肿、肥胖或口渴,知足、爱、慈悲是其意识能量;土元素构成身体的固态结构,赐予身体力气、结构与耐力,意识上土能促进宽恕、踏实与成长,也会带来依恋、贪婪和抑郁[10]。五大元素被认为是人体的先行要素,在此基础上,构成了三种生命能量、三大垢物、七大组织、七大身体类型、十大致病因素等系统理论。“五行”与“五大元素”都不是具体5种物质,而是5种物质属性的概括,并且于人体都有映射,体现了5种感官意识、生理活动和情志表现;区别在于,中医认为五行的每一个物质属性都和其他4个紧密连接,其通过相生相克的联系维持相互的平衡,而阿育吠陀的五种元素在古印度经典《圣典博伽瓦谭》中清楚地说明了先有纯净的以太,再依次显化风、火、水、土的过程[9],其之间更多地表现为线性联系。
2 生命特质观
生命体有异于非生命体,人类生命有异于其他生命,人类个体与其他人的生命个体不可重复——每个人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无论从肉体到精神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性,才能充分尊重和敬畏人类生命。
2.1 独特性
中医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出“因人制宜”理论,如《灵枢·寿夭刚柔》曰:“余闻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11],认为人的体质形成与父母先天之精气相关,并受后天之精气(来源于肺吸入的清气和脾胃运化的水谷之气)的影响,因此中医提倡审因施养,充分体现个性化防治方法。
阿育吠陀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宇宙能量的创作,具备独特的体质和人格特征,这种独特性从受孕那一刻开始,就基本形成。父母体质最为活跃、最占优势的能量因子,基于季节、时间、情绪、食物等影响因素,合成了一个崭新的个体,这就是“个体的唯一性”。因此,运用阿育吠陀疗愈时,要充分考虑到个体身心体质唯一性、生活环境唯一性、成长经历唯一性,针对每个人的疗愈方案应该做到个性化,这与中医“三因(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理论较为一致。
2.2 统一性
中医哲学思想非常重视“整体观念”,认为任何事物的各个部分是互相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其涵括了人体自身的完整性、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和人与社会环境的联系性。《素问·宝命全形论》提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11],说明人与大自然的构成成分相同,并受大自然的影响和制约,圣达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则可长寿。阿育吠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认为大自然充满自生的智慧,支配着生命的成长。人的组成要素空、风、火、水、土与自然界一致,个人生活法则应与自然规律和谐共生。在医疗实践方面,阿育吠陀通过多种方式,使人体内部总是与自然界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即阿育吠陀的核心目标是达到个人、社会、环境、宇宙的完美健康状态。中医与阿育吠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有着“渺小的自我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共识,而两者同样也认为个人身体的完整性、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性也是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
3 生命价值观
生命价值观是指个人看待自身和他人生命的重要性和价值,是个人心理结构的核心因素之一,反映个体态度、思想观念的深层,形成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和采取行动的标准。天地万物中人为贵是中医的“重人贵生”思想,《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言“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11]即为此意,庄子也提出了“尊生”和“不以物累形”的主张,《淮南子》也有“天下莫贵于生”的论述,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尊重生命,积极主动探寻生命价值的人生态度。阿育吠陀由于被赋予了宗教意识,因此“放下自我”成为了生命价值的核心理念,即觉知本体、净心无碍、无欲自在的超脱状态,其希望世人走出“小我”认知的局限性,接近宇宙本真;若世人刻意追求“小我”价值,就会偏离生命的本体,形成贪欲。中医和阿育吠陀在生命的价值认知上都认为人不应被物所累,以免由物及心、欲望过多而导致身心疾病;不同的是,中医主张万物中以人命为贵,而阿育吠陀则认为应摒弃小我意识去接近宇宙本真,达到人与神的连接。
4 生命超越观
生命超越观,是指人类通过生命本身的实践活动不断超越生命存在的现实,提升生命存在的价值。存在不是生命唯一的目的,体验生命存在的幸福感,寻找生命存在的认同感,升华和超越生命的生理本质才是意义所在。
4.1 体质变易
“人定胜天”是中医调变体质的最终目的,人的脏腑、经络、精、气、血、津液、神等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因此先天的体质遗传和目前的体质状况并不能决定后天的生命质量和寿命长短。张景岳曾说:“后天之弱者当之慎,慎则人能胜天矣”“我命在我不在天”即为中医强调后天养护的重要性和超越性。阿育吠陀认为“动态体质”是每个人当下的状态,尽管存在“自然体质”的潜在结构,但我们仍然会受季节、时间、年龄、饮食、外在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不断变化的思想和情绪的影响,引起督夏(Dosha)的波动甚或失衡。阿育吠陀注重充分运用人体内在自愈力,或通过人为自然干预,如改变饮食习惯、调整生活方式、情绪管理、瑜伽运动、冥想以及草药,帮助失衡者调整回平衡状态……阿育吠陀与中医在人的体质调变理论上如出一辙。
4.2 道德修养
“形神兼修”指形体与精神的统一性,是中医身心和谐的养生原则,“形为神之宅,神为形之主”,二者相互依存、存灭相关。后世养生家主张:“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明则形安,孔子也提出过“仁者寿”的养生理念。阿育吠陀是一种涉及身、心、灵的医学体系,注重道德、身体和精神的修行,将躯体视为心灵的庙宇,重视冥想的导入性,讲求心智的“戒定慧”。通过深化自己的内在精神,着眼于身体的强健,逐渐达到身心融合,此为生命的最佳状态。中医与阿育吠陀在道德的修炼上持有相同主张,认为精神道德的修养与身体调理同样重要,身心和谐是健康的第一要素。
4.3 心智体悟
中医的“天人合一”理念,即人生活于天地之间,天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的生命过程,人体对外界的变化也必然做出相应的反应。人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变化规律,正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古印度将“冥想”看作是一种生活修行之道,其会给身体、思维、情绪带来和谐。《薄伽梵歌》提出瑜伽修炼的最终目的是“梵我一如”。“梵”指的是宇宙的灵魂和本质,“我”指的是人的个体灵魂和本质,“梵我一如”也是阿育吠陀对修行者的至上要求,若修行者将自己的个体意识(小我)与宇宙的最高意识(大我)合为一体,就能达到“人神共通”。中医立足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更注重人体与大自然的联系,“顺应自然”“法于阴阳”、躲避“虚邪贼风”是治未病的重要手段;阿育吠陀因为被印度先民奉为“天启”,带有神性色彩,因此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人和天神的精神互通,这也是两者在哲学思想上最显著的区别。
5 结语
中国与印度都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史,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特征并传承至今。据考证,中印两国的友好交流始于东汉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因此中医与阿育吠陀在此后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也相互影响和渗透,在对自然生命、人类生命的认知上颇有相似之处。
但是,由于中医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影响较大,在对生命的认知上始终立足于唯物辩证法而少有神性意识,因此认为世界本原归于“气”,气之动荡交感衍化“阴阳”,阴阳化生万物,万物以“五行”制化相互促进和约束;而阿育吠陀最早被记录于《阿闼婆吠陀》时被认为是创世梵天所创立,之后由双马童、因陀罗传到人间,因此印度人民将阿育吠陀视为“神性启示”,在该医学体系中注入了宗教色彩,如洁净体内“Prana”在于唤醒身体内在精神能量、人体中同样存在宇宙“三性”等。此外,在防治疾病的养生理念中,中医多倡导“顺应自然”“法于阴阳”的理念,而阿育吠陀更多地重视“灵性”的修炼,以求人神之间的互通。就中医和阿育吠陀的终极意义来说,两者都是为了创造和提升人类的生命品质,在先贤们有限的生命里为后世之人创造了无限的价值,也为人类健康、生态平衡、保护自然、促进文明等诸多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