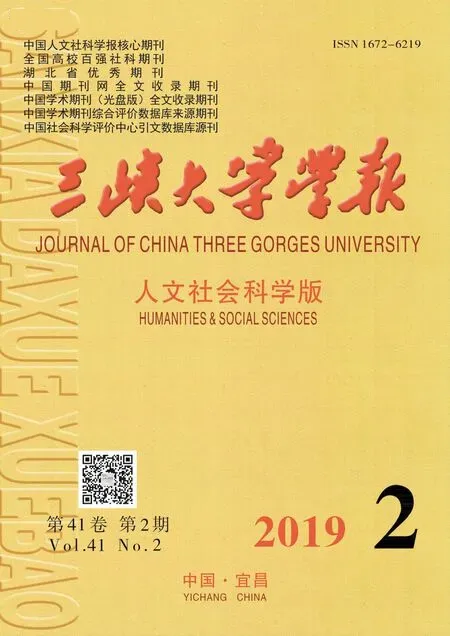文献与义理视野下的女嬃研究
曾广丽
(三峡大学 图书馆, 湖北 宜昌 443002)

一、女嬃身份的多元认知与判断
1.屈原姐姐或妹妹
女嬃究竟为何人?她与屈原是什么关系?历来众说纷纭。史籍最早记载东汉校书郎王逸《楚辞章句》的解读:“女嬃,屈原姊也。”这一解释此后多被采用。宋姜夔《探春慢》词序:“予自孩幼从先人宦于古沔,女须因嫁焉。中去复来几二十年,岂惟姊弟之爱,沔之父老儿女子亦莫不予爱也。”姜夔《浣溪纱》词序中又说:“予女须家沔之山阳,左白湖,右云梦。”清代黄遵宪《送女弟》诗:“粥粥扰群雌,申申詈女嬃。”郭沫若《女神·湘累》:“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其姐女须扶持之。”金开诚认为女嬃即屈原“老大姊”[1],都是将女嬃解为姐姐。
郑玄注《周易·归妹》六三“归妹以须”:“须,有才智之称。天文有须女,屈原之妹名女须。”这是将女嬃解为妹妹了。
闻一多在《离骚解诂》中有云:“嬃从须声,与妹从未声无别,嬃盖妹之异文。《世本》曰:‘陆终取鬼方之妹,谓之女嬇’。(《史记·楚世家·索引》、《路史后纪》八注引。)以妹又作靧(《汉书·礼乐志》注引晋灼曰‘沫古靧字’)例之,女嬃似又即女嬇,楚之先妣也。女嬃为人名,又为星名,与下文重华同亦星名兼人名同例。故通称女嬃曰妹,《世本》鬼方氏之妹即鬼方氏女,《易》归妹即嫁女,并可证。嬃妹同字,而妹即女,故贾逵云楚人谓女为嬃。(见《说文》嬃下引。今本《说文》女作姊,从本书洪注引。)女谓之嬃,则姊妹皆可称嬃”[2]。按闻一多之说,则呼称姊姊或妹妹均可。
文怀沙列举了历来的诸种说法,但他并没有明确表明态度。他也注意到了闻一多的考证,似乎倾向于认同[3]。
2.妻子
《周易·六三》“归妹以须”,《经典释文》解:“须、陆作‘嬬’,陆云:‘妾也’。”《说文·女部》:“嬬,下妻也。”嬬、须、嬃音转而义同,同谓之“妻”。姜亮夫《楚辞通故》有云:“女嬃者,战国以来妇女幼小娟好者之词尔……此不宜为姊氏,而当为小妻。”[4]黄琼《女嬃究竟是谁》也费大量笔墨论证女嬃为屈原之妻[5]。薛亚康撰文《关于楚辞中的几个问题》列举关于女嬃的几种说法,认为妻妾之说较为合理[6]。
3.侍妾、贱妾、侍女、使女、女伴
《广雅·释亲》引《说文》作出阐释:“古妾必幼于妻,别称小妻,故可曰嬃。”这成为女嬃为屈原侍妾说的义理之源。此说最早起于唐代,唐张守节在《史记·天官书·正义》解云:“须女,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7]明代汪瑗《楚辞集解》也持张守节之论:“须者,贱妾之称,以比党人……婺女,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尔雅》曰‘须女,谓之婺女。’婺又作务。是婺星之为须女,须女之为贱妾也明矣。故女嬃者,谓女之至贱者也。嬃正作须,女旁者,后人所增耳。”[8]184汤炳正《楚辞今注》:“女嬃,即侍妾……《说文》:‘嬬,下妻也。’下妻即侍妾。”[9]文章以嬬释嬃,赋予侍妾之意,可谓独见。施润章《愚山别集》卷三也论证为贱妾。明代李陈玉《楚辞笺注》:“人家使女谓之须女,须者,有急则须之谓……‘女须’谓‘美人’之下辈。”[8]185就是容颜美丽的使女。清代陈远新《屈子说志》:“嬃,女侍也。婵媛,侍女态。”[8]186这是将女嬃当侍女了。
郭沫若翻译《离骚·九歌》注曰:“女嬃,女伴。嬃,音虚。旧以为屈原妻,不确。”[10]文怀沙《楚辞今绎》认同:“译文从沫若师,作女伴。”[11]
4.母亲
龚维英撰文《女嬃为屈母说》认为:“从语言角度看,蜀、楚地域相邻,语言(方言)往往近似,今犹如此。譬若蜀人称妻为‘堂客’,两湖人亦复如是,特别是湘鄂西境与蜀毗邻者。那么,楚语‘女嬃’是不是径指母亲呢?何况古时往往母、女混用,故《天问》‘女歧无合’之女歧,到《吕氏春秋·谕大》内,便成了岐母(闻一多《天问疏证》),然则,《离骚》的‘女嬃’岂不就是‘嬃母’,也即‘妈妈’的同义语吗?”[12]认定女嬃为屈母。
不久,戴伟华撰文《女嬃非屈母》与龚维英商榷,从语音、嬃之释义、语境、历史文献等角度对龚说提出质疑[13],于是屈母说无法成为定论。
5.女儿
此说多在汨罗江一带的民间传说中流传,并与秦楚战争相关联。《长沙府志》载:“秀英墓,在县西花园洞,相传屈原女。”(《长沙府志》卷十六《益阳县》条)。相传汨罗江南侧有望爷墩,女嬃在望爷墩上遥望,希望投江的屈原归来。山下有楚塘,清《湘阴县图志》:“楚塘,大数亩。屈原女葬父于此取土,其地藕花重台胜他处。”刘石林撰文《女嬃考》,从历史、语境、音变、民间传说等角度推测女嬃为屈原之女。“屈原在长期的流徙中,其亲人可能失的失、死的死,到汨罗时,恐怕就只剩唯一的亲人——女儿女嬃了。”[14]但为什么屈原女儿称“女嬃”?作者没有解释。
6.神巫、巫长
《前汉书·广陵厉王胥传》:“而楚地巫鬼,胥迎李女嬃,是下神祝诅。女嬃泣曰:‘汉武帝下,我左右皆伏。’颜师古注曰:‘言其土俗,尊尚巫鬼之事。’女嬃者,巫之名也,见女嬃言武帝神下,故伏而听之。”[15]这是神巫说的滥觞。颜师古注曰:“女嬃者,巫之名也。”清周拱辰《离骚拾细》:“嬃,乃女巫之称,与灵氛之詹卜同一流人,以为原姊,谬矣。”[7]308湖北大学蒋方教授《<离骚>中的女嬃与上古时期的女性名号》一文,归纳上古时期带“女”旁的女性名字,认为可分“女神、女祖、女巫”三大类,最后总结“女嬃与重华、巫咸和灵氛一样,都是楚人中享有崇高地位的具有神性的人,只不过她是一位具有神性的女人。”[16]何剑熏《楚辞拾沉》:“《离骚》中的人物,或为古人,如尧舜禹汤,文王、夏桀、殷纣、吕尚之类;一为神人,如望舒、飞廉、宓妃之类,皆无实际,女嬃亦是。”[7]302-303张中一撰《屈原新传》有云:“《离骚》中能活动的人物主要有女嬃,是《离骚》主人公灵均崇敬的巫师长者,他听从女嬃的告诫后,便面对着先祖重华陈词中正。”[17]释女嬃为“女巫神的巫长”。女巫说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
7.杂类
此一类多为个别学者的学术观点,没有多大历史影响或其影响今已不传。所谓“妾长”、“保姆”、“党人”、“美女”、“寓言”、“假设”、“星宿”、“先妣”、“女修”、“方言”等等,均属此类。
清人王闿运《楚辞》释嬃为“妾之长称嬃”[8]188;游国恩释女嬃为“师傅保姆”[8]7;陈士林释为“侍妾或女伴中之长者”[18]。
闻一多在《离骚解诂乙》中有通过从切韵与音变角度论证“女嬃似又即女嬇,楚之先妣也”[19]。故先妣说从闻一多而来。他在同一部书中又论证道:“《开元占经·北方七宿占篇》引石氏曰‘嬃女四星。’又引巫咸曰:‘嬃女,天女也。’疑嬃即嬃女。”将女嬃解作星宿,这种说法有一定影响,李嘉言撰文《离骚丛说》论述“须女本是星名”[20]。戴伟华《<离骚>“女嬃”为女星宿名的文化诠释》一文,论述“须女,是二十八宿之一。《离骚》中的“女嬃”为二十八宿之一的‘女’星宿。”[21]他们都将女嬃视作星宿名须女的倒文。
黄震云撰《楚辞通论》称:“根据《史记·秦本纪》,秦之祖先未知何人,但其可知的母系血缘是高阳之孙女,名字叫女修,修即为嬃。”[22]按音同字异推测女修即女嬃,此论后人无应。
综上所述,有关女嬃身份的各种解读共有七大类二十余种。笔者认为,上述种种考辨除“姐姐说”之外,其余各有所据,但也各有不足,不足以成为定论。虽然“姐姐说”也并没有十分确凿的逻辑理路,但笔者还是认定此说,并认为女嬃具有巫师身份,理由如次:
(1)王逸之说最早,曾两注楚辞:除注《楚辞章句》外,另注《九歌·湘君》之“女婵媛兮为余太息”云:“女谓女嬃,屈原姊也。”[23]18这种说法影响最广,已成主流,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南宋朱熹《楚辞集注》、清戴震《屈原赋注》都承此说,后世的辨析与认定没有给出足以推翻王注的文献证据,不足为凭。
(2)楚地方言有“谓姊为嬃”之说。东汉经学家贾逵早于王逸,贾逵为许慎之师,许慎《说文解字》注“嬃”引贾逵《离骚经章句》之佚文说“楚人谓姊为嬃”,贾逵方言之说有较高可信度。
(3)“秭归”地名本称“姊归”。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叙述:“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姊归。即《离骚》所谓女嬃婵媛以詈予也……东北六十里有女嬃庙。”[24]洪兴祖《楚辞补注》:“秭与姊同。”[23]62可见至迟至东晋时乡人已为屈原之姊修了“女嬃庙”,传说不是虚言。

(5)女嬃具有巫师身份。按意大利人类学家维科之论,远古时代,初民由于心智的蒙昧,视万物有灵而发生交感巫术,这种交感巫术分为两种形式,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金枝》中对此有具体解释[25]。他们将土地生长谷物与女性生育视为同一神秘力量的体现,乃通过人为的手段——男女野合(人的性能量激动土地性能量,此为交感巫术)——达到人口繁衍和五谷丰登的效果,此为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由于巫师不仅是人鬼往来的桥梁,而且可使男女性活动与土地关联起来而同时获得五谷丰登和人口繁衍,确保国家兴旺发达,故巫师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巫术就在国家的重视中愈益发达,种类愈来愈多,巫师本人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得到有力保障。而处于母系社会的巫师当然绝大部分为女性,楚国由于远离黄河流域的儒家文明,仍然保留了母系社会的影响,巫师多为女性,如灵氛、女咸、山鬼、湘夫人等。在此文化语境中,女嬃具有巫师身份合情合理,根据诗中描述,女嬃善于捕捉微细的征兆而判断人物内心,预判人物命运,修饰自己以娱神,正是一个巫师的典型特征。
周拱辰《离骚拾细》的女巫之称,蒋方教授《〈离骚〉中的女嬃与上古时期的女性名号》一文的女巫归类,何剑熏《楚辞拾沉》的巫师认知,张中一《屈原新传》的巫长之辩(均见前文)以及颜师古对《前汉书·广陵厉王胥传》所叙述汉武帝时代之李女嬃巫师身份的注解,都在佐证笔者对女嬃巫师身份的认辨。
有人要问:汉武帝时代的巫师怎么也叫“女嬃”?笔者推测:应该是受屈原的影响,屈原成功描写了包括女嬃在内的大批巫师,此后女嬃就作为巫师的通名沿袭下来,正如我们将一切巧匠称为鲁班,一切智者称诸葛亮一样,今将女嬃作为巫师的通名,同此一理。
读者又可能生疑:女嬃既是巫师,为什么屈原没有写她的巫卜生活?读者须知:此事需放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语境中来理解,在《周易》开创的文化传统中,历来有一个关于巫卜的原则:“巫不占亲。”即巫师并不给亲人占卜,因为既然是自己的亲人,占者和被占者都会患得患失,那么“情感”会影响占者和被占者双方的心态而失去平静的理性与神秘莫测的悟性,从而使巫师失去解读征兆或卦象的准确性,则巫师在亲人面前其实无所用其能,她们至多根据个人生活细节来触摸人物心性(如女嬃根据屈原的喜好修饰判断他心性耿直刚断),从而用久已习得的社会经验预判人物未来的命运走向。
但这并不意味着女嬃的巫师人格特征被屈原所忽视,相反,他将女嬃的巫师特性投射到其他巫者身上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女嬃成为屈原观察楚地神秘巫术文化的一面镜像。灵氛、灵修、女咸、山鬼就是这种镜像的典型。由于屈原与女嬃具有如此至密的关系,这确保了他对巫师及其生活的观察与描写才能达到了至真至纯的地步。
是故,综合辨析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女嬃是屈原一个具有巫师身份的姐姐。
二、女嬃与屈姑
湖北秭归一直流传着有关屈姑的故事,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达到高峰。宁发新《屈原的传说》中有《幺姑鸟》[26]一文,叙述秭归一带有一种类似八哥的小鸟,常呼“我哥回哟,我哥回哟”之音,乡人认作是屈原妹妹屈幺姑化作了幺姑鸟,发出呼唤屈原的声音。宁发新《屈原的传说》与女嬃有关的故事共有八个:《九畹芝兰》、《女嬃砧》、《菖蒲剑》、《濯缨泉》、《三件宝》、《颂橘坡》、《神鱼》、《纱帽翅》,与屈幺姑的故事四个《幺姑鸟》、《照面井》、《珍珠岩》、《三星照半月》,秭归的传说故事并不将姐姐与妹妹细作区分。
谭家斌《屈姑考》认为,屈姑主要出现在传说故事中,史籍无考。作者推测:“屈姑的称谓对象在屈原诞生地乐平里是有区别的。屈姑为屈幺姑的简称,乐平里习俗称谓的‘屈姑’,多是屈氏家族之外者对屈家女子的称呼,故称谓中带上‘屈’的姓氏,对屈家的姐姐或妹妹均可用这种称呼,也就是说屈原的姐姐女嬃或妹妹香录都可称呼为屈幺姑,有的以示尊敬,则不带姓氏‘屈’,即称呼幺姑。”[27]按作者之意,女嬃与屈姑应为同一人,只是称呼者的辈分不同,故有名号之别。
谭家斌先生从姓氏源流的角度提出“女嬃即屈姑”的结论,笔者试图对此说提供音韵学的解释:从音韵学角度判断,女嬃与屈姑其实是同一人,由于地方方言的变异淆讹,女嬃被读成屈姑。根据郭锡良先生《汉字古音手册》提供的相关音韵学知识,女,泥母鱼部[28]119(即该字声母是“泥”,韵母是“鱼”),屈,溪母物部[28]116,“鱼”与“物”大致在同一韵母范围内,当秭归一带的地方方言发“泥”音与“溪”音、发“鱼”韵与“物”韵时,都有可能由于某一音韵的欠缺或重浊而发生音转——如红安话发“非常好”为“灰常好”;恩施话发“吃饭”为“七换”——则“女”音转为“屈”;嬃,心母侯部[28]117,姑,见母鱼部[28]92,此二字韵部相邻,构成旁转关系,即使没有地方方言的影响,也容易使二音重叠,从而使“嬃”音转为“姑”,故“女嬃”即“屈姑”。
至此,笔者大致可做如下判断:女嬃又名屈姑,屈原之姊——女巫,美丽聪明,通达世故人情,洞察人心,因亲情和同情而跟随流放的屈原,对屈原呵护备至,多有申斥劝谏,目睹并参与屈原后半世生活,她既构成了屈原诗歌女巫的原型,又是其诗歌灵感的来源。
三、女嬃意涵的英译与传播
许渊冲在《楚辞(汉英对照/文白对照)》一书以杨逢彬所编的《离骚》为底本,将女嬃译作sister,原文: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
许译:My sister gently comes down cast,oh! She warns me again and again[29]。
亦即将“女嬃”解作“姐妹”,究竟是姐姐或妹妹,英语sister的义项是模糊的。
卓正英《楚辞(汉英对照)》一书里,根据陈器之、李奕对《离骚》的今译底本,“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被诠释成“女伴牵持不舍地对我关切,曾经反复从旁边劝诫着我”,作如下翻译:
My sister, affectionate although discontent With my attitude, does repeatedly me chime……[30]
陈器之、李奕对《离骚》的今译将“女嬃”解作“女伴”,卓正英译为sister,于是sister又有了“女伴”的义项。
孙大雨《英译屈原诗选》根据游国恩、郭沫若、林庚对女嬃的解释,在英文译注部分为“女嬃”译成sister的原因提供了详实的说明,因而有如下翻译:
My sister,deeply concerned for me, short of breath,Blamed me with love in this wise again and again[31]。
杨宪益、戴乃迭译的《楚辞》采用杨书案的今译《离骚》为底本。杨书案将女嬃解作侍女,故杨宪益、戴乃迭把女嬃译成handmaid。
My handmaid fair, with countenance demure, Entreated me allegiance to abjure[32]。
Handmaid有“女佣、女仆、侍女”之意,侍女之说是国内学者解释的一个方向,杨书案、杨益宪,戴乃迭都顺应了此意。
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 )在其译作《楚辞:屈原等诗人创作的中国古诗选集》中翻译“女嬃”时,全面搜寻了中国学者有关女嬃的解释,最后将女嬃当作专名直接用拼音“NU Xu”标注,并在英译注解中将女嬃的多种解释一一列出,而表明自己偏向于“楚巫”义项,当关涉到对于“巫”的理解时,霍克斯又用中国北方的萨满巫师之义对应楚巫之义,使中国南巫居然领有了北巫之义[33]。
匡桂阳《<楚辞>“女嬃”的英译考辩》一文也注意到了上述情况,作者从考据学与诠释学的角度考察了女嬃的英译。这是一份新材料,学界多没有注意,但显然极有价值,不能忽视。作者经过比较诸多女嬃英译的歧义与优劣,认为相对而言,霍克斯的方式最佳,但也有不恰当处。作者从专名处理、诠释学与考据学三种视角作出论证:
专名处理:“霍译本拼音音译法把女嬃视为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独立信息,完整地保留在译本里,有助于女嬃在译语文化世界里广泛传播,使只能在人听觉范围内产生作用的声音,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在动态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语音固化,以语音动态定型的方式,让女嬃要在译语文本里产生了阅读功能,也是楚辞英译的一种创新。”[34]74
考据学:“霍译本的音译处理手段,巧妙地把‘女嬃’这个异质文化以‘异化’的方式固定在译语的文本里,规避了许、卓译本对‘女嬃’过度归化而造成的文化信息损失。”[34]76
诠释学:“霍克斯旁征博引,在译注中表现出广博的学术视野和运用材料的能力,其中,引汉书史实更是开创了《离骚》外译文史互证的典范。但是,霍克斯用shamaness译楚巫是不确切的。shamaness是指女性萨满巫师,笔者认为,将shaman(萨满)这个富含浓厚北方宗教色彩的词用于翻译南方楚国的楚巫,此种‘北词译南物’的译法,极易使目的语读者将我国南国楚地的‘楚巫’与北方萨满教的萨满巫师混淆”[34]75。
可以看出,屈原之诗以及对女嬃意涵的考辨与阐释也引起了英译者和英语世界的关注,这是中国文化传播的可喜事件。上述几种有关女嬃的英译,都以考据学为基础,进行诠释学的翻译,尽可能注意到了文史学者对女嬃的考据证据与诠释结论,特别是霍克斯的翻译方式得到了匡桂阳的认同,认为这是目前几种翻译方式中最好的,显示了翻译将来有可能是通行的道路,但笔者认为几位学者的翻译仍然不够全面精准,他们没有意识到女嬃作为屈原姊姊与巫师身份的统一,或将女嬃释为萨满,更没有注意到源自女嬃的屈姑传说。匡桂阳的点评相当具有学理的辩证意味,笔者认为他的点评是准确的,但其实匡先生也也没有意识到这两个问题(姐姐具有巫师身份;女嬃即屈姑和屈姑的相关传说)。
许、卓、孙、杨作为中国学者以考据为基础的女嬃英译向英语读者传达了部分意义,但没有给出女嬃的全部文化背景。霍克斯作为英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相当了解,他的成功与失误导致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发生歧义,使读者将女嬃理解为萨满。这么说虽有“吹毛求疵”之嫌,但这种“吹毛求疵”却正是翻译的最高要求!按这种要求,翻译对于意义的传达似乎永远不可能达到全面准确,我们对于终极真相的追求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