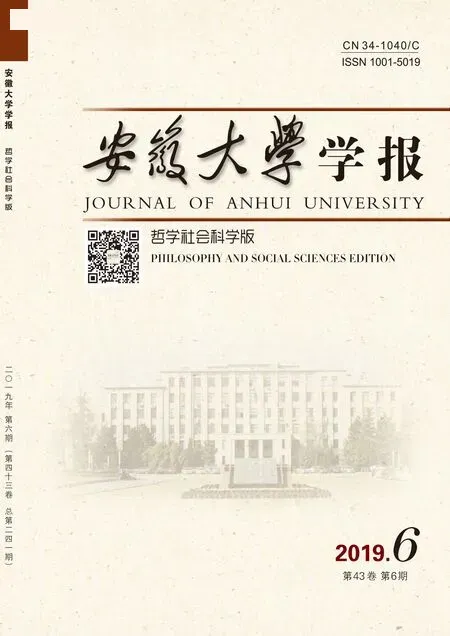以德抗位:先秦儒家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抉择
谢耀亭
先秦儒家的政治理念或说政治抱负,是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德位合一”是其政治理想,即施政者具有良好的“德行”,并以“德”治理天下。然而春秋时期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德、位往往难以合一,“德位相济”便成为儒家退而求其次的目标。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如何保持、践行自身理想,实现宏阔的政治理念,便成为儒家沟通理论与实践必须解决的问题。先秦儒家在处理德位关系时,始终以“德”的拥有者自居,以“以德抗位”的精神实现其政治抱负,但其具体表现形式和处理方式,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学界以往多集中探讨孟子思想中的“以德抗位”精神,且重点阐释孟子所言“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的精神。郭店简出土后,杜维明较早注意到这批竹简中表现的先秦儒家抗义精神。他指出:“郭店的这批资料主体性很强。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匹夫不可夺志’,不仅如此,这种主体性还可以与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没有关系。毫无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人,也可以有主体性,可以‘以德抗位。’”(1)杜维明:《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也有学者结合传世文献,认为“以德抗位”精神是“思孟学派一个极为典型的特征”(2)梁宗华:《从孟子看思孟学派的“以德抗位”精神》,《东岳论丛》2009年第12期。对孟子“以德抗位”思想的研究,还有杨丽霞《试论〈孟子〉中“以德抗位”的精神》(《甘肃理论学刊》2012年第6期)、王霞《以“德”抗“位”的回归——论孟子、赵岐和朱熹的君臣观》(《湖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等。。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主要记录了鲁穆公与子思和成孙弋之间的对话,其中“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的思想,为我们了解子思学派对德位关系的认识提供了宝贵资料,弥补了缺环,进而使我们清楚了从孔子到荀子,先秦儒家“以德抗位”精神的几种不同表现形式。
一、孔子的“以德谏位”
孔子认为,理想状态的政治局面是君主能够“为政以德”,如此就会出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的良好政局,在他心目中,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前代圣贤才能做到(3)《论语》中不乏对这些圣贤的称颂,如“天之历数在尔躬”(《尧曰》)的尧舜、“吾无间然”的禹(《泰伯》)、能“举伊尹”的汤(《颜渊》)、创造“郁郁乎文哉”(《八佾》)的文王、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的武王、“不复梦见”(《论语·述而》)的周公,都是孔子心目中具有很高德行的在位者。。然而孔子认为“天下有道”的政治局面已不复存在,如今的社会形势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季氏们并不具有“德”。在这世风日下之时,只能由有“德”之臣去辅助在位者,在位者则需要任用有德者,从而达到德位相济,形成良好的政治局面。基于这种“德”“位”关系的思考,孔子强调君臣关系必须遵循“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这一原则,如此君臣相济,才能改善政治局面。
礼在春秋时期对于整个社会仍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约束力,对违礼现象的谴责,无疑是希冀社会走向礼制,此时人们在主观上仍倾向于对礼制做出补救。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他推崇周礼,强调君君臣臣,且躬身实践、倾力维护,认为臣下一切行为也都要遵循礼。《史记》载:
陈司败问孔子曰:“鲁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退而揖巫马旗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鲁君娶吴女为夫人,命之为孟子。孟子姓姬,讳称同姓,故谓之孟子。鲁君而知礼,孰不知礼!”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4)(汉)司马迁:《史记》卷67《仲尼弟子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18页。标点略有更改。
鲁昭公的做法显然是违反礼制的,但鲁昭公“本习于容仪,当时以为知礼”(5)(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150页。,所以陈司败问孔子鲁昭公是否称得上“知礼”。孔子“昭公知礼”的说法,明显是为尊者讳。这种事实与判断间的矛盾,在孔子看来却是符合礼的。“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荀子·子道》),在所居之邑不指责其大夫的不良行为,是礼制的规定。孔子在明知鲁昭公的行为属“非礼”时,仍谓其“知礼”,恰恰表明孔子是依礼而行。由此可见,孔子自觉把自己定位在“臣”,依“臣”的标准行事。
孔子处理君臣关系讲求礼,但为臣之道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这一“道”便是“圣王之道”(6)(梁)皇侃《论语义疏》卷3《公冶长》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疏释:“孔子圣道不行于世,故或欲居九夷,或欲乘桴泛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02页)显然,此“道”是“圣王之道”。,如果所事之君不符合“道”,宁可退出政治,另待明君,因此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体现了孔子以德抗位的思想。孔子以其毕生的经历证实了其在“臣道”问题上的言行一致。
但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并非意味着君臣间只要出现不一致就要退出政治,而是在君臣关系最终无法调和时才做出的选择。那么,在“德”与“位”出现矛盾时,臣下该如何应对?《荀子·子道》所载一条孔子资料极可关注: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7)(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30页。
在孔子看来,“争臣”是国之栋梁,国家的兴盛离不开他们,真正的“臣”应该具备争臣的品质。当季氏将伐颛臾时,孔子说:“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论语·季氏》)臣要有臣的担当和能力,否则就应离去。臣的职责之一便是纠正君主的错误,所以孔子说“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孝经·事君》)。在孔子看来,当“德”与“位”出现矛盾时,具有“德”的大臣应该规劝在“位”者,具体的方式便是“谏”。这可以视为“以德谏位”。
谏的方式有多种,《说苑·正谏》载:“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乎。’”(8)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06页。依“臣不可言君亲之恶”的礼制,孔子采用的方式主要是“讽谏”。《白虎通·谏诤》载:“孔子曰:‘谏有五,吾从讽之谏。’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去而不讪,谏而不露。”(9)(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36页。“讽谏”就是以委婉的语言、隐喻的方式来规劝,这样既可达到“谏”的目的,又符合礼的规定,在屡谏无效的情况下,“臣”便可以采取“止”的抉择。孔子没有让“德”屈从于“位”,而是以退出不良政治体系的方式来保持自己对“德”的拥有。
总而言之,孔子认为当时现实中“德”与“位”是分属的,如果君臣二者相济,则能开出良好的政治局面;如果二者产生矛盾,在位者不能贯彻有德者的主张,有德者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讽谏——努力规劝在位者;如屡谏无效,则有德者应遵循“不可则止”的原则,退出政治舞台。孔子开启了儒家“以德抗位”的传统,其方式显然是温和的。
二、子思的“以德责位”
战国时代,士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孟子·滕文公下》载景春之语:“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士人的言行,有时会左右国家的发展和命运。列强争雄,诸侯兼并,各诸侯国为立于不败之地,争先恐后地尊贤、养贤,“尊贤”成为社会思潮。尊贤思潮的兴起,无疑让士人的自我认同、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升。社会的变化,也影响到儒家处理德位关系的态度。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的出土,让我们看到子思学派在此问题上的新变化。简文围绕“何为忠臣”展开对话: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成孙弋见,公曰:“向者吾问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尝有之矣。恒称其君之恶,未之有也。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恶闻之矣。”(10)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
子思“恒称君之恶者”才是“忠臣”的论断,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新气息。孔子依“臣不可言君亲之恶”的礼制,采取讽谏手段晓喻君王,开启儒家“以德抗位”的传统。子思不仅不为君主隐讳,反而认为只有不断指出君主过错的人才是“忠臣”。成孙弋为鲁穆公分析“恒称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的真实意义:臣忠于君,大多皆出于爵禄,甚至为了爵禄可以牺牲自我,这是基于利益而忠君,并非真正的“忠臣”。相反,能“恒称其君之恶者”,不受利益的驱动,是“有德者”对“在位者”的支持和帮助,其间体现出的是“道义”,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显然,在“德”“位”产生矛盾时,孔子“以德谏位”,而子思则表现出更为激烈的“以德责位”。这种“恒称君之恶”的“以德责位”思想,是“以德谏位”思想的发展。在我们看来,此种转化与儒者身份的自我认同发生变化有关。孔子始终保持在“臣”的地位上对待“德”与“位”的关系,而子思则特别强调自己“师”的身份认同。《孟子·万章下》载:
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
子思不悦,在于鲁缪公以“友道”与士人交,这在子思看来是错误的。论位,臣依“臣道”而行,不敢与君交友;论德,君有求于士,应以“师道”待之,不可为友。子思始终以“师”的立场处理“德”与“位”的关系。在《鲁穆公问子思》中,鲁穆公虽然不悦于子思的回答,但仍“揖而退之”,表明鲁穆公确实是以“师”礼待子思。《礼记·学记》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郑玄注:“尊师重道,不使臣位也。”(11)(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68页。君、师关系的定位,无疑会使“师”者自尊、自贵,以此体现其对“德”的拥有,对“道”的践行。对“师”者身份的认同,也有助于其自身刚毅品格的形成。文献所见,子思确有刚毅的品格。《孔丛子·抗志》载子思言:“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12)《孔丛子》所载内容,历来多怀疑其真实性。1973年八角廊墓汉简《儒家者言》的出土,使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包括《孔丛子》《孔子家语》等历来认为伪书的著作。就《孔丛子》而言,学界多承认其有原型,但并非一人一时之作,是在较长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定型的(可参考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黄怀信《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结合《孟子》中言及的子思品格,我们认为《孔丛子》此处所载子思之语是可靠的。子思的刚毅品格朱熹也有觉察,谓子思“恁地刚毅”(13)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十七册《朱子语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00页。。综合各种因素,当子思说出“恒称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其深层原因就是自“师”位观之。当然,这与此时社会兴起的“尊贤思潮”是分不开的。
《孔丛子·居卫》载:“曾子谓子思曰:‘昔者吾从夫子游于诸侯,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而犹圣道不行。今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无乃不容乎!’子思曰:‘时移世异,各有宜也。当吾先君,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故相诡,乃各时也。”(14)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2《居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0页。显然,对曾子“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和“观子有傲世主之心”的说法,子思是以“时移世异”来解说的,认为孔子之世“周制虽毁,君臣固位”,因此需要“执礼以求之”,而他所处的时代“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人君必须虚心待“师”,因此子思有“傲世主之心”也就显得十分自然了。《孔丛子》所记子思之言论,可以从上述对孔子“以德抗位”的分析,以及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所载内容获得支持。子思在具体处理德位关系时,把传统君臣格局下的臣的地位及尊严提到了“师”这一至高点。如果说孔子“以德谏位”还带有某种对国君的依附,那么子思“以德责位”更显示出他政治思想方面的独立意识,因此才会表现出较为强势的“傲世主之心”。子思这一观点,不仅直接影响到孟子,且对以后良好政治局面的判断及形成,以及“忠臣”的定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孟子的“以德易位”
孟子希冀的良好政治局面是“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入仕是儒家施展其治世抱负的必由之途,但孟子强调要遵道而仕。《孟子·滕文公下》载,有人曾以“君子难仕”的问题询问孟子,孟子回答道:“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不由道而仕,就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的男男女女,会受到人们的鄙视和指责。
孟子处理德位关系的思想有了新的突破。《孟子·滕文公下》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持“道”而行的人生态度及浩然正气的大丈夫形象跃然纸上,其“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思想秉承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原则,但其特立独行则更为突出。在具体“进”与“退”的问题上,孟子提出“三就三去”原则: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此为孟子处理“德”“位”关系的具体原则。《孟子·万章下》有段非常重要的对话: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
可见,孟子同样是把自己当作“德”的拥有者,他赞同“天子不召师”的观点,认同子思诸侯可以士人为师、不可为友的说法,即赞成子思的“以德责位”观点。但孟子进一步强调:“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甚至“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显然,孟子更加显示出士人自身的独立性,比子思更为突出,在“以德抗位”上走得更远。孟子继承子思“以德责位”的思想是非常明显的,这从《孟子》一书中大量引用子思在此方面的论述便不难看出,但孟子在强调自身之“德”的同时,更注重舍生取义的大丈夫精神,他说:“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孟子·公孙丑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以自己所拥有的仁义来抗衡现实中之富爵,不为富贵、贫贱、威武所动,保持人格尊严与道德完美。在孟子看来,“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下》),突破了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原则,强调道德之士可以背弃无德之君: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成既,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这里说的“君臣”及“君民”关系,显然大大超越了以往儒者的思想,给“以德抗位”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新气象。孔子在“德”与“位”发生矛盾时,以温和的“以德谏位”方式处理,局限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其中“礼”的约束仍时时可见。子思虽然在理论上提出“禅让”,采取较为强劲的“以德责位”方式,但仍可归为“改良”一系。因为其提倡的“禅让”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期望“德”与“位”重新合一,其实这在当时现实政治中无法实现。由此他们只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来显示自身的独立,表明自己对“德”的拥有。及至孟子,把“以德责位”推向“以德易位”,甚至提出“诛一夫”的口号,换易无德之君的暴力革命的因素骤增。从君臣间关系而言,子思学派承认君臣双向互动,但仍是一种传统政治秩序内的互动,即君位远远高于臣德。而在孟子的思想中,君臣间的关系有独立之两极的倾向,其关系也颇有“契约”的味道,有德之士的特立独行更为突出。更为重要的是,孟子基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强调国君失德无道之时,可以采取强行的“易位”措施,宣扬了暴力革命。这样的理论,确实不为古代统治者所喜爱,孟子也因此一度遭到朱元璋的罢祀(15)(清)张廷玉等:《明史》卷50《礼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96页。。然而,孟子“以德易位”思想确实是儒家德位关系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宣扬“失德即失位”的理论,开启了后世暴力革命易位的传统,影响极其深远。
四、荀子的“以德配位”
尽管子思“以德责位”和孟子“以德易位”都属于“以德抗位”范畴,都希望实现“德位相济”的良好政治局面,但他们都强调自己“师”的身份,实际上与孔子所认识的“德位相济”原则有所“游离”,因为孔子要求的是强烈的“入仕”思想,子思、孟子宣扬的则是臣相对“独立”的思想,两者略显不同。战国晚期,政治格局渐趋明朗,统一势在必行,诸子学说整体表现出一种务实倾向,即其学说可以切实地在政治中运作,荀子便着眼于从“制度”角度解决德位关系问题,提出“以德配位”思想,从而使君臣关系再次回归到“德位相济”这一原则上来。
《荀子·君道》云:“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荀子主张君主通过以德配位,构建良性官僚系统,使人尽其才,德配其位。显然,“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是从“制度”角度看待德位问题。有德之士入仕,得到其“位”,以实现治国理政的政治抱负,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因此,荀子“论德”“量能”思想仍属于儒家思想而非其他。而他强调根据“德”“能”高下授予才德之士相应官位,辅佐国君治理好国家,体现了“以德配位”的观点。尽管这是从“臣”的角度提出“以德配位”,强调国君选择的主动性,但仍然要求君主善于体察臣下,合理使用臣下,从而达到君臣相济,政和国强。
荀子并不仅仅局限于从臣的角度阐述“以德配位”,实际上他也从君的角度做过阐述。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理想的王是“圣王”。《荀子·王制》:“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广,神明博大以至约。”“圣王”是德位合一的王,是理想状态的王,但现实中实际在位者并非能达到“圣王”的境界。虽然如此,在荀子看来,君主仍是社会治理的关键之一,他们是效仿的榜样,因此要做好表率。《荀子·正论》声称:“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显然,荀子也强调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强调他们要以身作则,以达到上下“相有”,君臣相济。
相对于以往的儒者,荀子企望从理论上厘清君权的来源与君主所承担的责任。《荀子·大略》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显然,荀子在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上,进一步开拓下去,从上天生民立君的角度,进一步强调君王、诸侯、大夫的产生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天生烝民的懿德。这在政治理论上,进一步规范了“君主”,强调在位者权力来源与民众的关系,开拓了新的政治思维方式。实际上,从上述荀子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从君主角度阐述了“以德配位”思想,强调上天为民立君而非为君生民,既是为民立君,君德自然需要高尚,这样才能为民谋取福祉。故《荀子·王霸》明确指出:“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荀子把国之荣危兴亡,俱系于人主,强调行王者之法则王,行霸者之法则霸,行亡国之法则亡;国家的治理兴乱,在于君主的修养与谨择。
荀子之所以从君臣两个方面来论述“以德配位”,是因为他认为实现良好的政治局面,维护社会和谐有序,除君主要做好表率,遵道而行,还需要有良好的官僚系统。荀子强调,要实现圣王之道,君主需要依靠贤德之士辅佐,“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荀子·君子》)。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君子者,治之原也”,因此“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即主张君子养原蓄德,以利建立良好的官僚系统,实现政治良性运转。故君子作为人臣,理应恪守其职:“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荀子·臣道》)顺、谄、忠、篡、国贼,是人臣的五种类型。显然,荀子认为人臣应尽其职守,遵道而行,矫君之过,据道而争,除国之患,解国之危,这样的臣子才是德位相配的社稷之臣。
总之,荀子认为理想政治状态下,国君要清醒地认识到上天为民立君,因此需要提高自己的修养,以身作则,为天下表率,任用君子治世,确保政治实践良性运转。另一方面,臣子也要恪尽职守,循道而行,辅佐君主,以利形成良好的政治局面,使社会得以大治。但是理想并不等于现实,尤其是身处战国乱世,这一理想已成奢望。面对现实中不协调的德位关系,有道之君几近绝迹,应该如何处理与君之关系?荀子主张对不同的君主应区别对待。如事“圣君”,则“恭敬而逊,听从而敏,不敢有以私决择也,不敢有以私取与也,以顺上为志”;事“中君”,“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挢然刚折,端志而无倾侧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事“暴君”,“调而不流,柔而不屈,宽容而不乱,晓然以至道而无不调和也,而能化易,时关内之,是事暴君之义也。若驭朴马,若养赤子,若食喂人,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荀子·臣道》)。显然,荀子并不认同孔子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而是积极入仕,主张针对所侍君主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尽其所能,促进治世的出现。
当然,如果“德”“位”出现严重脱节,君失其义,矛盾激化,难以缓和之时,应遵循“从道不从君”的原则,甚至同孟子一样,主张“以德易位”。在《臣道篇》和《子道篇》中,荀子曾三次强调处理德位关系的最高原则——“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称:“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参天地,泽被生民,夫是之谓权险之平,汤、武是也。”《荀子·正论》云:“暴国独侈,安能诛之,必不伤害无罪之民,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昔者武王伐有商,诛纣,断其首,县之赤旆。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可见,荀子以汤武革命之例,强调如果在夺、杀之后,体现出来的是仁、义,“易位然后贞”,那么以德易位便是替天行道,“功参天地,泽被生民”,不仅值得赞许,更应奋力倡行。
荀子主张积极入仕,通过自己的努力促成治世的出现。他对君权与民众关系的思考,表现出新的政治思维,丰富了儒家的政治理论。荀子在德位关系的处理上,更加务实,更具操作性,拉近了儒家的理想政治与现实参与的距离,为儒家学说融入现实政治开辟出新的途径。荀子的“以德配位”思想延续了儒家“以德抗位”的精神与传统,遵循的是“从道不从君”原则。
五、结 语
先秦诸子,有的强调独善,坚守贵己;有的追名逐利,功利既是其奋斗目标,又是其坚持的原则。儒家则以积极的态度面世,以期通过入仕实现其内圣外王的理想目标。儒家入仕,遵从着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便是儒家对德位关系的坚守,秉持“以德抗位”精神传统。可以说,丧失了通过入仕而实现平治天下的努力,儒不能成为儒;因希冀入仕而放弃对德的坚守,儒不配称为儒。德位关系的处理,牵涉到“儒之是否为儒”的根本问题,是儒家实现其理想目标又不失其儒者本分的关键所在。
整体而言,自孔子至荀子,先秦儒家没有让“德”屈从于“位”,而是坚守“以德抗位”的传统。在儒者不能居上位的现实中,儒者以“德”的拥有者自居。曾子有言:“晋楚之富(贵),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此是先秦儒家“以德抗位”的原动力,既是儒家精神的自我要求,也是儒者得以傲立于士人中的资本。
儒家虽然努力实现“德位合一”,但在实际的政治中,德与位并不统一,“德位相济”是儒者努力营造的德位关系。当德与位出现矛盾,无法形成“德位相济”的局面时,因时代的不同,在儒家身上表现出不同的处理方式。孔子受礼制的约束,处理德位矛盾时采用较为温和的“以德谏位”,在谏而不听的情况下,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退出政治,坚守底线。子思则采取较强硬的“以德责位”,在“责”而无效的时候,采取不合作的方式,以此保持自身之“德”。孟子继承孔子、子思“以德抗位”传统,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提出“以德易位”,在理论上开启了暴力革命易位的传统。荀子则从君臣两方面论证“以德配位”,从制度层面强调君臣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主张在德位矛盾无法调和时,也可采取“以德易位”。荀子的理论大大丰富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表现出更加务实的态度,体现了新的政治思维和方式。
伦理与政治,乃儒家学说之一体两翼。伦理是其根基,规定着学派的特色和底蕴;政治是其目标,体现着儒者的奋斗方向和自我价值。血缘伦理尽情展开下的有序政治,即是《大学》所谓“明明德”“亲民”之后而“止于至善”的内圣外王之境。也即是说,“修齐治平”是儒者自身价值得以实现的判断标准,而“修齐治平”的实现,需要入仕这一平台。德位关系的处理原则,便成为儒者是否入仕、如何施政的根本性原则和底线。德位关系虽是儒家处理入仕为政的具体原则,但折射出来的,却是先秦儒家的根本精神方向和不可逾越的底线。
先秦儒家处理德位关系所秉持的“以德抗位”精神,是后世士大夫在现实政治中坚持理想追求的动力所在,是后世士人以孱弱之躯反抗暴政的精神支柱,也是儒者身份自我认同最重要的标识之一,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汤勤福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