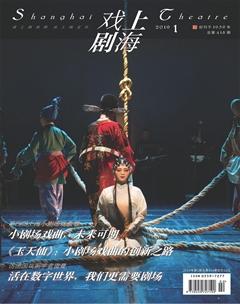活在数字世界,我们更需要剧场
浅草
在第六届乌镇戏剧节期间,本刊特别采访到了德国著名戏剧学者汉斯-蒂斯·雷曼。在接受采访时雷曼先生身体不适,说话间已是气若游丝般地断续,但他仍然认真地思考和回答每个问题。此后我们通过邮件沟通,雷曼就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补充,可见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
作为乌镇戏剧节的常客,雷曼与我们分享了他对乌镇戏剧节、对中国戏剧的观察和思考;作为《后戏剧剧场》的作者,雷曼为我们介绍了戏剧剧场、戏剧构作等概念,以及他所理解的戏剧本质……
问:您见证了乌镇戏剧节的成长,对这一届的印象如何?
答:乌镇戏剧节现在真的成长了,就像一个小孩,6岁了该去上学了。从2015年起我每年都来,从演出的数量来看增长许多,然而现在它没有必要让规模更大。在乌镇戏剧节的舞台上,有许多当代元素,但我希望在第七年能有更多强调实验性的戏剧作品。在观众方面获得成功或者说取得商业的成功是重要的,但就艺术的标准而言,这却不是最重要的,对戏剧节来说也不是。我们经常能发现,在艺术中许多新的、对未来有很重要影响的东西不能被当代立即接受——譬如印象派画家,曾经或多或少地被认作疯子,但很快印象派不仅在美术界掀起了一场艺术革命,而且极大地流行起来。
我想引用瓦尔特·本杰明的一句名言:“一个不教艺术家一些东西的艺术家教不了任何人任何事。”那是说从长远而言,艺术家能发现一些东西去学习是戏剧节的一个标尺。这意味着需要有勇气去展示有争议的作品。
问:本届开幕剧目是孟京辉导演的《茶馆》,戏剧构作是德国人,您如何看这部作品?
答:在这场演出中的确有一些柏林人民剧院、一些弗兰克·卡斯托夫(Frank Castorf)的味道——对观众直接、有时是激进的演说,正面的表演方式,以及跨文本引用的倾向。这可能部分归功于卡斯托夫的合作者塞巴斯蒂安·凯撒(Sebastian Kaiser)的在场创作。然而,我确实没有觉得这个戏受太多“德国”影响的印象。第一,这个戏完全符合孟京辉自己开放舞台过程与观众互动的风格。第二,这些技术通常是后戏剧的标志,而不是专门指德国戏剧的特征。
尽管我明白《茶馆》多少是有争议的,但我的确看到许多中国观众非常享受这个戏,其实我也是。这看起来像是孟式美学迎合了“西方的”心理,也迎合了中国观众的心理。我发现极其有趣的是孟京辉如何重读经典戏剧,摒弃了所有熟悉的对话体戏剧,推动我们以新鲜的方式听到他对社会苦涩的批评。你可以称孟京辉的这种姿态是布莱希特式的“陌生化效果”,同时我也认为这是一种高效选择的做法。
让我谈谈这部作品中“壮观的”元素。一般而言,我不喜欢剧场作品是“壮观的”。如果场景太丰富,我就不喜欢,因为这表示创作者仅仅满足于提供“好”的娱乐。但是孟京辉能使得“壮观”很有趣。这是一个导演难得的天才,他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缝合“先锋”风格与大众品味之间的缝隙。我发现,在今天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能力。过去几年,我看了《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他有两把左轮手枪和黑白相间的眼睛》《茶馆》,孟京辉的作品看起来变得越来越壮观。但是我接受艺术家孟京辉的这一点。我认为孟京辉也是一个老师,是许多年轻的创作者会加以摹仿的一个榜样。我希望他能“教导”他们只需要用一些小的手段就能做出精彩的剧场作品。
问:戏剧构作源自德国,近年来中国也开始学习和流行起来,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
答:戏剧构作,我描绘一个理想的样子——是在剧场中一个因其知識渊博而受到尊重的人物。他的身份就像一个学者和一个顾问,能够向演员解释他们的角色,并且在午夜时分还是导演的酒友。
在今天,如果我不得不为他选择一个定义,那就是:在这个制作团队中的知识分子。他的功能是去一次又一次地问问题,“这是什么?”“我们在这做什么?”相当于一个哲学伙伴,他将去引发在剧场中工作基本原理的讨论,这些很容易就在制作的压力和必要性中迷失的工作。
在历史上,戏剧构作的确是德国的发明。德国戏剧有很长的戏剧构作历史,可以追溯到莱辛的《汉堡剧评》。最初的想法是要对公共文本中的作品进行剧作评论和反思,这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典型想法。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戏剧的政治化和某种明显的知识化倾向提高了戏剧构作的地位,戏剧构作在那时有助于界定剧目的政治和历史语境。
由于剧场形式快速地、持续不断地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剧场向其他艺术和媒介持续地跨界,今天戏剧构作的任务又一次改变。今天的戏剧构作必须意识到在音乐、电影、装置艺术、电视和媒介艺术、多媒体、互联网,以及广泛意义上的数字世界等广阔领域内正在发生着什么,因为剧场一直涉及这些领域。
问:很多中国戏剧人都读过您的著作《后戏剧剧场》,这本书写于1999年,如今您对书中的一些概念和想法是否有变化?
答:你或许知道这个老笑话——有人问:“在20世纪最成功的戏剧是什么?”有人答:“19世纪的戏剧。”这值得我们反思到底什么是成功的作品。“成功”,正如我提及的,与影响是不一样的。
显而易见,在我们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性欲望。戏剧(Drama)意味着:赋予生命以秩序。我们喜欢把生活描绘为完整的开头、过程和结尾。现在我确信,我们现代的或者说是后现代的现实是以这样的一些方式构建的,戏剧化必然会歪曲它。社会冲突不再是领导者之间的斗争,政治现实中的决定不再以个人戏剧性的对话来实现,它们是通过庞大的权力集团长期战略计算来得出真相的。即使我们独自生活,也不再能体验到一个统一的戏剧性故事的开展。
在这些情况下,戏剧剧场(Drama)作为生活的再现就变得虚假,成为一个谎言,一种意识形态。后戏剧剧场(Postdramatic theatre)的出现和形成正是基于此。会有新的剧场形式,但是回归老式的戏剧不太可能。如果你问在德语世界中写作有何新发展,我认为除了老的一代(如汉德克、耶利内克、斯特劳斯)以及当代的一些(如Pollesch、Richter、Schimmelpfennig)之外的大部分年轻的作家都没有回归戏剧剧场。相反,在电影的领域,创作者还是很致力于戏剧的,但你会发现现在的趋势是电影在尝试用影像语言从戏剧的支配中解放出来。
问:您来过多次乌镇戏剧节,看了多部中国戏剧作品,印象深刻的有哪些?
答:从理论上我们知道,文本的意义最终只能由它的语境决定。中国剧场有它自己的语境,我并不熟悉。在我们两国之间,社会价值体系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判断是非常谨慎的。但是,我能主观地评价我看到的东西。甚至我相信冒险犯错去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是我的责任。比如说,孟京辉的《茶馆》,我能想象《茶馆》将会在柏林苛刻而自负的观众中实现非凡的成功。此外,李凝的肢体剧场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让我印象深刻。2016年,我非常喜爱《灵魂辞典》,它在真实生命表演与传媒之间设置了很有意思的装置。在看了其他的一些作品,并在莱芜会见了李凝导演后,我更坚定了我的第一印象。2016年前我也看到一部极其有趣的作品,是李建军导演的《飞向天空的人》。它由一系列或多或少的静态场景组成,就像一连串的静音装置。有人告诉我他不用文本是因为种种原因使他无法使用文本。但无论如何这形成他的一种视觉化的风格,我非常喜欢。我同样非常喜欢王翀导演的《平行宇宙爱情演绎法》,他在媒介与剧场之间构建了别出心裁的装置,为后戏剧的叙述打开了新形式的大门。你看,王翀、李建军、李凝和孟京辉有着完全不同的创作风格,后戏剧剧场有着创作不同呈现风格(不仅仅是表现)的巨大潜力,从而创造出新的观赏类型。
问:您认为戏剧的本质是什么?
答:对我而言戏剧的本质在于,艺术家倾听他或她自己内心的声音,去表达你个人看到的东西,并选择一种形式去呈现你所看到的,把你的作品当作你给予他人的礼物。你向观众分享你的感觉、体验和想法。当然,你会希望观众能够开放自我并参与你的体验。然后观众会以他们的关注来作为礼物回赠给你。每一场演出应该被看作是相互馈赠礼物的过程,一个从两个方面制作礼物的过程。你总是事先问是否你的艺术将会被接受,这种态度很容易就变成希望出售你的作品的可憎心态。可憎的是,如果你把你想说的话调动成想象中的期望,那你就是在欺骗你的观众,也在欺骗你内在的自我。如果你让你自己的作品商业化,你或许会暂时地受到观众的喜爱;但是因为你想售卖而调整你自己的作品,你就会摧毁作为艺术家的自己。
在乌镇的小镇对话单元中,有人问铃木忠志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接受度。铃木忠志回答:“我只是做我自己的作品,我根本不在乎观众怎么想。如果你在意,你就是在做生意,而不是艺术。”我非常高兴听到铃木忠志这样说。我也总是试着教导我的学生(和读者)这种态度。
问:在当今信息如此多元的网络时代,人们为什么还要走进剧场?
答:因为剧场是唯一允许我们用我们的身体交流的形式,不是通过科技,不是通过虚拟技术,而是通过真实的接触。我们越是生活在数字环境里,我们就越需要剧场。我并不担心戏剧未来的命运。基于人类学理论,可以说,剧场从本质而言首先是人类行为的“永恒”类型,其次才是艺术,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艺术,它始终具有非艺术性,因为从本质上说剧场始终是一种完全具象的现实行为,即便它竭力想企及至高的艺术纯度。正是由于这种基本結构,或艺术边缘的定位,才可能让观众有不同程度的参与,让舞台和日常生活产生不同的距离,让表演者具有各种各样的身份,让剧场作为整体能呈现所有戏剧的和后戏剧的情境。
(翻译:肖婷,南京大学戏剧系艺术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