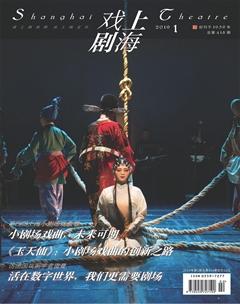忍踏落花来复去
刘轩
摘 要:在苏州举行的中国昆剧节自2000年开始,每三年一届。作为专门为昆剧艺术的传承和传播而举办的艺术节,中国昆剧节上演剧目和形式也随着昆剧在“非遗”之后的不断演进而呈现出新的面貌:从第一届昆剧节上多部古典剧目经典“全本”的整理与恢复上演,到落幕不久的第七届新编戏争奇斗艳,使这一昆剧界盛会不啻为昆剧艺术在本世纪复兴和发展的一个活态记录。本文就试图从“追本溯源”入手,通过回溯历届昆剧节演出剧目的概况和对本届昆剧界展演剧目的分析,抚今追昔,勾勒出昆剧艺术在本世纪发展的侧影。
关键词:中国昆剧节,新编戏,传统戏,“非遗”
2018年10月13日至19日在苏州举办的中国昆剧节迄今已是第七届了。从2000年开始,作为三年一次的昆剧界盛会,昆剧节随着昆剧艺术在本世纪初“非遗”文化身份的确立和演出市场的逐渐恢复,也声势日隆。所谓追本溯源,在讨论这一次昆剧节的观演感受之前,似乎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过往的数届情况,以图管中窥豹,明辨本世纪以来昆剧艺术发展的趋势。
首届(2000)昆剧节的宗旨是促进昆剧的保护和传承,增进海内外昆剧爱好者的交流,昆剧节清唱曲会和舞台搬演并举的基本格局也由此肇始。这届昆剧节的参演剧目多是经过整理恢复的传统古典剧目“全本”,例如上昆的三本《牡丹亭》,江苏省昆的《桃花扇》,苏昆的《长生殿》《钗钏记》,湘昆的《荆钗记》,北昆的《琵琶记》,浙昆的《西园记》,永昆的《张协状元》等。这其中,除了永昆的《张协状元》是根据宋元南戏底本改编之外,其余大多有明清传奇本做基础,并且在昆剧演出史上有折子戏或曲谱流传,因此恢复的“全本”基本都能遵循“整旧如旧”的原则,在“新”与“旧”之间协调出浑融一体的艺术风貌。再辅以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社团演出的折子戏,整个昆剧节的演出算得上全面呈现了当时昆剧艺术的较高水平。在当时昆剧尚未“入遗”、资金来源有限,且整个戏曲演出市场都略显低迷的大背景下,这一次昆剧节着实当得起“盛会”二字,使得人心为之一振。
第二届(2003)是昆剧正式进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后举办的第一次昆剧节。演出剧目与首届注重展示传承相比,已经呈现出了新老并呈的面貌:除了各院团带来的三台折子戏之外,不仅出现了更多改编宋元南戏底本的“全本”剧目,而且还出现了《班昭》《司马相如》等完全新创的剧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昆剧位列“非遗”后不久举办的这次昆剧节中增加了学术研讨会的部分,专家学者们就昆剧节演出的剧目对昆剧的继承和创新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种传统戏曲发展的终极性思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的定义中对昆剧“遗产性”的强调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伴随和影响了昆剧在21世纪的整个发展历程。
第三届(2006)昆剧艺术节举办之时,白先勇推广的苏昆青春版《牡丹亭》全国巡演方兴未艾,昆剧艺术在短时间内收获了较多新观众。国家政策也日益向承载了“民族—国家”文化代表意义的昆剧倾斜,扶持力度增大。各专业院团的资金状况开始有所好转。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剧团纷纷排演大戏新戏、推新人。在昆剧节获优秀剧目奖的三个戏中,除上昆《邯郸梦》略有折子戏作为支撑之外,苏昆的《西施》和浙昆的《公孙子都》都是新创剧目。由此看来,此时昆剧节评奖的风向标已与首届大相径庭。也因为受到更多关注,此次昆剧节的相关讨论也由专门研讨会扩展到了会外,不少学者和“老戏迷”都撰文表达自己对昆剧节新编戏过多的忧虑。不过与此同时,这次昆剧节期间也举办了两场沈传芷诞辰100周年纪念演出、一场纪念昆剧传习所85周年演出和一台昆剧继字辈艺术家演出专场,这也是历届昆剧节中借纪念之名集中演出折子戏最多的一次。与首届昆剧节全本戏与折子戏演出相得益彰的情形不同,在这次昆剧节上,新创的全本戏与守成的折子戏之间似乎代表了昆剧的两种发展路径,呈现出分野态势。
第三届昆剧节对新创剧目的批评似乎起了一些作用。2009年恰逢建国60周年,且临近昆剧列入“非遗”10周年,各大昆剧院团经过近十年的重振旗鼓,此时都气势正盛,挖掘恢复传统剧目也呈现出一个小高潮——在当年的第四届昆剧节上出现了四大古典名剧《西厢记》(北昆)、《牡丹亭》(苏昆)、《桃花扇》(江苏省昆)、《长生殿》(上昆、苏昆)齐聚一堂的盛况。除此之外,在这一年的昆剧节上,其他经典剧目也得以以不同形式的“全本”面貌呈现,例如中国昆剧博物馆和苏昆合作排演的小“全本”《玉簪记》,在传统戏台上搬演,小巧精致;上昆恢复的汤翁另一名作“全本”《紫钗记》虽然舞美和服化颇多新创,但基本戏剧结构仍然遵循了汤翁原作;永昆虽然财力有限,但是立足于自身传统,重排了“南戏之祖”《琵琶记》,搬演风格与南昆其他院团相比较为古朴,颇有宋元遗风;更为难得的是,上昆仅存的传字辈老艺人倪传钺亲授了暌违舞台甚久的传统剧目《寻亲记》等等。从参演人员来看,这一届昆剧节全面展示了昆剧演出团体的梯队建设和人才储备,不仅艺术已臻化境的“昆大班”一辈亲自登台,江苏省昆、浙昆、苏昆的中生代也基本做到了阵容齐整、文武兼备,同时各大昆剧院团也推出了一批艺术上可圈可点的年轻后辈。因此,这次昆剧节也可以看作是对昆剧演出经过近十年的重点扶持和发展后的一个全面展示。
第五届昆剧节(2012)举办之时,政府层面已经完成了院团体制改革和“非遗”保护的行政立法等一系列工作,随之对昆剧院团的资金支持不仅力度增大,持续性也增强,全国各院团的人力物力进一步落实完善,再加之2011年昆剧“非遗”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助力,专业院团“民族文化担当”的主体意识也增强了。因此这一年的昆剧节参演剧目不但数量最多,风格也更加多样化,设立的奖项内容也最多,几乎涵盖了昆剧舞台搬演的方方面面。本届昆剧节参演剧目占主流的仍然是全本戏,创作方法上基本延续了上一届的模式,以传统剧目的改编和重排为主,例如上昆的《景阳钟》、江苏省昆的《白罗衫》、永昆的《金印记》、苏昆的新版《玉簪记》和《满床笏》、北昆的《续琵琶》、湘昆的《白兔记》和《荆钗记》、上海戏剧學院的《拜月亭》等,另外北昆此次参演的另一部上下本《红楼梦》从曲词到舞美、服化创新程度较大,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但其可贵之处在于锻炼了一大批当时未满30岁的年轻演员,促使他们快速成长为当今昆剧舞台上的中坚力量。还有江苏省昆的串折版《红楼梦》,以传统折子戏创作方法为本而新编曲词,达到了“创新如旧”的舞台效果,为新编昆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同样是省昆和香港进念合作的“实验昆剧”《宫祭》取材于传奇《铁冠图》中久已失传的“观图”一折,以独特的戏剧构作为昆剧的“现代性”呈现提供了一个尝试的可能。同时,在省昆的这几场演出中,从舞美到表演,其清空幽冷的艺术风格进一步强化,凸显了院团演出风格建设的成效。此次昆剧节开幕式上还史无前例地设置了“拜师仪式”,从官方角度强调了昆剧传承的师徒关系。另外,此次昆剧节期间,除了昆剧展演,还增加了地方剧种参演,柳子戏、婺剧、苏剧也占有一席之地,不可谓不热闹。
第六届昆剧节(2015)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剧目数量的锐减,由于出台了每个院团只能演一部剧目的明确规定,因此参演剧目只有第五届的半数,并且取消了评奖。演出剧目中除了上昆《墙头马上》和苏昆《白兔记》算作有传统文学本依据改编而成的之外,其余几乎都是完全新创的剧目。折子戏方面新增了四场名家传戏汇报演出,算是对三年前“拜师”的一个回应。
10月落幕的第七届昆剧节从参演剧目类型来看,总体上延续了第六届的格局,即以新创剧目为主,穿插以八场各院团和专业院校“名家传戏”工程的折子戏汇报演出。从参演主体来看,除了以往的七大专业院团和中国台湾的昆剧团体之外,这次新增了一个近两年刚正式成立的“昆山昆剧团”(简称“昆昆”)。虽然目前来看,该团演出的主要班底以江苏省昆的演员为主,但从名目上算是建国以来大陆唯一新增的专业昆剧团体,并且立足于昆曲的故乡,颇有些“昆曲回家”的象征意味。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已经存在的七大专业昆剧院团的建立并不完全是行政决策的结果,而是结合了近代百余年以来昆剧发展情况的布局。因此,在建团之初,各个院团基本都有自己既已形成的传统——包括独特的表演风格和剧目积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昆昆未来将如何发展,还需要认真探索。
从参演剧目的内容上来看,开幕演出《顾炎武》的主创都可算作行业内的佼佼者,但大概因为是应制之作,全剧的呈现尚有较为明显的模仿传统折子戏痕迹,折与折之间的连贯性尚待加强,同时某些场次的唱词似乎有失精炼;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永昆的《孟姜女送寒衣》上,该剧的主创熟谙昆剧的音乐格律及传统折子戏表演,从孟姜女走上送寒衣之路的编排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对于传统折子《荆钗记·开眼上路》的借鉴,但从全剧的情绪基调来看,这里的借鉴是否合适,尚有待商榷。苏昆的《白罗衫》和江苏省昆的《醉心花》都是前两年各自院团着力打造的剧目,已经过了几轮演出的实践检验,舞台呈现相对比较成熟,但是曾经的问题依旧存在。例如苏昆《白罗衫》前几出以传统折子《井遇》《游园》《看状》为蓝本,再加之演员纯熟的表演,完成度很好,戏剧冲突紧张、层层递进,到最后一折前已铺垫至高潮。然而最后一折完全新创的部分对前面铺垫的化解处理略显生硬,情与理的矛盾白热化之后过于强调双方冲突对立的紧张,故而最后一折的曲词和演员的身段设计都忽视了“留白”的重要性,反而给观众一种拖沓过度之感。与此类似的情况在上昆2018年新排的《琵琶记》中也有出现。上昆此版《琵琶记》很明显是为蔡伯喈“翻案”之作——这无可厚非,高明创作南戏《琵琶记》的初衷正是为宋元杂剧《赵贞女蔡二郎》中的蔡邕正名。但是,上昆新版《琵琶记》的“翻案文章”选择了对孝道的宣扬作为抓手,有一种教化剧“耳提面命”之感——如何能既符合高明原意又能与当代观众产生共鸣,也是在创作中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另外,本届昆剧节中算得“传统戏”的全本搬演只有浙昆的《雷峰塔》和省昆的《桃花扇》。
另外,此次昆剧节上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一批“资深观众”的缺席。据笔者了解,在江浙沪地区聚集着一批长期关注昆剧艺术的中青年观众,他们在过去的十数年间,几乎逢戏必看,可以说陪伴和见证了昆剧艺术在本世纪复兴的历程,其中不少人还默默承担了相当于昆曲义工的角色。尤其是在近10年网络社区兴起之后,在新浪微博、博客、豆瓣等各个热门网络社区都能看到他们积极为昆剧奔走的身影。从2009年的第四届昆剧节到2015年的第六届昆剧节,几乎每一届拉开序幕之前,都有热心观众在豆瓣等网站建立专题讨论帖,详细介绍参演剧目、公布演出时间表,甚至还从颇为专业的角度解读每个参演剧目的看点。演出后,微博和豆瓣上的相关剧照和评论文章也层出不穷——对参演院团和一般观众而言,他们已然形成了专家学者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反馈圈子。但是在第七届昆剧节开幕前,笔者特意留心了此类豆瓣小组和论坛、微信公众号等,并没有发现类似的讨论,笔者熟知的一些观众也大多没有前往观看——这固然有工作日时间安排的原因,但也不可忽视的是,这些痴迷昆曲十数年的观众对昆剧节的冷淡,除了其自身个体兴趣转移的因素外,是否也有其他原因,比如近年来昆剧节上的新编戏是否占比过大?虽然昆剧演出的發展情景日渐喜人,观众的新旧更替也实属正常,但在现阶段,对于一些具有相当鉴赏能力的“老观众”的淡出,着实不应等闲视之。
在本届昆剧节的学术研讨会闭幕时,有老师伤感地表示,最美好的东西永远是留不住的。如花美眷终归付与断井颓垣,仿佛朱颜辞镜花辞树,人间无计可相留。其实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艺术,在昆剧发展演进的历史上,传统与革新也本无绝对的界线壁垒。絮叨至此,不过是站在当代人的角度抚今追昔,私心希望这历尽坎坷绵延至今、并且保持着如此完善精妙的艺术样式能走得更远更顺罢了。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