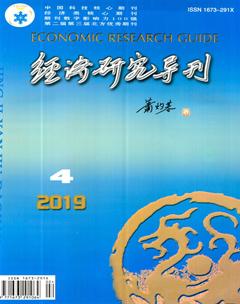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行为的外溢效应研究
杜沈悦 李存芳
摘 要:基于山西省采矿业2000—2015年的相关数据,对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行为的外溢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入的增加会减弱外溢效应;相比山西省采矿业研发费用投入,科研人员的增加对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行为外溢效应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相比山西省采矿业科研人员投入,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投资额的增加对外溢效应的促进作用更大。这一研究结论,可为资源枯竭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中西部资源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资源枯竭型企业;转移行为;外溢效应
中图分类号:F4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04-0007-04
引言
我国东部地区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渐趋耗竭,资源型企业在东部地区的生存与发展已难以为继。这些资源枯竭型企业[1],为了摆脱东部地区资源即将耗竭的困境,开辟企业生存的新空间与发展的新道路,谋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先后调整发展战略,转移到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东部资源枯竭型企业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丰富的管理方法,转入中西部资源富集地区之后,便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在东道地进行传播或转移,对东道地企业产生外溢效应。
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随着这一战略举措的提出,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的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那么对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行为的外溢效应进行系统研究变得尤为重要。研究结论可以为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行为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为中西部资源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一、文献综述
目前,学者们集中关注FDI外溢效应问题。Zhao和Zhang(2010)研究发现,FDI促进中国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Xu和Sheng(2012)研究发现,FDI对中国的外资企业具有正向的外溢效应[3]。汪洋(2014)研究发现,FDI促进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创新水平的提升[4]。张宏元和李晓晨(2016)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促进中国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5]。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都证实了外溢效应的存在。然而,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FDI对东道国(地)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很小甚至不存在外溢效应。Keller(2002)研究发现,FDI只在发达地区产生外溢效应[6]。Henny和Manuel(2002)研究发现,FDI对东道国技术创新外溢效应的溢出效果不明显[7]。Sun和Du(2011)、Wei和Liao(2013)研究发现,国际ICT产业转移对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外溢效應十分有限[8~9]。Lin et al.(2009)研究发现,来源于港澳台的FDI阻碍中国境内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来源于港澳台以外的FDI明显促进了中国境内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10]。罗军和陈建国(2014)研究发现,当研发投入低于门槛值时,FDI阻碍企业创新的产生;当研发投入高于门槛值时,FDI促进企业创新的产生[11]。成力为等(2010)研究发现,任何类型的FDI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都不产生外溢效应[12]。
上述学者们的研究结论表明,关于FDI外溢效应存在性问题还没有得到一致结论。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跨区转移具有相似的溢出机制,鉴于此,有必要对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行为的外溢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外溢效应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外溢效应,那么受何影响,影响程度如何?
二、机理分析
资源枯竭型企业进入东道地之后,打破了东道地原有市场的竞争结构,使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给本土企业造成了竞争压力。本土企业为了守住自己的市场份额,便会学习借鉴资源枯竭型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然而,如果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较弱,与资源枯竭型企业的技术差距较大,则难以将外来的先进技术转化为自身的生产力。因此,本土企业只有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并引进更多的科研人员,缩小技术差距,增强自身的吸收能力,有效利用学习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自身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产生外溢效应。
同时,本土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又会反过来对资源枯竭型企业在当地市场中继续维持优势地位构成威胁,这将迫使资源枯竭型企业引进更加先进的技术、更新管理方法,来保住自身的竞争优势,从而又会在东道地产生新一轮的外溢效应。
综上,外溢效应的形成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资源枯竭型企业带来的优势要素,二是东道地本土企业自身的技术改革与研发投入,即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基于机理分析,本文将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投资额、东道地科研人员投入、东道地研发费用投入引入模型。模型中相关符号的定义如下:Y为东道地行业总产值,C为行业消耗总成本,?仔为行业最终净利润,A为行业技术进步水平,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投入,w1为劳动力的工资,R为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投资额,N为科研人员投入,w2为科研人员的工资,RD为研发费用投入,r为利率,i为地区,j为行业,t为时间,?茁0为截距项,uijt为随机扰动项,?茁1~?茁5为变量的系数。
(二)数据说明
资源枯竭型企业转移现象是在西部大开发政策(2000年)相继实施之后逐渐涌现的,为了保证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具有代表性,选取2000—2015年的数据。经过在各种统计年鉴和相关网站上获取的资料整理获知,山西省是资源枯竭型企业转入较多的省份。因此,本文选取2000—2015年山西省采矿业连续十六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1.解释变量。资本投入K,选用山西省采矿业2000—2015年连续十六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通过价格指数平减法转化为2000年不变价格;劳动力投入L,选用山西省采矿业2000—2015年连续十六年的年平均用工人数;转移投资额R,选用山西省采矿业2000—2015年连续十六年的除去外资和港澳台投资的招商投资额,通过价格指数平减法转化为2000年不变价格;科研人员投入N,选用山西省2000—2015年连续十六年科研机构从事采矿业研究的科技人员数量;研发费用投入RD,选取山西省采矿业2000—2015年连续十六年R&D经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山西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2.被解释变量。用索罗残差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步骤如下:
其中,Y为采矿业工业总产值,K为采矿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L为采矿业年平均用工人数,分别选取山西省2000—2015年连续十六年的数据,其中采矿业工业总产值、采矿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均通过价格指数平减法转化为2000年不变价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山西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三)结果分析
表3的回归结果衡量了山西省采矿业的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科研人员投入、研发经费投入、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投资额对山西省采矿业本土企业外溢效应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表示山西省采矿业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反映出上述各个因素对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行为外溢效应的积极作用。从表3可以看出,模型(7)总体检验的F值为5.1114,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D.W值约为2.3689,表明不存在序列相关。
资本投入K的系数为-0.7274,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每多投入1%,外溢效应平均增强0.7274%,说明山西省采矿业的固定资产投入与外溢效应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产生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固定资产投入增加后,分配到技术创新、管理水平提升方面的资金便减少了,山西省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减弱,从而阻碍外溢效应;相反,则会增强外溢效应。采矿业劳动力投入L的系数为0.5625,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每增加1%,外溢效应平均增强0.5625%,但是劳动力的增加对外溢效应的增强效果并不显著。究其原因,采矿业企业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企业,企业的发展重点依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而增加的劳动力主要从事基础性生产工作,对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学习能力不足。
山西省采矿业科研人员投入N的系数为0.1681,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科研人员的数量每增加1%,外溢效应平均增强0.1681%。这说明,科研人员的工作成果可以增强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将本土企业从资源枯竭型企业学习到的先进技术,有效应用于本土企业,促进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增强外溢效应的溢出效果。研发费用RD的系数为0.192,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研发费用每增加1%,外溢效应平均增强0.192%,但是研发费用的增加对外溢效应的增强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虽然资源枯竭型企业的先进技术会在无意中外溢到本土企业,但是由于山西省采矿业本土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与转入企業的技术发展水平的差距较大,增加的研发投入在短时间内无法帮助企业迅速提高技术水平,需要经过一段时间逐渐增强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因此,当期的研发投入对外溢效应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
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投资额R的系数为0.4218,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转移投资额每增加1%,外溢效应平均增强0.4218%,说明转移行为对山西省采矿业本土企业存在外溢效应。R的系数接近N的系数的2倍多,说明相比东道地以增加科研人员投入的方式来增强外溢效应,直接加大转移投资额对外溢效应的促进作用更大,且效果更显著。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通过引入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投资额,中西部资源富集地科研人员投入以及研发费用投入三个内生变量,对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行为的外溢效应进行测度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固定资产投入的增加会减弱外溢效应。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体现在技术进步与管理水平提高等方面,而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主要依赖企业在技术研发和引进高素质管理人才等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一旦企业舍本逐末,将大部分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入,研发和管理人才引入方面的投入就会相应减少。这种“挤出效应”阻碍了本土企业引入资源枯竭型企业的先进技术进步和管理方法,从而减弱外溢效应。
2.相比山西省采矿业研发费用投入,增加科研人员的投入对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行为外溢效应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科技人员通过脑力劳动帮助本土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其增强本土企业吸收能力的方式较为快速、灵活,而研发费用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在研发项目完成后才能够实现,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3.相比山西省采矿业科研人员投入,增加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投资额对外溢效应的促进作用更大。增加科研人员的投入可以增强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将资源枯竭型企业流入的先进技术进行转化,提高本土及企业的技术水平。然而,如果资源枯竭型企业不再增加投入,那么本土企业只能吸收到有限的技术,只有资源枯竭型企业不断增加转移投入,本土企业才能学习模仿资源枯竭型企业更多的先进技术,进一步增强外溢效应。
(二)建议
为了实现资源枯竭型企业与本土企业互利共赢,促进山西省采矿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区域经济发展。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改善固定资产投入比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山西省采矿业应适当减少固定资产投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科研人员、管理人才的引进中,学习资源枯竭型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山西省采矿业全要素生产率。
2.增强本土企业吸收能力。鼓励山西省采矿业本土企业引入更多的科研人员和管理人才,注重人才培养与素质提升。跟踪研发项目进度,提升研发费用的利用率,加快研发项目的成果实现,从而缩小与资源枯竭型企业在技术和管理水平方面的差距,使本土企业的生产与管理系统能够适应引入的资源枯竭型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3.增加资源枯竭型企业转移投入,不断更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山西省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的资源枯竭型企业在本地投资项目,学习资源枯竭型企业的先进技术,增强本土企业的竞争力。随着本土企业竞争力增强,资源枯竭型企业需引进更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维持竞争优势。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产生新一轮的外溢效应,两方企业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1] 李存芳.中国可耗竭资源型企业转移区位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2] Zhao Z.,Zhang K.H.FDI and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in China: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in 2001-06[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0,(3):656-665.
[3] Xu X.,Sheng Y.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J].World Development,2012,(1):62-74.
[4] 汪洋.FDI对我国中小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J].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14,(1):19-22.
[5] 张宏元,李晓晨.FDI与自主创新: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证据[J].宏观经济研究,2016,(3):24-34.
[6] Keller W.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1):120-142.
[7] Henny R.,Manuel A.Determinants of Innovation Capacity in Small Electronics and Software Firms in Southeast England[J].Research Policy,2002,(31):1053-1067.
[8] Sun Y.F.,Du D.B.Domestic Firm Innovation and Networking with Foreign Firms in China's ICT Industry[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2011,(4):786-809.
[9] Wei Y.H.,Liao H.F.The Embeddednes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Chinese Cities:Strategic Coupl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J].Habitat International,2013,(40):82-90.
[10] Lin P.,Liu Z.,Zhang Y.Do Chinese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FDI Inflow? Evidence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Spillovers[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9,(4):677-691.
[11] 羅军,陈建国.研发投入门槛,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创新能力——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4,(8):135-146.
[12] 成力为,孙玮,王九云.引资动机、外资特征与我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效率[J].中国软科学,2010,(7):4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