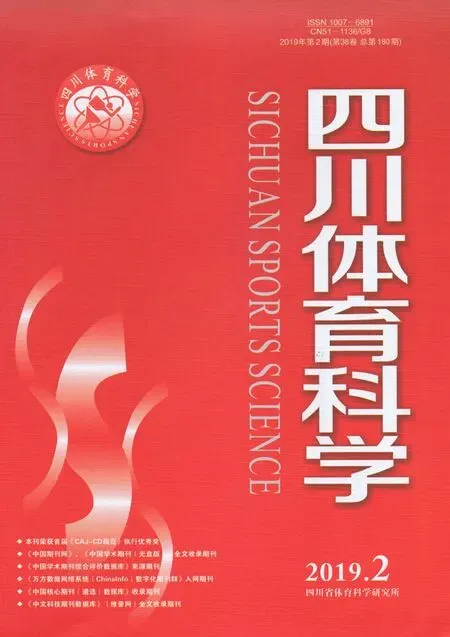我国民族传统球类运动地域分布与文化特征的研究
胡沛文,路凤萍,陈小蓉,王小龙
我国民族传统球类运动地域分布与文化特征的研究
胡沛文,路凤萍,陈小蓉,王小龙
深圳大学体育部,广东 深圳,518060。
采用文献资料法并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对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族传统球类运动进行分布特点的概述以及文化特征的研究。利用GIS技术在地图中标注,显示出我国球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分布区域为西北片区、东北片区、华北片区、华南片区。在此基础上分析分布地区的自然及人文地理环境的角度,探究影响球类运动的形成发展、制作器材、击打方式、项目个性特征等因素,从而进一步阐释我国民族传统球类运动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性、宗教性、历史文化等更深层次的地域文化特征。
民族传统球类运动;分布区域;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特征
我国民族传统球类运动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历史悠久且影响深远。国内最早发现的石球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人类开始用石球做投、扔、掷、抛等基本活动——“球”自形成伊始,作为生产工具而存在。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体育运动自身的演变,“球”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比如说它作为游戏的功能,进而发展成为竞技比赛等。脚踢、手抛接、借助器械击打等形式多样的球类运动诞生于我国众民族间,经过先秦直至明清时期数千年间的传承,球类运动在宫廷及民间都得到广泛的开展[1]。在中国,“球”作为一种特殊体育文化载体,与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宝藏。
1 我国民族传统球类运动项目分布状况
1.1 研究对象
通过笔者收集,目前在我国4批非物质遗产名录上的球类体育项目共有10项。其中包括国家级名录5项、省级(自治区级)名录5项。(见表1)

表1 中国球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布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GIS空间分析法以地理事物的空间位置和形态特征为基础,以空间数据运算、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的综合运算为特征,提取和产生新的空间信息[2]。首先,为了在视觉上更直观地呈现我国球类非遗的分布情况,掌握和分析球类非遗在我国地域空间上的分布特点,将表1数据借助于Arcgisl0软件进行视化处理,以省(自治区)级为研究单位,标注出其分布地理位置。(图1)

图1 中国球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地理区域位置分布
如图1我国球类非遗的省域位置所示:分布呈组团块状,较为不均,地域间差异明显;主要集中在西北、东北、华北、华南四个球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集团区;华中、华东、西南及东南沿海地区有较少球类非遗分布。
其次,采用分布密度来测算空间聚集区域,更加直观地对其发源地、传承地以及扩散范围及原因进行归纳和总结。利用ArcGIS软件中集成的Kernel Density工具,采取核密度估计法,本文选择带宽为4 00.0 km进行计算,绘制出我国球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布核密度分布图(图2)。

图2 中国球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布核密度
如图2所示:我国的球类非遗分布形成了四个小的核心圈。分别是以新疆南疆为代表的西部核心圈,部分分散在宁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和东部;以东北三江流域为中心的东北核心圈;以北京为中心的华中核心圈,辐射范围包括山东和河北;以广西为中心的华南核心圈,在广东中西部零散分布。
2 民族传统球类运动的文化特征分析
地理环境影响着中国体育文化的空间分布,从而形成不同级别、类型的体育文化区。游牧业、渔猎、农耕是我国古代三大传统经济基础,亦形成我国地区经济格局,根据王会昌等对中国文化区的划分,并结合中国球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GIS系统上的密度分布特征,可大致划分为西北游牧文化区球类,关东渔猎文化区球类和传统农耕文化区球类三大类别。
2.1 西北游牧文化区球类——强对抗性、竞争激烈性
2.1.1 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因素 西北游牧文化区大致位于大兴安岭以西,昆仑山一阿尔金山、祁连山以北,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此气候条件影响下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土壤类型多为温带荒漠土和温带草原栗钙土。
广袤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北部边陲的乌拉特后旗,是蒙古族驼球的主要分布地区。受干旱荒漠气候的影响,地表以砂砾石戈壁高原和沙丘戈壁沙地为主,具有其独特的草原及沙漠环境。生活在大漠风沙中的蒙古人是驯服使用骆驼最早的民族,他们把骆驼引入竞技比赛,开展赛驼活动,驼球运动的雏形就起源于这类追逐游戏,大致形成于赛骆驼和马球运动后期。当地人用遍布本地的西北柳、河套垂柳或者水曲柳木材制成赛杆和赛球,在草原节日上,双方队员身骑骆驼,挥舞赛杆,一场竞争激烈的驼球比赛在茫茫戈壁滩上打响,充分彰显了蒙古族勇士们的精湛骑术和标杆技术[3]。
新疆塔吉克族马球(塔语“高保孜”)史称“击鞠”,发源于维吾尔族自治区西南部的塔什库尔干地区。此地处于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东部,温度低,常年冰川,山路崎岖,水流湍急,不利于大面积的农业生产,但降水略多,草场质量较好。高原独特的地理条件,使马成为塔吉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运输工具和畜力,牧民养马规模大且培育了优良的马种,古老的牧马传统传承至今,也因此衍生出独具特色的“马背体育文化”[4],塔县在史书上称为“石头城马球场”。帕米尔高原当地人充分利用畜养的群羊,将粗羊毛绳缠成团,外用黄羊皮缝制,一颗柔韧坚实的马球就诞生了。在高原的空旷场地上,竞技者们驰马分为两队,手持球杖,共击一状若拳头大小的球,策马挥杆以打入对方球门为胜,赛场激烈壮阔的场面也是塔吉克族人游牧生活的真实写照。
维吾尔族传统曲棍球(维语“帕普孜”)主要分布在今天新疆南疆地区,在维吾尔族的聚居的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及吐鲁番盆地,帕普孜运动被当地人称作曲棍球运动的“鼻祖”。帕普孜运动中被击的“球”,维语称作“夏克夏克”,是用红柳木或杏木制成扁平状,或者用线织成球状。球棍用0.8m至1m之间的硬木制成,击球的一端和球棍呈现一定的角度,形状像阿拉伯数字“7”。在南疆沙土飞扬的空旷场地上,十多位帕普孜运动员挥舞着球棍,追逐着“夏克夏克”,努力打进对方球门内,展现了维族青壮年的威武雄姿。
达斡尔族人主要聚居于嫩江流域、呼伦贝尔草原和阿尔泰南麓的丘陵高寒地带。达斡尔人依靠当地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和宽阔的平原,以放地箭、挖陷阱、打围等技巧捕猎,逐渐演化成群体游戏——“波依阔”。比赛时所用曲棍和球的制作均根植于当地动植物资源:北纬45°至50°之间的高寒地带遍布耐寒针叶林,其中强度高,质地硬,耐寒性强的整颗矮小柞木成为加工曲棍球曲棍的最佳材料;所用的球“颇列”分三种:(1)毛球多为儿童球,是利用春季群牛脱毛时将牛毛搓制而成;(2)以杏树根块雕刻而成的木球,质地硬,弹性强,适宜中青年球赛用;(3)火球是以桦树上已硬化的白菌制得,夜间注入松明点燃,烟火经久不熄。天然资源为达斡尔族人开展和传承曲棍球运动提供了基础,也使其保持着广泛的群众性和持久的生命力[5]。
宁夏回族木球又称“赶牛”、马莲渠木球,主要分布在位于六盘水东麓腹地的泾源县,属低山丘陵区,境内河流纵横,重峦叠嶂、山塬相间。因受温带半湿润区影响,为森林草原气候类型,占总面积60%的林业、牧草坡地是发展畜牧业的理想之地。黄牛是长期繁衍在农牧交界处的蒙古牛类型的役用地方品种,役乳肉兼可用,生活在农牧交界区的达斡尔族人和宁夏回族人民自古善养黄牛,泾源山区分布的回族祖辈们靠在山里放牛为生,打木球就由回族青少年放牧时开展的“打篮子”、“赶牧球”演变而来[6]。牧童在地中央挖一个大窝称为“牛”圈,在“牛圈”旁挖两个小窝为“住屋”,用扔赶牛棍的远近方式确定1人为赶“牛”娃,其他人中有1人发“牛”(10cm长木疙瘩),即用木棒将“牛”击向远方,赶“牛”娃将“牛”赶入圈即为获胜。“赶牛”规则简单易学且便于开展,集竞技性、对抗性、游艺性于一体,深受回族群众的喜爱。
游牧民族社会实行部落制,过着食畜肉、饮潼酪、衣皮革、逐水草迁徙的生活,其生存发展与动物的驯化须臾不可分离。他们利用群居性有蹄类动物如牛、羊、马、骆驼、驯鹿等,开拓了生活空间,生物也成为游牧民族体育文化中不可缺少且独具特色的一部分,由此催成了具有游牧特色的体育文化。以畜牧业为载体衍生体育运动,动物作为运动竞赛中的一部分,必然呈现出动作幅度大、危险性高、竞争激烈的特点。
2.1.2 西北游牧球类的文化特征 (1)尚武的游牧民族精神:西北游牧文化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地,自古以来,以突厥和蒙古系统为主的草原型游牧民族为了生存,从建立部落起就相互征战厮杀,有幼习骑射,青壮从戎,至于老死的尚武精神;达斡尔族是古鲜卑族的契丹后裔,有“纵马于野,驰兵于民”的旧俗,曲棍球延续着达斡尔人的自强不屈的民族特性。塔吉克族马球与古代骑兵关系密切,供人娱乐游戏之余,还可作为军事训练之用,马背上剽悍的塔吉克骑手正是民族雄鹰般勇猛坚毅的品性体现;“赶牛”表现了回族男子们的阳刚之美,也积淀着回族人生生不息的民族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也是回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
(2)坚韧持久的宗教传统:蒙古族、达斡尔族等草原少数民族都源于阿尔泰语系,史上大多信奉萨满教,浓郁的萨满教文化影响下的体育运动就表现出粗犷奔放、崇尚武力的天然特性。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回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教义,民族意识较为强烈,特别回族有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伊斯兰教也起到纽带作用,成为民族体育文化的凝聚力量。
2.2 关东渔猎文化区球类——技能训练性与对抗性共存
2.2.1 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因素 赫哲族先民自古以来便在三江流域繁衍生息;满族是肃顺人的后代,始定居于黑龙江中上游、长白山北部、乌苏里江流域。本区域位于温带和寒温带的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地区,冬季漫长寒冷。河流是渔猎的先决条件:关东北部有鸭绿江、图们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环绕,江河纵横,湖泊星罗球布,盛产种类繁多的鱼类。这为先民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并衍生了具有渔猎特色的民族体育运动。
赫哲族为中国北方唯一的渔猎民族,自古就被称为“鱼皮部”、“鱼皮鞑子”,使用渔叉和激达的准确与娴熟成为赫哲族人的必备技能,赫哲部族里的孩子们将自然木杈或削尖的木棍当作渔叉或激达,将随处可见的茅草扎成长条形草把充当猎物,模仿用渔叉叉鱼和激达狩猎的动作,进行抛掷和争叉草靶的游戏,因此,演化成现代叉草球的雏型;比赛通常是双方在较平缓的河滩上,相距二三十步互相抛叉草球,还有用木叉、激达掷叉陆上固定或水中流动的草把等多种游戏方式,在河滩运球矫捷灵敏的身姿尽显赫哲族人的运动风采[7]。
满族先民除打鱼捞虾外,还捕获蛤蚌、采撷珍珠。采珠人将从江水中捞到的蛤蚌抛向渔船,渔船上的人伸出抄网去接,一时之间,其他的船只就会划过来争抢猎物。为体现渔猎生活的艰辛不易,渔民将蛤蚌神话,扮演“蛤蚌精”张开贝壳防护珍珠不被抢夺的情形,器具制作者将皮球做成类似于珍珠的白色,防守队员的球拍形状、花纹、颜色也都与蛤蚌相似,在被划分成船区、“蛤蚌区”、“河区”三个场地间进行比赛,这便逐渐演化成有具体技术、战术和攻防兼备的满族珍珠球运动。珍珠球的现今分布与历代满族人迁徙向南的过程息息相关,在辽宁、吉林叫“投空手”,在北京称“采珍珠”,迄今仍在北方满族聚居地区广为流传[8]。
2.2.2 东北渔猎球类文化特征 (1)渔猎民族精神:赫哲族和满族先民骨子里的渔猎文化特质扎根于对山林河流的崇拜。他们以天为被,以河为床,对自然依赖的本性、以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与东北地区的地理区域属性有机融合,形成了粗犷、豪迈、质朴与勇敢的民族风范。赫哲人和满族人将渔猎生活习性中的动作与技巧,演化成体育运动中的肢体语言,完美地映射出远古先民们的精神追求。
(2)萨满教文化相融合:渔猎民族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原生形态萨满教信仰。萨满教信奉人应自然而生,将自然万物化为生命本元,模仿宇宙神灵、飞禽走兽,传达着自由、和谐的生态气息,民族原始精神信仰与体育项目水乳交融,体现出别具一格的渔猎文化特色。
2.3 传统农耕文化区球类
根据GIS上呈现出的分布区域以及球类个性特征,将共处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的涞水踢球和山东蹴鞠划在华北农耕文化区,将广西壮族香火球划在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区。
2.3.1 华北农耕文化区——静定保守、更侧重娱乐功能
(1)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因素
涞水踢球始流传于河北涞水县平原地区农村。涞水位于太行山北部东麓,冀中平原西部,地域狭长,至唐县西部分布着古生代寒武、奥陶系灰岩、页岩,河谷两侧及山间盆地分布着新生代第三系地层的砾岩。正是由于涞水流域内的十几条河流从山区流向平原,冲来大量鹅卵石,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在农闲之余,便踢球状的石头嬉戏消遣,后来对鹅卵石进行雕刻打磨,规定使用的器具为石球和志子儿(树棍或竹竿、高粱秸秆所做,大拇指粗细,长约70-80cm),并制定比赛规矩,如分为隔物打、借势打、借力打、挑打和平打等方式,逐渐演变成这种集技巧、娱乐、趣味于一体的群体体育活动。
蹴鞠所用之“鞠”,传说为远古时期黄帝受石球启示所作,明《太平清话》记载:“蹋鞠始于轩后,军中练武之剧,以革为元囊,实以毛发”[9]。蹴鞠兴盛于战国时期的齐国,齐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地处暖温带,在曲阜地区鲁中南汶泗河流域傍河而建,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突出,蹴鞠在这片沃土上发展势头迅猛。此后蹴鞠的传播范围呈弥散之势,广为流传至华北中原各诸侯国。蹴鞠至汉代时就深受宫廷上流社会的青睐,还被引入军事上成为主流训练项目。发展至宋代呈鼎盛之势,为增强娱乐性和观赏性,其发展更为注重技巧的变幻莫测,衍生出了种类繁多的花法赋鞠。在球门设置上,为注重技巧的施展,大多采用整个足球场地上只设有一个球门的形式,球员只要射门而入并把球投入对方场地内就代表获胜。自宋元至明清期间,蹴鞠运动竞技功能逐渐消失,娱乐功能占据主流,逐渐由盛转衰。这也是中国儒家文化区体育的一个缩影。
(2)华北农耕球类文化特征
扎根于传统农耕社会的汉民族特性: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中国汉族传统社会,农民百姓安居一方,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牢固纽带,体现出稳定保守,自给自足的汉民族特性。扎根于农耕文化的民族价值观更强调群体利益,不突出个体,是一种尚群文化。此外,围绕在以北方黄河流域为主的平原农耕文化区,齐鲁文化和燕赵文化占据了“汉族政治文化轴心区域”。华北传统农耕文化区自古以来就是各朝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汉族政治统治者更加注重以严格的规章教条教化民众,因而其体育文化受政治管理制度、礼俗制度、道德观的约束较深。当农耕社会的统治阶层更偏好于寓竞争、娱人娱己、广适及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时,扎根于此的球类运动也就难免更加注重技法的变化莫测,侧重于观赏的高度文明性和娱乐性。
深受“儒释道”多重思想文化的影响:传统体育观念与文化思想密不可分,对我国汉族传统文化及其整个社会有着重大影响的主要有儒家、道家、佛家。“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教育,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德、至圣的理想人物;在道家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守中致和”的养生观、追求和谐的价值观和尚美的体育审美观影响下形成了顺应自然、动静相兼与形神共养的养生体育;佛教中诉求慈悲、平等、无常、无我、不争其所以然,强调运用“坐禅入静”的方法,进行身体外静内动的体育锻炼。在儒释道多重思想孕育成长下的汉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倾向于以调息、调心、调身的养保健养生方法达到体育实践的目的,促进人体的健康长寿。华北农耕体育深受“儒释道”多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呈现出“重人贵生”、“以和为贵”的文化特性。
2.3.2 西南农耕文化区球类——注重技巧施展与团队合作
(1)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壮族香火球流传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及钦州一带。广西地处云贵高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以喀斯特地貌最具特色,有丘岭连绵起伏、平原狭小、河流众多的地形特征。聚居于岭南西部的壮族先民把野生稻培育为栽培稻,是我国最早创作稻作文明的民族之一。由于疆域边远和地理交通闭塞,催生了以香火球为代表的独具地域边缘体育文化色彩的产物:将五六张坚韧耐用的圆形竹壳皮重叠压紧,剪成4-5厘米的圆板,用针线缝实,中间插入一截小竹筒,内套两枚铜钱。竹筒一端破开,弯坠而形成圆球状,在竹筒上端插上几根鸡羽毛,最后在中间插上香火并点燃,一个精巧的“香火球”就诞生了。这种将香与火巧妙地揉合在一起演变成香火球运动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壮族先民“刀耕火种”的农耕文化意蕴。
(2)西南农耕文化区球类文化特征
地域多民族交融塑造和谐精神:广西自古自然灾害频发,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壮族民众勤劳朴实的坚韧品性和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另一方面,广西毗邻湘楚滇黔,南通东南亚,壮族民众以宽阔的胸怀接纳着外来聚居移民,大家彼此平等友爱、协同配合,以此提高生产率和加强民族间的凝聚力;此外,相对于中国的主流文化而言,广西处于边缘化状态,深受多元民族文化的交叉影响,没有形成强烈而固定的宗教信仰,也就少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族居之弊,因而就恋爱、婚姻等方面来看,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亚区各族人民更为自由、灵活,而香火球其中男女混双的比赛形式也成为青年人结为良缘的一种媒介。可见,香火球运动体现了壮族儿女们为征服大自然协作互助的传统美德与包容和谐的人文精神。
承载着对“多神”的祭拜功能:壮族全民族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壮族人民将祖先、英雄人物和中举之人的奉为各类神明举行祭拜仪式的传统由来已久。据传香火球起源于三百年前古元村始祖班元亨创家业的艰难历程,出于感恩思源,后人用铜钱插上鸡毛和香火拜祭土地庙,之后当球抛耍娱乐,香火球从此流传于世;此外,为纪念壮族祖公布洛陀农历二月十九的生日,以及表示对在清朝广西抗击楼寇的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和古元村班家后人武举人的崇拜,壮族民众每年都会举行一系列盛大的祭祀活动。香火球作为这些祭拜活动的重要内容,意在祈愿五谷丰登、家和兴盛。可见承载着壮民族文化形式的香火球,不但延续了壮族人民对火的自然崇拜,也被赋予了人们将祖先作为神圣和祥瑞的表征去崇拜和祭奉的文化功能[10]。
3 结 语
我国传统球类文化起源和发展于不同地域和民族。西北游牧球类在竞赛中体现出的强对抗性以及追求团结互助而取胜的表现形式;关东渔猎球类以渔猎先民们训练子孙身体素质、协作精神与敏捷程度为始,衍生出集娱乐与技能训练于一体的运动形式;华北汉族农耕球类深受统治阶层管制与社会思想文化影响,呈现出技巧观赏性、目的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而西南农耕文化区人民将球运动融入在日常祭祀仪式和崇拜活动中,是一种注重团队合作、表演为主竞技为辅的独特运动形式。这都说明:一方面,地理环境为中国民族传统球类运动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及先决条件。其起源成因、器材的取材制作、所需场地、作战形式特点等属性,与所分布的三大文化地理分区之间迥异的气候、水文、地形地貌、生产生活方式、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综合地理因素息息相关。另一方面,球类运动作为中国体育文化的一部分,既反映着一定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内生产实践、社会风尚等多方面的情况,同时也蕴含着各族人民的民族精神、宗教观念等文化内涵。所以,要深入探究中国民族传统球类运动文化特征,挖掘地域人文价值,有针对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日渐式微的民族传统球类运动项目。
[1] 周 冰.我国传统球类文化探微[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01):95~98.
[2] 黎 夏,刘 凯. G1S与空间分析一原理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6~7.
[3] 杨 强.蒙古族驼球运动的文化意蕴及其价值[J].四川体育科学,2015(03):15~18.
[4] 郭红霞.新疆塔吉克族马球研究[D].新疆师范大学,2013:1~6.
[5] 白志忠.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文化探骊[J].山东体育科技,2014(04):26~29.
[6] 董 茜.临夏回族自治州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J].军事体育学报,2015(01):116~118.
[7] 崔小良,等.赫哲族体育旅游产品开发研究——以“叉草球”为例[J].商场现代化,2016(24):112~113.
[8] 张 霖.影响珍珠球运动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对策研究[J].福建体育科技,2007(03):18~25.
[9] 崔乐泉.中国古代蹴鞠[J].管子学刊,2004(03):43~51.
[10] 兰 政.广西壮族香火球运动的文化学分析[J].体育学刊,2008(10):100~102.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Ball Sports in China
HU Peiwen, LU Fengping, CHEN Xiaorong, et al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518061, China.
By using the method of documentation and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ball games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 Using GIS technology to mark the map, it shows that the spheri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is roughly distributed in northwest, northeast, north and South China. On this basis, from the angle of analyzing the natural and huma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the distribute are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all games, production equipment, hitting methods,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ents, so as to further explain the deeper reg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ball games in China, such as nationality, religion,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ese national traditional ball games; Distributio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1007―6891(2019)02―0087―05
10.13932/j.cnki.sctykx.2019.02.21
G812.17
A
2018-08-30
2019-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