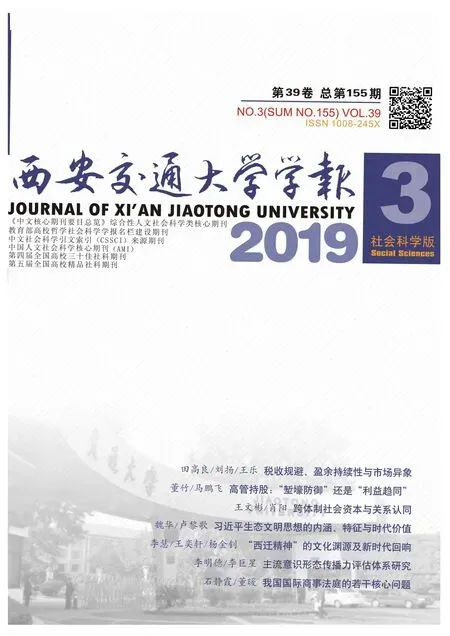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效果的影响因素——基于引导主体作用发挥视角的实证研究
蒙胜军,李建飞
(1.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陕西西安710049;2.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社交媒体在中国呈现出年轻化、移动性、全面渗透以及快速增长的特点,正在成为网络舆论的“风暴眼”和社会治理的关键[1]。国家对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工作非常重视,提出“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因此提升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必须抓住社交媒体这个“着力点”和“落脚点”[2]。从理论层面探究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效果的影响因素,可以为我们有针对性地提高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效果提供理论支撑与措施来源,是一项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舆论引导效果是多种因素所制约的综合效应,而现有文献大多从具体领域或单一视角探究舆论引导效果的影响因素。蒋忠波等[3]综合验证了媒介可信度、利益关联度以及公众文化程度三个因素会影响灾后重建媒介舆论引导效果的不同方面。吴振科等[4]基于“5W”理论、“三T”原则以及多中心理论,采用实证研究验证了影响食品安全危机中舆论引导效果的因素主要有应对技巧、信源公信力、沟通内容与媒介渠道。夏德元[5]从舆论引导主体视角,分析出舆论引导者的互联网水平、新媒体传播素养、互联网文化认知、互联网内容生产质量、价值竞争能力和意义诠释水平等对舆论引导效果具有影响。本文借鉴以往研究,拟从舆论引导主体角度,通过实证分析,验证影响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效果的诸多关键因素。
一、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设
舆论引导是一个主体见诸于客体的能动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所以舆论引导中的施动方(舆论主体)必然要以被动方(舆论引导客体)的改变为认识和实践目的。具体到舆论引导环境中,就是要产生一定的舆论引导效果。借鉴传播学“5W”模式,社交媒体环境中,舆论引导发挥作用即是引导主体传播信息获得传播效果的过程。因此,本文的基本理论假设是,社交媒体环境下,舆论引导主体需要发挥引导主体自身特点、引导内容以及引导方式的综合作用,才能达到舆论引导的最终目的。
客观环境的改变影响主体对客体作用的发挥。传统的舆论引导中,引导主体通过大众传媒平台发挥作用。显然,“一个组织、一个利益团体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运用大众传播进行舆论引导的能力,受到其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硬实力的双重制约”[6]21,也就是说,传统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效果与舆论引导主体本身情况密切相关。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认为,大众传播中二级传播的关键在于具有较高人格魅力、较强综合能力和较高社会地位或者认同感的舆论领袖的参与。在传统媒体时代的大众传播环境下,意见领袖对舆论的影响显而易见。而在社交媒体环境下,舆论引导主体将平台和传播者合二为一,自媒体的特征非常明显。所以,社交媒体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等同于意见领袖,其本身特征直接影响舆论的形成与传播。
具体到舆论引导主体特征和引导效果之间的关系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公信力、行为特征、政治效能感和“第三方影响”度等维度进行了验证。其中,政治效能(political efficacy)指普通公民自我感知到的影响政治过程的能力[7]。有学者将其分为内部效能(internal efficacy)、外部效能(external efficacy)和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内部效能指个体对自身理解和参与政治事务的信念,即个人相信自己具有能够了解和参与政治的能力;外部效能指个体对政治体制等外部因素能够回应公众参与的相信程度;集体效能则指个体对作为集体力量参与政治事务的认可程度。有研究认为媒体使用降低了公众对外部效能感的感知,因为媒体可能对政府有负面性报道。目前集体效能感的研究较少,但是就社交媒体环境来说,媒体的使用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得网络舆论成为一种可见的力量存在,社交媒体使用对集体效能感的影响需要加以验证。因此,对政府和媒体来说,由于现有的政治体系和媒介环境使然,其内部效能、外部效能和集体效能一直存在并始终强烈。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效能感的具体表现与引导效果的关系尚未有实证验证。
根据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假设1及其子假设:
H1: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特征对舆论引导效果各维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见图1),即公众舆论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的各种特征越满意,其表现出的接受舆论引导主体引导的倾向越明显。
H1-1: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公信力对舆论引导效果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
H1-2: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行为特征对舆论引导效果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
H1-3: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第三方影响”度对舆论引导效果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
H1-4: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政治效能感对舆论引导效果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
马克思主义舆论观认为,新闻舆论对社会舆论有“反应和影响”的作用。陈力丹[8]70指出,拷贝世界对个人意见或舆论的形成和发展方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里的“拷贝世界”即为新闻或者新闻舆论。也就是说,作为反映客观世界的新闻舆论对大众意见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国外学者的宣传与说服研究强调,不同宣传信息具有不同的宣传效果。议程设置理论进一步指出,议程内容可以“规范”和“影响”“公众议程”。
社交媒体环境下,内容生产便捷,信息量丰富。海量信息的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其内容特征是否如大众传播时代一样对舆论传播产生影响是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关于舆论引导内容与引导效果之间的关系,吴振科[9]18-21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传统媒体内容针对性、关键性、新颖性和易读性等5个指标对引导效果具有影响。借鉴相关成果,本文提出假设2及其子假设:
H2: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内容特征对引导效果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见图1),即公众舆论对社交媒体所提供的具体内容信息越认可,其表现出的接受舆论引导主体引导的倾向越明显。
H2-1: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内容针对性对引导效果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
H2-2: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内容关键性对引导效果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
H2-3: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内容全面性对引导效果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
H2-4: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内容新颖性对引导效果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
H2-5: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内容易读性对引导效果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
马克思交往理论认为,交往能形成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发展、拓展生活和生存空间。霍夫兰(Hovlang)的说服研究强调,说服方式的改进可以增强“意图式”说服的影响。议程设置理论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时间维度、议题设置数量、议题显著度等都对公共议程具有显著影响。“沉默的螺旋”理论在不断的研究中发现:“意见气候感知”和“多数人意见的一致性”会影响公众议程最终的表达与行动。而关于舆论引导方式与引导效果之间的关系,现有相关研究都强调了说服程度、议题设置程度、“沉默的螺旋”沉默度以及技术引导实现度对引导效果的影响。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假设3及其子假设:
H3:社交媒体舆论引导的不同方式对引导效果的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见图1),即社交媒体各种引导方式的实现度越高,公众舆论所表现出的接受舆论引导主体引导的倾向越明显。
H3-1:社交媒体舆论引导说服程度对引导效果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
H3-2:社交媒体舆论引导议程设置度对引导效果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
H3-3: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沉默的螺旋”沉默度对引导效果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
H3-4: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技术引导实现度对引导效果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

图1 本文的理论假设
二、研究方法及测量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采集数据,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检验研究假设,并使用SPSS21.0进行统计分析。
(一)样本来源

(二)变量测度
本文因变量为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效果。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效果的评估,主要借鉴和参考蒋忠波等[3]的量表,结合传播学效果研究经典范例,建构为引导后的主体信任度、态度改变度以及要求契合度三个评价指标进行分析。
解释变量包括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特征、内容表现和方式呈现三个方面。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特征的测量参考相关研究,主要从公信力、行为特征、政治效能感和“第三方影响”度等维度进行测量;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内容的测量参考相关研究[9],主要从内容针对性、关键性、全面性、新颖性和易读性等5个指标进行测度;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方式的测量综合相关研究,主要从说服程度、议程设置效果、“沉默的螺旋”沉默度以及技术性引导实现度等方面进行考察。其中,技术性引导区别于有偿删帖等不当行为,主要指在特殊情况下利用删帖、屏蔽等技术性措施进行的舆论引导,这是当前中国网络舆论治理实践中必不可少的引导手段之一。
本研究根据分析所得测量指标及专家访谈反馈意见设计问卷,并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题项,要求被调查对象根据自身情况如实填写。
(三)信效度检验及多重共线性诊断
通过检验,本研究中的各变量和量表信度值均在0.7以上,说明问卷信度较高。进一步通过SPSS软件对问卷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引导内容、引导方式、引导效果量表的KMO值分别为0.785、0.864、0.711和0.710,且显著性水平Sig.值均小于0.001,说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各量表都能有效反映所要研究问题的各个维度。
通过多重共线性诊断,本文中各解释变量容忍度均大于0.10,VIF全部小于10,说明各解释变量没有明显共线性问题,对因变量具有较好解释度,可以进入回归方程。
三、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根据问卷回收的基本情况,对原问卷的部分题项数据做了预处理。政治面貌方面,选项“民主党派”统计量为5,数量较少;另外,预处理的结果显示,选择“民主党派”和“群众”的统计结果差异不大,故将之做变量加总处理,形成新的变量“群众和民主党派”。职业方面,“公务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差异较大,故进一步进行变量转换,形成“公务员”“媒体从业人员”和“其他”三个变量。收入方面,也处理为“4 000元以下”“4 000—8 000元”和“8 000元以上”三个变量。进一步清除不相关变量后,形成表1所示的各变量基本情况。
从表1的结果来看:在引导主体的四个维度中,政治效能感得分最高,这表明在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中,主流媒体和政务“两微一端”有很强的政治参与和引导意识,明白自身是舆论引导格局中的重要力量,这也与当前社交媒体发展的背景相关。在引导内容特征的五个维度中,得分较为平均,且差别不大,说明社交媒体的舆论内容的各个方面都在舆论引导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在引导方式的四个维度中,说服程度的得分最高,“沉默的螺旋”沉默度得分最低,这说明说服依然是当前社交媒体最重要与最常用的方式,而在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环境下,试图一方独自发声从而影响舆论的方式正在效果弱化。在引导效果的三个维度中,引导主体的信任度得分最高,说明社交媒体环境下,对引导施动方本身的信任感最重要,一旦失信,引导主体的各种表现以及内容、方式将可能瞬间失效,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也将成为一句空话,这也基本印证了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同样遵循“塔西佗陷阱”的基本规律。
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表明: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特征、内容表现以及引导方式呈现都与舆论引导效果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因此,各变量均可进入回归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四、多元回归分析
本研究为验证社交媒体引导主体、内容、方式等各个方面对舆论引导效果各维度的影响情况,采用层级多元回归的方法,将控制变量和自变量逐级进入回归方程构建模型1和模型2,以观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实际影响情况。在构建模型1时,对相应人口统计学变量做了哑变量转换,并做了标准化处理。
(一)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特征对舆论引导效果的不同维度具有影响
表2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中,政治面貌和职业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效果影响较为显著,其中,中共党员与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后的态度改变度(β=0.143,p<0.05)之间有一定的显著性关系,说明相对于民主党派和群众来说,作为党员的群体更容易接受舆论引导中的观点和态度;媒体从业人员与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后的主体信任度(β=-0.166,p<0.001)、要求契合度(β=-0.115,p<0.05)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负相关关系,说明相对于学生、一般企事业员工来说,媒体从业人员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后的政府态度等缺乏信任,对政府的相关要求缺少相应的配合和呼应。而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效果并无显著性影响,且对引导效果各维度的方差最多只能提供5%的解释。但是,在将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公信力、行为特征、“第三方影响”度、政治效能感进入回归方程后,其解释方差最低达到38%,最高达到46.8%,且F值检验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F值分别为30.665、27.661、21.748,p<0.001)。说明该模型拟合度较好,可以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各方面与引导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很好的解释。
具体来看:第一,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的公信力与引导后的主体信任度(β=0.181,p<0.01)、态度改变度(β=0.148,p<0.01)有显著影响关系,而主体公信力与要求契合度(β=0.057)之间未通过检验。第二,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的主体行为特征与引导后的态度改变度(β=0.119,p<0.05)、要求契合度(β=0.124,p<0.05)之间的回归系数较为显著,而主体行为特征与主体信任度(β=0.096)之间未通过检验。第三,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的主体“第三方影响”度与引导后的主体信任度(β=0.232,p<0.001)、态度改变度(β=0.290,p<0.001)、要求契合度(β=0.250,p<0.001)之间的显著度水平均非常明显。第四,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政治效能感与引导后的主体信任度(β=0.253,p<0.001)、态度改变度(β=0.198,p<0.001)、要求契合度(β=0.273,p<0.001)之间的显著度水平都非常明显。总之,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社交媒体舆论引导的主体公信力、主体行为、主体“第三方影响”度和主体政治效能感都分别对舆论效果三个维度部分或全部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以说,社交媒体舆论引导的主体特征对舆论引导效果具有显著影响,假设1及其子假设得到部分验证。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特征对引导效果各维度影响的回归结果(n=474)
注:双尾检验显著度,***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二)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内容表现对舆论引导效果的不同维度具有影响
从表3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与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中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引导效果的影响相同,政治面貌和职业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效果影响较为显著,而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效果并无显著性影响,且对引导效果各维度的方差最多只能提供5%的解释。但是,在将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内容针对性、关键性、全面性、新颖性和易读性引入回归方程后,其解释方差最低达到31.3%,最高达到41.1%,且F值检验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F值分别为23.010、19.448、15.385,p<0.001)。说明该模型拟合度较好,可以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各方面与引导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很好的解释。
具体来看:第一,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内容针对性与引导后的态度改变度(β=0.144,p<0.01)、要求契合度(β=0.166,p<0.01)之间的回归系数较为显著,而内容针对性与主体信任度(β=0.054)之间未通过检验。第二,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内容关键性与引导后的主体信任度(β=0.138,p<0.01)、态度改变度(β=0.195,p<0.001)、要求契合度(β=0.194,p<0.01)之间的回归系数较为显著。第三,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内容全面性只与引导后的主体信任度(β=0.222,p<0.001)之间的回归系数表现显著,而与引导后的态度改变度、要求契合度表现不显著。第四,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内容新颖性与引导后的主体信任度(β=0.195,p<0.001)和态度改变度(β=0.241,p<0.001)之间的回归系数表现非常显著,而与引导后主体的要求契合度表现不显著。第五,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内容易读性与引导后的主体信任度(β=0.134,p<0.01)和要求契合度(β=0.180,p<0.01)之间的回归系数表现较为显著,而与引导后主体的态度改变度表现不显著。总之,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社交媒体舆论引导的内容针对性、关键性、全面性、新颖性和易读性分别对舆论效果三个维度部分或全部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以说,社交媒体舆论引导的内容特征对舆论引导效果具有显著影响,假设2及其子假设得到部分验证。

表3 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内容表现对引导效果各维度影响的回归结果(n=474)
注:双尾检验显著度,***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三)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方式呈现对舆论引导效果的不同维度具有影响
从表4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与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中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引导效果的影响相同,政治面貌和职业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效果影响较为显著,而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效果并无显著性影响,且对引导效果各维度的方差最多只能提供5%的解释。但是,在将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方式的说服程度、议程设置效果、“沉默的螺旋”沉默度和技术引导实现度引入回归方程后,其解释方差最低达到37.9%,最高达到43.8%,且F值检验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F值分别为27.281、22.486、21.614,p<0.001)。说明该模型拟合度较好,可以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各种方式效果与舆论引导最后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很好的解释。
具体来看:第一,社交媒体舆论引导说服程度与引导后的主体信任度(β=0.456,p<0.001)、态度改变度(β=0.414,p<0.001)、要求契合度(β=0.433,p<0.001)之间的回归系数都非常显著。第二,社交媒体舆论引导议程设置效果与引导后的主体信任度(β=0.137,p<0.01)和态度改变度(β=0.108,p<0.05)之间的回归系数表现较为显著,而与引导后主体的要求契合度表现不显著。第三,社交媒体舆论引导的“沉默的螺旋”沉默度与引导后的主体信任度(β=0.117,p<0.01)、态度改变度(β=0.136,p<0.01)和要求契合度(β=0.112,p<0.05)之间的回归系数表现都较为显著。第四,社交媒体舆论引导的技术引导实现度与引导后的要求契合度(β=0.186,p<0.001)之间的回归系数表现非常显著,而主体信任度和态度改变度未通过检验。总之,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社交媒体舆论方式中的说服程度、议程设置效果、“沉默的螺旋”沉默度和技术引导实现度都分别对舆论效果三个维度部分或全部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以说,社交媒体舆论引导的方式效果对舆论引导效果具有显著影响,假设3及其子假设得到部分验证。

表4 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方式呈现对引导效果各维度影响的回归结果(n=474)
注:双尾检验显著度,***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五、思考和建议
由前文的检验可知,本文的主假设都通过检验,表明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从引导主体作用发挥的角度看,引导主体特征、引导内容表现以及引导方式呈现都对引导效果具有显著影响。但分别来看,在引导主体特征的假设中,H1-3、H1-4全部通过检验,H1-1、H1-2部分通过检验,说明在对社交媒体环境中的舆论引导而言,熟人关系与引导者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对影响引导效果有着重要作用;在引导内容的假设中,只有H2-2全部通过检验,其他均部分通过,说明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信息的关键性、重要性最能对他人起到引导效果,也就是说,越关键、越重要的信息越能发挥作用,引导公众;在引导方式的假设中,H3-1、H3-3全部通过检验,H3-2、H3-4部分通过检验,说明在社交媒体环境中,说服方法和“沉默的螺旋”效应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和全面。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主体作用发挥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应该赋予和明确政务新媒体的舆论引导主体责任,切实发挥主体作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新媒体工作的通知》已经强调要“明确责任主体”。当前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效果需要政务新媒体等引导主体有权威更有权力。要适当放权,才能真正使得政务新媒体在舆论引导媒体矩阵中发挥应有作用,实现有效引导。
第二,重要关键信息要特别注意关键性,掌握发布主动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新媒体工作的通知》强调,信息发布要“紧密围绕政府部门职能定位,及时发布政务信息,尤其是与社会公众关系密切的政策信息、服务信息”,本文研究结论也对此有所验证。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内容关键性对引导效果的三个维度均有影响,影响面最大。所以,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一定要强调发布信息的实效性和重要性。特别是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是应该坚持的“黄金律令”。
第三,遵循舆论引导基本规律,强调说服等经典引导策略方法,尊重和发挥“沉默的螺旋”效应,慎用、少用删帖、屏蔽等技术性强制引导措施。本研究中,说服和“沉默的螺旋”沉默度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效果三个维度均有影响,影响面最大,而删帖等技术引导方式仅对要求契合度有影响,影响面很小。也就是说,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工作,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发出权威声音、加强与网民互动,减少于舆情管控、特别是强制管理措施。以笔者的实地调研经验来看,只有谣言、涉政、涉黄等极端性言论或者违法情形,才有必要动用删帖、屏蔽等技术性引导手段,而不加区分地舆情管控会浪费有限的政治资源,有伤舆论引导既得成果。
第四,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要抓住社会“中间力量”的关键多数。社交媒体舆论引导需要对引导对象有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这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另一课题。但是,从本研究中引导主体的角度来看,社交媒体舆论引导的对象和核心是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这个群体的特征是:人数众多、本科以上学历、收入中等。已有学者将其基本定性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从本研究差异性分析结果来看,这个群体对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效果的各项认知度表现最高,引导效果最好。所以,他们是我们维护社会稳定,特别是网络舆论稳定的中坚力量。要做好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工作,一方面要重视对社会“中间力量”的引导,他们是最容易接受并达到预期引导效果的一个群体;另一方面更要从战略层面培养和扩大社会“中间力量”的数量和质量。大量的“中间力量”代表主流民意,扩大主流声音,消弭和对冲了底层受侵害者的极端言论和上层既得利益者的保守言论,是我们国家进步、社会稳定安全阀的基石和力量来源。所以,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一定要抓住这个群体,把“中间力量”变成“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