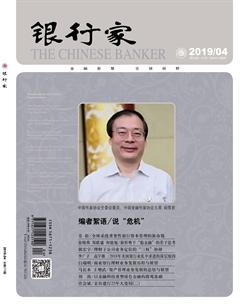拿什么来点缀我们的生活
高续增
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富裕了,按理说我们的生活也应当变得更轻松、更丰富多彩一些,可实际上却还是有很多很多人在喊累,天天生活在焦虑之中。
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被衣食所累,长年累月辛苦恣睢,一生一世都在盼望着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现在,我们是衣食无忧了,可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却在怀念以前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呢?
我捉摸着,是人们普遍地对生活意义这样的问题陷入了迷思。现在的人们受从众心理的驱使都在盲目追求未来生活的“高质量”,从小就教育孩子一定要上最好的大学,要创造机会及早地出名当明星,要千方百计地挤进公务员队伍当大官……而把眼前生活的意义和情趣抛在了一边。
如果我们的社会有这样的一种机制,能让所有的青少年都能心平气和地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来设计自己,社会组织的力量也能帮助他们找到最适合于他们将来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千军万马都奔着那几条窄窄的就业门路挤独木桥,事情本来会好许多的。
为此,我认为,我们现在应当提倡和推广“轻松闲适”的生活方式,把我们先人那些让生活变得轻松有趣的艺术项目推广开来,让年轻人都能成为有追求、有品味、有专业特长的后辈,让年轻人都有一颗“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平常心,我们的生活会比现在变得好得多得多。这样同样也能够为将来的社会生出许多新的高雅的社会消费需求,也可以为社会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岗位。
我希望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发起、最好是由政府出面把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传统艺术门类发扬光大,让它们进入我们社会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这样,在提高我们的社会品味的同时,也会扩大和丰富我国的消费市场,没准还能把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远播四海造成一股宏大的文化洪流,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的作用。
话说得有点远了,还是回归眼下说说我生活中的琴棋书画吧。
琴棋书画中我最早接触的是棋,当然,现在说的棋主要是指围棋,我最早接触的是中国象棋,家父在什么时候教我下象棋的,我已经没有了记忆,至少是在我五岁以前,我已经常常跟我父亲下象棋了。我小时还常常到我家附近天津墙子河边迪化道桥旁边(现在是鞍山道南京路交口)看大人们下棋,这里只要不是三九寒天总是会聚拢一大群的棋迷,这当中大部分人是下象棋或看象棋的,偶尔也有下围棋的,那时看得懂围棋的人不多,我也只对象棋感兴趣。开始我就在旁边静静地看,不知什么时候,我也有时成了一个下棋的人,观棋的成人们对我这样一个幼年棋手很感兴趣……这是至今仍然留在我记忆中的一个片断。
后来接触围棋是1966年的事情了。同班同学张冠群,因为在保定的武斗中受了伤,右脚伤的不轻。打上了厚厚的石膏架着双拐才能走路。我去学校的路上正好路过他家,因此时不时地去看望他。他在家一个人很腻烦,看我常常去看望他,就提议教我下围棋,这正合我意,也正好陪他打发养伤的时光。
不久我的围棋上了瘾,就在家门口招呼一些发小开始下起了围棋,这些发小以前在一块的时候经常是打扑克下象棋下军棋。为了能随时随地对弈,我在旧货市场买了200多个白色的和深棕色的小扣子,我自己又用一块淡蓝色的布画了一张围棋盘,这就成了我可以随身携带的一副简易围棋,以后我到了哪里,就带出一个围棋爱好者的小圈子。
大学时,同班同学中有几个爱下围棋的,不过学业繁重,我又先后担任了学院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和秘书长,能痛痛快快地下棋的时候不是很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进入国家计算机总局工作,很幸运地发现这里有好几个围棋棋迷,水平还跟我不相上下,这个爱好帮助我很快就融入了这个新的工作环境。棋迷中有个叫杭承仁的,是当红歌星杭天琪的父亲,他是文革前留苏的大学生,棋瘾很大,不过总是下不过我。另一个棋力比我稍强的棋手叫赵悦平,他年龄与我相仿,他是一个对我后来生活轨迹很有影响的人。他是学自动化的,知道我不愿意在国家机关工作,后来他让他的妻子祁之杰把我介绍到经济科学出版社来工作。
到了经济科学出版社以后我发展了好几个围棋迷,逢年过节出版社组织娱乐活动时,围棋比赛总是一项很热门的比赛项目。特别让我沉溺围棋的最高潮,是我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的那一段时间。体改所的位置离中国人民大学很近,人大在读博士生中间有不少棋迷,不过他们的棋龄都比我短。我的这些对手主要是王松奇、邓乐平和吴晓求,常常一下就是一夜。有时下到半夜,不走了,我就睡在那里,有时干脆一直下到天亮。等天亮我再回家或者直接上班去。
我跟这些后来很有影响的金融界人物结识是很偶然的,开始时是王松奇拉我去给他“出气”,他跟吴晓求下过几盘带彩的棋,由于棋力不济处于下风,损失了几百块钱,他鼓励我“教训教训”吴晓求,让我也跟吴晓求下彩棋。我从来没有下过彩棋,起初想打退堂鼓,王松奇一个劲地鼓动我,向我许诺“输了是他的,赢了是我的”。还好,一上来两盘我先声夺人拿了下来,有这四百元垫底,我就一点也不紧张了,以后无论怎么下也是我胜多负少,最后我都赢得不好意思了,就转战跟邓乐平下“卫生棋”。我两个的棋力相当,杀得难解难分,最后决定下“一百盘棋”来分出雌雄,几个星期下来,我渐渐地吃不住劲了,下到二十几盘时,差距就拉得很大了,我忘了是我以什么理由选择了躲避,于是原订是“一百盘棋”的战书也就中途“打挂”了。
我还有跟专业棋手对弈经历。那是在九十年代初的一年冬天,在北京棋院跟吴肇毅九段下的一盘指导棋。那次对弈却成了我心中的愧疚。
我的棋友刘训国引荐我到北京棋院跟专业棋手下的指导棋,刘训国是国家地震局的围棋高手。是我參加棋院定段赛时认识的,我俩住得不远。他住在祁家豁子,国家地震局的集体宿舍;我住在苇子坑的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宿舍,只要有时间我就经常到他宿舍去下棋。我俩是在华苑棋社定段赛上认识的,华苑棋社的社长是围棋名宿金同实。那次定段赛我定成个业余初段,他定了个业余二段。王汝南院长亲自给我们发的段位证书。
这一天刘训国约我到中国棋院去下棋,在路上刘训国跟我介绍了这次活动的来历。是中国棋院的头头们为了给专业棋手增加点外快,安排时间在棋院给业余棋手下指导棋挣钱。价码是一段十块,七段七十,八段八十,九段九十。可是我当时身上真没带多少钱,到棋院后我本应当找个理由逃掉就对了,可是一直没有这样做,出于侥幸心理,我心想让我四个子,我怎么也不会输掉吧,于是顺水推舟把我分配给了吴肇毅九段了。结果我被杀得一塌糊涂。我本应当问问刘训国带没带钱,好借钱给我付费,但是后来糊里糊涂就忘了,最后不明不白地散了场,吴肇毅九段也很大度,没有再提“指导费”的事情。事后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羞愧无比,这九十块钱欠款成了我一块心病,如果能再次见到吴肇毅,我宁愿给他打款九千块钱以了结我的这块心病。
在中国棋院我还跟陈丹淮将军下过一盘棋,我还幸运地赢了他。事后复盘时,我礼貌地说:“我通过这盘棋向您学到了许多”,陈将军打趣地说:“您赢了,还这么谦虚……”
迄今我的光辉形象唯一一次出现在银屏上是在贵州卫视的围棋频道上,也是刘训国邀请我去做的节目,主持人是王元八段,节目的内容是业余棋手心中的围棋明星。平时很腼腆的我,没想到第一次面对摄像机时一点也没有紧张,把我多年来对国内围棋高手的仰慕之情侃侃道来,节目做得非常成功。
前几年我还写了几篇关于围棋的文章,其中一篇《从围棋文化看中日韩三国的国民性》发在本杂志上。还有一篇对围棋的哲思没有最后完成,内容大意是,从围棋内在的哲理看,它不同于其他国粹,围棋原理和规则理性所阐发出的智慧更接近西方文化理念而不具备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你看,别的有着国际影响的棋类,如国际象棋中国象棋等,都体现了不同程度的等级观念,规则也更加远离了文化的自然属性。而唯独围棋,能体现出围棋主体元素(棋子、棋盘)的“无差别”原则,而且也是唯一一个最后用精确的计数方法来确定胜负的棋类竞技游戏。我分析其中的原因是发明围棋的先人所在的社会环境还是中国人敬畏“天志”的时期,那时还没有“人间神”作为特权者可以主宰一切的权力极。我更进一步遐想,这与古代希腊神话时期的哲思是不是如出一辙呢?
近年来网络的兴起给围棋迷带来了更多的欢乐,只要是在能上网的地方,我就能跟天南海北的围棋迷们对弈了,有时还能进行网上跨国比赛,跟日本、韩国的业余棋手玩上几盘。这让我的业余文化生活又增添了不少成色。
迷上围棋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对弈者一进入棋局,就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生活中的一切忧愁荣辱都暂时不存在了。“一局一春秋,一盘一世界”,人生何尝不是一盘大棋啊!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下围棋一样,对每一天、每一件事都认真思考,深思熟虑,相信每个人在暮年回首往事时能够坦然地对自己说:我已经尽力了,舍此无复他求。
感谢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围棋,感谢现在的网络围棋的工作者,也很幸运于天下有那么多与我一样的棋迷,這一切让我的业余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沉醉于围棋天地成了我的真正的“忘忧秘笈”。
(2019-03-03)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