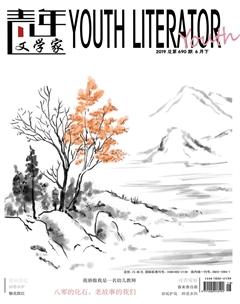解读《长恨歌》中的“姐妹情谊”
郑直
摘 要:姐妹情谊是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的基本原则,也是女性文学乐于构建的理想国。但不同于西方女权主义对性别政治等问题的敏感,也不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刻意解构传统、反抗父权的女性主义写作,王安忆抛弃了性别叙事的立场,以天然的、生活化的视角,从人际间细密曲折中沉静、细致地勘察着女性之间虚荣与冒险、世故与脆弱的感情。本文以《长恨歌》为例,通过细致地文本解读,具体考察和分析小说中姐妹情谊建立和发展的状态,试图在女性主义立场外找出姐妹情谊自身存在的导致其最终破裂的真正原因。引导人们摆脱控诉模式,正视女性及其情谊自身。
关键词:王安忆;姐妹情谊;《长恨歌》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8-0-02
引言:
贝尔·胡克斯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说,“姐妹情谊”主要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出现在女性主义运动中,虽然之后淡出了女性主义。但它依然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与批评的一个关键词,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正如肖瓦尔特所说,姐妹情谊标志着女性之间团结一致的情感。但在现实中女性主义所高扬的姐妹情谊往往付诸阙如——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姐妹情谊的易碎和虚幻的品性。即便如此,姐妹情谊依然是女性文学乐于构建的理想国。它出于女作家争取女性团结以获得力量的愿望,也基于女性四分五裂而无力反抗压迫的实际。
在中国,男性主导的历史致力于创造男性情谊神话,女性却一再被书写为互相排斥的群体,导致了姐妹情谊的历史空缺与压抑。五四女作家对女性友谊展开了正面书写,但这一时期的描写往往是为了表现女性对传统的反抗,并没有回到情谊本身。在当代,女性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放,“此时的女性书写逐渐从对男权的反抗转化为个体指向的边缘化趋势”,姐妹情谊也得到了专门的书写和表现。
不同于西方女权主义层面的“姐妹情谊”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女性在性别困境中固守自我的“姐妹情谊”,除了顺应八十年代末在中国掀起的西方女性主义潮流而创作的《弟兄们》,王安忆很少以女性主义视角来写作。她的作品中女性的结交是自然而然得——同性之间的精神交流既是女性的心灵需求,也是人性的自然属性,而这些女性又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之中成长变化,因此她们之间或倾轧或扶持的感情都是对现实生活环境的自然反应。批评和研究领域也有一些对于她的具体文本如《天香》、《弟兄们》中的“姐妹情谊”的研究。但大多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将姐妹情谊破裂的矛头指向男性,而忽略了女性以及姐妹情谊自身也负有责任,因为姐妹情谊自身具有多种形态与模式,而那些“畸形”的情谊本身就难以长久地维持。
笔者抛开了女性主义立场,通过对《长恨歌》中具有代表性的姐妹情谊进行解读,立足于姐妹情谊自身,循着其情谊从发生到破裂的轨迹,探究其破裂的真实原因,试图将“姐妹情谊”这一论题回归到自身的范畴来对待和讨论,并为王安忆笔下的姐妹情谊做出合理的感悟与分析。
(一)女性间的吸引与崇拜
《长恨歌》虽然以描写王琦瑶与李主任等男性之间爱而不得的情爱故事为主笔,但作家在以真实、日常化的笔触来描写王琦瑶一生时,不可避免地要写到王琦瑶那些“真心对真心”的小姐妹情谊。
王琦瑶的第一个女伴是吴佩珍。“吴佩珍是那类粗心的女孩子。她本应当为自己的丑自卑的,但因为家境不错,有人疼爱,养成了豁朗单纯的个性,使这自卑变成了谦虚”,因而她“总无意地放大别人的优点,很忠实地崇拜,随时准备奉献她的热诚”。而她崇拜的对象正是王琦瑶,她对王琦瑶的感情“有点像一个少女对另一个少女,那种没有欲念的爱情,为她做什么都是肯的”。两人因为差异互相吸引,这种互补式的平衡看似能使友情日渐加深,但其实将两人放在不平等的位置上。吴佩珍对王琦瑶的崇拜,使王琦瑶也将自己放置于偶像的位置上,试图在吴佩珍面前保持完美的形象,所以当吴佩珍见证了自己的失败之后,她开始躲避吴佩珍,“像有什么底细被她窥伺了去似的”。当这次失败作为伤感的一笔留在王琦瑶的心里时,已经预示着这份友谊的破裂。直到吴佩珍去香港前到爱丽丝公寓向王琦瑶辞别,王琦瑶一席“你嫁得如意郎君,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是妻不妻,妾不妾”的自我嘲讽算是主动打破了两人之间崇拜与被崇拜格局,吴佩珍却一再表明心意:“我从来把你看作比我好”。直到吴佩珍离开后,王琦瑶才明白两人之间“全凭的是友情”,但这段情谊已经是难以挽回了。
薇薇与张永红之间的情谊也是差异引起的互补和崇拜。薇薇羡慕张永红对时尚的独到见解,对张永红的行为亦步亦趋,这种崇拜是种对自己不具备或求之不得的东西的转移与填充,认为她作为张永红的朋友,“张永红出众了,自己也跟着出众了”。而在张永红看来“薇薇的心地单纯和她的不具备威胁性”吸引了她。显然这种情谊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是以其中一方的平庸来衬托另一方的特别,这种情谊不以平等的精神交流为前提,虽然以互补的模式使双方的虚荣心得到了暂时的满足,但是难以稳定持久。因此当张永红寻得了真正的导师王琦瑶时,两人一拍即合的想法,和相见恨晚的亲昵,使她们跨越了年龄的隔阂成为了忘年之交。
(二)女性间的情感捆绑
王琦瑶和蒋丽莉成为朋友是在她成为“沪上淑媛”之后。蒋丽莉作为王琦瑶的众多仰慕者之一,对王琦瑶充满了崇拜和好奇。而蒋丽莉在班级里营造的神秘感也吸引着王琦瑶。在她们俩的交往中蒋丽莉不仅对王琦瑶一片赤诚之心,并且对她十分依赖,不论干什么都要拖着她。蒋丽莉“对父母兄弟都是仇敌一般,唯独对个王琦瑶,把心里的好兜底捧出来的”,在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的时候,蒋丽莉更是尽心竭力“就好像‘上海小姐是她家的,王琦瑶也是她家的,她都有权一手包揽”。虽然她的真心都写在脸上,但这份沉重的关切却让王琦瑶有些招架不住——“她知道蒋丽莉是对她好,可这好却像是压迫,是侵犯自由,要叫人起来反抗的。这就像用好来欺人,好里面是有个权利的”。但渐渐地王琦瑶也尝出了蒋丽莉一片热诚里的私心,那就是程先生。异性的出现往往使同性情谊面临危机与挑战,但与其说是三人之间阴差阳错的情爱导致了友情的破裂,倒不如说她们的情谊早已经存在着裂痕——情感的捆绑。蒋丽莉具有极强的“权利心”,从小养成的任性使她自认为对王琦瑶是有权利的,而家庭失和、父母温情的缺失,又使她将王琦瑶当做“爱的靶子”,将自己的情感一股脑地射向了她,导致她的“好”是变了味的好,有着不容拒绝的蛮横和控制,是早晚要引起王琦瑶的反抗得。因为捆绑式的姐妹情谊是虚幻和不成熟的,它忽视了个体的独立性,单纯地追求一种理想的共生状态以达到自救的目的,却在这一过程中粗暴地抹杀了一方或双方的个性与意愿,形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情感控制。漸渐地也造成了交往双方的不满情绪。因此这种情谊不仅难以持久,也是不攻自破的,异性的出现只是加速其破裂而已。
结语:
可以说《长恨歌》中描写的女性情谊都是自然状态下生发得,它们以成长期的陪伴为始,也随着青春期的结束而渐行渐远。这种简单、稚嫩的友情女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这些情谊因为各种原因不断进行着分裂与结合,但却没有任何破坏性。它们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同性崇拜和情感捆绑的形态出现,蕴含着女性自然真实的情感。作家并不回避女性善妒的天性,以及女性在姐妹交往中的小心思,但这些都是无伤大雅的。同时,在小说中,女性的情谊也会因为异性的出现而中断,但作家并没有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来批判男性权力对女性情谊的抹杀与残害,而向我们呈现了由于女性关系自身的不平衡和不成熟导致得情谊的破裂。因此,作家王安忆在《长恨歌》中描写的女性情谊,在展示女性情谊的基本类型、表现女性情谊的丰富性和延展性时(如王琦瑶和张永红的忘年之交),也对女性及其情谊自身提出了要求,即同性情谊应该建立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之上,认识到交往各方是独立并有价值的个体,在交往中不仅要互相欣赏、互相尊重,而且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3]宋晓萍.女性情谊:空缺或叙事抑制[J].文艺评论,1996,3:60-66.
[4]潘圳.“女性情谊”与生活世界——对王安忆小说的一种解读[D].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3.
——笔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