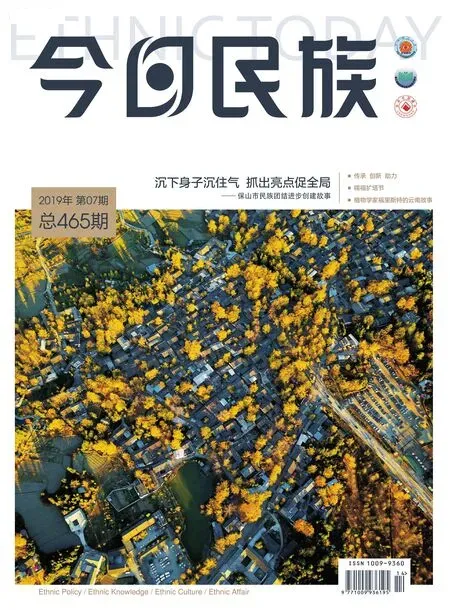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在新时代的使命与担当
□ 文 / 《版纳》杂志社 罗云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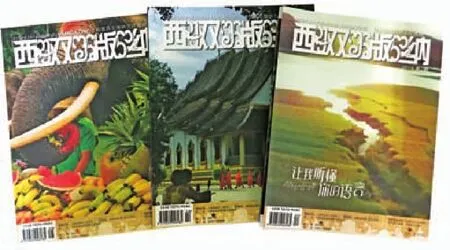
新时代需要新思维、新作为,新时代更需要明确责任与担当。
回顾历史,云南有着培养少数民族作家的光荣传统。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作协云南分会创办了文学刊物《边疆文艺》(后改为《边疆文学》),西双版纳傣族著名歌手康朗英、康朗甩、波玉温都有幸在《边疆文艺》发表了自己的诗歌作品。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边疆文艺》的指导帮助下,康朗英、康朗甩、波玉温创作的叙事长诗先后出版,在国内文坛引起强烈反响。1981年西双版纳创办了《版纳》杂志汉文版,第二年又创办了《版纳》傣文版。创刊伊始,《版纳》便把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坚持至今。近四十年来,《版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少数民族作家,有被誉为“哈尼族书面文学创作第一人”的哈尼族作家朗确,创作并发表傣族第一部傣文小说的傣族作家刀正明,“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诺族文学创作领头人、基诺族作家张志华等。其中,有5人先后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走进新时代,作为传统媒体的少数民族文学期刊,自然也需要与时俱进,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走多媒体、融媒体协调发展之路。但传播手段或形式的多样化、现代化却始终无法改变、替代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培养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独特、核心作用。
现代传播形式的多样化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多样化的手段、渠道和平台,对文学创作本身而言,有促进作用,但不是决定作用。传播形式于文学发展来说,终究只是后端,前端还是要有文学创作。没有文学作品,再现代的传播也只是摆设,是空泛的喧哗与骚动。这就需要再回到原点——办好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将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作为头等大事。
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日新月异,但发展并不平衡,这是客观存在的。在迈入小康社会之际,不能让一个民族掉队,这是社会经济目标、政治目标,也是文化目标。文化目标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学期刊上,就是为每个少数民族培养了多少作家,多少文化代言人。
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也需要“扶贫”,这个“贫”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从经济上看,少数民族作家大多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基层,经济条件不太好,生存的压力大,生活与创作的矛盾突出。从文化上来说,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相对汉族作家又有诸多不同。他们的区别在于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地域环境、思维模式乃至语言表达等许多方面都与汉族迥异。他们在用汉语创作时,存在一个如何转换或者切换的艰难过程,这个艰难的过程就需要编辑的扶持与帮助,需要培养。不仅如此,少数民族文学期刊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责任,就是对那些有创作潜力、创作才能的少数民族作家,既向外推介其作品,激发其创作热情,同时更要向外推介其本人,为其不断提高创作水平提供更多更宽广的学习、交流平台与渠道。
近年来,中国作协、云南省作协持续加大了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力度。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除了在院本部举办少数民族作家高级研修班外,还在云南、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的省、自治区举办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云南省作协根据省内少数民族作家的特点而举办的笔会、改稿会更有针对性,对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如此种种,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期刊来说,都是推出少数民族作家的良好途径与机会。
今天,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这些民族文化的代言人,通过他们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展示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心路历程与时代变迁,为中国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绚烂多姿的奇花异彩,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庄严承诺。这一成就不可谓不大。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强化文化自信、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期刊不仅不可或缺,还必须在经费、编辑力量等诸多方面加大投入,加大重视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