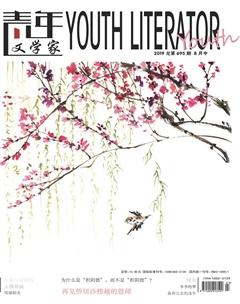从城市记忆到乡村笔触
罗大艳
摘 要:王安忆的小说创作,综观之下始终是有两个主要审美空间,一个是都市,一个是乡村。她的城市小说创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于乡村的书写也别有风致,她始终不懈致力于题材的开掘。但由于人生经历的原因使得她对乡村的书写虽上升为一种审美形式,却始终存有一种距离。
关键词:王安忆;城市;乡村;创作拓展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3-0-02
王安忆是一位活跃于新时期的高产作家,从小受其母亲茹志娟的影响,阅读了大量书籍且养成了记日记的好习惯。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为王安忆后来的写作生涯奠定了基础。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小说创作取得了很大成就,短中长篇她都有作品问世。王安忆说:“我自认为是一个远离一切文学潮流的作家,其实却得了一切文学潮流的好处。”①所以,不管文坛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是怎样发展,她都能继续在文坛的蓝天里飞翔,始终活跃于文学潮流的浪尖之上。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从开始的“雯雯系列”到90年代成熟的城市小说直至投向乡村的笔触,这些转变似乎具有某种内在的连贯性,尤其是《长恨歌》以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篇幅小了,也更收拢了。
一、城市的书写
王安忆的城市小说创作,真正是开始于《流逝》,她在散文《独语》中写道:“雨,沙沙沙地响过那么一小阵之后,人们开始要求王安忆——开拓题材面。本人也想从小雨中走出来,拔起腿,却疑惑起来——这一步跨出去,是往前了,还是往后了?不知道,真不知道,但必须跨出去。”②这是王安忆为《流逝》写的后记,她知道不能再局限于抒写“雯雯”的个体内心的困惑与烦恼,而应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迈步,至1995年长篇《长恨歌》的问世,宣告了她的努力得到了回应。《长恨歌》是她对老上海临摹的一幅写实画,其中无不显露王安忆对于老上海的细致观察,也可窥探出作为新时期女性作家的王安忆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敏锐度和独特感悟。《长恨歌》中,繁华与破败并存的都市里的弄堂、阁楼、大世界;弥漫罗曼蒂气息的法国梧桐和优雅的淮海路;喧嚣的人家住户和走在上海大街小巷的王琦瑶;令人向往却暗自拨弄命运之弦的片场……都清晰呈现在读者眼前。
王安忆的城市题材小说可说是别具一格的。她不似张爱玲的绝望虚无,她也没有茅盾抒写社会宏大政治经济的眼光,更不是老舍对于外来文化的排斥批判和对逝去的文化传统的追忆、流连,她的笔尖规避着对社会历史事件的描写,以女性作家的独特视角,从平民生活的琐碎出发,用日常生活细枝末节的变化来映射社会历史的变迁;她钻进城市的“芯子”里,从柴米油盐,从个体的喜怒哀乐,实打实地描绘这城市,再现这城市。上海是給了女性一个好舞台来展现自己再现这座城市的点滴,而女性也当之无愧为上海最贴切的形象代言,所以我们不难发现王安忆小说中的主角基本都是由女性形象一贯始终。《长恨歌》中,王安忆眼中的上海就是一个王琦瑶一样的女性形象。这个普通弄堂人家的女儿,也代表着老上海这座城市里千千万万个同样花季年龄的少女,“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留声机哼唱《四季歌》的,就是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③与其说王琦瑶是这个都市上海的形象代表,不如说女性是对这座城市的最好诠释。柔到骨子里的一呼一吸、霞光异彩的服饰、细至微处的柴米油盐,都是女性对城市的理解与表达,无论时势如何变迁,社会如何更迭,王安忆是抓住了这城市的精髓。
《上种红菱下种藕》以小女孩秧宝宝的视角,向人们展示了江南小镇的独特风光,揭开城乡发展变化的幕布,也展示了在这变化中人的现实状态。《富萍》着力描写的,是从贫困落后的乡村远来居住在这座城市边沿的农民,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同时也在社会的底层。但他们身上有着顽强的生存意志和抗争精神,这种意志和精神支撑着他们不被城市生活所抛弃,但也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的主流生活。富萍悔婚、执意留在城市的选择与决心,舅舅、舅妈以一条运垃圾的船为生计的努力,棚户里的那对母子以及生活于这城市边缘却格外团结的人们,这一个个真实可感,有血有肉的个体与群体,向我们展示了上海这座大都市另一面,它不是一个象征符号,而是一座有生机、血肉可辨的城市。
王安忆的城市小说,对于城市的描述观察细致入微,仿佛一幅摹像写实画摆在你面前,但这种写实却似有几分让你看清生活,看清人生的无意义。小说中女性的乐观独立坚强,仍逃不掉命运这把枷锁,逃不出性别给她圈画好了的生活轨道。在王安忆的城市小说中,无论是王琦瑶、蒋丽莉,还是富萍、奶奶亦或是吕凤仙,甚至是秧宝宝的妈妈,这些女性角色带给人的,少了几分昂扬向上的激励,更多的是女性好似活在生活安排的围场里挣扎悲戚、患得里患失,在那个女性生命的围场里进行着一生忙碌却无意义的生命形式。但值得肯定的是,在乡村与城市叙事并存的今天,城市叙事的美感不仅没能得到提升,城市在一些作家眼中还沦为了金钱、权势、利益、甚至腐朽生活的代名词,与乡村叙事对比,常是否定的对象,王安忆用却她的创作证实,对城市的认识与表达,完全可以有另一番新景象,她孜孜不倦的奋力开掘城市小说创作题材的背影,不禁让人感动。综观王安忆的城市小说创作,她的努力如今已结下了累累硕果。
二、投向乡村的笔触
王安忆的城市小说创作,取得了让人无法忽视的成就,我们纵观她的创作历程,可清晰窥见其笔触轨迹。从80年代的《大刘庄》、《小鲍庄》中篇小说开始,已伸向淳朴自然的乡村世界,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她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如《姊妹们》、《开会》、《喜宴》、《隐居的时代》等乡村小说相继问世,王安忆巨大的创作转向着实让人大吃一惊,不过却现实存在着她创作转向的合理原因与现实需要。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为文学开拓了一个书写地域,也为知识分子筑造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那是心灵的寄居与回归。王安忆,作为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同样需要心灵的寄居与回归,千疮百孔的都市,其真正面目让人心酸、为之心痛,好比《人人之间》中王强新爷爷的一句话:“我在上海滩混一生一世,旧社会,新社会混了各有三十年,我总算明白了:人好比是条鱼,钞票就是水,鱼离开水,一脚去了。”④都市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赤裸裸的金钱物质关系难有几分人情温暖,城市留给人的,是无尽的挣扎与抗争。《长恨歌》中的长脚身上所体现的人性软弱与贪婪,为了满足内心渴求承认与肯定的虚荣心理,为了一点点钱财让平日热情招待他的王琦瑶死于非命,命丧黄泉;而“在农村贫困的、温饱难以维系的生活里,其实是含着健康的性质,这是以简朴为基础的……春夏秋冬有序地交替,恪守各自的职责,自给自足着。这是合理的生存环境。”⑤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人们少了城市里那种因为生计的千方百计,也不必为了外在光鲜的虚荣去算计,城市的藏污纳垢在乡村简单的生活方式中不复存在,有的是诚诚恳恳,实实在在的生活态度,甚至形成了一种达观的天命观,这种天命观里的是一种健康的人性与生存方式。王安忆觉省自己的作品,也该具有这种生活态度和立场,为心灵找寻一方净土,创造一方属于自己、属于社会公众的精神故乡,这是王安忆小说创作转向的原因,也是她小说创作题材拓展的需要。不能仅仅局限于都市生活,局限于都市的弄堂阁楼、街头巷尾,也应该要看到乡村广袤的土地,以及那土地上的人们生活的困窘与欢乐。所以,王安忆的乡村小说是对淮北六七十年代乡村生活的书写与回忆,是对逝去了的乡村生活记忆的追寻与记录。她不像鲁迅《故乡》是对于农村封建落后的批判与揭露,也不像沈从文《边城》中对奇特诡美、原始自然的湘西世界的向往与流连,王安忆笔下的淮北乡村,弥漫着淳朴民风同时兼有乡村特有的自然理性。
王安忆的乡村小说创作,开始于80年代《大刘庄》、《小鲍庄》,其中《小鲍庄》并不仅仅是乡村生活的记叙与抒情,它偏重的,是从道德和文化两个视角对乡村进行的审视与批判。王安忆有两年半的知青下乡农村生活经历,当真正目睹了农村现状的时候,她感到的是梦想的破灭,加上生活习惯的不适应,王安忆对乡村始终有一种距离感,她是把自己排在乡村生活之外,以一个过客的身份书写乡村生活,所以具带着一种理性与冷漠的态度。“我将自己封锁起来,既与农民隔阂着,又和知青同伴们远离着……于是写出了一些插队日子里关于希望,关于失望的种种心情。”⑥这是王安忆乡村小说创作初期作品所呈现的。她回复刘志云的《我写<小鲍庄>》中写道:“许是插队时太小了,或是太娇了……虽说才只两年半,其中有半年以上还是在家里的,可感觉却是十年,二十年。因此我无法像很多人那样,怀着亲切的眷恋去写插队生活,把农村写成伊甸园。”⑦这是王安忆乡村小说创作初期作品中所体现出的那种俯视与理性甚至几近冷漠的原因。直至90年代中后期,王安忆才不是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窥探和描写乡村,她舍弃了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識和个人化叙事的个体好恶,而用“我们”、“我们庄”的叙事语言,以细腻的笔触从乡村的日常着笔,将乡村纯朴健康的人性与生存方式铺展开来,展现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乡村生活方式。《喜宴》中一场乡村婚礼所包含的农村婚礼风俗,从中又突出新郎学友的聪敏、镇定、开朗;《姊妹们》中未婚女子的美好年华和乡人们的爱护与宽容以及《开会》中孙侠子的能干与纯朴;《隐居的时代》则以一个知青的视角,通过一系列人物展现乡村生活方式,通过生活方式的展现来透析乡村独具特色的生活,以及乡村悠久沉稳的文化和这种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包容力。她显然有“以审美眼光展示乡村的生活状态以及支撑、决定这种状态的乡村精神和乡村理念。”⑧的内在自觉,对于农村的书写已不仅仅是出于怀旧或者对逝去生活的追忆,而是乡村的生活和农民的生存状态在她的眼里已是一种具有审美性的形式。
王安忆对于乡村小说创作的自觉探索与开掘,使得她的作品一直活跃于文坛之上,具有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她不断地拓展自己小说创作的题材面,用创作成绩向人们证明,对于城市和乡村可有别样的书写,而不是提起城市便是金钱权势与罪恶,提起乡村便是落后封建与愚昧。但是,由于生活经历的原因,作为城市知识分子的王安忆,对于城市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缺乏深刻的了解,乡村的描写也更多的是一种局外冷静、理性的描写,虽上升为一种审美形式,却也产生了一种距离感,乡村生活在她的小说创作中更多只是一种观念上的审美形式。
参考文献:
[1]①②⑥⑦王安忆.面对自己[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8:99;90;144;165.
[2]③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19.
[3]④⑤王安忆.喜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7:103;67.
[4]⑧李芳.从城市到乡村——王安忆小说创作风格的转变[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