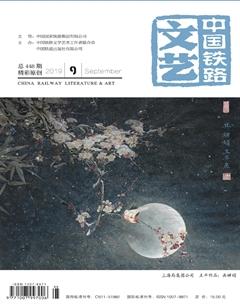铁路一线职工的 真实写照
福泰来
《远情》是一篇典型的铁路题材短篇小说。写得是一位铁路高铁建设者——桥梁施工队队长,带领施工队伍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在一次暴雨时,疯狂的洪水将一座年久失修的水库冲决口,为了营救自己两个落水同志,英勇献身的故事。
《小说选刊》杂志推荐评价是这样写的:“《远情》能让我们遥想起建国初期,人们无私建设祖国的热情。作品书写得是铺设高铁线的当代建设者。他们抛家别子,斗严寒,赶工期,无畏奉献,赢来‘中国速度。伟大感情,高迈、出尘,在小说中要让人信服,更考验作家的笔力,伟大感情一旦写真切,高山仰止,又是最富感染力的。作品钻进人物内心,写高铁线建设者的自豪之情,让读者贴近小说人物,体验人物脉跳,感受到伟大情感的温度。‘远情不仅是指当代建设者的献身精神,也是對无私奉献的一代代建设者的回望,由《远情》我们可以走进前赴后继的建设者淳朴、剔透的心灵。”
《远情》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深深的一个情字。里面有夫妻情、父女情和同志情。这个桥梁施工队队长甚至连个正式名字都没有,他只是“丫头爹”。这是作者特意为之,还是偶然这样,不得而知。但我还是坚信,肯定是作者特意为之。因为小说全篇都是在书写最普通的铁路一线职工,或者说,作者最关心、关注、关爱的还是我们最基层的铁路建设者。为了高铁早日建成,他们没日没夜奋力苦干。在目前高铁八横八纵驰骋万里的情况下,有谁知道,我们的建设者,他们付出的除了汗水、心血,还有他们的生命。在高铁光鲜亮丽的背后,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建设者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时间演进到今天,一个全新时代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物质充盈与生存压力并存,数字科技与智能生活同构,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相交,大众文化消费与精英精神共存,信息爆炸与媒介更替交织。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与最坏、至繁与至简、快乐与焦虑的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网络新时代降临,信息如潮涨潮落一样海量产生和迅疾流通,一方面,读者和作家站在了同一信息高地上,另一方面,构成时代的点、线、面复杂多样且瞬息万变,作家似乎更难把握所处的时代,更难概括时代的精神实质,更难寻找到那个撬动时代的支点,写作不由自主地陷入某种困难和尴尬之中。
就文学而言,高大勇猛的传奇,与平凡琐碎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多大差异。相反,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长年如一不声不响,坚守自己工作岗位,为了某项事业,默默无闻的奋斗者,会更加让人敬佩。正像有人所说,表面看,我们的高铁是行进在钢筋铁轨之上,其实,那是用千千万万普普通通铁路职工用肩头扛起来的。飞速行驶的高铁,承载的是我们铁路人的希望和责任。正如诗人所言:“这是举向天空的道路,每一个桥桩都是扎进大地的根须,每一寸路基都是匍匐大地的脊梁,每一座大桥都是建桥人精神的雕像。”
京沪高铁于2011年6月30日15时,G1与G2次高速列车,由北京西站和上海虹桥站双向首发,京沪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这是新华社发出的消息。
举世瞩目的京沪高速铁路,是中国铁路建设的里程碑,是一部写在东方大地上的史诗。这趟高速列车,越过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水系,越过南京大桥、长江大桥、济南黄河大桥以及淮河特大桥、阳澄湖大桥,穿过西渴马、龙山、韩府山、金牛山等隧道,接连起北京南、天津南、济南南、南京南、上海虹桥等7省市,沿线24座崭新亮丽的车站,全长1318公里。高速列车穿梭于华夏大地上,飞驰在成真的梦想中,优美的轨迹宛若飞翔的长虹。京沪高铁的建设,是中国铁路品质提升的重要标志,尽管并非一帆风顺,也有坎坷风雨,但是,建设高速铁路的进程,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提速的世纪工程,是造福于民、利在子孙的伟大事业。
正是这样一项举世瞩目,千秋功业的壮举,我们铁路建设者抛家舍业,披星戴月,日夜奋战。从2008年4月18日开工建设,至2011年6月30日正式通车,历时3年多,经历了无法言说的艰难困苦,终于建成。让我们看看工地上铁建工人后一代的名字,每一个都是一项工程,每一个都凝聚着我们建设者的希冀。兄弟姐妹的名字,如果连接在一起,就是父辈修建的铁路线:张西干、王天兰、李宝成、赵沈大——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每一个名字都传承着光荣与梦想。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局集团公司徐州公寓段工会主席杨洪军,创作了短篇小说《远情》。我不知道小说中丫头爹是不是有原型?但是,我坚信,“丫头爹”就是我们千千万万铁路建设者中的一员。如此生动感人的作品,绝不是关在书宅院落中所能编纂出来。
从技术结构层面上看,作家精心设计了交叉叙述方式。
开头是倒叙。作者写道:娘将放学回家的丫头揽到怀里捋着她被风吹乱的头发说:“丫头,你爹单位里叔叔来电话了,说你爹在的时候建的高铁通车了。明儿不上学,娘带你去坐高铁。”
然后才介绍丫头爹的身份和工作内容。大约是两三年前吧,丫头爹才将他所在的工队调到已经开工的高铁工地。丫头爹在去高铁工地之前,回了一趟家。“一进门就拉住娘的手,兴高采烈地说,丫头娘,这下好了,我们队也被调去建高铁了。以后丫头大了,俺也能自豪地拍着胸脯跟她说了,丫头,知道不?高铁,你爹建的!”真是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当丫头放假,娘带着丫头去看爹,想亲眼看看被爹吹得神乎其神的高铁建设到底是啥样时,却和当初的想象完全不一样。“这天冷极了,凛冽的寒风卷起尘沙在天空中肆虐,四下里一片昏暗。”娘忧心忡忡地说:“你看咱娘俩躲在生着炉火的屋子都冻得跺脚,真不知你爹在无遮无拦的工地是怎么受的?”
爹从工地回来,丫头看到,“爹头上歪扣着一顶破柳条帽,又宽又厚的安全皮带紧束在已经辨不出颜色的旧棉衣外面,长筒靴上溅满了黄泥巴。双颊也塌了,鬓部和下巴上胡须邋遢,疲惫和操劳让他明亮眸子罩上了密密麻麻的血丝。”作者借丫头的眼睛,描述了高铁建设者这样一幅样子。可他衣服里面又是一种什么情景呢?小说接着写道:细心的娘看到了一些端倪,总觉得哪儿不对劲,有时候抬手都要皱下眉头。娘问他哪儿不舒服,边说边去捉他的胳膊,爹一闪身,立刻疼得大叫了一声。这时候,娘拨开爹的棉衣领子,往里一看,一下子怔住了。“后背不知什么时候受的伤,内衣和伤口都黏在一起了。娘一边蘸着温水给他泡开结在伤口上的内衣,一边止不住地眼泪叭哒叭哒地滴在爹的背上。爹满背的累累伤痕让娘无暇多想,就从背后紧紧地箍住了他,把头贴在他的脊背上,放声大哭起来——”这是从侧面反映高铁建设的艰难,当然也为后来丫头爹的牺牲,埋下伏笔。
如果我说这就是当下我们铁路建设大军的真实写照,可能有些人会不相信。他们会发出疑问,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科技正在打造我们新生活——足不出户或远行千里,均可自行选择,工作和生活系于网络,自媒体时代正在替代报纸电视时代,信息的发达和畅通让人们成为无所不知的“上帝”。现代生产还会出现那样的场景吗?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样的场景,对于我们铁路职工来说,一点都不夸张,有时候,比上面的描述更艰苦。
新生活正在塑造我们全新的观念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有些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新的时空感觉悄然建立;丰富的社会情态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正在悄然形成。一句话,都市文化和技术文化正在塑造新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每一部有价值的时代之作将无法绕开这一现实。另一方面,是作家的想象力和思考力滞后于时代。当今天的信息、游戏、影视和廉价小说代替经典小说的叙事魅力时,美国当代评论家乔治·斯坦纳指出:“在小说家和天生编故事的人之间,已经出现了无言的深刻断裂。”作家的“想象力已经落后于花哨的极端现实”。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早在1936年就预言过:新闻信息“给小说带来了危机”,他将这一切归咎于经验贬值,说“经验贬值了,而且看来它还在贬,在朝着一个无底洞贬下去。无论何时,你只要扫一眼报纸,就会发现它又创了新低,你都会发现,不仅外部世界的图景,而且精神世界的图景也是一样,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我们从来以为不可能的变化。”经验泛滥和过剩导致经验贬值的同时,也导致了小说家经验的逼仄和肤浅。因为经验的大量传播,将具有想象力优势的小说家置于与读者平等的地位,小说家经验甚至不及于一个分工细微的职员,所以,在今天的时代,小说家的想象自信正在被打垮,他们不断重复一句话:生活比小说精彩。既然这样,我们还要小说干什么?还如何写小说?而过去小说家身上拥有的那种“好的小说永远比生活精彩”的写作信念,在今天的时代面前黯然失色。那么,我们还怎么去写小说呢?
《远情》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或者给出了答案。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描述一个人对一件事的感受上。集中于一个人的灵魂,写出在这个时代大潮中,还有一个人的灵魂是这样。《远情》中的丫头爹,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似乎在与一己之力,对抗当下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人群。
在一次连续暴雨,上游一座年久失修的水库突然发生决口。愤怒的洪水掀起了万丈狂澜呼啸着扑面而来,也就是眨眼之间,昔日人声鼎沸的工地霎时变成了恶浪滔天的海洋。要命的是,从上游漂流下来的树木很快便把刚刚修造好的铁路桥洞给卡住了,如果不及时弄走,飞流直下的洪水很快就能把这座桥连墩子都翻过来。抢险过程中,丫头爹和另外两名工友被掀入激流之中。本来丫头爹完全可以自主逃生。但他没有,他先是抢救出工友刘复学,又去抢救董向华。可是,当丫头爹不顾一切,拼着性命托举着董向华抓住树枝时,自己却被一个巨浪卷得无影无踪。等到同志们找到他时,已经不省人事了。
好在丫头娘和丫头还是看到了丫头爹最后的时刻。丫头爹最后求丫头娘的事情,是“死后也和老队长一样,埋在高铁线旁,要亲眼看看,他亲手铺设的高速铁路到底能跑多快。”当丫头爹又在寻找副队长,想要交待施工任务时,副队长抢先表示:“一定按期完成任务,绝不后退一步”后,“丫头爹是想说‘好,可是,嘴还没张开呢,一口浓浓的鲜血喷了出来——”
有人可能认为丫头爹这样的人物有些过于夸张,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不要命的人。当一个人的生命与工作和他人发生冲突时,人的第一反应是保护自己,因为这是一种本能。作家刻画丫头爹时,是不是太理想化,或者说拔高了人物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理解,与我们的现实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完全不同。我的理想主义比他们的现实主义更为现实。理想主义曾经预测到的事实,已经得到了证实。”他认为,“要按现实的本来面目写现实”。这样的现实不可能有,“因此要给予观念的更多的余地并不要害怕理想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第327页,漓江出版社,1988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也是遵从“酷似生活”这种艺术假定性的,不然,他就不属于现实主义经典作家,但他懂得现实主义文学在本质上必须是营造有魅力力量的“意义世界”的神圣精神创造。这种文学同时提供的缤纷人间世象亦即“生活图画”,都不是创作的真正旨归,其使命最终在于结构出作家所欲宣达的关涉人之生命生存的思想、价值观、信念和趣味等,用以影响接触这种文学的人们的精神和行为。我们稍一翻捡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就不难发现,许多赫赫有名的经典作家都同时是思想家。什么是思想?一位当代中国青年哲学家这样说:“仅仅说出一些事实是不够的,这不是思想,甚至不是一种有意义的期待。有意义的思想必须同时是关于未来的一种积极的和善意的理念,如果不能说出希望之所在,那么,又有什么意义呢?说它干什么?”“这是思想的一个秘密,思想只能往好处想,否则就不用想了,只有往好处想,世界才有希望。”(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第36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有思想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是理想主义者。
每个时代都有文学,但并不是每个时代都能成为时代精神的增长点。情感力量永远是读者走进文学的最先和最有力量的吸引,假如文学里一切应有尽有,但若是缺失了情感,那么,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成为人们冷淡乃至疏远文学的充足理由。情感力量是现实主义文学最能捕获读者的威力无比的精神之箭:文学从情感上劝动读者,差不多就是劝读者认同文学家借文学具象诗意宣达的一切,包括思想、价值观、信念及趣味等等。我们在文学这里看到了情感和思想亲密的“神圣同盟”:生动的文学具象首先成就了情感,守护住了一方充满迷人魅力的文学完美领域;同时,也成全了思想,使其在惯常的逻辑形态之外,拥有了另一种生动迷人的存在形态。情感因与思想相融而深沉、悠远;思想因在具象里与情感一体同步而具有了生动的表情性,并有希望成为容易被情感所记忆而被心灵留驻的常效思想。
真正铁路题材作品,是有要求和条件的。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只要小说里面的人物在铁路工作就是铁路题材小说,这种说法是对铁路题材的误解。我们知道,目前全国产业大军约有四亿人左右。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和科技工作者奋战在生产和工作一线,参与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推广应用。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国家建设的中间力量。面对这一群体,我们书写工业题材,塑造工人形象,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他们身上具有力量之美和崇高之美。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而铁路职工,除了上述说的力量和崇高之美外,还具有速度之美和奉献之美。一代代铁路人,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在没有人没有路没有电,甚至没有水的情况下,生生用自己的力量和血汗开辟出一条路,一条铁路线,然后让那个叫做火车的家伙,在线路上往来穿梭,呼啸前行。
文学艺术是一种独特的叙事,是其他学科不能取代的。它通过审美、虚构,活生生地展现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的心灵世界,触及历史辩证法,在历史辩证法作用下,不可避免地要展现历史主体,张扬社会积极因素,彰显人性闪光素质。
《远情》正是这样一部优秀小说,在作家杨洪军勤奋亲切温暖深情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铁路建设者形象。这篇小说的成功,我认为,作为铁路作者,应该知道如何写好我们的铁路文學,如何通过我们手中之笔,书写一线职工的艰辛和奋斗,书写他们的喜怒哀乐,书写他们身上那种铁路人特有的伟大精神。这些都指向超拔而神圣的终极目标,因而,作品具有了追寻崇高的美学风格,具有了英雄赞歌的特殊价值。我想,这些正是《远情》成功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