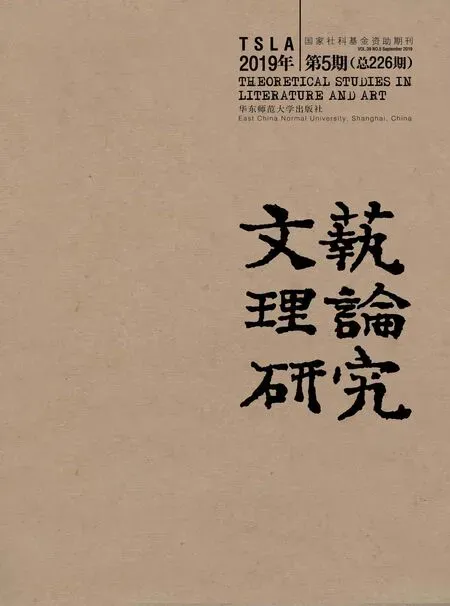人学话语与新时期初年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
卢亚明
20世纪80年代的人学话语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指在新时期文论场域中与“人”相关的种种不同取向的话语,包括“文学是人学”“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共同美”“主体性”“个性”等等表述。人学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参与了哲学、美学、文艺学、人类学等诸多人文学科的建构,哲学与人类学甚至还产生了“人学”学科。但人学话语并不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也不是一个具有同质性、单一化的话语形态,而是有着多种意涵、多个向度、多重意义空间的话语形态。人学话语同样不是自产生以来就天然地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在特定的时刻以特定的方式成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一部分,并参与了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
因此,这里所探讨的“人学话语”,并不是所有与“人”相关的种种话语形态,而是指真正参与了新时期初年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对人学文论知识建构起到重要作用的话语实践。文学理论的“人学化”与文学理论的学科化密不可分,文学理论自此开始有了将自身建构成人文学科的自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为文学正名’作为新时期文学思潮的标志性口号,其所蕴含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把文学从政治的战车上解脱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存在,根本上说乃是为人正名,是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学领域的话语表征——即此而言,一种蕴含着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学理论话语开始形成。”(李春青145)正是在此种意义上说,人学话语标示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特殊性。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人文学科,其知识生产并不是纯然客观的,而是一种有温度的、与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体现着人的价值诉求与价值判断的知识生产。
一、 人学话语的形成与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
新时期文学理论知识体系中人学话语的形成离不开两个重要事件: 一个事件是朱光潜于1979年10月,在《文艺研究》第三期上发表题为《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的文章;另一个事件是钱谷融于1980年10月在《文艺研究》第三期上发表题为《〈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的文章,并于1981年结集出版了题为《论“文学是人学”》的论文集。这两个事件一前一后,时间跨越1979—1981年间,这一时间段正是人学话语参与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时期,而这两个事件对于新时期人学主题的恢复与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人学根基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卡尔·曼海姆在建构知识社会学的时候曾引入了“位系”这一概念:
位系(constellation)一词来自占星术,指的是在一个人出生时星的位置和相互关系。研究这种相互关系的人们相信初生婴儿的命运是由“星座”(constellation)决定的。广义的“位系”一词指的是在特定时刻特定因素的特定结合方式,如果我们有理由假定,各种因素的并存导致了我们所感兴趣的某个因素形态的构成,那么这就是要求我们对此结合方式进行研究。(《卡尔·曼海姆精粹》6)
可见,曼海姆引入“位系”这一术语并不是对占星术感兴趣,而是想借助这个术语的意涵来说明知识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由各种知识内在理论问题的逻辑发展理路所决定,也同时会由与理论知识相关联的社会实在方面的外在因素所决定。曼海姆就此认为,一个问题没有成为现实问题之前,是不会先成为知性问题的。“位系”的研究方法就是要求我们在考察理论知识问题的时候,同时要考虑到特定时刻的社会实在生活中的问题,要从社会实在中产生问题之处来寻求理论知识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此,曼海姆提出了产生知识社会学的四个相互作用的因素:
(1)思想与知识的自我相对化;(2)由精神的“揭露性”倾向所带来的新的相对化形式;(3)一种新参照体系的出现,即社会领域,从而思想被认为与社会领域相关;(4)使这种相对化总体化的愿望,从而不再将某种思想或观念,而是将整个观念体系与基本的社会实在相联系。(《卡尔·曼海姆精粹》13)
这些因素提示我们任何知识和思想都不是天然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而是有着自身的相对性。这并不意味着某一时期的知识和思想没有了正确与否的判断,没有了评判的标准。曼海姆并不想将知识社会学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他只是想指出某一时期的知识与思想和相关的社会实在领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而某种具体的知识表述或思想观念应放在当时整体的知识观念体系中去研究。研究知识和思想问题的“位系”,就是要回到这一时期与其相关联的社会实在所产生问题之处,具体厘定知识和思想问题的结构、位置与社会实在问题所关联的特定时刻、特定因素和特定结合方式。
依据曼海姆研究知识问题“位系”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出,人学问题也不能只从自身知识系统来解释,也需要研究人学问题的“位系”,也就是要研究人学问题与社会实在问题所关联的特定时刻、特定因素和特定结合方式。人学话语正是在人学问题的“位系”中形成的,人学话语的形成也只有在人学问题的“位系”中才能得到解释。
朱光潜事件在新时期美学、文学理论学科领域恢复人学主题具有破冰之举的重要意义,这一事件标志着在文学理论知识领域讨论人学问题的禁区被打破。禁区的形成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直接成因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1957年,周扬在“反右”运动的总结性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将“人性论”指认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产物,并将之称为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24)。1960年,为了配合当时政治上反修防修的需要,周扬在当时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其中专门有一个部分题为“驳资产阶级人性论”。至此,一系列二元对立已经形成:“人性论”-历史唯心论-阶级调和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的人性/“阶级论”-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高尚的人性。从中可以看出,“人性论”与“阶级论”的对抗与哲学(历史唯心论/历史唯物论)、政治(阶级调和论/阶级斗争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动/革命)、道德(腐朽/高尚)上的对抗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倡导“人性论”不仅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其哲学基础是错误的,而且在道德上是败坏的。此后“人性论”更是被极左势力视为社会主义战线的“大毒草”。这样,“人性论”成了文学理论知识界不可触碰的禁区。新时期伊始,朱光潜的这篇文章正是为了打破文学理论界的人学禁区。在1980年8月出版的《谈美书简》中,朱光潜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稍作修改后作为第六部分出现,题目变为“冲破文艺创作和美学中的一些禁区”,文中主张冲破五大禁区:“人性论”“人道主义”“人情味”“共同美感”和“三突出”原则对塑造人物性格所设置的禁区。其中,“人性论”禁区又是其它禁区的源头,所以要首先冲破它。朱光潜在文章最后倡导:“冲破他们所设置的禁区,解放思想,按照文艺规律来繁荣文艺创作,现在正是时候了!”(朱光潜76)可见,朱光潜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正是为了打破文艺界讨论人学问题的禁区,而实际上这一事件也确实起到了打破禁区的作用。此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有关人学问题的探讨层出不穷,这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知识体系人学话语建构的开端。
人学禁区被打破之后,钱谷融事件便起到了建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人学根基的作用。这一事件的特殊性在于,钱谷融的文章并不是在新时期创作的,而是以一种旧文重提的形式出现的。钱谷融在《文艺研究》1980年第三期上发表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即《我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实际上是作于1957年10月的旧文。同样的文章,同样的观点,却在不同时期遭遇了极不相同的命运。在1957年,“文学是人学”命题遭到批判,而到了1980年,这一命题却得到认同和张扬。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理论知识的生产与建构,包括它的内容和形式是与社会存在和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钱谷融写于1957年2月的那篇《论“文学是人学”》是为同年3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而作的。而这篇文章之所以能以这样一种与当时主流观点不同的形式出现,是和1956年实行的“双百”方针直接相关的,而“双百”方针的提出是与当时的社会实在问题紧密相连的。1956年,中国宣布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一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崭新阶段。正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时代语境下,“双百”方针应运而生。“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并不是同时提出的,“百花齐放”于1950年提出,而“百家争鸣”于1953年提出。1956年初,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将两者相提并论并作为一个方针提了出来。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重申了“双百”方针。5月26日,时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对一批艺术家、作家、科学家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至此,“双百”方针在文艺界、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渐渐深入人心。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再次解释了“双百”方针,促使“双百”运动全面展开。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正是在这种社会情景中产生的。
然而,当时的社会历史情景处于一个尚不稳定的阶段,中国社会情景的变化不仅受到国内各种因素和社会问题的影响,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1956年实行的“双百”方针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具有长期有效性的稳定的国家方针政策,前有1955年3月发起的肃反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发生了胡风事件,这次运动实际上确立了对整个知识分子的严格的思想控制(梅斯纳152—54)。后有195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发起的“大学风暴”,同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成为“双百”运动结束的信号。社论的矛头指向了“右派分子”,社论指责“右派分子”在滥用自由,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后来相继发表的社论反驳了“鸣放”期间出现的各种观点,并警告说,无限制的对党的批评有导致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强调需要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双百”运动中自我暴露出的敌人。到1957年6月中旬,过去知识分子批评党的座谈会变成了党的官员谴责批评者的会议。在短暂的“双百”运动之后,一场持续时间长达一年之久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梅斯纳215—16)。正是由于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产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这篇文章作为文学理论知识的命运也就随社会历史情境的变动在肯定与怀疑、赞誉与批判之间摇摆不定。
钱谷融的文章在新时期的重新出场,是在知识界人学话语已经解禁且日益成为主流话语的情况下出现的。这时的社会情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已经与那篇文章产生的年代大不相同。中国自1978年以来,确立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本发展方向,重新启动“现代化”方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文化思想界开始了解放思想运动,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冷战时期的国家策略,而代之以新时期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针政策。“双百”方针被重新启用,并写进了宪法,成为一条国家长期性的文艺政策和根本方针,这为文艺界形成民主自由的空间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同时,国际局势这时也发生了变化,与20世纪50—60年代有了明显不同。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这场发生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历史转折并不能仅仅从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来讨论问题,而应该在全球视野下看待这场历史转折。从全球视野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与全球性的历史转折同时发生的,是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结果(贺桂梅24)。全球经济危机激发了外国海外资本市场扩张与第三世界合作的需求,而中国自身的经济危机和技术落后现状也促成了“改革开放”的新政。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国际地缘结构格局和国内新时期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情境下,人学话语才逐渐参与到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去,并为文学理论在新时期的知识体系建构确立了人学根基。
二、 人学话语与文学理论场域的生成
人学话语作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除了要考虑上述特定的国际国内历史情境和社会实在因素外,还应将其放在新时期文学理论场域的生成过程中来考察。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一书中研究了法国第二帝国时期文学场的生成过程,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研究新时期文学理论场域的生成过程颇有启示作用。
布迪厄认为,任何一个场域的生成都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就是一个由众多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大大小小的关系空间构成的世界,而这些关系空间被布迪厄命名为“场域”。可以看出,场域并不是一个在社会中天然存在的空间,它是有其生成条件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一空间的相对自主性的确立与自身的运行逻辑和规则的形成。一个场域就是一个服从自身法则的相对独立的领域,因此,自主性的获得就成为一个场域出现的关键阶段。
依据布迪厄的研究,法国第二帝国时期文学场和艺术场的生成与那些具有落拓不羁特质的年轻人有关。以波德莱尔和福楼拜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人来到巴黎,他们没有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却从事作家或艺术家的道路,而这在此前一直是贵族和巴黎资产阶级的专利。为了走上以艺术为生的道路,他们喊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极力散播落拓不羁的观念和价值观,崇尚一种追求精神品质的他们认为的完美生活方式。他们靠文化资本获得服饰上的标新立异,烹饪上的奇思异想,爱情上的唯利是图和娱乐上的高雅脱俗。他们在新的社会世界开始了自身的身份、价值、理念、规范和生活方式的建构(布迪厄68—71)。
然而,布迪厄认为文学场的生成并不是仅仅通过自身建构来完成的,场域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任何一个场域都是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形成的。文学场也是如此。当时在法国第二帝国的工业扩张支持下,工业家和商人的出现使得金钱的统治无处不在,对金钱和利润的追捧与拿破仑三世的政策一拍即合,暴发户与当权者的品位趋向最通俗的连载小说,报纸成了当时最重要的媒体。沙龙成为了在根本对立的强大力量周围建构文学场的重要场所。布迪厄指出,文学场和艺术场正是在与“资产阶级”世界的对立中形成的,这个艺术世界的形成恰恰与世俗世界的产生密不可分,对世俗世界和权力集团的反对促使艺术家和作家的独立逐步得以实现,他们的创作与服务于权力或市场需要的生产截然不同,他们明确制定了新的合理性规则,为一个自主的场的形成赢得了条件(布迪厄62—76)。
依据布迪厄的研究,可以看出,任何一个场域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场域的生成需要具备一些相关条件: 首先,相对独立自主空间的获得是一个场域形成的首要条件。一个场域作为社会空间的一部分被明确辨识出并顺利运行,就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其次,场域的形成需要有制定其合理性规则的主体,这些人需要制定一些新规则与社会中存在的其它场域相区分,同时标示出自己的场域的独特性,新形成的场域要依照新制定的规则来运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当时社会主流场域相区分的标新立异成为一个新场域生成的重要因素。再次,新场域的生成需要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保障,一个非法的场域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从“场域”的视角来审视新时期初年的人学话语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我们会发现,新时期初年正是文学理论建构自身场域以结束其作为政治权力场域的附属地位现状的重要时期,而人学话语正起到了为建构文学理论场域制定新规则的作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一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解放思想运动在全国展开。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发展策略,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新时期“双百”方针的重新确立,改变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现状,废止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尊重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尊重文艺家的个人创造精神,这些都为文学理论场域的形成赢得了必要的相对独立自主的空间。文学理论逐步摆脱政治权力场域的支配和从属地位,开始建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新的空间场域。
建构文学理论新场域的主体正是以朱光潜、钱谷融为代表的一批曾经受过批判的文艺界知识分子。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朱光潜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1925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然后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讲授美学等课程。钱谷融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教授现代文学等课程。可见,他们是新中国建国前培养的一批知识分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正值他们的学术研究旺盛期,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看待问题的视角。正如曼海姆所言:“某一视角的特殊性的确定,就成了相关群体所具有的社会地位的文化标志和思想标志。”(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331)这种视角既不同于工农大众的视角,也不同于政治权力场域和经济场域群体的视角。钱谷融曾于1945年写过一篇题为《艺术化人生》的文章,文中援引王尔德的名言“美的追求是生命的真正秘密”,并不无感慨道:
创造你的生命,像创造一首诗,一支曲,或者一幅画吧!你要用最艳丽的辞藻、最激荡的旋律和最新鲜的色彩来勾出你生命的伟大杰作。这搅动人心魄的花花世界,要没有千百万欢欣狂醉的灵魂歌舞其上,实在是太可诅咒的杀风景了!(钱谷融21)
由此可见,像钱谷融这样的文艺知识分子有着人生艺术化的追求和想象,他们的视角是独特的,是一种具有审美性、诗意性、想象性、非功利性的视角,他们更注重精神层面的修为,更倾向灵魂的自由与欢欣。而这种视角在社会生活中的内在化就会成为某种惯习,这种与主体社会位置相连的某种持久的性情倾向就是惯习。可见,这种视角和惯习一方面,正是他们作为文艺知识分子的思想标志和文化标志;而另一方面,也带给他们某种局限性,使他们对于工农民众、政治权力以及经济场域的视角并不敏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身体地位一度是摇摆不定的。特别是20世纪50—70年代,知识分子曾一度受到怀疑,成为思想改造的主要对象。随着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得以确立,以朱光潜、钱谷融为代表的一批文艺知识分子才能够成为建构文艺理论场域的主体。他们所建构的人学话语为文学理论场域制定了新规则,以区别于之前的革命话语和阶级斗争话语。
除了朱光潜、钱谷融外,还有黄药眠、钱中文、曲若镁、张炯、白烨、敏泽、毛星等一批知识分子参与了人学话语与新时期初年文学理论场域的建构。黄药眠对当时占主流的文学反映论进行了人学话语的再阐释:“有人说文学是反映客观现实或反映客观世界,我认为这是把反映的范围扩大了。其实,文学只是反映人的生活。”“文学不限于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有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主观的反应,所以作品里面总是包含有思想和感情。”(“关于当前文艺理论问题的几点意见”17)可见,黄药眠强调的是文学反映的是人的生活,是主观感受的人的生活。这在他后来解释的文学创作的客观与主观上体现的更为明确:“所谓艺术文学创作上的客观和主观,就是指人的社会生活的客观和作者对于这客观的人的世界的看法和感想,自己的感觉和感受。”(1)黄药眠指出,文学不是反映纯粹的客观世界,也不是一种客观的反映,因此,文学反映的对象和反映的方式都具有主观性,都离不开人。也就是说,文学理论所研究的问题都带有人文色彩,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研究。钱中文则论证了“共同人性”的合法性,与朱光潜提出的“共同美”相呼应。钱中文指出:“认为人除了阶级性,还具有共同人性,乃是这场人性问题讨论的重要收获”,“共同人性是现实的人的根本特征之一和现实关系的组成部分”(钱中文82—83)。曲若镁在论证文学表现人性、人情合法性的同时,更强调作为“具体的个人”的个体价值。曲若镁指出:“表现人性、人情,是文学的固有属性和基本特征,也是作家反映现实、变革现实的基本手段。”“阶级社会中的人是有阶级性的,但是,这种阶级性只有通过具体的个人才能表现出来。”“从具体的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属的阶级的某些共性,可是从某一阶级共性上,我们却看不到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曲若镁66)对个体价值的诉求和合法性论证,是新时期初年文学理论建构自身场域的重要一维。
人学话语在1985年后的文论生产中呈现为“文学主体性”“向内转”等话语,文学理论也随之开始了对于“精神主体”“文艺心理学”的建构。以李泽厚、刘再复等为代表的“主体性”话语既可以视为对人学话语的一种深化,也可以视为一次转折。因为,从文论自身的发展来看,文论已经从新时期初年的突破期开始进入建构期;而从话语资源来看,“主体性”话语对“内宇宙”“精神主体”的强调已经跳出了新时期初年主要倚重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诚然,一个学科的相对自主性与自身运行规则的确立,才是其有可能有效参与到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前提条件。然而,在文学理论的学科自主性、体制化与知识生产的社会化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因此,处理好学科自主性、体制化与社会化之间的关系,成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重要问题。
同时,文艺知识分子要想建构文学理论的场域还需要社会制度上的保障。正如布迪厄所言:“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根据他是否能够独立于各种权力、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来加以判定。而要确保这种独立自主,就必须以各种制度化的有序性对话阵地的存在为前提。”(布迪厄 华康德60)新时期以来,新的文艺制度的确立为文学理论场域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保障。新时期伊始,人们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对于长期使用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进行了反思。在1979年3月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李子云率先对这一口号提出质疑(刘锡诚221)。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顺利召开。邓小平所作《祝词》中已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而代之以“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邓小平210)。1980年2月,周扬在一次剧本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说法(周扬,《周扬文集》第五卷216—17)。同年7月《人民日报》即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明确指出了:“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口号应当是: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自此,新的“二为”方针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成为新时期文艺界总的指导方针。
综上所述,新时期具备了文学理论场域生成的几个主要因素: 文艺界相对自主独立空间的获得,作为文论场域建构主体的文艺知识分子为新的场域制定规则,加之“双百”方针的常态化和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解释为文论场域提供了制度上的合法性保障。这些因素促成了新时期文学理论场域的生成,而人学话语正是在文学理论场域生成的过程中参与了文论知识体系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的新阶段,文学理论界开始有条件改变作为政治权力场域的附属而存在的现状,逐步建构相对独立自主的自身场域。正是在文学理论场域的形成过程中,一批文艺界知识分子开始为新场域制定运行规则并建构知识体系。在当时处于人学知识型的知识界关系整体中,人学话语成为这些知识分子为文学理论场域制定新规则,建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重要话语实践。
三、 人学知识型下的文学理论知识范式
新时期伊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是在人学知识型的关联整体中进行的,人学话语成为当时建构文学理论场域,并为新场域制定运行规则的主要话语实践。福柯用“知识型”这个概念指出,知识生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过程,而是在一个与认识论形态、科学以及话语实践相关联的整体中进行的,这既揭示出知识生产的复杂性,也规定了知识生产的限度。人学知识型下的文学理论知识范式同样也既有其复杂性,也有其限度所在。
首先,人学文学理论知识范式以人作为理论知识阐述的中心,突出文学活动中主体的重要性。无论是探讨文学创作、文学接受的问题,还是探讨文学标准、文学的目的和任务等问题,论述的焦点都是人,“文学是人学”成为这种文论知识模式的核心观点。这种对人的聚焦实则体现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对主体性的诉求。在文学活动中安置主体是为了应对文学理论知识界长期存在的机械反映论问题,扭转文学创作领域长期形成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通过强调审美主体、个人、个性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性,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注入活力,解决文论日益走向僵化的问题。但对“文学主体性”的强调乃至膨胀,也使文学理论作为知识的客观性、科学性维度有所削减。
其次,这种文论知识在思维方式上善于在关系中辩证思考问题。人学文论往往从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二元对立模式,以更加辩证和复杂的思维方式处理矛盾和问题。人学文论以一种辩证思维方式从关系的角度来质疑机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以阶级革命话语为主导的“政治论范式”文论,将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个人与社会、共性与个性等范畴置于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框架中,形成了一系列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将对立的话语赋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就被移植到上述认识论的对立之中。这种对立模式还进一步被引申到价值层面,从伦理道德层面上被界定为“高尚”与“败坏”的对立。这样一来,“主观”“主体”“个人”“个性”等范畴就不得不以非法的形式隐于文艺体制中。新时期以来,为了突破这种日渐僵化的文论模式,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从关系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曾经对立的二元结构。朱光潜从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关系角度去安置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的位置,钱谷融则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去重新思考文学中描写具体的个人与反映整体现实的关系,描写人物个性与塑造典型的关系。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他们实质上推行的是一套具有排他性的“一元论”知识模式。在明确的主张与排斥下,不同的话语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对话。只有将矛盾的双方置于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之中,才能揭示出问题的复杂性,寻求突破的可能。人学文论正是采用这样一种更加辩证的思维方式来建构自身的知识体系,增加了知识生产的异质性、多元性空间。
再次,人学文论知识生产是与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实践紧密相连的。人学文论并不是仅仅从自身场域内部进行知识体系的建构,而是与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保持的密切的关联。人学文论既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理论性体现,也为从“人情”“人性”“主体”“个人”“个性”等角度创作文学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文学创作基于现实的这种变化需要在文论中得到理论阐释与支撑。而文论中对人学问题的探讨与深化,也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走向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的文学创作逐渐改变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模式,从之前注重宏大的政治叙事逐渐转变为关注微观的生活叙事。注重刻画人物丰满复杂的性格,关注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与独特的思想世界。从人物的生活细节与日常琐事去展现人物真实的现实生活。文学创作不再通过“脸谱化”的人物来书写革命话语,而是通过一个个既独特又典型的具体人物来展现个人的日常生活与错综复杂的大千世界。
最后,人学文论知识生产具有强烈的公共关怀色彩,人学文论正是人文知识分子面对现实困境作出的回应。当突显阶级意识的革命话语逐渐式微,不能再起到“精神导师”的作用时,人们的公共生活需要新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人学文论正是在这样的公共关怀意识下出现的,成为社会公共生活新的精神整合力量,“人性化社会”成为人们继“共产主义社会”之后新的理想之境。没有社会内涵的理论是无生命的,公共关怀是文学理论自身生长的源泉。
综上所述,人学文论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确立了人学根基,为正在形成中的文学理论场域制定了新规则。人学文论突破了单一的“政治论范式”文论,以人学话语取代日渐僵化的阶级革命话语,将文学研究的聚焦点从政治场域的阶级革命转向了文学理论场域的人学。
人学文论在新时期文学理论场域形成的初始阶段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由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和知识资源所限,人学文论的政治启蒙和社会动员作用要远远大于它的理论创新实绩,因为它并没有提出多少新的概念、观念和方法,而是更多地沿用了以往的知识资源和话语形态,也没有建构出多么严密的知识体系,但是人学文论却为刚刚开始形成的文学理论场域提供了一套可以按照自身规律运行的新规则,为建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开创了创造新概念、新观念、新方法的可能性空间。正是有了人学文论的话语实践,此后出现的审美-情感文论等文论形态以及各种新概念、新观念和新方法的确立才成为可能。
注释[Notes]
① 虽然朱光潜的文章并不是最早在新时期讨论文学理论中的人学问题的文章,比朱光潜的文章早几个月已有王磊的“人性和阶级性的对立统一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此文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第2期。当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双月刊,而《文艺研究》于1979年才创刊,当年只出版了四期。因此,从时间上推断,王磊的文章比朱光潜的要早发表了几个月。但其影响远不如朱光潜的文章,并没有起到解禁的作用。参见王磊:“人性和阶级性的对立统一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979): 75—78。
② 此文后来发表于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和1958年3月11日的《文艺报》第5期。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皮埃尔·布迪厄: 《艺术的法则: 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Bourdieu, Pierre.The
Law
of
Art
:The
Forma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 Trans. Liu Hui.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01.]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Bourdieu, Pierre, and Loïc 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Trans. Li Meng, and Li Kang.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Press, 1998.]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
[Deng, Xiaoping.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ume
II
).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4.]贺桂梅: 《“新启蒙”知识档案: 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He, Guimei. “New
Enlightenment
”Knowledge
Archives
:Research
on
Chinese
Culture
in
the
1980s
.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黄药眠:“关于当前文艺理论问题的几点意见”,《文艺理论研究》3(1980): 17。
[Huang, Yaomian. “Several Comments on Current Theoretical Issues of Literature and Art.”Research
on
Literary
Theory
(1980): 17.]——:“关于创作上的几个理论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1982): 1。
[- - -. “Several Theoretical Questions about Literary Creation.”Literature
Theory
Research
1(1982): 1.]李春青:“论人文主义价值诉求与新新时期以来文论话语建构之关联”,《中国政法大学学报》3(2017): 145。
[Li, Chunqing.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umanistic Value Appe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Discourse Discourse since the New Era.”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3(2017): 145.]刘锡诚: 《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Liu, Xicheng.On
the
Edge
of
the
Literary
World
:Editorial
Notes
.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04.]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年。
[Mannheim, Carl.Ideology
and
Utopia
. Trans. Li Bulou,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 - -.The
Essential
Karl
Mannheim
. Trans. Xu Bi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莫里斯·梅斯纳: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张瑛等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Messner, Maurice.Mao
Zedong
’s
China
and
its
Development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 Trans. Zhang Ying.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92.]钱谷融: 《钱谷融论文学》。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Qian, Gurong.Qian
Gurong
on
Literature
.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8.]钱中文:“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文学评论》6(1982): 82—83。
[Qian, Zhongwen. “On the Description of Common Forms of Human Nature and its Evaluation.”Literature
Review
6(1982): 82-83.]曲若镁:“人性·人情·人学”,《求是学刊》2(1980): 66。
[Qu, Ruomei. “Humanity, Human Feelings, Humanism.”Qiushi
Journal
2(1980): 66.]周扬: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北京: 作家出版社,1960年。
[Zhou, Yang.A
Big
Debate
on
the
Literary
and
Art
Front
. Beijing: Writer Publishing House, 1960.]——: 《周扬文集》(第五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 - -.A
Collection
of
Zhou
Yang
’s
Works
. Vol.5.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4.]朱光潜: 《谈美书简》。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Zhu, Guangqian.Letters
on
Aesthetics
.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