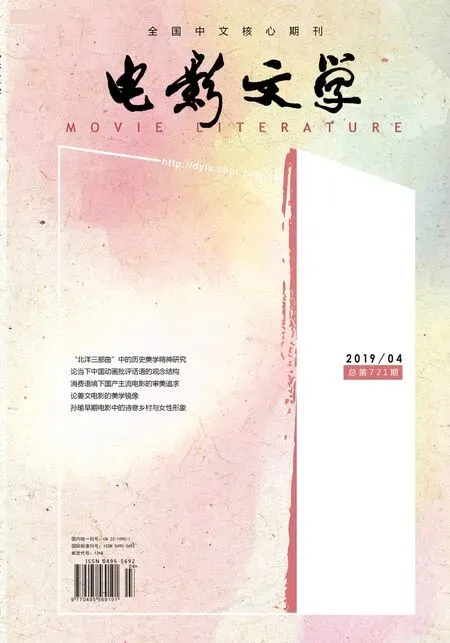论当下中国动画批评话语的观念结构
陈树超 (福州大学 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动画理论与批评逐渐从萌芽阶段开始起步与发展。这70年来,是中国动画探索自身艺术道路的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受众群体的分化与稳定、创作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介景观的渐次更迭、海外著述的译介等,给动画学者带来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为动画批评提供了愈加丰富的话语介入空间,也出现了诸多的新观点。但是,正因为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批评话语逐渐丰富,也形成不同价值标准的错位与偏差。在这里,我们借用齐泽克的“视差之见”来形容这种现象,按他的话来说,“客体的位移”令“主体瘙痒”[1]25,引发主体的延宕和分裂。理论与批评的话语愈加丰富,一方面提供了不少深刻的洞见,同时也造成了等值的困惑。通过以下两个侧面可窥见一斑。
一、“低幼”与“成人化”
当人们谈及中国动画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时,经常有人会脱口而出:中国动画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太“低幼”了,应该多生产成人化的动画片。在百度搜索“中国动画”“低幼”两个关键词,搜索结果就有65万余条。中国知网的文献检索显示,2008年至2018年的10年间,涉及“动画”“低幼”“成人化”论题的中文学术论文近70篇。这样,“低幼”和“成人化”的批评话语在今天如此深入人心,便不奇怪了——按照结构主义和意识形态理论的说法,人生活在语言营构的意义框架中,不仅我们在说话,同时“话也在说我们”。“低幼”和“成人化”的二元对立话语看似能够方便每个人对动画片发表看法,体现出学者和媒体对中国动画发展的责任心及其焦虑感。但不容忽视的是,它也限制和简化了我们的思维,带来至少三个层面的困惑:
第一,“受众细分的产业逻辑”与“类型划分的文化逻辑”。动画产业的发展一直是中国动画研究领域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受众细分”也基于分众化传播思路的产业发展策略的共识。但在现实的批评实践中,却总是出现产业逻辑与类型划分的思路相混淆的现象,呼吁“成人动画”类型形成了一种声势(1)这类论文有很多,比如《东南传播》2016年12期的文章《把握受众、兼容市场的华莱坞成人动画》等,不一一列举。。分众化传播的思路究竟如何践行暂且不表,问题的关键是,产业发展和类型划分是两回事。在电影理论中,类型电影具有明确、可辨识的形式特征和与之相符的观众期待视野,麦克白称之为“类型元素”[2]——辨识稳定的作品形式特征与题材,及其背后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是电影类型分析的常识性技能。在文学中,文学类型的两层依据“一个是外在形式(如特殊的格律或结构),一个是内在形式(如态度、情调、目的等以及较为粗糙的题材和读者观众的范围等)”[3]。如果将成人动画视作一种类型,那么就需要符合基本的类型化要求。而且,类型的惯例是在不断创作和接受实践中形成的,绝非纯粹人为的划分。金敏、押井守等人的作品的确为儿童的接受带来了难度,但是,这是因为大师们对稳定类型的突破性探索。换句话说,孩子们不易懂,是创作者们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而非原因。真正符合类型化意义的“成人动画”概念的,反而是日本的“色情动画”。即便从产业发展的逻辑上讲,“成人化”也未必是唯一的道路,有学者就不这么认为,而是主张兼顾各个年龄段,比如迪士尼的作品就是“老少咸宜”的,应“把握人类共有的童真”[4]。或许还有人认为,成人和低幼的划分有利于对儿童的积极保护。那么,这就涉及了第二个层次的困惑。
第二,“儿童成人化”的“波兹曼问题”和“成人儿童向”的后现代审美文化问题。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很早就对“儿童成人化”展开了批判,他认为印刷媒体使成人和儿童在观念上相区隔,电子媒介却带来“童年的消逝”[5]。这一趋势在网络媒介时代有增无减——今天的儿童接受的信息量和接受信息的便利程度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不论是学术论文,还是大众媒体,对不良动画片的批评声音一直没有中断。但是,一方面批评动画片对儿童的侵害,另一方面呼吁动画的“成人化”,这在逻辑上无法自洽。而“成人儿童向”也是后现代审美文化中的典型症候——国内外都不缺乏批评“御宅族”对童稚感之迷恋[6]的声音,国内也有学者对“卖萌”背后的“柔性暴力”[7]提出警示。一方面的学者反思成人儿童化的问题,另一方面的学者在呼吁动画片的“成人化”。那么,“大儿童”的娱乐趣味到底是成人的还是儿童的呢?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些不是在同一个标准下所提出的问题,的确如此。理论研究固然可以人为设定致思路径,但它无法忽视其解释力去面对复杂现实时的检验,追求鲜明的立场并非放弃理论整体性和开放性的理由。当“儿童”和“成人”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超出动画片本身的范畴时,第三个层次的困惑也就接踵而至。
第三,动画片的审美和教育功能问题与大众传媒的治理问题。红遍全球的《小猪佩奇》是为学龄前儿童创作的动画片,这部作品童趣盎然,同时带有合作和亲情主题的教育意图,受到世界范围内儿童观众的青睐。“小猪佩奇”变成了“社会人”是由于网络亚文化的影响,是个大众传媒的治理问题,其实根本与动画片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一部优秀的作品因此受到轻视,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尤其是有些年轻的动画从业者,甚至会对这样的作品不屑一顾,将它简单地归于“低幼动画”的范畴,认为“成人向”的作品才更有艺术追求。教育、陪伴儿童的良好出发点反而变成轻视类似教育动画的理由,其中的悖论引人深思。当然,资本的逐利本性看起来和教育格格不入,《小猪佩奇》及其衍生品在今天的传播和消费如此火爆,当然是基于它的娱乐性和话题性,而不是“教育”这个看似严肃的字眼。但是,这个系列的动画片的初衷,的确是帮助孩子们成长,告诉我们教育原本可以轻松活泼。究其根本,并不是观点、立场和出发点出了问题,而是“低幼”和“成人化”的话语框架对上述复杂的问题缺乏解释力,反而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麻烦。
儿童是动画片的重要受众群体,为孩子们创作动画理所应当。不管动画片的创作如何繁荣,这都是需要正视的客观事实。但是,“低幼”和“成人向”占据了多方言论的显赫位置,形成了动画批评话语的第一个明显侧面。由于这两个词组被赋予鲜明的褒贬含义,致使二者呈现出明显且武断的对立倾向。该二元对立的话语结构的生成固然是基于对中国动画发展的责任心,但其中的视差之见并没有导向齐泽克意义上的解放性质,却带来了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困惑和混乱。
二、“童心—自然”与“理性—文明”
在中国动画批评话语体系中,与“低幼”“成人化”相并列的,便是“童心(初心)”和“理性(反思)”的话语结构,形成了与第一个侧面相并行的另一个侧面。这一并置的批评话语范式之所以能够被广为接受,是因为相对于“文明”的成年人来说,儿童的思维和审美认知心理更多停留在“自然”状态,关于动画片的相关讨论无法忽视“童心”和“理性”的关系;以宫崎骏等为代表的日本动画人正是由于对“自然”“生态”的关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为国内的动画批评提供了众多话语介入的空间。同时,“生态美学”“生态批评”在国内的流行也为“童心—自然”向度的批评话语提供了众多理论资源。
“童心”向度的动画批评具有较大的理论延展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形成了对“低幼”概念的修正。马修斯的《童年哲学》《哲学与幼童》等著作被译介到国内以来,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其核心观点是儿童的思维经常比成年人更加“深刻”——“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他对弗洛伊德“童年健忘症”[8]106重新阐释也激活了动画批评的思维——成年人很难确保七岁之前的记忆是可信的,所留下的往往是清醒记忆中的一个个碎片。这样的说法都促使一些学者开始严肃地思考动画片与教育的相关问题。教育学者更进一步,认为“儿童观的进步,不只是为了解放儿童,而且也是为了成人自身的解放”[8]213。动画学者对此也早有感受,比如有文章出现“逆城市化”[9]“生态文明”[10]这样的主题,其核心论旨是,人类在文明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童心和自然成为永恒的乡愁。同时,这也呼应了西方新近哲学思潮的部分观念——“潜能之物的沦丧”形成了阿甘本的思想构境:“作为人类成年的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缺失的一个重要的内在潜能,是生命本身应该具有的某种先验的幼年式的纯真经验。”[11]
可见,在动画批评领域,“童年”“自然”的重新发现与成年人对文明的反思是并行的,毕竟,动画片中也存在不少文化反思类的作品。这就形成了“理性(反思)—文明”的批评话语向度。在这个思路下,出现了诸如“认同焦虑”[12]“政治寓言”[13]“伦理评价”[14]的角度,还包括通过对国外动画的分析,展开工业文明反思的论文。
这一组话语从另一个角度来关注儿童和动画片的发展,并且,该并行的观念结构其实渊源已久。比如卢梭的“爱弥儿”倡导回归自然的教育观,弥尔顿的诗歌写道“儿童引导成人,如同晨光引导白昼”(《复乐园》)等。中国的先贤也有不少类似言论,比如《孟子·离娄下》言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李贽提到“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焚书》)。与这一脉络相对应的,则是自马克思、弗洛伊德直至法兰克福学派以降所秉承的“文明—反思”的批判话语。在艺术史领域,里格尔以“艺术意志”与自然的关系,即“人类的艺术创造是对自然的竞争”[15]来构架他的历史叙事。“童心—自然”与“理性—文明”并置的话语结构在动画批评中的广泛呈现,体现出许多学者不断努力,把动画研究带入到更为广阔的人文学术传统中去,因而非常值得肯定。
中国动画从新中国成立前开始起步,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化探索的高峰,尤其是21世纪以来,国家提出大力发展动漫产业的倡议之后,动画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太快了。我们经常说,我国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之路。因此,“不忘初心”也被评为2017年度流行词语。动画片一直深受孩子们的欢迎,我们国家的动画作品曾经是一代儿童共同的快乐回忆。这种情结无所谓中西,斯皮尔伯格最新的电影《头号玩家》所传达的,也正是这种朴素的快乐及其必然失落的无奈。
三、“视差之见”及其应对思路举隅
我们不难发现,在上述两个侧面的批评话语内部、两个侧面之间,存在着齐泽克意义上的“视差之见”:如果要分析一个客体,那么批评主体便需要寻找参照系,但在这个以加速主义为主题的世界中,客体的位置变幻莫测,致使主体悬置乃至分裂。观点论断层出不穷,但世界获得阶段性“照亮”时,新的疑惑与层出不穷的悖论也被制造出来,被不断加速的时代压缩到一个扁平的空间之中,容不得人们将诸多问题放到广阔的历史中慢慢抽丝剥茧。这便是我们对动画的阐释不断释放焦虑,同时又迎来新的焦虑的原因。但如果将这些问题化繁为简,归根结底是艺术自律与承担社会介入责任的关系问题。按齐泽克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构成性的认同”(constituting identification)与“被构成的认同”(constituted identification)的区分[16]。与他举出的“母亲的抱怨”(2)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齐泽克用“母亲的抱怨”来解释“构成性认同”和“被构成的认同”。家庭中的母亲一方面抱怨繁重的劳动和无聊的生活带来的摧残,另一方面这个负责任的母亲形象也是她存在价值的依据。柔弱感性和坚韧隐忍分别体现了意识形态认同机制的“构成”与“被构成”。的例子一样,动画片在各方的角力中谋求自身的发展,“自律”的迫切使得关于它的认同导向“脆弱的、被动受难者”的“美丽灵魂”角色,同时又无法放弃社会文化所规定的形式结构所设定的伟岸姿态。[16]
艺术自律和社会责任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只不过在今天以“不确定性”为主调的世界中,它变得更为复杂了。形形色色的观念“视差”极易消解动画批评者的问题意识,沉溺于“为批评而批评”的话语狂欢之中。然而,齐泽克认为哲学从诞生之日就深陷于“视差”之域,“和马克思眼中的交换一样,哲学寄身于不同共同体的间隙中,寄身于不同共同体之间那不堪一击的交换、流通空间之中”[1]11。图像学家米歇尔也在不断地思考这个艺术史上由来已久的问题,他将之称作“艺术价值”和“形象价值”的矛盾,引用列维纳斯的“他者的面容”,为视觉形象作为工具和主体二者寻找平衡的办法,即“视觉领域的社会建构”要持续不断地被重放成“社会领域的视觉建构”[17]384。
1988年,日本动画出现了两部重要作品,即宫崎骏的《龙猫》和大友克洋的《阿基拉》。在迪士尼引领潮流的当时,动画片的风貌经常是角色无休止的运动,《龙猫》反其道而行之,呈现了一个稳如泰山的妖怪。佐藤忠男评价道:“怀特·迪士尼的作品出现以后,动画片人物永无停歇的运动似乎成了大势所趋,而这部作品却只是为人们呈现了一个迷迷糊糊、呆立不动的妖怪,就令人们感到兴奋激动,心情舒畅。可以说,这是在动画片里开创了小津安二郎式的境界吧。”[18]《阿基拉》则追求激烈的场面,孩子们在恐惧中发出念力,这种念力具有极大的破坏力,被国家利用来研制武器,充满了反思性。如果将这两部作品并列来看的话,似乎可以很轻易地将之分别纳入自然和反思向度的批评话语,并且对其中的问题史了然于胸。然而,如果换个思路,去思考二者同时期对待“运动”——这一当时对动画片至关重要的事物的态度,便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朗西埃“美感革命”的意义及其背后的超越性质。根据蓝江的介绍,朗西埃意义上的“aisthesis”“常呈现为某种毫无意义(a-significiance)之物瞬间变成了感性的关键,正如爬出银幕的贞子,正如朗兹曼电影《浩劫》(Shoah)用集中营里琐细的生活细节抵抗着大屠杀这个宏大情节”[19]。龙猫的“静”同样毫无意义,但却有很关键的抚慰意义。也就是说,朗西埃主张通过图像操作,超越艺术的社会意义与自主意义的二元对立,在新的“美感共同体”的层面上,重新思考图像叙事统合的解放性质。
与朗西埃不同,巴迪欧试图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古希腊的“自然”概念。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诗性作为无蔽的存在显现,是本真的起源;而世界被理解为“数”,则是遗忘的第一步。巴迪欧由此展开思考,调和“数”与“诗”,“一般的多的稳定性确保了自然的诸多的同质性”[20]。他主张在具体的形式事件和自足朦胧的诗性二者居间的“情势”中思考事物。
也有学者对动画片中具体的“形式事件”思考较多,比如同样是儿童的问题,在谈到教育动画时,聂欣如提到了“光晕”的出现[21]。就“光晕”的含义而言,当教育的意图介入动画片的创作,作品的形式会呈现出某种易被感知的“权威”与“崇拜价值”。这正是本雅明所描述的古典艺术的朦胧的、神圣的诗性,而在动画片中,则是关于教育的、具体的“形式事件”。“现代技术非但没有把我们从我们自己人工建造的神秘氛围中解放出来,反倒生产了由‘事实崇拜’构成的新的世界秩序,也就是一方面由科学和技术事实,另一方面由物崇拜、图腾崇拜和偶像崇拜构成的一种新的综合。”[17]26“光晕”在动画片中营造了施教的气氛,而“气氛美学”在更为宽阔的感性认识论层面上,则可导向“关于自然的审美知识”[22]的生态美学维度。古典的神圣启示与现代教育观念正是在动画中的“光晕”中实现了诗性的综合,在今天变动不居的文化境况的机变之间,营造出一个新的、具体的“形式事件”。这样的分析,都是在各种话语场域的“视差”中把握“主体间性”,以寻求超越的思路。如此,审美反思眼光的自律和动画创作介入现实的跨界、融合不仅并无矛盾,反而可以相辅相成。
四、结语
艺术的自律与社会责任、图像的崇拜价值与形象价值、自然与文明等从古典时期遗留下来的关系问题在今天并没有消失。这些看似对立的范畴在我们的时代极大加速了批评话语的增殖,也暴露了动画片理论与批评实践中众多无法避免也难以调和的“视差之见”,批评主体含混摇摆,游移于两端。韦尔施对这一现象给出过原因:“只要艺术活动的目的是创造独立的作品,人们就无法超越平行论。如此看来,人们无法进入到一个与现实相包含的艺术状态之中,也无法进入到艺术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之中。其原因是,人们无法同时既保持差异又拆解这一差异。”[23]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范畴中,“自然与文明”对于动画批评来说,更显得尤为关键,这不仅因为关注这个话题的动画作品数量众多,更因为动画片对很大程度处于自然状态中的孩子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形式。超越范畴对立的理论思路有很多,粗浅地说,其要义不过“执其两端而用其中”。这当然不是退缩或逃避,而是提醒我们要时刻对流行的强势话语进行检醒,更重要的是,关注弱势话语与强势话语的境况关系本身。“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道德经》)“‘知雄守雌’实为居于最恰切妥当的地方而对于全面境况的掌握。”[24]在老子看来,有了这种“常德”,才有可能切近婴儿的真朴状态。
——介绍一部你喜欢的动画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