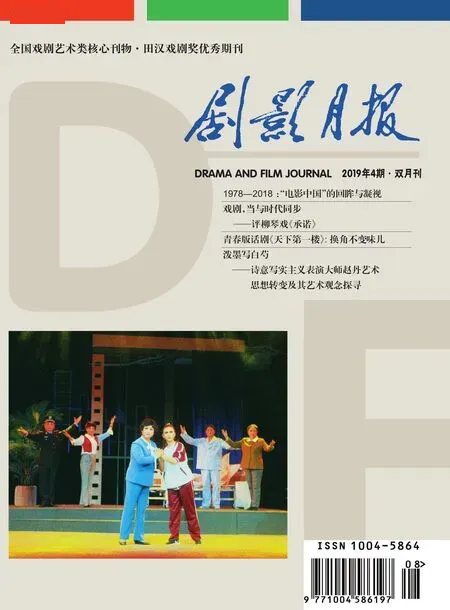历史语境下《半生缘》的文本改编及其文化诉求
《半生缘》由东方电影制作有限公司于1997年出品,该片改编自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由许鞍华执导,黎明、吴倩莲、梅艳芳、葛优主演。该片以19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通过沈世钧和顾曼桢的爱情悲剧,反映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旧上海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也突出了张爱玲小说的一贯主题——说不尽的苍凉故事。影片通过一对有缘无分的恋人所构成的遗憾来展示一个永恒的人生悲剧,伤感的情调贯穿始终,影片中许鞍华融入了她对人生苍凉的提示和理解。
一、生产语境
《半生缘》由香港女性导演许鞍华执导,天山电影制片厂与香港国大娱乐电影有限公司、上海安氏影视传播有限公司三方合作拍摄,于1997年香港回归这一特殊时期上映,这部电影的生产恰如其分地印证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香港电影公司与大陆电影公司的合作,香港导演对于大陆女作家的认可,香港对于自我身份的迫切认同,建构了一个必然又巧合的生产语境。
1.合拍契机
九十年代国产电影面临着尴尬的境遇,各厂之间的生产竞争已很激烈,同时还要应对电视、录相带的冲击和外国影片带来的市场压力。北京电影制片厂与上海电影制片厂早开合拍片先河,但其昂贵的要价使香港电影公司退而求其次寻找价格合适的制片厂进行合作,《大漠紫禁令》的成功使电影人看到了国产电影的新出路,“合拍”一时成为包括天山厂在内的各电影厂行之有效的经营方式之一。
对所有中国电影企业来说,1993年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年。当年1月5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这一被电影行业称之为“三号文件”的基本精神在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企业必须适应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四十年来计划经济下电影的“统购统销”的经营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分配上的不合理。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进口影片仍统一由中影公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司发行);二、电影票价要原则上放开,具体由各地政府掌握。市场经济体制给予本就奄奄一息的电影厂更大的压力,电影厂为谋生路更加坚定合拍片这一经营方式,而《半生缘》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
2.文本选择
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许鞍华选择拍摄张爱玲的作品,自然是源于对她作品的喜爱。“我大约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看她的作品,不是因为她的文章写得好而是我认同她的世界观,觉得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很耐看。她常指出,即使在顺境中人与自己本身或其他人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这是人性此外,我觉得她写的环境、背景与我的出身和看法很相似,我们都活在中西合璧的文化中。”《半生缘》是许鞍华第二次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提起之前的《倾城之恋》,她表示当时对于原著的理解不够,未能把握原著的精髓,失了张爱玲小说的魂,她试图在《半生缘》里弥补这个遗憾,通过影像去表现张爱玲小说中的人性和苍凉。张爱玲的诸多作品中,《半生缘》显得有点不那么张爱玲,原因在于其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无数的巧合与误会交织,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落寞收场,这样的情节,恰好符合了影视改编的条件,选择《半生缘》当然在情理之中。
二、文本改编
在电影改编的过程中,许鞍华尽量还原小说的场景,怀旧的老上海,昏暗的光线,以结婚为目的的女性和苍凉的爱情故事,但要将一部长篇小说缩减成为一百二十分钟左右的影像,势必要对小说中的某些情节进行一些删改,于是在张爱玲的故事里,也多了一些许鞍华对于爱情和人生的理解。
1.主题风格
爱情是张爱玲的小说永恒的主题,但她所言说的爱情并不是极尽梦幻浮于虚空的梦,而是在俗世红尘里为了爱情和婚姻挣扎算计的灵魂。《半生缘》与张爱玲以往的小说是有一些不同的,沈世钧与顾曼桢的爱情在一开始是梦幻的朦胧的,乐观的积极的,是昏暗巷子里的天光,是一片荒芜里的红手套,而电影通过有条不紊的剪辑和光影气氛的营造,将初恋男女的心动与暧昧展现的细致入微。故事的开始有些不一样,但结局却没有什么不同,祝鸿才像是一只丑陋的野兽,将一切撕毁,囚禁,误会,妥协,分别再相见,物是人非,爱情早就枯萎在颠沛流离的路上。电影同样遵循了小说的轨迹,情节在后半部分急转直下,将美好的爱情撕毁给人看,多年之后,沈世钧和顾曼桢再相见,他们都知道,谁也回不去了。影片的叙事从容不迫,画面精雕细琢,力图在这一百二十分钟的世界里刻画出张爱玲笔下三十年的上海的浮世绘。感伤的情调贯穿电影的始终,梦以无可挽回的姿态破碎,是许鞍华对于张爱玲苍凉爱情故事的认同和再书写。
2.叙事情节
对于叙事情节的删减是影片对于原著最大的改编,原著中沈世钧的家庭关系,沈世钧与翠芝的关系,翠芝与叔惠的感情都做了大量的删减,将沈世钧与顾曼桢的爱情作为影片的主线。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不能一概而论,单一的主线更符合影视表现手法,避免剧情过于混乱冗长,从这一角度看,电影的改编无疑是成功的,观众的目光始终聚焦在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发展上,戏剧冲突的核心始终是男女主。但较为遗憾的是,这样的删减同时也去掉了一些张爱玲式婚姻的独特表达。无论是被生活所迫沦为妓女的曼璐,还是独立的新女性曼桢,亦或是旧式大家庭的小姐翠芝,无不被婚姻困扰着,曼璐嫁给祝鸿才被当顾母当做是无上成就和炫耀的资本,曼桢心之所属不是顾母关心的事情,她只张罗着曼桢应该和谁订婚,翠芝则是被当做家族联姻的工具在几个家境优渥的少爷之间挑选未来的丈夫。她们都曾向往着爱情,曼璐对张豫谨,曼桢对沈世钧,翠芝对叔惠,但最终她们的爱情都葬送在婚姻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是聪明且有所保留的,对爱情是一种精打细算的计较,不是飞蛾扑火的追求,她们清楚的知道爱情是不现实的,婚姻才是现实的,她们向往爱情,却也坚强的活在俗世中。影片对于这些情节的删节,减弱了对于张爱玲爱情观的展现,也使得影片某些表达过于生硬,比如删掉了叔惠与翠芝通信的部分,使得叔惠陪曼桢去南京的行为显得莫名其妙,他们这条爱情线的淡化也使得叔惠在沈世钧和曼桢结婚后决定去美国的情节有些站不住脚。沈世钧家里正房与姨太太的争斗是极具张爱玲特色的,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去掉这一部分便使得沈世钧决定留在南京的逻辑有些弱,也使沈世钧这个人在脱离家庭背景后显得有些虚无。
3.人物形象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并不美好,他们都是活在弄堂巷子里艰难生存的小人物,尖酸刻薄、自私懦弱、精于算计这样的性格经常出现在主角身上,她笔下的人都是确确实实活在柴米油盐婚姻嫁娶中,《半生缘》中的人物自然也是这样。叔惠与曼桢是相熟的同事私下叔惠对曼桢却颇有微词,顾母在曼桢被祝鸿才强奸之后居然为了保全声誉让曼桢嫁给他,曼桢为了照顾孩子选择妥协嫁给毁了她一辈子的祝鸿才,沈世钧懦弱自私对曼璐始终芥蒂,这些小说中对于人物缺点毫不掩饰的展现在电影中却几乎寻不到踪迹,导演极力将人物美化,曼桢始终是坚韧的,叔惠无愧于好友的身份,翠芝这个人几乎是模糊的,黎明的形象也将沈世钧的缺点完全掩盖,这样的主人公固然是受观众喜爱的,但却不完全是张爱玲笔下的主人公。影像的表现手法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像文字那样将人物刻画的入木三分,面面俱到,但这并没有影响影片的整体表达。在爱情的包装下主人公虽然被美化,但许鞍华还是极力维持了张爱玲的人物,性格的美化并没有干扰到情节的发展,电影在最大程度还原了原著。
4.时空背景
小说《半生缘》将故事置于三十年代的上海,时间跨度长达十四年,但关于国家和历史环境的表述相当琐碎,仅仅在第十五章提到“八一三抗战开始的时候”,而许鞍华导演对于电影的处理则更加含糊,仅仅是在片头以字幕的形式打出了“上海一九三〇”的字样,电影巧妙的用上海这一特殊地域取代了时间,隔绝了上海以外的大时代。小说在将近结尾部分提到六安沦陷,曼桢的救命恩人被日本人强奸这些对于历史的零碎直射,在电影中完全被清除掉了痕迹,上海彻底悬空于历史之外,成为纯粹的故事发生地,而失去其历史意义。导演这样处理,一方面是为了更容易通过香港政府的审查,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她对张爱玲个人“在大时代面前,个人是渺小的”的人生哲学的尊重。在《倾城之恋》中,香港的沦陷只是为了成全白流苏和范柳原,同样的《半生缘》的上海,也仅仅是为了见证沈世钧和顾曼桢这十四年的浮浮沉沉,情深缘浅。
三、文化诉求
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半生缘》作为张爱玲的小说,由知名香港女性导演许鞍华改编,就其文本和改编固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两人在1997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将香港与大陆联系在一起,这并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有其特殊的文化诉求所在。
1.身份认同
1997年正值香港回归之际,但对于香港的民众来说,却面临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尴尬境地,长期的殖民生活将大陆变成一个完全陌生化的存在,而香港也无法认同殖民宗主国。在政治上给予香港新的身份,却并不能在文化上迅速获得认同,在一片欢呼声中,香港民众的心情却是复杂的,摆脱殖民地身份固然值得欣喜,同时却也陷入了无家可归的焦虑。香港民众迫切需要寻找到一种身份的认同,却又无法立刻认同大陆的所有文化,那么上海便成为一个迂回的选择。从历史语境来看,三十年代的上海是特殊的,内陆地区硝烟弥漫,革命烽火却并未点燃到上海,作为租界,上海依旧是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是中国最西化最安逸的地区。许鞍华曾经提到她和张爱玲的生活环境是相似的,都生活在一个中西合璧的文化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香港和上海是相似的,作为租界和作为殖民地的环境及心境将这两座遥远的城市联系了起来,而张爱玲出生于上海,曾在香港读书,她成为能够连接这两座城市的一个契合点,对她作品的认同和尝试,其实是香港民众对于回归大陆文化的一次试探,从陌生的文化中找寻到一丝认同。从电影角度来说,张爱玲前期所代表的是上海作为电影中心的中国传统电影,后期曾为香港电懋公司编写多个剧本,香港电影人对于大陆可能是陌生的,但对于张爱玲是熟悉的,作为一个合拍片,选择张爱玲的作品进行拍摄,是对于香港和大陆的双重认同,同时也是导演对中国传统电影的初步认同。
2.时代动荡
《半生缘》所讲述的三十年代的故事,历史上中国的三十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适逢日本侵华,中华民族的命运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与不安,这一历史背景又与九十年代的世界形成对照。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产生动摇,香港刚刚摆脱自己的殖民地身份,但对于未来走向却没有任何的方向,30年代的动荡在几十年后重新引起香港的共鸣,《半生缘》的时代背景与九七年的香港实现跨越历史的弥合。然而这种不安又是隐晦的,不可言说的,主流社会都沉浸在香港的回归中国收复失地的欣喜中,这一点点的不安只隐藏在一片欢愉中,被历史的记录者所忽视。如同三十年代的上海,我们对于三十年代历史的书写,是大片大片关于日军侵华,革命根据地革命者的故事,上海租界是游离在主流历史之外的故事,居住在租界的小人物的生存现状自然是被隐去的。张爱玲的故事中生活在大时代被历史所忽视的小人物的命运正是九十年代香港民众的一个对照,《半生缘》的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但她的主人公也可以生存在九十年代的香港。
3.重构历史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历史的纵深感消失,历史终结于八十年代,我们几乎是献祭了所有的传统文化从而迎来了中国的现代化。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将张爱玲捧上神坛,却对鲁迅、郭沫若等人严厉批判,他重写的不是中国现代小说史,而是以西方的眼光在重写中国的历史。那些被主流记录的言说的认同的是他所批判的,而被主流所忽视的批判的抛弃的则是他大肆赞扬的。对于张爱玲作品的重新翻拍,是对张爱玲的一个重新认知,也是对于中国历史的一次新的认知。《半生缘》中关于革命主流历史的部分被不着痕迹的隐去,它所要展现的是一个被忽视的上海的由张爱玲书写的历史。
现如今张爱玲的作品无论是在文学史还是在电影史依旧是争论不休的议题,而在这种争议的背后其实是我们对于传统历史和现代历史认知。我们的历史断裂在八十年代,我们正处在一个对历史和对未来都不能确定的一个虚无的维度,我们应该去用现代文明的眼光审视我们传统的文化,但不应该对过去进行全盘的否定,我们的历史不是用于被西方观看审视解构重写的,我们应当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口,应以现代的也是中国的眼光重新看待历史和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