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克艺术,确实如珍珠串起般华丽

几年前,我正是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以下简称东艺)欣赏了黄英演唱亨德尔的著名咏叹调《让我痛哭吧》。她是位擅长诠释亨德尔作品的歌唱家,在访谈中,她也确认了这一点。为了准备这次的巴洛克专场演出,歌唱家先后赴欧洲和美国,跟随不同的声乐指导学习。通过声乐指导掌握原作意境和韵味,是黄英在歌剧表演中一直所倡导的实践。
● - 张可驹 ○ - 黄英
● 请问巴洛克音乐是从何时开始进入你职业生涯?
○ 其实巴洛克音乐我一直在唱,我很喜欢这些作品。虽然唱的不是特别多,但确实是职业生涯的每个时间段都在唱。亨德尔的《让我痛哭吧》(Lascia Chio Pianga)你上次听过我唱,这次也要唱,但处理可能会不一样。这就是艺无止境。光为这一首咏叹调,我就做了许多研究工作,除了背景资料的翻译和上声乐指导课,还要研究不同的版本。并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考虑装饰音如何运用。2009年,我在比利时皇家歌剧院主演了亨德尔的歌剧《赛魅丽》(Semele)。张洹做导演,他是中国的装置艺术家,韩峰做的服装,他是我的好朋友。当时很轰动,连演九场,持续演出。为此我特别去英国找了声乐指导,至少花了一年时间。剧中有七首大的咏叹调,都是七八分钟的长度,都唱下来了,还有宣叙调,都要排演,花了很多心血。在没有第二组演员的情况下,我坚持到最后一场,前后一共三个月。那是我非常重要的一次经历。当时是克里斯托弗·侯塞(Christophe Rousset)担任指挥,他是克里斯蒂(Willian Christie)的学生。而之前,我还同库普曼合作过。你还别说,我同不少古乐专家都合作了。我和库普曼合作,是与他的巴洛克乐团演出莫扎特的《魔笛》,依照本真的音高,低半度音。我作为一位歌唱家,也要考虑一些转型(注:指对于巴洛克曲目进一步的拓展),不断完善自己的歌唱。目前自己正处在事业巅峰期,同时也是音乐学院的专家教授。在这几年的教学当中,我发现学生们古乐唱得太少了,巴洛克音乐要多唱,莫扎特要多唱,贝利尼、罗西尼、多尼采蒂的艺术歌曲要多唱,意大利歌曲集也要多唱。这次要演唱的《围绕我崇拜的人》(Intorno Allidol Mio),就收录在《意大利歌曲集》当中,五年级之前的学生都要多唱这些歌曲。这次我呈现巴洛克专场,觉得十分荣幸。在自己二十年的歌唱生涯当中,十年前演的是大都会歌剧院的高清电影《魔笛》,那是他们的第一部高清歌剧电影,再往前十年,就是《蝴蝶夫人》。二十年后,转向巴洛克,也就是进入返璞归真的阶段。通过我这样一位歌唱家来普及巴洛克音乐,有一定的影响力,也会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 在你看来,演唱巴洛克作品对于歌唱家而言,是否很必要?看来的确如此。

○ 那当然,是很必要,唱得太少了!在高等音乐学院接受训练的学生尤其需要。在你这样公开发表的访谈平台上,我要公开呼吁一下,为什么前面说巴洛克还有莫扎特都要多唱?这就像造房子,地基都没造好,直接就唱《为艺术,为爱情》等等。这都是经典作品,但技术没有打好,根基就是空的,摇摇欲坠。因为在训练嗓音、技术的同时,就是要唱巴洛克和古典的东西。这也是从语言的风格、味道开始培养,循序渐进。至少我试验了,在之前五年的教学中,几个学生依照这个路子出来,全是对的。技术扎扎实实,你才能在不断完善技术的同时,继续去唱适合你的作品。像《为艺术,为爱情》,唱这些作品是一辈子的事,以后还有很多机会。但“地基”不打好,真是很糟糕,以后就很局限。
● 通常人们所熟悉的意大利歌剧,都是莫扎特和他之后的作品,然后是威尔第、普契尼他们。而你这次要唱的,恰恰是莫扎特之前的意大利歌剧。
○ 就直观的体会来说,关于巴洛克时期的歌剧,首先巴洛克这个词的原意是“不规则的珍珠”。虽然“不规则”是关键,这个在此不展开,但珍珠也是一个有意思的比喻。从音乐、绘画、建筑当中,都可以窥见其特点。这样的“珍珠”串在一起,豪华、铺张(Extravagant),我在米兰的时候欣赏巴洛克时期的绘画,同样感受到这种特质。并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种直入人心。这个我感到和演释莫扎特也有一定区别。莫扎特是技术非常高,精神境界也很高,难度真的非常高。但有时技术非常高的时候,情感方面并非那种热诚、狂热(Passionate),而是处于一种精神至上的状态之中,这和作曲家本人的精神境界有关。而巴洛克却是特别的直指人心,就像《让我痛哭吧》,电影還拍过《绝代妖姬》(又译《法里内利》)。电影中结合了历史上真实的故事,以及进行夸张的情节。当时,剧中人物身处一段苦难的历史,带给我的启发很大。电影中,他唱这一段的结尾,为何要(用高音)翻上去?其实也是为了表现一种痛苦的呼喊。我们现在唱的时候未必需要翻上去,你根据作品,也根据整场曲目效果来安排。总之就我的理解,巴洛克歌剧的特点,就是那种直入人心的喜怒哀乐。痛苦、悲伤、欢乐,对我来说,巴洛克的音乐,尤其是亨德尔的作品,是非常能够直接连接人心,表达情感的。还有那些宣叙调也是如此,就像“Se pieta”前面的宣叙调,讲清楚自己的状况,表现四面楚歌。咏叹调中,A—B—A的三段,第三段(A)是一定要加装饰音的,现在我还在考虑很多唱段应该怎么加。
● 现在人们提到维瓦尔第,通常都是关于他的协奏曲。但事实上,这位“红发神父”一生中有很多的时间都是围绕着声乐的,无论创作,还是训练合唱团及独唱演员。你通常表现维瓦尔第是以哪些作品为主?歌剧还是圣乐较多?
○ 我先前唱他的作品倒不太多,《意大利歌曲集》中有几首是他的。其实我的声音状况是适合唱圣乐作品的,但我还是唱莫扎特的圣乐较多。莫扎特考验技术,而我的技术也不错,因此很幸运地,在美国学习的时候,老师让我唱了一些莫扎特的圣乐。关于维瓦尔第,以这次的演出为契机,我想发掘他更多的声乐作品,自己唱,也教学生唱,我也买了他的歌曲集来研究。
● 目前对一位抒情花腔女高音来说,演唱莫扎特或罗西尼的作品,几乎被视为天经地义,而连唱半场亨德尔,就多少带有专家之演的意味。你之前就曾提到,亨德尔是你擅长的,也是贴近你内心的曲目。那么能否请你简单地谈谈他的音乐?如果说莫扎特是古典时期代表性的歌剧大师,那么巴洛克时期的代表则毫无疑问就是亨德尔。
○ 是的,毫无疑问就是亨德尔,虽然在英语歌剧方面,珀赛尔的歌剧也有其分量。我确实擅长亨德尔,也感到他刻画每一位人物和每一位人物的性格,才华确实太高了,既直至人心,又有激情,唱起来也很舒服。我发现唱他的作品和演出其他伟大作曲家的作品之间,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感到自己非常容易投入到角色当中,投入到该作的音乐风格当中。这可能也是因为我和这位作曲家有一种内在的共鸣。
● 一位擅长亨德尔的女高音需要具备哪些特点?
○ 和唱莫扎特一样,音色要好,技术要好,这是基础的。语言要好,这在宣叙调的处理中尤为需要,风格的把握也要好。总之就是技术要完善,风格要纯正,离开这些,一切都无从谈起。你看,我反复在强调韵味的发掘,因为太重要了。就像莫扎特的作品,女高音们都在唱,但唱得好非常稀有,就是取决于这一点。《纽约时报》将我称为莫扎特的“最佳演绎者之一”,这不是我自己表扬自己,是那位乐评人听出了音色和韵味之中的差别。就像为了准备这次的亨德尔,我在2019年8月去了欧洲,之后9月和10月又去了纽约,就是为了和声乐指导上课。这也是为了获得灵感,那些专家所带给你的灵感。包括第三段(A)里面的装饰音,如何从他们那里获得灵感,然后再通过你的理解、你的风格来展现。
● 由于这次曲目的独特性,你与声乐指导的学习也让我更为好奇。相对于舒伯特、舒曼的歌曲,或是罗西尼、威尔第的歌剧,亨德尔和维瓦尔第的很多作品,其实都有过一个演释的断代时期。它们在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早期演得极少。那么,声乐指导所讲授的演释风格等等,是否大多都建立在本真的基础上?
○ 当然了。还是以装饰音为例,这就像爵士乐中的即兴演奏,必须在一个风格的规则之内来运用那样的即兴,有些人加了,你就觉得不好听,感觉很怪。这次我去和声乐指导学,除了他们对于作品、对于历史背景的理解之外,主要就是在第三段(A)里面加装饰音的时候,他们给你一个概念。他们有些是钢琴专业的,有些在作曲方面有才能和灵感。在装饰音方面,他们给概念,某些做法我感觉好,就化入到自己的演释之中。他们对此都有不同的分析和解释,根据对位法结构来设计装饰音,要给你分析乐队的部分,音程关系不能打乱等等。但还是他们给你灵感,每个人讲得也不一样,我还要总结一下。就我个人来说,倾向于不要用得太复杂,然后写下我自己所用的版本。最好写下来,也要有感觉地加,是要直入人心的。这样传递给观众才会有真正的说服力,否则连我自己都不确信,只是综合几位声乐指导的意见,结果也是不可能有说服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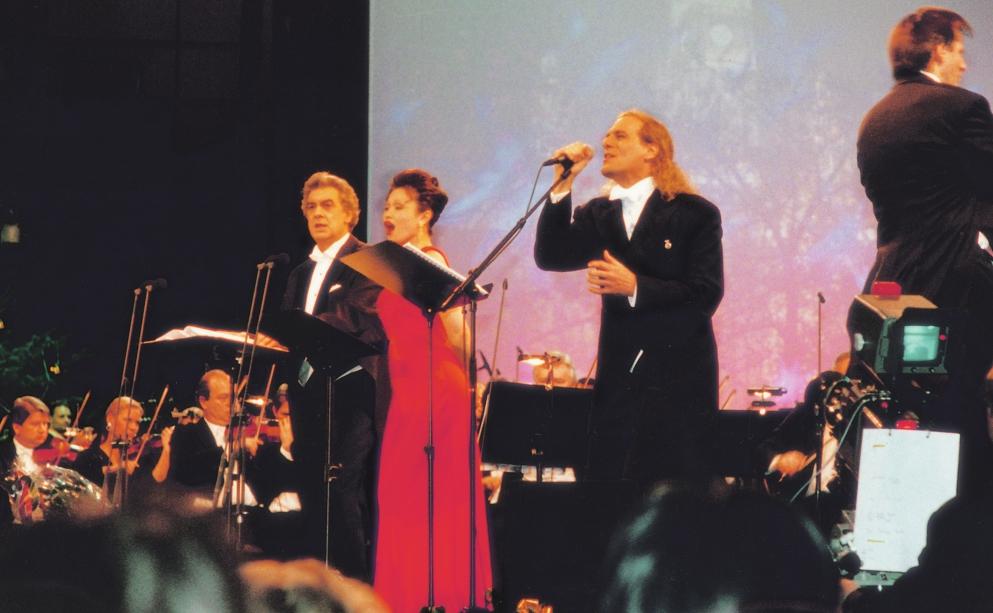
● 克里斯蒂灌录亨德尔《弥赛亚》的唱片时,合唱团一共才三十多人,居然請了十六位英语读音方面的指导。
○ 这个是语言指导(Diction Coach)。亨德尔是德国人,长期生活在英国,又在意大利活动。他写意大利语的歌剧,《弥赛亚》又是英语清唱剧,其中都有很多的讲究。就以唱《弥赛亚》为例,唱的时候当然是用英式英语,不会是美式。但有些美国人唱的时候,也会选择一种折中的发音,被称为“Mid Atlantic”,因为语言指导也和我抠过这些,所以我清楚。灌录唱片很重要,克里斯蒂这样的大家,当然很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对于这个例子,我要说:太好了,就应该这样,因为太重要了,无论歌剧,还是清唱剧,都是用语言唱出来。《弥赛亚》是用英语唱的,还有意大利语的、德语的作品。演出德语的作品,你就要找德语的语言指导,这是进行专业的表演之前最最重要的。我们这边需要加强。说回你提到的克里斯蒂灌录《弥赛亚》的故事,这种情况说明这位指挥家太严谨了,他想要的是什么,他一定非常清楚。其实也不仅限于古典音乐界,好莱坞要找一个好的美国演员来演一个英国人,也需要语言指导来给他指导啊。当然他们的语言指导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一些美声技术的方面,理解内容之后,如何在歌唱中表达。所以说,成为一个好的歌剧演员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成就的,绝对不是声音好一点就可以唱了。如果你不善于学习,一样被淘汰。单纯地考进来,不知道如何学习音乐,不能把握好语言,还是干不了这一行。
● 指挥巨匠卡尔·伯姆在二战前崛起于德累斯顿,战后数十年中成为维也纳和拜罗伊斯的灵魂人物,是最有影响力的德奥歌剧专家。二战后他到大都会指挥,被那里歌手的语言水平所震惊,感到美国本土培养的歌唱家唱念也是如此纯正,欧洲真的不能再以文化落后的新大陆的视角看待美国歌剧教学。他在六十年代出版的自传中特别记下了当时的惊讶之情。
○ 没错,美国歌剧教学的好处在于教育体系完备。所以我的学生毕业之前,我要提醒他们,你要再完善学院派教育的话,去哪里呢?美国,主要是在纽约。当然柯蒂斯也好,但那里主要是器乐更好。其他一些学校也是,都要看具体的老师。但综合来看,还是直接去纽约,因为你学完了之后,还是要进军纽约的,还不如直接到那里。西边的旧金山歌剧院,那边的青年艺术家计划也是好的,没问题。而另外的选择是哪里呢?就是德奥。你在美国学到完整、系统的技术之后,也要继续到欧洲“泡”。这是我为青年音乐家做的发展规划,我不仅是教声乐,也给他们一些指点。所以在我班上的学生都走了正道,我教给他们适当的审美理念,也教他们选择适当的曲目,不要乱唱。
我在美国接受语言指导,歌词某些地方念得很重,加重某些辅音等等。而我到了欧洲,到了意大利,意大利人会跟我说,你不用这么念,可以轻一点。这时我就理解了,原先在美国学习欧洲的东西特别认真,因此在某些地方做了加重。但加重总比不加重好,就像在舞台上表演太夸张了,导演会跟你讲,要收一点,可如果没有内容就不行。学生一毕业就到意大利很危险,因为意大利的教育每况愈下,学校没有好老师,好老师都在校外,都是实战的歌唱家在教。教得好,教不好,看个别的情况,所以也麻烦。
继续深造就是德奥和美国这两个方向。去德国学习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太贵。茱莉亚音乐学院是有特别才能的人才能获得全免奖学金。而在波士顿音乐学院、曼尼斯音乐学院,奖学金极少,学费是三万九千美元一年,加上生活费,差不多要四五十万人民币一年。家长有能力的去美国,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就到德国,因为学费是免的,只要支付生活费用。
● 这次你准备演出巴洛克专场,又要和英国协奏团与毕克特合作。他们是目前最重要的古乐组合之一,你先前同他们合作过吗?
○ 这是第一次,我很仰慕这位指挥。我作为一位擅长这些作品的歌唱家,这次和这样一个顶尖的古乐组合携手,一同演出这些巴洛克曲目,希望能带给听众全新的感受。表现巴洛克音乐的风格是一门独特的艺术,这也是我多年在学习、在研究的一种风格。我不仅非常热爱这种艺术,也对其深有内在的感受。这几年在欧洲演出、工作之余,我也欣赏了许多巴洛克的建筑、绘画,对那个时代有了更丰富的体验。因为艺术都是相通的,我也一直告诉学生,不仅要接触其他门类的艺术,其他的演奏也要去听。真正杰出的演奏,无论钢琴还是小提琴,或者长笛,都是在“歌唱”的。歌唱家要唱好作品,需要向杰出的演奏家靠拢,学习那种技术上的精准。要多唱室内乐作品(注:艺术歌曲有时被归入室内乐的范围),多唱莫扎特、巴洛克的音乐,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由此打下扎实的基础,才能成为一位“完整的歌唱家”。
——以辉煌大圆舞曲为例
——亨德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