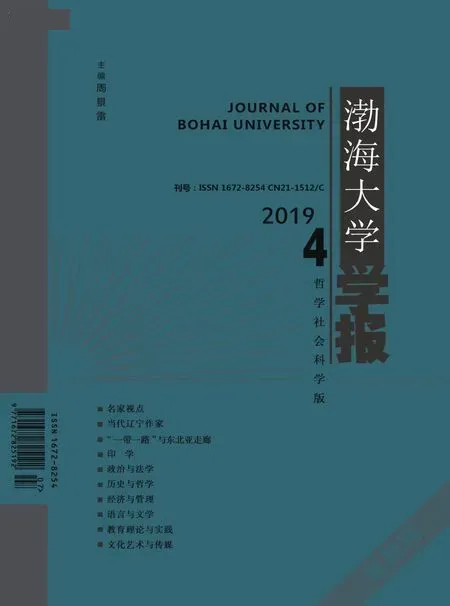论滕贞甫《刀兵过》的文化意义
周景雷 杨 雪(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叙说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和风云激荡的社会变迁,是当下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个比较热门的选题。特别是从文化中心出发向边疆漫延的创作路径,不断扩大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空间,丰富了长篇小说的审美内涵。比如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到阿来的《尘埃落定》,从范稳的《水乳大地》到贾平凹的《老生》,内地和边疆的历史书写相互激荡、彼此呼应,演绎了中华大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凌云壮志和慷慨悲歌。这一历史时段之所以成为文学书写的富矿,不仅在于社会变迁的剧烈和全球一体化的相互冲撞,也不仅在于变迁和冲撞过程中的自我形象塑造和有关民族国家的想象,而且更在于一种文化交融和改造上的自我反思。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先后经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资产阶级改良以及新文化运动,终于从器物技术层面经政治体制层面上升到文化养成层面,为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规定了形制。但总结从那时到现在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显然在这样一个进程中,上述所提及的各个历史阶段并不是线性更替和相互取代,而是呈现了一个相互交叉和冲突的状态,甚至在很多时候,这些阶段性特征是叠加在一起的,尤其是在文化观念、民风习俗等诸多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因此,有关这方面的历史叙说,不管是原始愚昧,还是文明进步最终都会归结到文化层面来进行理解和阐释。
有关东北地区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书写,近些年来也有重要收获。比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一位老萨满绵长而哀婉的叙述,为鄂温克民族文化流传和变迁唱起了挽歌。这是对现代化与地方化之间关系的透视和考量,在文化怀旧层面建立起了对现代性的认知。刘庆的《唇典》也是最近几年描摹东北历史文化的重要收获。这部小说同样从萨满视角出发,通过大气磅礴的叙述再现了东北地区百余年来的动荡史、发展史和建设史,小说的最终指向仍是文化性的反思。但从几十年来中国整个的历史文化叙事角度而言,东北地区有关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叙事还相对薄弱,特别是在过去的叙写中,注重了边疆和少数民族文化,注重了民间视角和区域独特性,却多少忽略了文化的整体性、交融性,以及在诸种文化并存发展过程中如何通过濡化方式而实现的地方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读到了滕贞甫的最新长篇《刀兵过》。
一、《刀兵过》与地域文化
《刀兵过》以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为背景,在一个社会动荡、文化冲撞的环境中,通过文化和刀兵之间的对抗,描述了辽河湿地芦苇深处的小村庄九里的生存记忆和发展传奇,呈现了底层百姓的生存智慧,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深刻挖掘了中华传统主流文化在东北地域的传播和发展历程,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东北文化的生成史。东北地处偏远,历来为荒寒之地,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因此少数民族文化比较发达。但它又不是与世隔绝之地,千百年来,流民迁徙和官儒流放不断为其注入中原文化和中华主流文化,因此这使东北的文化构成比较复杂。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一方面因展示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特色的需要,大多数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对萨满文化和匪性文化的青睐,而忽略了其他文化的存在和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现代文学诞生以来所形成的文学传统,在对东北文化的挖掘上也并没有将更加广阔的视角放置在以中原地域为中心的中华主流传统文化上,因此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展示。比如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萧军、萧红的创作尽管没有刻意去展示东北文化的特质和内涵,但这些创作在不经意间为东北地域进行了旷达、浑厚和粗蛮、愚昧两极性的文化塑形,这多少影响了人们通过文学作品对东北文化的整体认知。而《刀兵过》却在另外一个视角上为我们弥补了上述不足。主人公王克笙祖上居于安徽,诗书传家,行医救世。因裹于战乱而被迫隐姓埋名,流居天津,创办酪奴堂。到了王克笙一代,因不满足眼前安逸和对远方的向往,王克笙追随茶商师傅远赴东北黑龙江。到黑龙江后,因其志未遂,复又南下至辽河湿地苇荡深处创办了新村九里,于是在此将儒释道主流文化发扬光大。虽历经多次刀兵,但文化之魂始终未散。在这样一个传播路径中,有两个问题是值得玩味的。
一是地理空间问题。从安徽到天津再到黑龙江,再到人烟稀少的湿地芦苇荡,王克笙凭一己之力,筚路蓝缕,终有大成的过程,还原了中华主流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向外播散的过程,也是东北地域文化逐渐向主流文化融合的过程。安徽、天津、黑龙江、辽河湿地的荒芜之处,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地理空间,它更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节点和以此节点为中心的文化上的再次转承。比如,在小说中作者刻意安排了两个细节。一个细节是,王克笙之所以追随师傅远赴黑龙江卜奎,乃是受了流徙到黑龙江的天津知府张光藻的启发。应该说在这里朝廷官员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主流文化,也代表了主流文化向关外播散时的载体和方式。另一个细节是王克笙在黑龙江的一座寺庙中通过萨满与道姑合作的扶乩之举。通过扶乩,王克笙获得了南下辽河湿地的箴言,并依此箴言建立了文化中心九里。这个细节不仅强调了北方文化的融合性,也更是强调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刀兵过》所描绘的历史就不仅仅是一段文化对抗武力的历史,也不仅仅是东北人民抵抗外来入侵的历史,它本身充满了人类学色彩,是今天我们认识东北文化、了解东北日常生活的重要文本。
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文学是时代的先声,应该最先感知时代的变化并通过文化的方式予以确认。在过去有关东北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中,现代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东北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互动也没有得到更深入的研究。比如,我们在描述和研究新文化运动在东北区域的传播和影响时,到现在为止还缺乏足够的文学文本的支持。在刘庆的《唇典》中,他是通过照相机和火车这两个意象来表征现代化对一个封闭古老的小城镇的介入,乌拉雅族人的白瓦镇由此被裹挟进了现代化的进程。但现代性本身所具有诸种特征以及对世俗生活的干预和影响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才在白瓦镇显现出来。现代性的这一迟滞性表现是不是回答了东北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此类问题在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也同样存在。但在《刀兵过》中却明确地回答了一些问题,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现代性问题。这里同样有两个情节值得研究。一个情节是,九里的创始元老姚大下巴的二儿子姚远在北京大学读书,经历过五四运动后回到九里养病。姚远是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文化的化身。但他回乡后,既拒绝了王克笙用传统医学为其治病的提议,又试图颠覆代表着传统文化主脉与精神的三圣祠,从肉体到精神层面彻底阻绝传统文化。最后我们看到,姚远不幸离世,新文化、新观念也未在苇荡深处生根发芽。在我看来,姚远的失败既不在于九里对新文化的拒绝,也不在于新文化对九里没有吸引力,而是姚远所代表的新文化对传统文化没有足够的尊重和包容。另一个情节是,九里姚家长子姚松小时候到奉天读书,后来与日本人、俄国人经商,再后来就移居日本娶妻生子。1931年时突然回家乡欲与日本人一起开办造纸厂,后来遭到抵制未能完成。造纸厂是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但在日本入侵中国前夜的当口,这一所谓的工业文明自然带有了掠夺的意味。作者用了两章的篇幅来叙述上述情节,显然不仅仅是要表达文化与刀兵的对抗,还是表达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作者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当然这种反思中显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之魂的深沉的敬意。这也使我们相信,只要文化精神不散,就会永远传播开来。
二、《刀兵过》与文化自信
《刀兵过》所要极力展现的是文化和武力之间的对抗且最终以文化的胜利而点题。小说中的弹丸之地九里在数十年时间中,有数次刀兵经过,但每一次过刀兵,九里人都以自身的文化智慧和气度度过危机,化险为夷。小说立足于九里这样一个极小的视野,却俯瞰了整个中国的近代史。几十年间数次过刀兵的过程也正是中国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小说中所写到的九里第一次过刀兵是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最后一次过刀兵则是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但在这数次过刀兵的过程中,每一次危机的化解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的不同呈现。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刀兵经过,都会在传统文化中找寻到不同的处理方式。作者这样处理,意在说明中华文化的强大的包容力、凝聚力和化解万物的冲击力。比如第一次刀兵经过,清军抗击倭寇,出现了黄开、老地羊两位英雄。九里人将他们埋葬在万柳塘并为他们树碑立传,传示后人,这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中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的特质。1931年,日本人占领东北,九里未能置身事外。面对倭寇入侵,九里人制订《御倭九戒》,与日本人斗智斗勇并最终坚持到日本人的投降。这仍是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的延续。不论是土匪的到来还是义和团拳民经过,九里人都会因对文化的坚守而化解危机。作者这样的认知和处理方式,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也表达了对文化自身所拥有的力量的高度瞩望。
从历史过程上看,中华文化优秀品质的形成和凝练始终是与历史曲折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几千年的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华文化的发展史,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中华文化的优秀品质不仅经受了考验,而且还在这些考验中不断生发出新的内涵。比如,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虽然统治者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但以儒释道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仍然构成他们安邦立国的柱石。不仅如此,他们所带来的游牧文化也在建章立制和日常生活中不断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拓宽了原有文化的视野。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历史感的民族,这种特征不仅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也更多地表现在普通民众身上。正是因为存在了这种历史感,我们才能“将自己的历史内化,从而使其成为发展的动力。”[1]在《刀兵过》中,正是这种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合力才能使他们在一次次过刀兵的过程中经受住了考验。王克笙在荒芜的九里土地上建立三圣祠,以儒释道三圣为旗帜,刻意以物的存在形式保存文化记忆,至王鸣鹤时期仍坚守不辍,继续强化这种记忆。这些不仅反映了文化传承过程中某些规律性的内容,也有意无意地申明了在历史转折时期,文化一旦深入到我们的记忆当中便会为制胜提供智慧和力量。
从现实层面而言,《刀兵过》的文化主题也为我们当下确立文化自信提供了历史发展依据。近代以来,关于文化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讼不已的话题,特别是在进入市场经济后,我们在很多层面出现了伦理失范的现象。在那些失范的现象中,既丧失了道德基础,更无从谈起核心价值理念问题,很多人以普遍的人性和普世价值相标榜,或者整体性地或者零打碎敲式的围攻起了传统文化。归根到底,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就是丧失了文化自信的表现。《刀兵过》中以王氏父子为核心会同蒲娘、塔溪道姑师徒及广大民众,以文化抗拒武力,坚拒刀兵,其中所阐释的文化理念是不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姑且不论,但其柔中带刚的智慧、从容凛然的正义和舍我其谁的坚定为凝练和提振我们的文化自信提供了典范和楷模。
三、《刀兵过》与乡贤文化
倡导乡贤文化是《刀兵过》另外一个重要主题。乡贤这个起源于东汉的称谓在过去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们稳定乡村、守护道德、规范伦理、凝聚人心,在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以此为核心所形成的乡贤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贤就是中国文化滋养出来的人,是本土本乡因德行而被本地民众所尊重的贤达之人,而乡贤文化就是这一地域历代圣贤积淀下来的文化形态,它影响和激励着民众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追求,从而引领社会,造福社会,维持社会和谐。”[2]“传统社会的乡贤不仅是道德模范、价值观的引导者,同时他们也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传统社会中的乡村,因为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并不太重视法律和契约的作用,而是更加看重有威望的乡贤对于社会公正的维护。”[3]可见,无论是从文化意义还是从社会学意义上,乡贤都是一种包含了价值性和道德性的存在。乡贤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长篇叙事中并不鲜见,尤其是在最近几十年的长篇小说写作中,几乎可以形成序列。不过,认真研究起来就会发现在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乡贤内涵界定和表现形式并不相同。比如张炜的《古船》、李佩甫的《羊的门》、赵德发的《君子梦》、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关仁山的《日头》以及贾平凹的有关创作,这些作品中乡贤大都有所变形,没有完全回归到传统意义的乡贤文化上,况且这些作品似乎也并没有专此立意。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最具乡贤文化色彩的作品当属陈忠实的《白鹿原》。以“仁义白鹿村”为线索的乡贤文化始终为那个正在破裂的乡村社会做最后的粘合努力。这种乡贤文化既为乡村个体存在提供道德伦理上的规约,同时更为乡村的公共事务提供道义支撑。今天我们从文化层面来理解《白鹿原》,这种对乡贤文化的精细描述应该是最为重要的收获。
长篇小说《刀兵过》精心刻画了王克笙、塔溪道姑、蒲娘和王鸣鹤等众多人物形象。作者尤其为王克笙、王鸣鹤父子设定了多重而确定的身份,即乡绅、村医和塾师,每一种身份都是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九里,有《九里村约》以抚百姓示仪轨,有《酪奴堂纪略》以记村史,有《彰善》《记过》劝善黜恶,有《御倭九戒》表民族大义,更有万柳塘彰英烈传正义。所有这些内容既是乡贤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国传统乡贤文化的精神体现。因此,为了完成这一主题,作者无论是从结构安排上,还是情节推进上,无论是从叙事空间的建构上,还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都显现出了鲜明的写作意图。首先,作者把故事发生置于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上,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转折将最终无疑落实在文化所面临的挑战上。在这种局势中,既有传统文化,又有新文化,既有传统主流文化又有区域地方性文化,既有本土文化又有外来文化。多种文化交织激荡,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带来秩序和伦理的失范,因此乡贤文化便会呼之欲出。其次,为了凸显乡贤文化的意义,作者刻意突显了刀兵(战争)的暴烈和频仍以及普通民众在刀兵面前的无措和无奈,深度反思了战争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小说中正面描写的大大小小的“刀兵过”有七八次之多,大到民族战争,小到地方土匪劫掠。从表面上看,每一次过刀兵都可能带来物质的和肉体的乃至生命的伤害,而其实考验的却是智慧、凝聚力和道义观、价值观,这就必然上升到文化层面。没有一种强力韧性的伦理维系,所谓的道义和价值便会随着物质和肉体的丧失而分裂,因此乡贤文化的存在就显得迫切而意义重大。再次,小说虽然名为《刀兵过》,而且也确实主要通过文化与刀兵之间的对抗来彰显传统优秀文化的力量,但显然作者也并不仅仅将之局限在两者之间的角力上,而是将之延伸至底层民众生活秩序的维系上。九里小村从最初的三五户人家发展到后来的三十八户,这些人均是从外地迁居而来,不同的来处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伦理标准。在小说中,这些普通民众杂处共居,不管是否有刀兵过往都能安然有序、同力相协,全赖有王氏父子这样的乡贤存在,也全赖在九里建村之时所确定和逐渐丰富延伸的乡贤文化的存在。因此,可以说,乡贤、乡贤文化及附着在其中的道德规范成了维系中国乡村结构稳定、生活和谐的重要的力量。
综上所述,《刀兵过》的语言内敛、洁净,对辽南的地方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运用精准、形象,叙述上充满了理想主义激情。作者不仅能深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真髓、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纹理,更主要的是通过他的叙事和渗透在叙事中的关于文化问题的思考,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和治理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