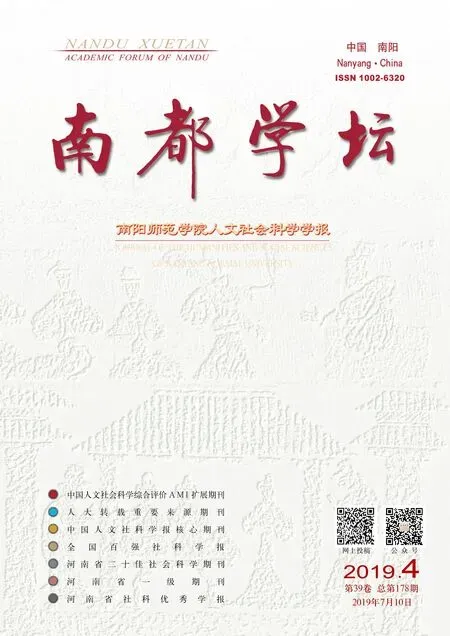汉代“诣阙讼冤”研究
涂 盛 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阙,门观。《周礼》称之为“象魏”。《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1]1195郑司农云:“象魏,阙也。”[1]1396既然万民来“观治象”,免不了将自己或者他人的冤案、冤情在“象魏”处诉说,由相关负责官吏转呈至最高统治者。《水经注·谷水注》亦云:“阙者,上有所失,下得书之于阙,所以求论誉于人,故谓之阙矣。”[2]往往上官之失,可能造成吏民之冤情、冤案,所以“阙者”实际上是吏民将其冤情、冤案向上官表达的一种途径。
西汉人之“阙”,指未央宫。“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颜师古注曰:未央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谒北阙。”[3]64故西汉时所诣之阙为“北阙”。
东汉之“阙”与西汉之“阙”有所不同,西汉都长安,东汉都洛阳,东汉之阙为“鸿都门”。安帝之废太子为济阴王,大臣来历邀结众臣进谏劝阻,“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帝与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诏胁群臣……乃各稍自引起,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4]591。先言俱诣“鸿都门”,后言“历独守阙”,可见,东汉人之所诣之阙为“鸿都门”。
诣阙,指百官吏民赴君主宫门办事或者上章奏。“诣阙讼冤”,指由于司法制度、吏治、政治斗争等原因造成冤案或冤情,受冤人本人、亲属、朋友、下属、治下之民(以下简称为治民)、学生甚至同情受冤人的其他无关人士远赴京城君主宫门,力求将冤情、冤案申诉至最高统治者,以求其能够平反冤案或明察冤情;在某些情况下,讼冤人有可能要求最高统治者对造成冤案、冤情的相关责任人做出处置。
另外,还要对四个名词进行定义。受冤人,指遭受冤情、冤案之人。讼冤人,指为受冤人诣阙讼冤之人,讼冤人既可讼己之冤,亦可讼他人之冤。冤案指受冤人遭受不当刑事处罚之案件。汉代的刑罚有死刑(枭首、腰斩、弃市)、徒刑、笞刑、徒边、禁锢(终生不得为官)、赎刑。冤情,指受冤人虽未涉刑事处罚,但是因为遭受种种不公平、不公正待遇而受委屈。如细民无端被官吏加税赋、官吏因得罪上官而被降级或罢免、本应升迁而因故停滞、政治斗争被罢黜;等等。
目前,尚没有单独研究汉代“诣阙讼冤”的著作或文章,但与其相关的文章有几篇,赵光怀《“告御状”:汉代诣阙上诉制度》认为,由于法律条文的疏漏、以经义断案、司法制度的严重缺陷,导致诣阙上诉源源不断,但该文对于告御状的实体、程序等问题皆未涉及。张积《汉代法制杂考》认为,诣阙上书是汉代提起诉讼的一种方式,案件的处理方式有“覆案”“录囚”,其中录囚有皇帝录囚、郡守录囚、刺史录囚,但该文对于诣阙上书的产生、主体、受理机构、局限性均未研究。李胜渝在《汉唐时期直诉制度探析》中指出,直诉制度是司法程序中的一种特殊制度,是对常规司法程序的一个补充,由最高统治者裁决。该文对于直诉案件的产生与局限性尚未阐述,对于直诉制度的实体和程序问题论述尚有一定疏漏。刘林凤《论公车府职能演变及唐代诣阙上书的类型》认为:汉代至唐,公车府基本一直存在,职能也无明显变化,公车府主要负责处理诣阙所上之书。该文主要从唐代的制度和事例来研究直诉制度,所涉及汉代的制度和事例不多,仅可作为本文的参考。
综上所述,以上文章所称“诣阙上诉”“诣阙上书”“诣阙鸣冤”“直诉制度”尚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仅从司法程序来研究,实际上“诣阙讼冤”不但涉及司法,往往还涉及行政,此在本文中将有所论述。
一、“诣阙讼冤”的历史渊源
原始时代存在一定程度的军事民主,即氏族成员对氏族首领存有意见可向氏族首领提出。原始时期提意见的形式有如下记载:
《管子·桓公问》:“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5]1047
《三国志·魏文帝纪》载:“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6]
《吕氏春秋·自知》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7]
其中,“明台”“衢室”是采纳氏族成员意见的场所,意见自然包括氏族成员的冤情、冤案。氏族成员可通过“明台”“衢室”向氏族首领反映冤案、冤情。“诽谤之木”指氏族成员可将冤情、冤案写在木头上,既可让氏族其他成员探讨,也可让氏族首领看到。“欲谏之鼓”指氏族成员可以以击鼓的方式,向氏族首领反映冤情、冤案。
无论是“明台”“衢室”“欲谏之鼓”,还是“诽谤之木”,我们可知在原始部落时代,部落成员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将自己或者他人的冤情、冤案向氏族首领反映,以求得到解决。此种形式,可成为后世“诣阙讼冤”的雏形。
周朝有路鼓和肺石制度。《周礼·夏官·大仆》载:“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邃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郑玄注:御仆、御庶子,直事鼓所者。”[8]2499《周礼·秋官·大司寇》载:“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8]2754可见周朝,对于贫苦而告状无门者,可以击路鼓,达于“御仆与御庶子”,由其转呈于周王;或者“立于肺石三日”,由“士”听取其辞,然后转呈于周王。实际上路鼓和肺石制度已经很接近汉代的“诣阙讼冤”制度。
春秋战国时,齐国有“啧室”,可让讼冤人通过“啧室之议”的形式,将冤情、冤案反映给齐侯。“名曰啧室之议,《注》谓议论者言语讙啧。”[5]1048齐威王下令求谏,并下令分三个等级进谏,“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9]。在此种宽松言谏的氛围下,讼冤人可以通过“面刺”“上书”“谤讥”的形式将冤情、冤案送达于齐威王处。郑国子产反对拆毁议论时政的乡校,“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10]乡校为时人议论执政的地方,讼冤人亦可以在此处将冤情、冤案诉说于相关官员,由其转呈执政。无论是“啧室之议”“下令求谏”,还是“不毁乡校”,实际上都为讼冤人提供了表达冤情、冤案的机会,从而希望得到平反。演变到汉代“诣阙讼冤”成为冤情、冤案表达及得到平反的一种机制。
二、汉代“诣阙讼冤”产生的背景因素
汉代“诸阙讼冤”的产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法律制度设计之问题、君主专制制度本身、黑暗的政治。这三个原因导致汉代必然出现大量的冤情、冤案,推而广之,不仅汉代如此,后世封建王朝亦如此。
(一)汉代法律制度设计之问题,必然产生大量冤假错案
汉代法律制度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法律制度的演化进程导致法律条文逐步趋于繁苛,条文之间互相矛盾,百姓摇手触禁,长官断案不知所从。“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3]1103“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3]1103即使吏治清明,中央地方官吏皆奉职守法,芜杂的法律也让官吏无法公正断案,更何况封建时代吏治清明时少、浑浊时多,官吏多贪残诛求,利用法律之芜杂,上下其手,以权谋私,造成无数人间冤案、冤情。“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3]1101另一方面,汉代以经义断案。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倡以春秋决狱,并著《春秋决狱》一书,实行所谓“以心定罪”,“本其事而原其志。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11]。主要考察犯罪分子主观动机是否符合儒家“忠”“孝”精神来定罪,而往往忽视犯罪的客观事实,因主观动机很难客观评估,而为酷吏肆意滥施刑罚打开方便之门。汉代法律制度的上述两个特点,导致冤情、冤案必不可免,甚至随处皆是。
(二)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产生冤案、冤情的渊源
汉代君主掌握国家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军事权,以及对群臣吏民生杀予夺的权力。在施政过程当中,并不一定很有理性,往往因为个人的喜怒、爱好、周围人的影响(如宦官、后宫、幸臣等),很多时候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和决策。即使各朝有所谓的法典,皇帝也是可以突破的。杜周“专以人主意指为狱”,认为:“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3]2659君主专制制度本身是冤案、冤情产生的渊源,无论是治世抑或乱世皆如此,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区别。
即使是开国之君,为巩固政权,确保“万世一系”,对功臣要么大肆杀戮,要么防范高搁,对于异动势力更是强烈镇压,为维护统治秩序肆意瓜连蔓引,很多无辜吏民受其牵连,造成人间无数冤情、冤案。汉高祖时,异姓王被诛杀,功臣被猜忌。如韩信、彭越被杀,黥布被迫谋反然后被诛杀;萧何为民请命却被高祖无端系狱;张良深知高祖猜忌的个性,托于神仙,遗落世间之事,以打消刘邦的猜忌。“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阳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12]363
汉武帝时尚处治世,但却重用酷吏,酷吏以鹰击为治,不用法律,大兴刑狱,大肆株连,致使“盗贼”兴起。“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13]3151此本为武帝治国之失策,武帝却不予纠正,不但不采取措施予以安抚,反而采用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强烈镇压,“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3]3151。然而“盗贼”多如牛毛,诛不胜诛,不为大赦以安之,而为“沈命”之酷法进行更暴力的处置,“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3]3662-3663。不但小民产生大量的冤情、冤案,甚至连政府官吏也产生不少的冤情、冤案。
明君之世,尚且如此,昏君之世,更是暗无天日,冤情、冤案遍布天下。
桓帝即位以来,大肆杀戮,诸多外戚、幸臣被杀;直谏之臣李云、杜众因言取祸,天下人皆知其冤。“自陛下即位以来,频行诛伐,梁、寇、孙、邓,并见族灭,其从坐者,又非其数。李云上书,明主所不当讳,杜众乞死,谅以感悟圣朝,曾无赦宥,而并被残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4]1077
宦官专权是专制皇权的畸形产物,灵帝时,宦官专权达到顶峰。宦官唆使灵帝敛天下财以修宫室,宦官从中谋取私利,残害百姓,百姓安能不冤?“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雇一,雇谓酬其价也。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4]2535而地方官员刺史、郡守趁机盘剥百姓,导致百姓呼天喊地。“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4]2535
(三)黑暗的政治,往往是产生大量冤情、冤案的渊薮
黑暗政治产生的原因众多。因地方官员不能秉公执法、公正判案,造成冤案、冤情;或因地方官员没有按照国家及法律的规定收取赋税和征用劳力,反而对百姓横征暴敛、刻意诛求、过度役民,导致百姓遭受疾苦和受冤。讼冤人在当地到处申诉,而地方官员彼此之间官官相护、互相推诿,致使受冤人只能“诣阙讼冤”。“刑罚不中,众冤失职,趋阙告诉者不绝。”[3]315“令长守相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远诣阙上书诉讼。”[14]68
以上只是涉及地方政治的黑暗,如果中央政治黑暗,必当会影响地方,二者叠加,时局暗无天日,更是制造冤案的渊薮。如东汉时期的外戚与宦官便是当时政治黑暗的根源,东汉和帝之后,外戚开始持权;顺帝之后,宦官开始持权;再之后,宦官与外戚交替持权。
和帝时,窦太后临朝,政事委任窦宪兄弟。窦宪兄弟专权后,地方官员多窦宪之党,且多贪纵之辈,对百姓横征暴敛,一方面中饱私囊,一方面用于贿赂窦氏兄弟,“刺史、守、令,多出其门,竞赋敛吏民,共为赂遗”[15]。
桓、灵时期,政治极为黑暗。宦官专权,他们控制和影响最高统治者,“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政治势力蔓延,中央和地方皆有其党,更如豺狼一般,大肆贪污受贿,侵吞国家财产。“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生活骄奢淫逸,大兴土木,安插兄弟姻亲于州郡,盘剥百姓,导致百姓生活不堪,流为盗贼[4]1852。“皆竞起第宅,以华侈相尚,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兄弟姻戚,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无异,虐遍天下;民不堪命,故多为盗贼焉。”[12]2521即使不是宦官之党,由于腐败之风气兴盛,其他官吏也是贪残诛求,盘剥百姓。“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如豺虎,暴殄烝民。”[12]1837
所以在黑暗的政治下,一方面,在中央地方各级贪官污吏、宦官、外戚欺压和盘剥下,老百姓产生大量的冤情、冤案。另一方面,因政治争斗,正直之官僚、士大夫与贪官污吏、外戚、宦官作斗争,因后者往往亲近君主,利用君主的权威对正直之官僚、士大夫做出随性处置,导致官僚之间亦产生不少冤情、冤案。
三、“诣阙讼冤”的基本问题
(一)“诣阙讼冤”的主体
汉时“诣阙讼冤”的主体比较广泛,受冤人本人、亲属、朋友、学生、属吏、治民皆可“诣阙讼冤”,甚至与受冤人没有丝毫关系、与冤情或冤案毫无关联之人,但同情受冤人,亦可诣阙讼其冤,为其仗义执言;“诣阙讼冤”可以是一人、几人甚至数百成千上万人。以下分而述之。
1.受冤人本人
指本人通过“诣阙讼冤”的方式向最高统治者表达自己的冤案、冤情,请求其予以处理。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最能将自己的冤情、冤案表达清楚的形式。在此种情况下,受冤人的人身自由没有受到约束,尚可亲力亲为。
孔僖与崔骃相友善,同在太学游学,因二人私下讨论汉武帝,并对其进行了指责,被人上告诽谤先帝,刺讥当世。汉廷将派官吏对二人进行处置,孔僖本人诣阙上书讼自己之冤于明帝,“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4]2561。寇荣性格“辩絜自善,少与人交”,皇帝周围宠臣对其十分忌惮,寇氏家族又和皇族联姻,富贵显重,更是被皇帝左右嫉妒,故群小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寇荣被陷害且家族受牵连,寇荣本人诣阙自讼冤情[16]405。匈奴单于于扶罗在灵帝中平五年立,但匈奴国内其杀父仇人叛变,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于扶罗走投无路,亦诣阙为自己讼冤,“持至尸逐侯单于于扶罗,中平五年立。国人杀其父者遂叛,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而于扶罗诣阙自讼”[4]2965。
2.受冤人亲朋
受冤人蒙冤后,有的受冤人身陷囹圄,无法脱身;有的受到种种干扰和阻拦,导致无法亲自诣阙;有的受冤人被迫害致死,只能由他人诣阙上书讼冤。封建时代,刑罚残酷,经常实行株连政策,往往因一人之案件而牵连周围亲朋好友,尤其是自己的近亲受案件牵连。如不存在株连,作为受冤人的亲朋基于亲戚之情、朋友之谊可能会主动为受冤人讼冤。如存在株连,受冤人亲朋为受冤人讼冤,即是为他人,亦是为己,实则作为利益共同体而讼冤。
汉灵帝时零陵太守杨璇平定了“零陵贼”,不但功劳没被认可,反而被荆州刺史赵凯诬奏,被槛车押送京师,在押送途中赵凯命人夺其笔砚,不让其写章奏,防止其申诉于皇帝。杨璇只能写血书,由其子弟“诣阙讼冤”至皇帝。史书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杨璇字机平,平零陵贼,为荆州刺史赵凯横奏,槛车征之。仍夺其笔砚,乃啮臂出血,以簿中白毛笔染血以书帛上,具陈破贼形势,及言为凯所诬,以付子弟,诣阙自讼,诏原之。”[17]
班固被人飞章诬告私改国史,此在当时为大罪,班固本人被京兆狱收押在监,本人身陷囹圄,无法自讼,“固弟超诣阙上书,具陈固不敢妄作,但续父所记述汉事 ”[18]。郡民王凭罪不至死,而郡守却将其冤杀,王凭家属“诣阙称冤”[14]810。马援被帝婿梁统飞章诬陷,光武帝震怒,马援病死战场后家属不敢为其正常举行葬礼,宾客亦不敢送葬,只能草草了事,其故人云阳令朱勃诣阙为其讼冤,《后汉纪》曰:“于是援家属惶怖,不敢归旧墓,买城西数亩地,葬其中,宾客故人不敢送葬。故云阳令朱勃诣阙上书。”[16]146
3.受冤人下属或治民
汉代之“诣阙讼冤”,多为上官之冤,亦即下属、百姓为上官讼冤。在官场,由于触犯刑律、政治斗争及政治迫害,受难的一方官员往往被降职、免职甚至身陷囹圄,本人及其家属由于某种原因无法亲自诣阙讼冤,而且汉代官场上不但君主与臣下存在君臣关系,甚至上下级之间亦存在“君臣关系”,下级应为上级排忧解难,这在当时被认为理所当然。“是时郡吏之于太守,本有君臣名分。为掾吏者,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19]102若上级官员蒙冤,下属要为上级受冤官员申冤,其形式为下属或单独,或组织其他属吏,或组织治下之民,奋力为上官周旋,奔赴京师为上官讼冤。宁阳主簿诣阙讼其县令之冤,在京城滞留六七年[注]《后汉书·虞诩传》曰:“宁阳主簿诣阙,诉其县令之枉,积六七岁不省。”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引《后汉书》皆出自这一版本),第1872页。。东汉章帝时赵相李统被冀州刺史阮况诬奏“耳目不聪明”,其属吏“咸用忿愤”,均欲诣阙为其鸣冤[20]。史弼公忠正直,与宦官作斗争,被宦官侯览诬奏下狱,当地的属吏、治民纷纷赴京城为其鸣冤[注]《后汉书·史弼传》曰:“侯览大怨,遂诈作飞章下司隶,诬(史)弼诽谤,槛车征。及下廷尉诏狱,平原吏人奔走诣阙讼之。”第2111页。。灵帝时期,宦官专权,在举谣言时,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承宦官之意,对于宦官子弟宾客皆不敢纠举,而是纠举没有背景、有治化良迹的边远小郡官长,导致当地属吏及治民诣阙为其长官诉冤[注]《后汉书·刘陶传》载:“时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诣阙陈诉。”第1851页。。
4.受冤人之学生
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实行通经入仕,此种入仕方式渐成风尚,亦为时人所重。儒吏在官场逐步占据重要地位,黄老之士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最终,官场成为儒吏与法吏的世界,且高级官员儒吏出身者较法吏更多。很多官吏少时师从大儒(此时之大儒往往亦是官吏,一边为官,一边带门徒)学经,学有所成后通经入仕。门徒从仕后,可能官阶甚至比恩师高,但师徒之谊始终长存,恩师有难,门徒往往周旋于缓急之间。
高获曾拜欧阳歙为师,欧阳歙因贪赃问题下狱当斩,高获诣阙为其请命[注]《后汉书·高获传》载:“(高获)师事司徒欧阳歙。歙下狱当断,获冠铁冠,带铁锧,诣阙请歙。”第2711页。。外戚大将军梁冀污蔑李固与甘陵刘文、魏郡刘鲔共为妖言,被执下狱,李固门生诣阙上书,证明李固被冤[注]《后汉书·李杜列传》载:“甘陵刘文、魏郡刘鲔各谋立蒜为天子,梁冀因此诬固与文、鲔共为妖言,下狱。门生勃海王调贯械上书,证固之枉。”第2087页。。太尉杨震于安帝时被宦官进谗言而免官,之后愤而自杀;顺帝即位后,其门徒延放诣阙讼杨震之冤[注]《后汉书·虞延传》载:“(延放)少为太尉杨震门徒,及震被谗自杀,顺帝初,放诣阙追讼震罪。”第1154页。。杜弘少时拜同郡太守焦贶为师,焦贶因楚王刘英涉嫌谋反事而受牵连,其在逮捕赴京途中病死,家属系京师诏狱,杜弘为其师诣阙上章请冤[注]《后汉书·郑弘传》载:“弘师同郡河东太守焦贶。楚王英谋反发觉,以疏引贶,贶被收捕,疾病于道亡没,妻子闭系诏狱,掠考连年。弘独髡头负铁锧诣阙上章,为贶讼罪。”第1155页。。
5.仗义执言之士
东汉和帝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走向黑暗,一直延续到桓、灵帝。政治黑暗之时间如此长久,社稷却没有倾覆,原因种种,东汉人之尚气节为其中重要一因,而东汉人之尚气节,往往能拯救国家于危难。两汉相较,东汉仗义执言之情形更为普遍。赵翼有评论:“盖其时轻生尚气已成习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然举世以此相尚,故国家缓急之际,尚有可恃以搘拄倾危。”[19]104尚气节之重要表现之一在于仗义执言之士遇到他人之冤情、冤案,虽与其非亲非故,但理解和同情其遭遇,为其仗义执言而不计后果。
李固被梁冀诬陷与甘陵刘文、魏郡刘鲔共为妖言而下狱,不仅有其门生王调“诣阙讼冤”,而且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与李固非亲非故,亦为其“诣阙讼冤”[4]2087。皇甫规不愿意接受宦官的索贿且不愿意与宦官交通,多次冒犯宦官,所以宦官诬陷其下狱,其属官欲敛财为其打通关节,但皇甫规不同意,而此时他人“诸公及太学生张凤”为其“诣阙讼冤”[注]《后汉书·皇甫规传》载:“中常侍徐璜、左悺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规终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于吏。官属欲赋敛请谢,规誓而不听,遂以余寇不绝,坐系延尉,论输左校。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第2135页。。朱穆与宦官作斗争,宦官赵忠葬父逾制,朱穆将其事下郡案验,属吏惧其威严而重治赵忠家属,导致得罪宦官,被“诣廷尉,输作左校”,而非亲非故之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为其“诣阙讼冤”[4]1470。以上受冤之三人,在仗义执言之士“诣阙讼冤”后均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赦免。
前已经论述,汉代“诣阙讼冤”主体十分广泛,而目前案件之上诉主体只能是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有严格的代理手续和限定范围,且人数不超过两人,若无代理手续,即使是案件当事人之至亲也无法为其上诉。因上诉主体有限,导致能向公权力机关主张权益的主体有限。故“诣阙讼冤”之广泛主体可为当今司法提供良好之借鉴,若能够从法律上保障上诉之主体广泛,不但更能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亦能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也可减少冤假错案。
(二)讼冤的对象
“诣阙讼冤”的对象指受冤人及其他人讼冤,所倾诉的对象,即汉代最高统治者。在汉代,最高统治者有两类,一是皇帝,一是称制太后。在西汉,除吕后称制且掌握最高权力外,其他太后如景帝母窦太后、成帝母王太后虽在政治上影响很大,但并未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至于东汉,由于皇帝年寿不永,继嗣不昌,导致或诸侯继承皇帝,或幼童临朝,不得不借助女主临朝听政。“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谓安、质、桓、灵。临朝者六后,章帝窦太后、和熹邓太后、安思阎太后、顺烈梁太后、桓思窦太后、灵思何太后也。”[4]401
前已论,封建时代,皇帝、称制之太后掌握最高权力,对吏民百姓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自然挟刑赏以治天下。虽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冤情、冤案必不可免,官官相卫,官吏之间互相推诿,导致冤案、冤情很难平反。但一定程度上,如冤案、冤情过多,尤其是官吏自身的冤案、冤情过多,会严重影响统治秩序。因为他们的门生、故吏、治民以其官长之冤情、冤案能否平反作为评价当时朝廷、最高统治者的标准,他们没有对最高统治者的愚忠思想却与师长有君臣之谊、师生之情。如果最高统治者对他们师长的冤情、冤狱长期不闻不问,他们可能与朝廷离心离德,这样亦有害于封建统治秩序。故最高统治者为了表示“仁义”且为维护统治秩序,往往会对一些影响比较大的或其比较同情的冤案、冤情进行平反。当然,相对浩如烟海的冤情、冤案,实际只有少数得到平反,但正是这点微薄的希望,导致讼冤人络绎不绝“诣阙讼冤”,甚至在京城长期坚守讼冤。
当今案件上诉之对象为上级法院,即基层法院一审案件上诉于中院,中院一审案件上诉于省高院,省高院一审案件上诉于最高院。从司法实践来讲,大多数案件一般在地方中院案件就二审终止。能够上诉至高院的案件很少,至于上诉至最高院的案件,因其有严格程序和规范要求,一年尚无几例,最高院的主要角色是司法指导,制定司法规范。而在两汉,可以直接上诉到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每年花很大的精力处理冤案、冤情,此在下文诣阙讼冤处置中将论述。
(三)讼冤的请求
讼冤人“诣阙讼冤”所提出的请求在一般情况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对冤情、冤案进行平反;二是对制造冤情、冤案的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但很多情况下,如果冤情、冤案是最高统治者直接造成或部分与最高统治者有关,其请求可能只是对冤情、冤案进行平反,而且这种平反极可能只是有限的平反。对冤情、冤案进行平反的内容比较广泛,主要包括刑狱以及其他方面,因其他方面内容芜杂,毫无规律可循,只能列举。
1.刑狱
汉代法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重在刑法。芜杂的法律中,刑法条款最多,所涉及的对罪犯及其亲朋的处置亦层出不穷,刑罚普遍偏重。刑狱可剥夺罪犯甚至其亲朋的生命、人身自由、财产。即便不如此,刑狱经常迫使罪犯及其亲朋受鞭、杖之刑,亦可能强迫罪犯及亲朋做苦力。故此,刑狱在汉代波及面广、影响深,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也往往是造成冤案最多的缘由。如前述班固之弟诣阙所讼其兄班固之冤为班固私改国史而下狱、李固门生王调所讼其师之冤为李固被梁冀诬有妖言而下狱、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所讼皇甫规之冤为其作战没有将敌人完全消灭而被下狱、杜弘所讼其师之冤为其受楚王刘英谋反案而本人及家庭受牵连、平原吏民诣阙讼史弼之冤为宦官侯览污蔑其下狱而论死刑等事例可见,刑狱所涉之人可上至中央地方各级官吏,下至细民百姓,其史料不胜枚举。
2.其他
这种冤情、冤案由于不涉及刑罚,没有一定规律,比较散乱,只能做一些列举。如太子无端被废,安帝时诸名臣来历、祝讽等守阙固争太子无罪被废为济阴王事;重臣无端被免职,杨震之门徒虞放讼杨震因宦官谗言被免而自杀之事;甚至桀骜不驯之匈奴单于对于自己无端被国内反叛之人所废,亦“诣阙讼冤”;地方小吏讼其上官之冤,如宁阳主簿诣阙,诉其县令之枉。
四、“诣阙讼冤”的处理
汉代讼冤人“诣阙讼冤”,将讼冤章奏交到朝廷相关机构后,相关人员对受冤人的冤情、冤案进行相应的处置,章奏多数会被扣留,讼冤如石沉大海,但也可能会将其中一部分讼冤奏章转呈最高统治者,由最高统治者进行处理。其处置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覆、录囚、君主亲省章奏或面见。
(一)主管机构和人员
公车司马负责吏民奏章的转呈,“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4]3579。应劭汉官仪上:“公车司马令,周官也,秩六百石,冠一梁,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21]从中可见,作为六百石的公车司马,职掌吏民上章奏,而“诣阙讼冤”亦基本上采取诣阙上章奏的形式,“章”“奏”内载有受冤人冤情、冤案的内容,讼冤人交予公车司马,由公车司马转呈最高统治者。
西汉中后期,权力慢慢移转至尚书台,尚书或领尚书事者负责先行处理上书事务。“诣阙讼冤”主要采取上章奏的形式,亦自然先交到尚书或者领尚书事处,由其进行初步的处理,再根据尚书或者领尚书事安排,决定是否再由最高统治者进行处理。“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3]3135“(成帝时)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民曹尚书主凡吏上书事。”[4]3596东汉权归台阁,自然继承此项制度。
(二)最高统治者之处理方式
1.覆
何为覆,《尔雅·释诂》云:“覆,审也。”《华严经音义》释之为:“覆谓重审察也。”综上两点,“覆”实为对案件重新审查。具体到“诣阙讼冤”,指讼冤人讼冤后,最高统治者派人或者亲自审查案件,以查明是否有冤,从而做出处理。
覆起始于何时,史无明载,无法确定,但是秦朝时期已经有对狱案重新审查之制。赵高负责审理李斯之狱,从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二世使人验斯”[13]2561,可见,对于重大案件,秦统治者往往会非常谨慎,派自己的近侍或相关官员去重新审查。
秦朝之亡,严刑峻法为重要原因。故汉代虽大体继承秦代法制,但鉴于秦亡教训,在具体执行上更有韧性,对秦朝的“覆”即案件复审制度予以继承,以体现统治者“慎刑”之意。“覆”案可以防止官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随意“出入”罪,从而减少冤案。汉代统治者在复审案件过程当中,并不只做表面文章,如发现官员的问题,即使是高官,也会予以追究。
赵广汉治理京兆,政绩卓著,威名远扬,为汉兴以来最有名之京兆尹,史称“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长老传以为自汉兴以来治京兆者莫能及”[3]3203。赵广汉听信“客”之报告,派属官枉法整治苏贤,以军事违法而罪之,苏贤之父诣阙上书讼冤,并投诉广汉滥用职权。宣帝不因广汉政绩卓著、声名远扬而回护,而是直接将此案下有司“覆治”,导致京兆属官尉史禹被腰斩,主审官员建议逮捕广汉,宣帝诏令广汉接受询问,广汉承认自己之罪过。因正好有赦令,广汉虽未被免官,但宣帝还是对广汉进行了处置,将其秩禄降低一等,以示惩戒[3]3204。
对地方郡守的枉法行为,如囚犯家属或他人“诣阙讼冤”,汉廷亦往往派遣使者“覆考”,对于违法乱纪的官员会予以处置。周燕作为“郡决曹掾”,郡守枉法杀人,囚犯家属守阙讼冤,朝廷派遣使者“覆考”,周燕将责任全部包揽在自己身上,曰:“愿谨定文书,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时病而已。”使者并不知,将周燕关入监狱,并刑讯逼供[4]2675。
当然,从制度设计本身来讲,覆,包括“覆考”“覆案”“覆治”,出发点在于对案件进行复审,从而避免冤情、冤案。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再好的制度设计,如执行之人故意滥用,将其当作权力争斗、利益豪夺、政治迫害的工具时,“覆”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如上文所述赵高审理李斯之案,赵高故意“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审”。二世虽派人复审李斯案,但已经得不到真相,李斯最终含冤被杀。昭帝时,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行天子之权,丞相车千秋谨慎自保,不关大政,更不敢与霍光争权。而霍光仍旧利用“覆治”侯史吴案的机会,欲通过此案牵扯少府徐仁,而少府徐仁为车丞相女婿,从而达到打击丞相的目的。“奏请覆治,劾廷尉、少府纵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数为侯史吴言。”[3]2662最终处理结果是“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轻重,皆论弃市,而不以及丞相,终与相竟”[3]2663。此案虽未牵连车丞相,但其女婿被杀,车丞相经此打击,不久后就去世。
2.录囚
录囚在两汉典籍中最早见于《汉书·隽不疑传》:“(隽不疑)拜为青州刺史,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颜师古释之为:省录之,知其情状有冤滞与不也。”[3]3036-3037何为“录囚”?指长官巡行各地监狱,面见罪犯及相关人或阅读案卷,从而平反冤狱。两汉时期,录囚主要有四种方式,最高统治者录囚、郡守录囚、刺史录囚、使者录囚,其中涉及“诣阙讼冤”的录囚有两种,最高统治者录囚及其所派使者录囚。
汉代最高统治者录囚,应该从宣帝开始。《汉书·刑法志》曰:“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3]1102宣帝在宣室决刑狱,虽无录囚之名,实有录囚之实。皇帝录囚之有其名实者,始于汉明帝。《后汉书·第五伦传》载:“会帝幸廷尉录囚徒。”《后汉书·寒郎传》言:“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自明帝之后,东汉最高统治者录囚徒成为惯例,录囚之事亦非常普遍。
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刑罚体系注定监狱中的囚徒不在少数,汉处于自然经济时代,经常会发生干旱。如遇干旱,汉统治者往往会反思自己的执政行为。汉时盛行灾异说,认为刑罚之事属阴,如果遇到亢阳久旱的灾害,时人便认为刑狱可能出现失误,应该录囚及平反冤狱,之后才能阴阳和谐,旱灾消失,最终应时吉雨。干旱发生后,大臣们往往会上章奏要求皇帝录囚、平反冤狱,皇帝也会反思自己的刑政是否有缺失,从而录囚、平反冤狱。讼冤人亦认为这往往是劝说最高统治者录囚并平反冤狱的好时机,故他们会诣阙上章,要求录囚并平反冤狱。史籍因干旱而录囚的记载不胜枚举,如:
三月,旱。遣使者录囚徒。[4]254
六月,旱。遣使者录囚徒,理轻系。[4]255
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阳寺及若卢狱,录囚徒,赐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属以下各有差,即日降雨。[4]210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时洛阳有冤囚,和帝幸洛阳寺,录囚徒,理冤囚,收令下狱抵罪。[4]3278
另外,因囚徒过多,最高统治者一人根本忙不过来,往往派遣使者录囚并平反冤狱。有常规的使者,如刺史和司隶校尉,刺史在武帝时职掌主要是依据“六条诏书”,其中有关于狱政方面的监察,虽没有明确其录囚的职掌,但狱政之监察实则包括录囚。光武帝时期确定刺史录囚职掌,明确规定代表皇帝巡行郡国“录囚徒”;年终时,刺史本人或派人赴京师上计,汇报录囚等各项工作。“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4]198
也有不常规的使者,任务在于最高统治者之派遣。光武帝早期,尚未建立刺史制度,直接派遣使者赴郡县录囚徒。“至邯郸,遣异与铫期乘传抚循属县,录囚徒,存鳏寡,亡命自诣者除其罪,阴条二千石长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4]640
汉代录囚是一项善政,其所实行,并无一定确定的标准,全在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但一方面,汉时盛行灾异说,如遇干旱,最高统治者内心往往产生恐惧,从而录囚;官员或者讼冤人亦假借干旱之机力谏君主录囚。汉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干旱时常发生,所以录囚很频繁。另一方面,讼冤人大规模“诣阙讼冤”后,其哀求之上章和面见之恳辞使得最高统治者内心产生怜悯,一定情况下也会录囚。
录囚可以让受到株连的无辜百姓从牢狱中释放出来,可让他们重新过上安定的生活。另外,录囚可以加大最高统治者对地方各级官吏的监督。最高统治者录囚或遣使录囚,不但可将冤狱平反,而且对造成冤狱的官吏往往会加以处罚,可以对地方各级官吏形成一定的威慑,让他们一定程度上不敢滥用职权,擅自出入人罪,从而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司法状况。正因为录囚制度有这两种功效,所以为后世各封建王朝所承袭。
3.最高统治者省章或面见
从皇帝本人角度来察,大规模的“诣阙讼冤”,针对其中少部分的冤情、冤案进行处理并平反,处置一批造成冤情、冤案的官吏,可以达到肃清吏治、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效果。最高统治者阅读了讼冤者奏章后,可能会直接将冤案、冤情平反;或者接见讼冤者或其他人,了解情况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处置。
孔僖与崔骃涉嫌诽谤武帝案件,孔僖诣阙上书,自讼冤情:“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明帝览其奏章之后,“立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
郑弘恩师焦贶牵涉楚王刘英谋反案,郑弘“独髡头负鈇锧诣阙上章,为贶讼罪”。明帝览其章奏,觉悟焦贶之冤,立即释放焦贶家属。
皇帝览奏章后,有可能对冤情、冤案进行平反,但也有可能不予平反,甚至对于章奏中不逊言辞生气,反而加大处置力度。宁阳主簿之讼县令冤,汉廷拖沓六七年不予处理,责任本在政府。故宁阳主簿言辞激烈,曰:“臣岂可北诣单于以告怨乎?”顺帝览章后大怒,把奏章拿给尚书看,尚书顺旨劾宁阳主簿以大逆[4]1872。
以上是皇帝阅读讼冤人讼冤之奏章后,对被冤人的冤情、冤案立即予以处理的事例。在一些情况下,最高统治者在阅读讼冤人的章奏后,并不立即做出处置,往往先接见讼冤人,对被冤人的冤情、冤案进行了解,然后再做出相应的处置。
汉明帝时,班固涉嫌私改国史,为人所告,明帝“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班固之弟班超担心“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诣阙上书为班固讼冤,汉明帝召见班超,班超“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明帝经过召见,发现班固有史学才,不但撤销案件,而且召班固诣校书部。
讼冤人虽“诣阙讼冤”,得蒙皇帝召见,可在皇帝面前陈述被冤人冤情,皇帝未必听取。高获曾拜欧阳歙为师,且与光武帝早年有交往,在欧阳歙下狱当斩的情况下,“获冠铁冠,带铁锧,诣阙请歙”,光武帝召见了高获,但并没有赦免欧阳歙。
在汉代,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冤情、冤案很多,最高统治者往往亲自处理冤情、冤案。对于重大案件,最高统治者往往主动派使者复审,以求发现冤案、冤情。对于部分冤案、冤情在讼冤人诣阙上书讼冤后,最高统治者对于其中的一些讼冤章奏会亲自处理,甚至会接见一些案件的受冤人或讼冤人,了解冤情、冤案的情况。对于冤情、冤案的处置,最高统治者可能立即做出处置结果或者派遣使者调查之后再做出相应的决定,这些都可以为我们当今的冤假错案处置提供借鉴。
五、“诣阙讼冤”的局限性
汉代法律并未限制“诣阙讼冤”的主体,从表面上来看,汉代“诣阙讼冤”基本上是人人都具有的权利,人人皆可“诣阙讼冤”。但客观情况来看,绝非如此,汉代“诣阙讼冤”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诣阙讼冤”对于多数贫苦百姓只是画饼而已,不具有可行性
一方面,广大下层百姓,根本承担不起远赴京师的高额费用,东汉王符指出:“细民冤结,无所控告,下土边远,能诣阙者,万无数人。”[14]208其中指出普通百姓远处“下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诣阙讼冤。另一方面,即使诣阙,未必能够讼冤,即使讼冤,冤情、冤案多数不能够得到处理。“小人有怨,不远千里,断发刻肌,诣阙告诉,而不为理。”即使冤情、冤案的奏章被朝廷受理,但冤情或者冤案能够得到关注并处理的不到百分之一。“其得省治者,不能百一。”[14]177薛宣为丞相时,定制“府辞讼例不满万钱不为移书,后皆遵薛侯故事”[22]。百姓本穷苦之人,家产安能满万钱,更何况辞讼能达万钱。此项规定,实为富豪权势之家大开方便之门。所以百姓之冤情、冤案“守阙连年,而终不见理”[4]1616,甚至即便是官吏,其冤情、冤案所拖之时间亦旷日持久。如顺帝时“宁阳主簿诣阙,诉其县令之枉,积六七岁不省”。
(二)主管“诣阙讼冤”的“衙门”对讼冤者多方诘难,对冤案、冤情处理并不认真,经常借故推托,为难讼冤者
“不能照察真伪,但欲罢之以久困之资,故猥说一科,令此注百日,乃为移书,其不满百日,辄更造数。”[14]214甚至官官相卫,鱼肉百姓,互相推诿,尚书不责三公,三公不责州郡,州郡不责县邑,使得冤情、冤案无法处置,“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让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14]68。
(三)“诣阙讼冤”之冤情、冤案往往是官长之冤情、冤案
在两汉典籍当中,往往多见门生、故吏为其师长讼冤。“自汉制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从事,二千石得辟功曹,掾吏不由尚书选授。为所辟置者,即同家臣,故有君臣之谊。其后相沿,凡属吏之于长官皆如之。”[19]70“是时郡吏之于太守,本有君臣名分。为掾吏者,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19]102由于制度之规定,长官与下属之间实际形成君臣之谊,下属为上官周旋被时人认为理所当然。之所以这么做,也是由封建专制的本质所决定的,封建社会的法律和制度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的,广大“细民”在“诣阙讼冤”上不可能与权贵们享有同等地位。
两汉之“细民”“诣阙讼冤”虽不在少数,大多是作为讼冤之附庸,所讼之冤都是官僚或者富贵之人之冤而无自己之冤。
综上所述,因汉代法律制度本身、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黑暗的政治,导致冤情、冤案必不可免,甚至随处皆是,由于地方官吏互相请托和官官相卫,冤情、冤案在当地无法处理,讼冤人只能络绎不绝“诣阙讼冤”。“诣阙讼冤”的对象为最高统治者,包括皇帝及称制之太后。“诣阙讼冤”的处理机构是公车司马和尚书台,最高统治者的处理方式有“覆”“录囚”“省章或面见”。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最高统治者对于少部分冤情、冤案会平反,对于少数造成冤情、冤案的百官吏民会加以处置。“诣阙讼冤”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广大细民无法承担“诣阙讼冤”的高额费用,官吏之推诿、腐败、诛求,导致百姓之诣阙之冤难。另一方面,“诣阙讼冤”主要是属吏、学生讼师长之冤,而无百姓之冤,这是由封建专制的本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