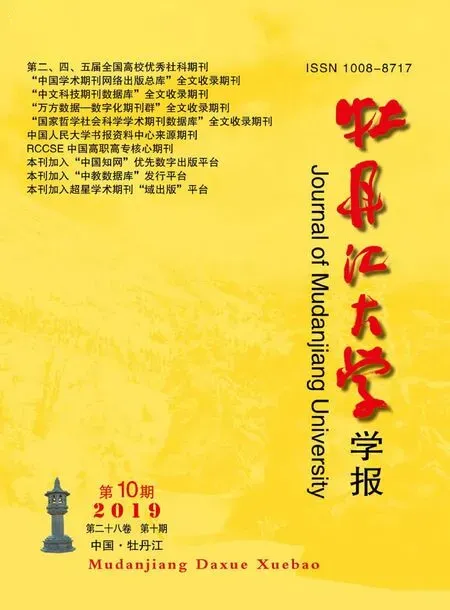罗尔斯正义论与精准扶贫“三个耦合”价值启示
孙 珊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二0二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贫困问题是世界性难题,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美国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撰写的名著《正义论》是一本专门研讨理性性质的正义理论的专著,强调公平是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树立公平的观念来取代主导当时社会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在书中,罗尔斯尤其关注民权和贫困两大基本问题,论述的两个正义原则体现对“最不利者”弱势群体的关怀。罗尔斯认为,“最不利者”是衡量社会平等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社会实现正义的归宿。在中国语境下,精准扶贫正是对“最不利者”贫困人群的关注与帮扶。体现了正义原则价值基础和正义性内涵。因此,在罗尔斯“正义论”视阈下,从正义概念与精准扶贫概念的耦合、最不利者与精准扶贫对象的耦合、两个正义原则与扶贫目标的耦合等方面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精准扶贫,具有一定的哲学诠释意义和实践启示作用,并以此指导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价值前提:正义与精准扶贫的概念耦合
从古自今,“正义”(justice)一词概念宽泛、众说纷纭、争论不止。据记载,“正义”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荀子》:“不学问,无正义,以富丽为隆,是俗人者也。”在最初的文字记载中发现,正义主要是从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出发,指一般意义上的正当,包括全部美德和完好的道德行为,后来又和平等、慈善等区分开来。事实上,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不同思想家对“正义”有着不同界定与解释,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看来,正义就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等级各司其职。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平等就是正义,且正义分为“数量相等”的平均正义和“比值相等”的分配正义,主要应用于人的行为。英国的哲学家休谟则认为,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唯一源泉。但在20世纪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的罗尔斯看来,其正义论中的正义即公平的正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1]罗尔斯把当时西方社会现存的两种主导正义理论分为功利主义正义观和直觉主义正义观。具体来说,功利主义正义观主张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直觉主义正义观则通过反思自身来达到一些基本的原则,强调道德事实的复杂性使人们无法解释人们的判断。罗尔斯均不赞同这两种正义观,尤其是反对功利主义正义观。按照罗尔斯的愿景,“要确立一种正义论,以作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对象,来替换那些长期支配着我们的哲学传统的理论。”[2]
“精准扶贫”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1月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的。从内容上来看,精准扶贫的主要意涵包括第一层面困难群众的精准识别、第二层面贫困原因的精准分析以及第三层面扶贫措施的精准采取等。纵观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陆续调整完善扶贫开发政策,历经了从大规模区域扶贫向小范围群体扶贫的过程。自从精准扶贫理念提出以来,为了实现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于2020年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及地方不断出台精准扶贫政策文件,既有宏观层面五年规划,也有微观层面针对特定地区如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偏远地区;针对特定人群如低收入群体、残疾人群体等特殊人群等具体政策措施,具有强烈的正义性内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的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理念契合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热切期待,体现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积极回应。精准扶贫以解决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问题是实施“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任务之一。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成果如何与全体人民共享、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如何带动后富,还有部分贫困地区、贫困人民如何脱贫致富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回答并解决。罗尔斯认为,所有社会的基本善或者称为基本价值,包括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自尊都需要尽可能平等地分配。由此可见,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即公平的正义对当前精准扶贫工作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二、价值基础:“最不利者”与扶贫对象的耦合
平等作为人民的基本权利,体现重要的政治价值。“最不利者”是罗尔斯在平等价值里关注的重中之重。改善“最不利者”的社会处境是罗尔斯平等价值观的逻辑旨归。罗尔斯认为,在良序社会里,“最不利者”是指“拥有最低期望的收入阶层”,即对社会底层人员的统称。他认为,正义的社会应该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采取措施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配差距。在此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基本善”的概念。他认为,“基本善”是作为政治社会中每一个合作成员所必需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条件和适于各种目的的手段。关于基本善,罗尔斯提出了五种指标:“一是基本的权利和自由;二是在拥有各种机会条件下的移居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三是拥有权威和责任的官职和职位之权利和特权;四是收入和财富;五是自尊的社会基础。”[3]“基本善”的概念为论证正义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区分“最不利者”提供了标准,为原初状态中的人提供作出合理选择的动机。同时,“基本善”与正义原则之间也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即权利与自由对应第一个正义原则,权力和机会对应机会平等原则,收入和财富对应差异化原则。在罗尔斯的框架里,“最不利者”就是指对“基本善”保持最低期望的人,他们拥有最少的权利、机会、财富、收入和自尊的社会基础等。
在当下中国语境里,“最不利者”指的是贫困人民等弱势群体,主要是那些因为某些障碍而使得自身在社会中处于竞争劣势的人群,当然这些障碍可以是因自身条件引起、也可以因社会条件而引起。因此,当前的学术界将弱势群体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处于“最不利者”的弱势群体如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城乡贫困人员等并未充分享受到发展成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存在收入低、工作不稳定、生活条件差、社会保障水平低等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改善“最不利者”的境况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外,从“基本善”概念为如何区分“最不利者”提供基本指标来看,精准扶贫中精准识别贫困者、认定弱势群体也需界定相关指标,从而真正做到有据可依、有的放矢,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真正做到精准化扶贫。
三、价值旨归:关于正义的两个原则与扶贫目标的耦合
与社会的基本机构相配套,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两个著名的正义原则。第一,每一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第二,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应该作如下安排:首先应被合理地期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其次要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第一个原则应用于在公民政治权利中体现平等自由的价值,第二个原则应用于社会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中体现差别化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但是,这两个原则并不是同等存在的。在罗尔斯看来,应按照词汇式序列秉持一种优先原则,即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
罗尔斯认为,因每个人所处社会地位、出生条件、等级阶层不同,导致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起点就不平等这样的情况是不公平的。所以,平等自由作为第一个原则应运而生。然而,罗尔斯提出的差别原则一经提出,就受到很大争议和激烈批评。然后,罗尔斯通过构建原初状态模型和无知之幕的一系列假设,为差别原则巧妙提供了合乎逻辑的证明。差别原则包含着某种平均主义,最基本地反映了一种“平等的倾向”。差别原则首先意味着一种补偿原则,即应当对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进行补偿,虽然差别原则不完全等同于补偿原则,但它力图达到补偿原则的目的;其次体现一种互惠的概念,即差别原则是追求相互有利的一种原则;再次,则体现为一种博爱原则。在西方社会语境中,与自由和平等相比,博爱处于较次要的地位。某种意义上来讲,差别原则表明了一种公民友谊和社会团结。在罗尔斯看来,这些均为理想主义的原则,然而当时的西方社会并没有实现这些原则,或者至少说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在罗尔斯的框架里,两个正义原则的提出是为了支配权利和义务的分配,进而调节收入与财富的分配。现实社会中,机会、自由、财富、收入、自尊等“基本善”是无法得到合理分配的,始终存在“基本善”分配不平等的状况。罗尔斯将其归咎到两个方面原因,即个人偶然因素和社会偶然因素。从个人偶然因素来看,人生来就拥有不同禀赋、能力、素质的特点决定其拥有不同“基本善”的客观事实。虽然有些人认为天赋较高、资质较好的人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并且也应该获得较大的利益。罗尔斯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由个人的天赋资质来觉得自己的收入分配是不应当的,毕竟天赋和资质并不是受人的主观动机去支配的,这些个人的偶然因素不足以决定利益分配的好坏。从社会偶然因素来看,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出生条件、等级阶层不同,导致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起点就不平等,在罗尔斯看来这是不公平的。所以,他提出了第一个原则,即平等自由原则。在个人偶然因素和社会偶然因素之间,由于社会偶然因素可以通过平等自由原则来消除不利,而因个人偶然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却难以消除。为此,罗尔斯提出了补偿原则,他认为,既然因个人偶然因素导致不平等是不应得的,这些不平等就应该被补偿。
基于罗尔斯的观点,政府作为“良序社会”的设计者、组织者,在当下中国语境下需将公正平等塑造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来调节社会。新时代的精准扶贫体现政府自觉构建公平“社会结构”的责任,是相对于粗放扶贫在总结以往扶贫工作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行动方略,包括物质、精神、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立体多维式扶贫。扶贫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位、驻村安排、脱贫成效等六个方面的精准内容彰显平等公正的正义价值内涵。一系列精准对策的有效实行,维护了“最不利者”的切身利益,可以最大程度上确保“最不利者”享受经济发展红利和改革成果,又快又好走向共同富裕,彰显国家与社会的正义性。此外,在罗尔斯看来,由于客观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对人们的社会地位、竞争机会产生分配上的影响,并使一些人沦为因社会偶然因素导致的弱势群体。为了尽可能消除这种不平等,要着眼于“最不利者”的贫困群体并为之进行补偿,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现有贫困地区、贫困人民大都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应发扬“先富带动后富”精神,让先富裕起来的“领头羊”“领军人”广泛参与脱贫攻坚战,将“输血”与“造血”、“授鱼”和“授渔”相结合,通过先富的社会既得利益者对弱势贫困群众进行扶持和补偿,满足弱势群体需求,实现社会资源二次分配,深刻体现罗尔斯“补偿”的价值内涵。
罗尔斯的《正义论》于1971年一经问世,就在西方国家引起广泛重视,被视为二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所说:“罗尔斯的著作在英语国家立即被承认是对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贡献。”[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公平”一词出现近30次,“正义”一词出现6次,“平等”一词出现7次,自由一词出现7次。由此可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将公平正义视为人民群众的核心诉求、视为一切工作的重要准绳。实践证明,新时代精准扶贫的价值导向与罗尔斯的正义观有相通之处。罗尔斯认为社会基本结构就是正义的对象,个体间存在因个人偶然因素带来的天赋等差异难以消除,需通过制定社会制度来尽可能调节消除不平等。精准扶贫强调精准到村到户到人,更着眼微观层面的个体对象“以点筑面”,要求精确配置扶贫资源、精准扶持扶贫对象,帮助“最不利者”贫困群体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彰显国家从社会制度上对弱势群体的后天补偿,体现正义性的理论价值。诚然,罗尔斯所阐释的两个正义原则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其更多依赖于道德因素。正如罗尔斯自己所言:“所有的理论都有错误,我们应把正义论看作一种指导性结构,用来集中我们的道德感受,在我们的直觉能力面前提出有限和较易处理的问题以便判断。[5]
四、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中国贫困人口到2020年全部实现精准脱贫。精准扶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这一目标的实现则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和实事求是。从个体、社会、国家三个方面来说,精准扶贫有着强烈的正义性价值基础。
然而,从罗尔斯的正义观遭到批评的事实中不难发现,罗尔斯提出的正义理论建立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所建立的良序的正义社会,不依赖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而是在现存社会制度框架下,通过两个正义原则来调整各种制度和政策,使得社会资源朝向“最不利者”方倾斜分配。显然,这与马克思提倡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领导、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方式使得无产阶级获得真正的平等与自由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将本身应该属于无产阶级占有的被异化的剩余价值反而被资产阶级打着正义的旗号进行分配,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取的。然而,无论如何,罗尔斯正义理论对我国当前精准扶贫工作仍具有一定的价值借鉴,或许可以更好地提供一定意义上路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