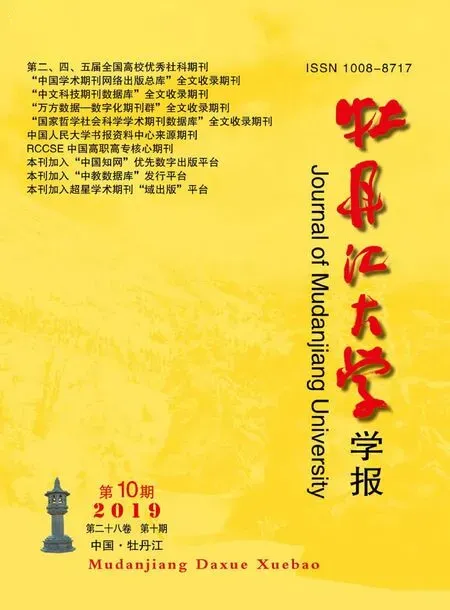论窃取型贪污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刘 伟 琦
(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我国《刑法》第382条规定了贪污罪的行为类型包括“侵吞”“窃取”“骗取”以及“其他手段”四种类型,当行为人以窃取的方式犯本罪时,便构成窃取型贪污罪。在实践中,以窃取的方式侵占公共财物,既可以成立窃取型贪污罪,也可以构成盗窃罪,其区分的关键是,窃取型贪污罪的成立以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为必要,盗窃罪的成立并不要求具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可见,对窃取公共财物进行定性时,窃取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解释结论将直接关系到此罪与彼罪。再者,基于法律文本的简明原则,“法律不会说多余的话”,[1]既然我国《刑法》规定了贪污罪的行为类型包括“侵吞”“窃取”“骗取”以及“其他手段”,上述四种行为方式的含义应当有所区别,由此形成四种类型的贪污罪所利用的“职务”范围及其利用的“职务便利”应当有所区别。因此,有必要研究不同类型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限于篇幅,本文仅对窃取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探讨。
一、“窃取”的含义
关于贪污罪中“窃取”的含义,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其一,认为贪污罪中的“窃取”是指“秘密地将由其本人合法保管的财物据为己有,即通常所说的监守自盗。”[2]该观点是多数通行教科书所持的观点。[3]其二,认为贪污中的“‘窃取’和盗窃罪中的‘窃取’含义相同”,“是指将自己没有占有的公共财物变成直接占有”。[4]其三,认为,“窃取”,“是指违反占有者的意思,将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并且“只有当行为人与他人共同占有公共财物时,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窃取该财物的,才属于贪污罪中的‘窃取’”。[5]
首先,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窃取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行为手段的秘密性,二是行为对象属于自己合法保管的财物。但是,这样的见解不可取。其一,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窃取是相对于财物的保管人、占有人以及持有人而言具有秘密性,这就意味着,将非法占有自己合法保管的财物解释为秘密窃取,从逻辑上讲不通。其二,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根据占有的手段是否秘密来区分侵吞与窃取,如是这样,就会导致将夜晚悄无声息拿走自己合法保管、占有的财物认定为窃取,将白天大摇大摆拿走自己合法保管、占有的财物认定为侵吞,[6]这种区分标准殊不可取。其三,贪污罪中的“侵吞”和“窃取”是并列而非包含的关系,针对行为对象而言,“侵吞”是将自己合法占有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窃取”是将他人占有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据此,第一种观点把“窃取”解释为“将由其本人合法保管的财物据为己有”,混淆了“窃取”与“侵吞”的界限。
其次,刑法理论通常认为窃取是和平夺取财产手段之一,其含义是指“将他人占有的财物,通过和平手段转移为自己占有”。[6]从窃取的含义看,窃取的对象应当是他人占有下的财物。后两种观点将窃取的对象解释为他人占有的财物或自己没有占有的财物,符合窃取的一般含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后两种观点也有一定的缺陷:第二种观点将贪污罪中的“窃取”解释“将自己没有占有的公共财物变成直接占有”。但是,贪污罪另一行为方式——“骗取”,是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使他人将财产转移为行为人或第三人所有,即“骗取”也是“将自己没有占有的公共财物变成直接占有”,据此,第二种观点无法区分“窃取”与“骗取”。第三种观点认为,只有行为人窃取“与他人共同占有公共财物”时,才属于贪污罪中的“窃取”,但这样的解释会不当限缩贪污罪的成立范围。例如,甲和乙各自保管某国有银行金库的钥匙,甲窃取乙保管的钥匙,用两把钥匙打开金库,拿走金库中的现金20万元。甲乙只是保管金库的钥匙,可以解释为二人辅助占有金库中的现金,但并不能解释为甲乙共同占有金库中的现金。按照第三种观点,甲拿走金库中的20万元不能认定为贪污罪中的“窃取”,又由于甲在侵占现金之时并没有占有金库中的现金,也不能解释为贪污罪中的“侵吞”,更不能解释为“骗取”,①这样,只能解释为盗窃罪中的窃取,只得以盗窃罪论处,无疑限缩了贪污罪的成立范围。
我们认为,在理解贪污罪的“窃取”时,既不能脱离窃取的一般含义,又要注意和贪污罪的其他侵占手段以及与盗窃罪中的窃取相区分。既然窃取的一般含义是指“违反占有的意思,取得他人占有、为他人所有的财物”,[7]那么,贪污罪所“窃取”的对象也应当是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此外,“窃取”与“侵吞”的区别在于,“侵吞”是将自己独立控制、支配的公共财物非法占为己,[8]“窃取”是将他人占有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窃取”与“骗取”的区别在于,“骗取”是行为人以不违背财物占有者意志的方式取得财物,窃取是以违背财物占有者意志的方式取得财物。贪污罪的“窃取”与盗窃罪的窃取的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对侵占的财物具有职责义务,因为:贪污罪是亵渎职务行为廉洁性的犯罪,如果行为人对侵占的公共财物不具有职责义务,即使侵占公共财物,也不具有侵犯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可能性,就无法认定为贪污罪,所以,在贪污罪中,行为人对窃取的公共财物应当具有职责义务;但是,盗窃罪并不是亵渎职务的犯罪,行为人对其窃取的财物也并不具有职责义务。据此,贪污罪的“窃取”,应当是指以违背他人意志的方式将其具有职责义务的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当然,为了更好地保护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对这里的“他人占有”需要作扩大解释,包括行为人辅助占有、监视占有(例如流水线上的工人、安保人员占有财物的情形)以及与他人共同占有等。
二、窃取型贪污罪所利用的“职务”范围
由于“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9]“每个不法构成要件均有其要保护的法益”,[10]既然如此,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以保护法益为指导给予实质的解释。[11]又于刑法理论与实践均将贪污罪理解为贪利性渎职犯罪,[12]即贪污罪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及公共财产所有权,本罪所利用的“职务”正是征表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要素。据此,对窃取型贪污罪所利用的“职务”范围的解读,应当以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法益为指导,以避免形式解读而导致不当扩大或缩小窃取型贪污罪的成立范围。
如前所述,贪污罪中的“窃取”是指以违背他人意志的方式将其具有职责义务的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非法占为己有,这就意味着,在窃取型贪污罪中,行为人在行为时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形成一定职责义务的法律状态。正是基于此,行为人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才形成“廉洁、奉公”的职责义务,其利用对公共财物形成的上述法律状态窃取公共财物,才能解释为违背了其职务附带的“廉洁、奉公”的职责义务,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法益,进而,才有成立贪污罪的可能;相反,若行为人对其侵占的公共财物并未形成一定职责义务的法律状态,即使其将该公共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因没有可亵渎的职责义务,并无侵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进而不可能构成贪污罪。现结合两个相关案例进行讨论。
[案例1]某国有企业的门卫李某周末值班时发现本单位某财务科办公室通宵未关灯,前往巡查时见室内无人,遂起贪财的意念,将2台笔记本电脑(价值1.2万元)窃为己有。法院判决李某犯盗窃罪。
[案例2]申玉某为中国人民银行某分行业务部出纳,其与另一出纳共同保管保险柜的钥匙。申玉某与个体户高金某通谋盗窃该行保险柜内的现金。申玉某事先将高金某带进该行业务部的套间,乘其他人员离开办公室之际,将自己保管的保险柜钥匙交给高金某,自己即离开业务部。高金某窃取另一出纳员保管的钥匙,然后打开保险柜,盗走30万元人民币。公诉机关以贪污罪起诉高金某,一审、二审判决高金某犯盗窃罪。②
在案例1中,李某虽然属于国有公司的工作人员,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资格,但是,由于其从事的职务是门卫,即看管人员、车辆进出公司大门的工作,并不负责看管公司其他办公区域的物品。据此,李某对公司财务科内的笔记本并无看管的职责义务,其窃取2台笔记本并没有侵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因此,就本案而言,其窃取公共财物时只是利用了其作为门卫的方便条件,但不能解释为利用了其职务上的便利。进而言之,针对李某窃取2台笔记本而言,其所从事的职务不属于贪污罪所利用的“职务”范围。法院认定其犯盗窃罪的定性正确。
在案例2中,法院判决高金某犯盗窃罪的理由是:保险柜有两把钥匙,申玉某仅保管一把钥匙,仅以其个人职务便利尚不足以与高金某共同侵占这笔公款,其利用职务之便仅仅为高金某实施盗窃提供和创造条件,因而,不能以申玉某的身份和其行为确定本案的性质。但问题是,申玉某保管保险柜的一把钥匙就对保险柜内的公款具有一定的职责义务,其利用保管钥匙的职务便利与他人共同侵占其具有职责义务的公款,必然侵犯了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因此,本案应当认定高金某与申玉某犯贪污罪(共同犯罪),法院的判决有误。
对比分析上述两个案例,从行为人对其侵占对象的占有状态来看,在不构成贪污罪的窃取型案件中,比如案例1,侵占对象为他人占有的财物;在构成窃取型贪污罪的案件中,比如案例2,侵占对象也为他人占有的财物。从行为人与其侵占的公共财物之间的关系看,在不构成贪污罪的窃取型案件中,行为人对其侵占的公共财物没有职责义务,比如,案例1中,李某对其侵占的2台笔记本电脑没有职责义务;在构成窃取型贪污罪的案件中,行为人对其侵占的公共财物具有职责义务,比如,案例2中,申玉某保管保险柜的一把钥匙就对保险柜内的公款具有一定的职责义务。据此,在窃取型贪污罪中,行为人在行为时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形成一定职责义务的法律状态。又由于行为人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形成一定职责义务的法律状态,来源于其从事的职务,因此,应当将窃取型贪污罪所利用的“职务”界定为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职责义务的工作。
三、窃取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实质内涵
窃取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核心内容包括其所利用的“职务”和“便利”,在明晰其所利用的“职务”之后,尚需讨论其利用的“便利”内容。《现代汉语词典》将便利解释为“使用或行动起来不感觉困难;容易达到目的”。[13]何为窃取型贪污罪所利用的“便利”呢?我们认为,结合窃取型贪污罪的行为对象、行为类型以及保护法益,窃取型贪污罪所利用的“便利”应当具有如下内容:
其一,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优势地位。在我国,窃取型贪污罪是侵占公共财物的行为,行为对象是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那么,具备什么有利条件才使得行为人侵占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时不感觉困难,容易实现侵占的目的呢?如果行为人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不具有任何制约性的优势地位,其实现侵占行为就比较困难,不利于实现侵占公共财物的目的。相反,如果行为人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某种制约性的优势地位,就有利于其顺利地实施侵占公共财物的行为,实现侵占公共财物的目的。所以,窃取型贪污罪所利用的“便利”内容之一,就是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优势地位。
其二,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的优势地位不需达到独立控制、支配的程度。在我国,贪污罪有侵吞、窃取、骗取等不同的侵占类型,相应地,不同侵占类型所利用的“便利”内容有所不同,如果行为人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的优势地位已经达到独立控制、支配财物的程度,即使以窃取、骗取的手段非法占有该公共财物,应当归入侵吞型非法占有,而不是窃取型非法占有。
其三,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的优势地位与行为人从事的职务具有关联关系。由于窃取型贪污罪是侵犯职务行为廉洁性的犯罪,那么,行为人所利用的优势地位就必须与其职务有关联,因为,如果与其职务没有关联关系,即使其利用此种优势地位侵占公共财物,也只是侵犯了公共财物所有权,并无侵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据此,应当要求窃取型贪污罪所利用的优势地位与行为人从事的职务具有关联关系。
结合上述“便利”的三方面的内容,窃取型贪污罪所利用的“便利”应当是指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职务关联性的优势地位,据此,窃取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职务关联性的优势地位。
四、窃取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路径
上述窃取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实质内涵为其认定提供了实质标准,为了实现其认定的规范性,提高其认定的可靠性,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两个因果关系的判定实现其认定的规范性与可靠性。第一,判定行为人是否基于从事的工作而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职责义务,即判断行为人从事的工作与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职责义务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职务关联性的优势地位窃取公共财物,即行为人利用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职务关联性的优势地位与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若上述“两个因果关系判定”都能得出肯定性的结论,应当对窃取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肯定性的评价。
之所以上述“两个因果关系判定”能够实现窃取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认定的规范性与可靠性,其根据是:第一个因果关系的实现,即行为人基于从事的工作而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职责义务,行为人承担的这种“职责义务”涉及公共利益以及公共责任。由于行为人承担的职务代表公共利益,行为人对基于承担的上述“职责义务”就具有廉洁、奉公的义务。如果行为人利用上述“职责义务”的关联关系实现第二个因果关系,即利用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职务关联性的优势地位窃取公共财物,便背离了廉洁、奉公的义务,属于滥用“职务”。而滥用“职务”正是权力异化的表现,这种权力异化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可见,行为人实现上述“两个因果关系”,也就引起了法益侵害的结果。所以,只要上述“两个因果关系判定”成立,就可以对窃取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肯定性的评价。
以下尝试运用上述“两个因果关系判定”规则来分析前文列举的案例,以检验该判断规则的可靠性。
在案例2中,申玉某与另一出纳各保管保险柜的一把钥匙,二者事实上共同保管保险柜内的现金,那么,申玉某基于保管保险柜钥匙的职务内容,当然对保险柜内的现金具有谨慎保管的职责义务。由于申玉某单独用自己的一把钥匙无法打开保险柜,故,其并没有占有保险柜内的现金,保险柜内的现金仍然视为单位占有。据此,申玉某基于承担的职务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职责义务,从而实现了“两个因果关系判定”的第一个因果关系。申玉某与高金某通谋,由高金某利用申玉某与另一名出纳的钥匙打开保险柜,窃取保险柜内的现金,可以解释为二人共同利用申玉某与另一名出纳保管的钥匙窃取单位公共财物,从而实现了“两个因果关系判定”的第二个因果关系,即利用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职务关联性的优势地位窃取公共财物。因此,应当对本案中窃取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肯定性的评价。由此观之,应当认定高金某与申玉某构成贪污罪的共同犯罪,而非盗窃罪。
可见,上述“两个因果关系判定”规则不仅具有规范性与可靠性,而且,运用该规则可以对窃取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恰当的评价。
注释:
①因为骗取需要他人处分财物,而上述情形并无他人处分财物。
②参见《高金有盗窃案》,载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05-1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