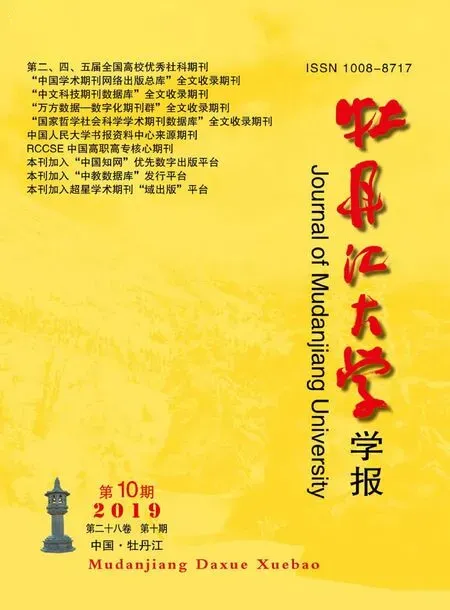探析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是否适用于约翰·密尔
周 家 华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在约翰·罗尔斯的著作《正义论》的第二十七节,无知之幕被逐渐拉起。无知之幕犹如一个竞技场,让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与古典功利主义和平均功利主义相互竞争。本文的目的在于在无知之幕下弄清楚罗尔斯对以上几种功利主义批判的逻辑,并考虑罗尔斯在其预设的场域下是否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视作敌手,借着对以上几种功利主义的批判驳斥密尔式功利主义的逻辑。
一、罗尔斯对古典功利主义的批判
罗尔斯对古典功利主义的批判在《正义论》中主要集中在第三十节。在第三十节的开篇,罗尔斯便指出,在这一部分他要考察古典功利主义的公平观察者的观念,寻找出其直觉基础。[1]176而在寻找出这个基础后,罗尔斯便要将其置于其原初状态或者无知之幕的场域下对这种基础进行批驳。
对于古典功利主义而言,正义的制度便是为公平的观察者所赞成的制度。休谟的“同情的观察者”便是上述公平的观察者的典型代表。这一同情的观察者会站在一个一般的观察点上,将自己置身于每个人的处境中,不偏不倚、理性和不考虑自己利益地估量每个人受制度影响的愿望和利益,然后对同情的快乐和同情的痛苦进行累加或者抵消,最后选择能够带来同情的快乐最大化的制度。
罗尔斯认为,古典功利主义笔下的公平的观察者是利他主义的,而在原初状态下,如果个人选择了古典功利主义来进行制度选择,也便是在假设个人是利他主义的公平观察者,其所赞成的制度也便是能够最大化同情的快乐的制度。先不论这种利他主义的人性假设是否违背了无知之幕的预设,即便承认在原初状态下的这种利他主义,罗尔斯认为它在其设计的无知之幕的场域下,利他主义都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病。
首先,利他主义的问题在于当每个人都投票做其他人要做的事时,因为每个人得到的票数是一样的,这样就无法作出决定,也就无法决定正义的契约。罗尔斯指出,正义问题产生于两个人以上的可能存在的、相互分离的利益的冲突的解决。所以,利他主义不引出一个正义问题。
其次,公平的观察者站在普遍的观察点,从每个人的处境出发考虑个人受制度影响的欲望的满足程度,这等于他将共同体中所有个体的欲望合成一个欲望体系,通过比较这个欲望体系在不同的制度下被满足的程度来判断对各个制度的赞成度大小。罗尔斯认为,这个欲望体系的建立体现了古典功利主义的一个非人格性特征。更加具体地说,欲望体系的建立会导致公平的观察者会作出为实现集体功利最大而忽视或牺牲个人功利的决定,于是便产生了如下悖论:观察者是公平的,但最终却没有公平地照顾每个人的幸福。
再次,如果公平的观察者不进行欲望的整合,如休谟的公平的观察者以仁爱的态度爱共同体中的他人像爱自己一样,那么,公平的观察者的难题是,其他人的目标可能是相互冲突的,或者如阿罗可能定理所指出的——因为个人的偏好顺序的不同,因而可能导致我们根本无法通过共同体中个人的偏好得出群体的偏好,所以仁爱的观察者将面临与上述古典功利主义第一种缺陷相同的困境:无法作出判断。
二、罗尔斯对平均功利原则的批判
在《正义论》的第二十七节,罗尔斯介绍了引向平均功利原则的推理。在这一节中,罗尔斯首先比较了古典功利原则和平均功利原则。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指出,罗尔斯认为古典功利主义有利他主义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下他们主张最大化集体功利。而在原初状态下,罗尔斯认为个人并没有最大化集体功利的欲望,而倾向于最大化个人功利。所以,在原初状态下,对个人而言,平均功利原则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此,在无知之幕下,根据平均功利原则的计算,获得最大平均功利的制度便将是个人将会选择的制度。由于在无知之幕完全被拉下来后,个人的如下信息都被屏蔽掉了:(1)个人的社会地位、阶级;自然禀赋,比如智力和体力。(2)个人善的观念。(3)生活计划的细节。[1]131所以,罗尔斯指出无知之幕下的个人不得不依据不充足理由原则来进行功利计算,即个人“假设有一种使他成为任何人的平等的可能性,并充分地赋予那个人的偏爱、能力和社会地位”,因而他的功利前景便是:1/nu1+nu2+nu3+nu4+……+1/nun,而这个计算结果恰恰与平均功利值相同。
第二十七节的任务是介绍导向平均功利原则的推理以及介绍个人在由“无知之幕”导致的“相对无知”的状况下如何计算平均功利,第二十八节的任务则是对平均功利原则作出批判。在第二十八节中,罗尔斯指出平均功利原则在原初状态的场域下会有两个方面的困难导致其最终会被罗尔斯本人推导出的两个正义原则替代。
平均功利原则的第一个困难源于它的或然性计算。因为无知之幕屏蔽了前文已述的几种信息,个人不得不根据不充足理由原则假设成为每个人的平等可能性,在此基础上进行平均功利的计算。这种计算方式的问题是任何一种可能都被平等地纳入考虑中,而有些可能在无知之幕被拉起来后是我们所无法承受的,即便我们愿意承受,我们可能也不愿我们的后代承受。举例来说,个人可能根据这种计算最终选择了一个实行奴隶制的社会,并且他恰恰沦为了奴隶。所以,平均功利原则在原初状态的场域下的困难便是它给个人带来个人未知的以及可能在无知之幕别拉起来后不愿承担的风险。
平均功利原则的第二个困难来源于平均功利的计算结果将是一个失真和虚假的结果。在无知之幕未被拉起、个人的能力、生活计划的细节以及职业等信息为个人所掌握时,个人对社会中所有个人的功利计算建立在其单独的偏爱体系的基础上。但当无知之幕屏蔽了上述的信息个人依据不充足理由原则判断每个人的功利时,他不得不将他人的能力假设为自己的能力,他人的目标假设为自己的目标……在此基础上进行功利计算。所以,有多少个个人,便有多少个期望体系。这导致,除非每个人的偏爱体系是同一和一致的,否则根据这些人的偏爱体系计算出的平均功利便与无知之幕被拉起来后个人根据单独的偏爱体系作出的计算有很大的差距,而根据这种失真的计算结果选出的社会和制度的合法性很难令人信服。
三、对密尔功利原则与罗尔斯所批判的功利原则差别的考察
如果约翰·密尔的功利原则属于罗尔斯批判的古典功利主义或者平均功利原则的一种,那么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便自然而然地也适用于对约翰·密尔的功利原则的批判。问题是,密尔的功利原则与罗尔斯所要批判的功利主义是否是契合的呢?
首先,约翰·密尔与罗尔斯所要批判的古典功利主义以及平均原则对幸福的定义是有巨大差别的。对于后两者,幸福是一种感受或者说知觉,如边沁将幸福理解为快乐减去痛苦,而西季维克将幸福理解为快乐的知觉与令人厌烦的知觉的差额。平均功利原则对幸福的定义也是继承了上述的古典功利主义。正是由于他们将幸福理解为一种感受或者说知觉,他们才会企图对幸福进行量化以寻找出能够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制度或者政策。而密尔却并未采取这种对幸福的理解。对于密尔而言,幸福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正如罗尔斯指出:
“请注意,密尔在说到最终目的(最大幸福)时,是把它作为一种存在(第二章第10段),或者作为存在的一种类型,或者作为存在的一种方式(分别见第8段和第6段)来谈的。幸福不只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或者惬意的情感,也不是一系列这样的情感(feeling),不管是简单的情感还是复杂的情感。毋宁说,它是一种模式,或者有的人会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以这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所经历和生活的那样。在这里我认为,只有当这种生活模式或多或少成功地实现了它的目标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它是幸福的。”[2]265
将幸福理解为一种生活状况或者生活方式时,便不会有上述的古典功利原则以及平均功利原则在功利计算上的困难(如非人格性以及期望不统一——笔者注)。
其次,在关于自由和幸福的关系上,密尔与罗尔斯批判的古典功利主义以及平均功利原则是有差别的。对于古典功利主义与平均功利原则而言,自由与幸福是相互独立的,最大化最大多数人幸福的制度未必是自由的制度,因而自由制度可能被他们所撇弃不用。换言之,对于他们而言,它们对自由权利的承认是服从于其对总体社会福利贡献的判断。当罗尔斯在无知之幕的场域下批判古典功利主义的非人格性以及平均功利原则冒险时,其对这二者的指责的要点正在于他们可能出于集体功利最大化或者平均功利最大化的考虑而站在自由的反面,创建出个人无法忍受的制度或政策。对于边沁等人的这种思想倾向,密尔已经意识到了。正如乔治•萨拜因指出:
“一如密尔本人在其他文字中所说的那样,他父亲那一代的功利主义者之所以追求自由政制,并不是为了自由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以为它是一种有效的政制;事实也确实如此,当边沁从信奉开明专制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时候,除了一些细节以外,他的确没有做什么改变。”[3]641
相较于父辈以及平均功利原则对自由与幸福关系的理解,密尔倾向于认为自由与幸福是一体的,促进共同体幸福的制度一定是自由的制度。自由在密尔看来,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的幸福的一部分,“自由……除了对幸福有贡献以外,还是幸福的固有属性。”[3]395而且,相较于其父辈从总体功利最大化的方式来论证自由的必要性,密尔“论辩的有效部分并非是功利主义的。”[3]395他并不借助总体福利的最大化来说明自由的价值,而是从“它能够造就高尚的道德品格并给这个品格以发展空间”[3]396的角度来为自由辩护,比如在《论自由》中,密尔认为,有些事情即便个人未必会比政府官员办得好,但依然应交给个人去办,因为这可以增强他们的主动性和判断能力。有人可能会反驳道,密尔从人格价值角度来证成自由的价值,表面上看并未诉诸功利主义,至于为何培养这种人格价值,密尔会诉诸他所谓的“普遍的功利”,所以密尔依旧是在以功利主义论证自由原则”。笔者认为,这种反驳是无力的,因为当密尔用“普遍功利”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来取代其父辈的精致功利概念时,已经将这种功利这种概念置于一种无用之地。如果我们将密尔视为一个聪明的作者,我们便要承认密尔不会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问题。而之所以他置这个问题于不顾,一个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依然将个体的道德和人格价值置于根本的地位。
再次,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论述的,古典功利主义者有可能为了实现集体功利而牺牲个人功利,而平均功利主义者在无知之幕下避免了这种古典功利主义的困境,但却可能导致个人被迫面临其根本无法忍受的结果。所以古典功利主义和平均功利主义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并没有为个人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保障,使每个人获得基本的道德权利。但密尔却十分关注“人类福利的基本要素”(即每个人的基本道德权利——笔者注),认为正义观念的本质便是个人的道德权利。[4]正是因此,罗尔斯认为密尔的正义观体现了基本正义权利的优先性。
四、结论
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论述的,罗尔斯所批判的古典功利主义与平均功利主义与密尔的功利主义在关于幸福的界定以及幸福与自由的关系上是有巨大差别的,这种差别如此重要以至于密尔的功利主义与古典功利主义和平均功利主义根本不能混为一谈,而密尔对基本的正义权利的看重更将其与罗尔斯所批判的古典功利主义和平均功利主义区别开来,所以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评是并不适用密尔的功利主义的。而且,罗尔斯本人也没有将密尔视为其理论的敌人,密尔的功利主义和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具有同样的实质。[2]278-280
有人可能会从罗尔斯所批判的利他主义与密尔所谓的“与其他人和谐一致的愿望”的心理特征的角度认为,罗尔斯对古典功利主义中利他倾向的批判实际上便是对密尔舍弃利己主义的批判。笔者想要说明的是,或许密尔的那种心理学假设的确会具有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指出的古典功利主义的弊病,但因为在幸福的定义上的差别,以及对自由与幸福关系理解的差异,加之对个人间平等道德价值的承认与否的差别,密尔的“功利主义”与罗尔斯所批驳的古典功利主义以及平均功利原则已经具有十分悬殊的不同,所以,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所批驳的功利主义的缺陷并不适用于密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