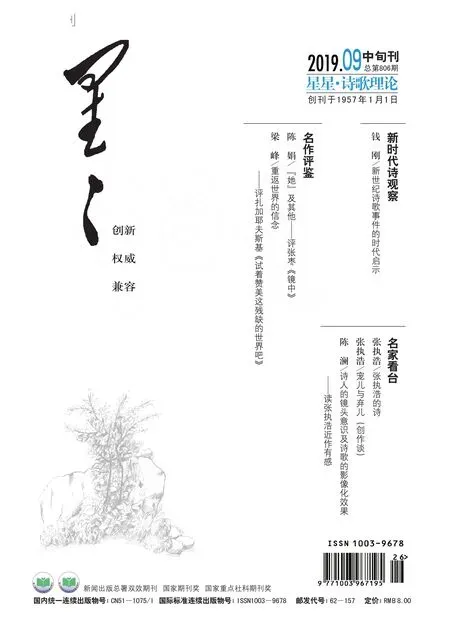火与斧:反哺汉语之途
——评苏奇飞的诗
■ 李啸洋
猛虎与丽辞
虎,是自然的,历史的,美学的,象征的,哲学的。虎,是一个激情者的形象,在野兽的庞大面前,诗人选择了美学的轻盈。
虎,是思考的分节符——它是一个动词,一个残忍的化身,一个美的对象,一个佛经中的典故,一个修辞者的谜语。
虎,在立体主义的火焰里,在古典与现代的裂隙里,在历史与丽辞的辩证里,在佛陀般的静默与词语的跃动里。
《伏虎集》是一首长诗,诗歌共十小节,呈现出先锋、精警、思辨的精神风貌。诗人在诗行中追索人类世界中的恐惧、鹤唳与惊患,以此来揭橥“此在”处境。“一只猛虎,在词语的破碎处/一跃而起,它沉醉于这有力的一跃……”这是长诗《伏虎集》的第一句,也是全诗之引。《伏虎集》召唤“虎”,召唤历史的修辞术。“虎”要去何方?要到格奥尔格所言的“词语的破碎之处”。第十节,作者写到:“伏虎,一种用旧了的/而带点磨损的修辞/一盏被言说擦亮的灯/它在对我们的密谋中/言成肉身。”诗人苦心孤诣,塑造了一只“思之虎”,这是一只游弋于“实与虚、灵与肉、词与物”之间的、游移不定的“猛虎”,终为美学制伏,变成“伏虎”。
猛虎,是美学比喻。美学麾下,虎有着不同的形式:猛虎、怒虎、雅虎。比如诗的第二节:“猛虎伏草,这是一个隐喻/一场死寂的风暴/一股铜质的、静止的、闪光的力/显现在我们的盲视中。”这一节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豹》有着相通之处:“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两位诗人都注意到了猫科动物迷人的行走步态:虎有着“闪光的力”,豹有着“柔软的步容”,二者都是美学的、隐喻的。
猛虎,是历史的修辞。诗的第八节,诗人写到:“长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见/兵起,虎出没/从斧钺、符节和盔胄一跃/而僭越成为青铜宝鼎上的虎纹。”这一节里,虎是起义与符咒的化身,最后积淀为青铜器上的花纹。虎是坐骑,诗人骑着猛虎,轻嗅蔷薇。《伏虎集》这首诗中,读者可以看到语言的自然收束,文化学的内容进入诗歌,舍身饲虎、照猫画虎、与虎谋皮、苛政猛于虎等原型或者典故,都成为诗人进行灵感裁剪的场景。比如,诗的第九节:“而画虎的人,画皮画骨/竟被自己所画之虎/吓出一身冷汗/这是一只误以为真的虎。”这句诗中,从“照猫画虎”到“画人画鬼难画骨”,从“真老虎”到“纸老虎”,诗行指向了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经典哲学命题:“我们唯一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第一辑收录的这几首长诗里,有个整体性特征:丽辞。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到:“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扬雄和司马相如的骈文也称为“俪体”,“俪”意同“丽”,它是修辞的、文采的、装饰的、巴洛克的,骈文俪体,即通过辞藻达到华美。与丽辞相反的是自然主义,去修饰、去雕琢、去象征的文风,陶潜是也。簪花与伏虎,本就是现代诗学中的“新俪体”的代名词,一如宋词中的婉约与豪放两派,成为美学上的两重象征:一曰美女,一曰野兽,一者静,一者动。词在盆地,高原上老虎纵身走下,八千里暗夜蒙着虎的花纹。诗里,词蜕掉沉重的肉身,枕着睡熟的虎做梦。
词语与佛陀
老虎不仅是个原始的低音,老虎也是醒目的节奏,明亮的线条,语言重新赋予其美学之力。长诗《托孤集》《隐忍集》《剖心集》《伏虎集》构成 “伏虎四集”。“虎”的意象得以延续,“虎”继续充当诗人美学思考的线索与桥梁。《托孤集》思考了怒虎之死与虎之重生,读来有英雄就义的悲壮意味:“突然止住的,是伏虎和断剑/而死亡把万物聚拢,又散开,抛洒/入一阵悲风之中。”《隐忍集》又多了一颗慈悲的佛心:“必须用我的肉身/饲养一只猛虎/才能取得它的真心/哦,擒虎者先擒虎心!”《慈悲集》中,诗人加入了佛教的冥想与顿悟,诗人以诗修禅,诗即是禅,禅即是诗。词语与佛陀的世界里,诗人尝试回归到清凉、宁静的世界中去。《受难集》思考宗教中的“受难”命题,诗人匍匐大地,在栽种的诗行里思考舍身精神。比如这行诗:“我不来这世上,会有谁替我前来?”这句诗就是佛教名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仿写。诗中涉及了死亡想象,死亡似乎是诗人书写的起点。枯形灰心,垂死万劫,入火不焚,入水不溺。这首诗,恍若穿行在佛教之林,步步禅机,句句偈语,诗人就是那个书写玄机的人:“行刑吏,在挥下大刀之前/我已将诗偈写好。”
《营救集》写的是营救,写作手法上有着叙事笔调。《火斧集》则以长句见长,内容上书写繁殖衰退、衰老、父权、家园等命题,行文中不再讲究炼词,形容词和副词皆为我所用,读来更像抒情散文。《黄土高原之歌》揭示高原人的苦难与坚毅,不向恶劣自然环境和艰难命运屈服。诗歌风格上,黄土与风沙飞扬,旱魃与祈雨共存。诗人用句子虚拟出西北特性:“男人是轭和犁,女人是辔头和缰绳。”《黄土高原之歌》有如电影蒙太奇,随处可见质感的画面和民俗景观。比如祈雨场景:“敬天的万民,敬地的万民,敬神明的万民,叩拜到干枯如土的万民。”
顾随在《驼庵诗话》中讲到,诗的真实才是真正的真实。亚里士多德也讲,诗比历史更真实。那么,诗之真实是什么?顾随给出了答案:诗的真实是转“无常”为“不灭”。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无常,都是灭,而诗是不灭。花朵易逝,可是诗歌却让花朵长存。布罗茨基的经典命题更能回答这个问题:美学是伦理学之母。换言之,美学大于伦理。诗歌的真实,在于美学真实,它是一种比历史更抽象、普遍的真实。《伏虎集》便达到了美学的真实。
父性与召唤
《赴难之诗》《钢铁之诗》《对抗之诗》等系列,保持了一贯的先锋与警醒,其中的异质性成分清晰可见。《诗的艺术》《诗人自画像》《中年搬家记》《书籍》《读者》《星空》《顶峰》等诗作,描述了自己即将步入中年的过程而产生的忧郁、虚无以及荒诞之感。
《书籍》和《雪鹰低低掠过》以物为命题,探讨物与物性幽暗的声部。《词的皇冠》中,诗人恢复了诗词与古典写作的惯性:“用花插在你的脸上,用花插在词语的间隙。”海德格尔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写到:“命名是一种召唤,正是召唤才将未被召唤者带入到某个切近之处。”诗歌是一种召唤术,经由召唤,事物得以重新命名。生、老、病、死乃是佛教八苦中的内容,诗人反复地切近这些主题:《诞生之诗》与《默默祈祷》里的难产与诞生,《恐老经》与《白发赋》中的老,《亡灵书》和《对一个临终病人的描述》中的死亡,都显现出诗人对生活经验的发掘能力。
海德格尔笔下,宁静的本质在于静默。作为寂静之静默,宁静总是比一切运动更动荡,比任何活动更活跃。诗歌的语言就是为寂静之音说话。庇护于宁静之中就是静默。中国古人讲大音希声,苏奇飞似乎在《雪花落在一头东北虎身上》也悟出了同样的道理:“深远的声音是听不见的。”苏奇飞的诗中有着随处可见的修辞、宗教、隐喻,以及历史与文学语境。诗人站在词语漩涡的中心,制造了一场美学的风暴。汉语诗歌界中,洛夫对于“石室”、欧阳江河对“凤凰”有着新的美学开拓。苏奇飞对于“虎”的开拓,是对诗坛前辈美学开拓的延续。苏奇飞的诗是维特根斯坦的“可言说”和“可沉默”之间的把握,同时以中国古典美学和哲学来反哺新诗,在同质化、快餐化的诗歌阅读环境中,这是难能可贵的坚持。
附:苏奇飞的诗(二首)
伏虎集(节选)
一只猛虎,在词语破碎处
一跃而起,它沉醉于这有力的一跃。
我们则为它虚构出危险的悬崖
和巍峨的绝壁。
而在这跃起之前,
它是一个谜,一种暗示,一个
晦暗不明的象征。
它长久地静伏于沉默之中。
它就是伏在我们嘴唇上的沉默。
而我们全都暴露在
它的窥视之中。
这是一只为我们陈述和言说的猛虎,
一种可被我们用恐惧
和颤栗把握的存在。
(注:节选自《伏虎集》第一节)
雪花落在一头东北虎身上
卧在林中雪地,半眯着眼睛,
这头猛虎神情悠闲。
雪花飘落在金黄的虎纹上,就像
飘落在火焰中,
但看不到一点火星迸溅。
哦,一束就要结冰的火焰!
万物寂灭。这头猛虎
仿佛已经入于涅槃,
像我们膜拜的伟大导师。
然而,耳朵偶尔煽动一下,掸落几朵雪花。
如果放大一万倍,就是高山雪崩。
而深远的声音是听不见的。
一片雪花落下来,去压制千钧之力。
用最轻的,最深情的,
去降服最残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