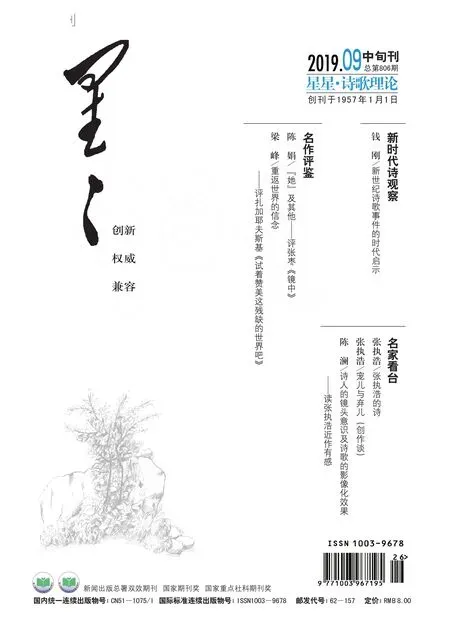诗歌“广场舞时代”诗人何为?
■ 阿苏越尔
文学的金字塔上,诗歌一直被奉为塔尖。在这几年,这些我们熟识的观念正在被崭新的现实所质疑和挑战。有人感慨道:诗歌已经沦落为文学金字塔的塔基。套用尼采那句著名的话:“诗歌(原句:精神)曾经是上帝,后来变成了人类,而现在更变成了一般群众。”一方面,诗歌的群众基础在扩大,另一方面,诗歌的精神和技艺在退化。这是喜忧参半的事情。作为一个诗歌的国度,何以在短暂的几年时间内,诗歌的观念竟然有如此大的改变?这是值得今天的诗人、评论家深思的问题。在我看来,时代发展了,从物质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心灵被思想和情感表达的新热情挟持着,对一切触手可及的手段都跃跃欲试。诗歌因其简短的“身材”和高大上的气质成为人们的首要选择。
以上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主观条件。正当人们的精神生活已经寻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时,新媒体的适时出现为实现诗歌“广场舞时代”提供了自由的空间。新媒体亦由此吸引了更多的客户,更大的点击量以及更多的消费。
从前,人们普遍的观念是:写诗是诗人或想要成为诗人的人干的事情。如今,写诗就像日常的吃饭穿衣一样成为普遍,不需要积累沉淀。凡是能识文断句的人都可以写出一首属于自己的诗歌,而且可以大方地发布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网络媒体上,这成了心安理得的事情。写诗的门槛不是降低了,而是没有了。人们卷起裤脚在曾经认为神圣和神秘的诗歌殿堂里进出自如,春风满面,为朋友或路人的一个点赞或彻夜难眠、或兴奋难当。
诗歌曾经高不可攀的塔尖地位下降成了塔基,其象征含义可能更多,但有一点似乎明白无误:任何想要用文字展现自己的人都可以随手拈来片言只语,以分行的诗歌形式张贴出来,群众性诗写特征由此获证。除了这一形式的简易写作,大多数写作者无力介入其余文体。
2017年的2月,在一篇序言中,诗人徐敬亚惊呼:“这简直是一个诗歌的广场舞时代”。为什么称其为“诗歌的广场舞”?诗学上的这个概念与现实中的广场舞有何惊人的相似之处呢?愚以为有这么几点:1、没有门槛;2、分贝高;3、群体性;4、自娱自乐。
据此,有人也许会说,八十年代的诗歌流派复杂,看上去亦是如此。这是被八十年代诗歌五花八门的表象所迷惑,没有深入研究八十年代诗歌本质的结果。首先从第一条来说,八十年代写作诗歌是有门槛的。一个毫无诗歌写作基础的人,你投奔任何一个诗歌流派都不会被轻易接纳,更不要说在流派的油印刊物上发诗了。公开发表的诗歌作品更是经过专业编辑的层层把关,对于没有基础的习作者,不太可能降格以求送版面,刊物的声誉备受器重。
从第二点来讲,当今诗坛,每个诗歌群体都占据一个诗歌的广场,所谓广场,有的形式是一个网络平台,有的是一本刊物,有的则是一个微信群……音量开到震耳欲聋,按照自己的理解且歌且舞,没有人考虑别人的感受和评价,也不太在乎周围有没有人驻足观看。
“诗歌广场舞”的群体性和自娱自乐的特征那是说,成员中彼此不一定都认识,踩着同一节拍也难得整齐划一。加入其中不需要报备,更没有审批环节,组织松散,来去自由。
在诗歌的广场舞时代,有这么几个方队是要提及的。第一个方队来自部分“名气诗人”。在拥有一定的名声和地位积累之后,个别诗人俨然成了诗歌的道具,以千篇一律的语调和立场,配合着各种以诗歌为名的形形色色的演出。在不断的串场中,这些诗人精疲力竭,哪能腾出时间和精力去做出诗歌的创新和突破?这个乔装打扮过的方队虽然不是广场舞的主流,但它却对诗歌广场舞的形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作家韩少功有一句话,可谓对症下药:“归根结底,作家不能活得太热闹,还是要给自己留一张安静的书桌,想想那些有关文学、文化、精神、社会的难题和大事。”
诗歌广场舞的第二个方队以民间的旗号呈现。这个方队的写作热情颇高,写作素质却参差不齐。他们中的大多数表面清高,内心势利,对主流媒体的态度也是晦昧不清。时而不以为然,诽之谤之,时而又拉拢靠近,引以为荣。
第三个方阵就是诗歌广场舞的主力军,在新媒体平台上大量的诗歌爱好者。这个方队人员庞杂,他们的写作特点是:采用直白浅显的文字,零碎、应急似的抒发生活第一现场的直观感受。他们的作品大多简短,也不太在乎错别字和语病。由于没有诗歌表现手法的专业训练,写出来的诗歌如果不进行分行,实则与日记、段子等别的文体没有丝毫差别。因此,很多写作者并不以诗人的身份自居,直到有人重拾牙慧,冠之以某某流派,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才趋之若鹜,恍然大悟自己原来可以戴上诗人的桂冠。因为要掩盖自身天然的缺憾,在某些诗歌活动家的授意、指使下,他们聚集成群,不以一切深奥的诗歌为意,对一切批评和建议愤愤不平,将关于诗歌的一切学说弃之如敝履。诗坛不时硝烟四起,这帮广场舞的主力军自然功不可没。
或许还应该举出一个由机器人小冰引领出来的诗歌方队。据说,它花了100个小时,学习了百年新诗期间519位诗人的现代诗,然后通过深度神经网络技术,模拟诗人的创作手法,创作出了几乎以假乱真的机器人诗歌。粗听起来,这似乎是个好消息。仔细一想,这正好是诗歌广场舞乱象的深刻反讽。“情为诗根”、“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王国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可以说,机器人小冰冷冰冰的诗行一出现,这些关于诗歌的久远而普遍的共识被颠覆了。情不见,真不存,诗歌的灵魂何以依附?诗歌的广场舞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诗歌的繁荣?
没有媒体铺天盖地的舆论配合,没有帮派无孔不入的自吹自擂,让辨别力受限的读者从良莠不齐的众多诗歌中慧眼识珠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善良愿望。还苦撑的各类诗刊中有诗歌的光明和希冀存续。不管怎么说,专业的诗刊拥有一批经过千锤百炼的诗歌编辑,还拥有层层把关的编审程序,公开刊载出来的作品相对要值得信赖一些。对于诗歌风尚的引领,公刊和官方评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年来,人们没有记住几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却记住了诗坛的负面消息。不一而足。污损诗坛是小事,久而久之,动摇人们对于诗歌和生活的信心就酿成了大事。
八十年代诗坛的轰轰烈烈是见成果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成果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吉狄马加的《黑色的河流》、李亚伟的《中文系》、尚仲敏的《桥牌名将邓小平》、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放眼当下,诗歌的广场舞时代,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中,还有多少诗句能够超越圈子,被社会广泛铭记并传播?
如此这般,目前的中国诗坛有没有值得荣耀的诗人?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有一批清心寡欲的老诗人,我们有一批坚守诗歌高地的中年诗人,我们有一批不乏才华的大学生诗人。是这一群诗人共同组成了新时代蔚为壮观的诗歌高地。他们没有在诗歌广场舞的滚滚洪流中随波逐流,他们的身影在繁华的诗坛虽然只是若影若现,但他们的存在是诗坛的定海神针。
回顾新诗的百年历程,一开始,胡适等先辈首倡的白话诗成果并不显赫。为什么新诗的辉煌出现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呢?改革开放的时代使然。在我看来,当时被热捧的朦胧诗正是抓住了汉语诗歌这么一个伟大的传统:意境和诗意。在朦胧诗中,汉语自带的文字魅力重新散发出光和热,汉字兼具的“形、音、义”特色得到充分显现。这意境和诗意都离不开文字的歧义和暗示,从某种角度讲,汉字的歧义和暗示拓宽了审美空间,让读者回味无穷。
今天,跳起“诗歌的广场舞”,没有多少诗人真正拥有自己独到的诗歌主张。
八十年代,朦胧诗的巨大成就引来了新的反抗。这股反抗的力量以五花八门的诗歌流派形式出现,其中大学生诗派为主的口语诗的反对声浪尤烈。被朦胧诗弄得晕头转向的他们厌倦了繁复,梦想一扫诗坛含糊不清的趋势,重新返璞归真,回到简单和直率。平心而论,口语诗的首倡有正面的启示意义。它对高深和博学诗风旗帜鲜明的戒拒即使放在今天也还具一定的警示性。一些诗人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获得了求新求异者的掌声。但是,物极必反是事物的定律,一味地主张诗歌的明白晓畅,自然会侵害到诗意的存在。不可否认诗歌从来都不是可以一语道破的东西,从本质上看,这些试图让诗歌简单纯粹化的努力与诗歌的本力天生是背道而驰的,这些诗写注定会受到质疑。
在诗歌的广场舞群中,诗歌审美的崇高性和意义的张力被肆意消解,在过分的平铺直述中,诗歌变得呆滞、想象力匮乏。想想看,作为对西装革履着装的反抗,诗歌的广场舞者存心让自己的着装更加生活化,以至于不知就里的跟风者以为着装邋里邋遢才是王道,料想这是对中规中矩的诗歌主流的最有力反抗,殊不知,在全民皆诗的“诗歌广场舞”时代,他们卷起的尘土还来不及飘向远方,就已经吞没了自己,广场上空笑声一片。
“文之难,而诗尤难。”这是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说的。作为有难度的文体,诗歌还是适宜放在文学的塔尖部分。沉湎于集体的狂欢之中,满足于圈子内的肉麻吹捧和已有的一点“广场舞技能”,没有对人类苦难的揭示和抚慰,没有对人类生存意志的精神激励,没有对未知世界的探寻和好奇,可以预计,迟早有一天,诗人的桂冠将不再熠熠生辉。
每个诗人都应该成为受人尊敬的独立的“舞者”,为新时代,也为诗歌滋养着的人民。
——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国成立70周年阅兵精彩回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