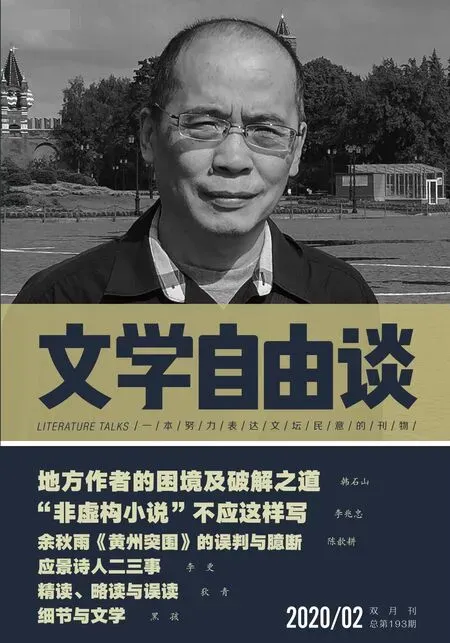地方作者的困境及破解之道
□韩石山
来河南,我是听从河南文艺出版社的调遣,为《边将》宣传敲边鼓的。这么一本破书,人家给出了,叫来配合一下,好意思不来吗?在郑州讲了两场,刘晓飞副社长要来濮阳,她是大美女,更得来了。讲什么呢?昨天一来,书店经理刘学武先生就说,讲讲地方作者要出名咋就这么难,有人写了大半辈子,仍寂寂无名,什么原因,又如何破解?这话说到我心上了。为什么呢?我自己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有亲身体验,有切肤之痛。
这个问题很复杂,牵涉的方面很多,过分地强调哪一方面,指责哪一方面,都不公道。昨天晚上想来想去,只能就大的方面,简略地说说。一是观念上的,一是方法上的。
观念上的,有社会观念的制约,也有个人主观的迎合。
什么叫社会观念的制约呢?别的不好说,就说机构的统属吧。文联,作协,都属于宣传系统,主管部门是宣传部,这样我们的一切作为,必然带有宣传的色彩。时间久了,就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你一拿起笔,没人教你,就知道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要挣脱是很难的,都受制约;地方作者受的制约更大些。还有一点,地方作者刚露个头,领导一重视,给你个小官,要么去通讯组,要么去文化馆,忙于写材料、写报道,文学创作的心就没了。这不是坏事。在地方上混,没个一官半职还真不行;不是你不行,周围人看你,家里人看你,脸面上就下不来。靠写作当了官,是凭本事吃饭,不丢人。问题在于,刚当上挺兴的,说不定还要仿李太白说上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时候,不管是暗中,还是表面上,都要感谢文学待自己不薄。过几年,升不上去,尤其是你仍不忘写作,领导也觉得你不是干行政的料,好久没有升职,这时候牢骚就来了,说不定会说上句“文章误我,我误苍生”。这种情况,只能说你对文学的要求太高了。文学可以是敲门砖,不能当一辈子的龙头拐。
这话说过撂下。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说你该下多大的功夫,是同样的力气,该怎样下,下到什么地方,才会有较大的收获。
这儿是濮阳市新华书店的二楼,下面就是售书大厅,在这儿谈文学,能一针见血,一吐为快。如果你的东西,人家给钱要你写,写了不卖,只要不黄色、不反动,让怎么写就怎么写;要是你写下,送出版社出书,出了书你还要拿版税,那你去售书大厅看看,就知道该怎么写了。有的也是正式出版的,可卖不动,你就该想到,你就是使了吃奶的力气,出上这么一本,又有什么意思呢?架子上摆放一半年,到了还是去造纸厂化了纸浆。卖的最好的是什么?中外文学名著。为啥都爱买呢?看了会聪明,长见识,考试说不定都能加分,这钱花得值。对了,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心里一定要存下这么一个念头,就是我的书放在书店里,人家花钱买了是值得的。有了这个念头,你就是个有良心的作家,就知道该怎么写作了。一说良心,老觉得是一种责任,一种负担,很少有人能悟出,良心常是成事的最好的方法,最好的保证。
齐白石画画,大写意的荷花叶子、葡萄架子上,画个工笔的小蜻蜓、小蚂蚱,不管人们怎样说是艺术上的创新,我总觉得,起初说不定是,老先生画了大写意,觉得要人家两块大洋心里过不去,于是便添上个小玩艺,让买家看了觉得值。这可不是考证出来的,是由我经历的一件小事上悟出来的。早年间在吕梁山区一个镇上教书,镇上年年都有庙会。有一年庙会上来了个画画的,就是用小木片蘸上颜料,画那种弯弯曲曲的老虎呀牡丹呀,现画现卖,不贵,一边画一边唱:“上山虎下山虎,一个老虎一毛五!”跟前要是有小孩靠得太近了,一边推搡一边唱:“小娃娃小娃娃,快回去告诉你妈妈,就说是画老虎的又来啦!”有个妇女要了一张,递过两毛钱,那人接了也不找零,在画的一角画个小鸟,一边画一边唱:“两毛就两毛,没有零钱给你找,我给你添上个小飞鸟!”这个人要是出了大名,不就是个齐白石吗?老虎头上有个飞来飞去的小鸟,五分钱的良心,让他有了这么美好的一个创意。
古人说的“心学”,是说家庭伦理、社会治理,凡事从仁心出发,没有做不好的。写作也是这样。不要多想,想想人家的买书钱,想想写不好跟奸商、跟骗子没有二致,该怎么写就明白了大半。我们都是过来人,我讲你们听,实际上就是在一起交流,对了你们会认同,不对了你们肚子里准定会骂娘。不用说出来,脸上看得出来。怎么写,写下的才是好作品呢?不必唱高调,最切实的就这么两条:一是要关乎世道人心,让人对世道人心有深层的了解;二是要让人能看得下去,要么笑起来,要么哭出来,最少也得郁闷两天,心里想着书中写的事儿。
先谈谈我自己的写作经历,一会儿再归到这两条上去。因为对这两条的认识,我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摸索出来的,明确起来的。
我这人,看着不大,实际不小。“文革”前上了大学,“文革”中毕业的。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吕梁山里当了教师,今年这个村,过上一年又到了另一个村,第三个地方是镇子,第四个地方是县城。怎么到的县城?高考恢复了,调我去办高考复习班。这四个地方,都在一条河的岸边。这条河从这个县的西北,流向东南,到了洪洞县,注入汾河。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散文,回顾自己的教书生涯,口气很大,叫《我的学生一条河》,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开玩笑。我老家在晋南,是平川,过了河是河南的三门峡。过去我从未去过山区。吕梁山可不像南方那样山清水秀,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荒山秃岭,沟壑纵横,地地道道的穷山沟。从到了山里的第一天起,就想着怎么能走出去,走不出去,爬也要爬出去。出身不好,想当干部调出去,根本没门儿。那个地方缺教师,有平川来的,二三十年都调不回去。真的就要终老是乡吗?想想都后怕。想来想去,只有写作这一条路。在公社机关,见省文化馆办了个刊物叫《革命文艺》,写了稿子投去,居然也登了。再后来,见报上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了电影《青松岭》,就写了个电影剧本寄去,没拍,不过为此还去了一趟北京,参加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本写作学习班。改革开放后,刊物多了,就今天一篇散文,明天一篇小说,轮番往外投。怎么会有这么多稿子?投出去不登,就再投出去,基本上不会过夜。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稿子放在自己抽屉里,是绝不会发表的。
还有一点也很明确。常听人说,稿子发表不了,是没遇上识货的编辑。我对自己的稿子没这么自信。我的想法是,遇上好编辑,人家未必看得上眼;遇上个平庸懒散的编辑,或许能从他手里溜过去。怎么做呢?主题要迎合当下的时势,故事要巧妙有新意,最最重要的是,语句通顺,书写清楚,标点符号都没错的。你们要知道,编辑最怕的是“顺稿子”,字句要改,标点要改,烦死了。再就是,字,不必多么工整,太工整了人家一看就是新手,要清楚而又老到。那时刚粉碎“四人帮”,许多老作家都重新拿起笔来。我的稿子是从山村中学寄出的,最好能让对方认为是个落难的老作家,没辙了去中学当了个语文老师。主题没问题,故事没问题,连错别字也没有,还可以想象是搭救了一个落难者——对一个平庸懒散的编辑来说,这不是最理想的稿件吗?大笔一挥,发!于是韩某人的小说散文,一篇一篇全见了天日。那几年,一年差不多要发十来篇短篇小说,好几篇散文。
这样说也太轻巧了,好像自己真的才高八斗似的。这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刚粉碎“四人帮”,社会上一派新气象,社会和内心是合拍的,看到什么,脑子一机灵,就能构思出个小说来。就好比到了舞厅,轻快的音乐一响,人的身体就由不得扭动起来。这样,1980年,我就去了北京的文学讲习所,1984年调到太原,进了山西省作家协会,当了专业作家。我的劲头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媳妇孩子都在老家农村,不光要自己从吕梁山里爬出来,还要把媳妇孩子拽出来,到大城市跟我生活在一起。这些,靠了写作,全都实现了。
后来为什么又不写小说了呢?原因是那样的小说越写越没劲,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从1993年起,转而写传记,写了《李健吾传》《徐志摩传》。这次河南出的《边将》,原本也是一部传记,后来改成小说,但故事框架是我的,情节是我的,细节是我的。改成小说,等于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个台阶能上得这么好,这么轻松,是因为这二三十年来,我一直关注中外小说的发展,一直在琢磨小说的写作技巧。
好了,现在扭回来接着前面的话题,说说力气该怎么下,下到什么地方。
地方作者写小说,总想着既展现自己出众的才华,又展现自己优秀的品质,还要显示自己超卓的见识。贪多务得,一样都不肯落下。这上头不好过多地指责,说轻了不抵事,说重了是唆人作恶。还是撂远点,打比方说吧。《边将》里有条线索,就是名士王世懋,两次来看望杜如桢,都谈到了《金瓶梅》,没有明说,但暗示是他哥哥王世贞写的。王世贞是明嘉靖年间的大诗人,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部书呢?除了影射仇家之外,我给出的解释是,展现诗文所表达不了的才华,具体的说辞是“邪思淫喻,呈才使性”。这是旧时代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钱锺书那么大的学者,写了《谈艺录》,足以维护大学者的身份,还要写个《围城》,一来是上学、出国、教书,多年来对文人学者有太多的观察了解,不吐不快;再就是写学术文章,做做旧体诗,展现不了满腹的才华,于是便写起小说,走上“邪思淫喻,呈才使性”的路子。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亦可作如是观。看看古今这些大学者的作为,就知道,写小说最最重要的,不是别的,就是展现自己的才华。河南农村我没有去过,山西农村去过好多地方。哪儿的农村都会有这么一种人,人不坏,就是油嘴滑舌,爱开个玩笑,爱说个荤段子,大姑娘小媳妇一面骂他,一面又爱跟他搭讪,听他鬼说六道。村里老年人逗笑,说这种人是一肚子的“坏水”,咕嘟咕嘟往外冒。这个比方是俗了点,可我觉得写小说的人,就该是这么一副德性。
既关乎世道人心,又让人爱听的,要数相声演员。这几年,我在北京闲住,说是看孙子,实际上是老伴看孙子,捎带着看我。闲得无聊,要么看京剧,要么听相声。不出去,就在电脑上看。京剧不说了,相声起先爱听郭德纲的,这两年爱听岳云鹏的。小岳岳是你们濮阳南乐县人,真是个相声天才,什么时候看,都不厌烦。师徒二人相比,在世道人心的启迪上,我喜欢郭德纲。他的书《过得刚好》,一出来我就买下看了,还写了评论文章。这个人屡受挫折,对世态炎凉感受极深,许多相声段子,当是来自亲身的体味。比方他说:“说人心都是好的,我敢保险你没有见过天下所有的人。”还有个段子极为精辟,说是你见过要饭的,可你见过要早饭的没有?肯定没有。要是能起得那么早,他就不要饭了。
从相声艺术上说,又得承认,岳云鹏比他师傅高了一筹。看小岳岳的相声,给人的感觉,他就那么喜眉笑眼地瞅着你,身子朝后退着,一只胳膊抬起,朝你招手,来呀来呀。身子挡住的另一只胳膊,手里拿个铁锹,走两步挖个坑,再走两步再挖个坑,跟在他后头的人,没有不跌上一跤再跌一跤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其故事情节和叙述语言,就应当有这样的功力,这样的效果。
光打比方,你们听了肯定不满意,在叙述语言上,我举两个例子。为什么只举语言上的例子,而不举故事结构上的呢?这与我的小说观念有关。我总觉得,故事结构上没有多少新意可谈,连好莱坞的动作大片,一年一年演下来,都没有多少新意,我们又能出什么新招呢?可全世界,好小说仍是层出不穷,道理在哪儿呢?依我之见,全在语言上。再好的故事,没有好的语言也是白搭。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这话听起来极端了些,但委实是肺腑之言,不刊之论。我举的这两个例子,都还是有名的作家,一个是前多少年颇有名气的马原,一个是前面提到的钱锺书。举马原的例子是想说,小说语言是如何连缀起来的,举钱锺书的例子是想说语言的穿透力。
1987年,我在太原郊区一个县挂职深入生活。那时对写小说,已起了厌倦之心。喜欢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一茬作家,于是便以送稿子为名去了上海。住下后,又往南,去海宁参观了徐志摩、王国维故居,去富阳参观了郁达夫故居,去桐乡参观了丰子恺、茅盾故居,来去都住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是个石库门房子,一层两间,我住在三层;二层主间,住的是马原,正在给《收获》写一部长篇小说,后来出版了叫《上下都很平坦》。我这人爱交朋友,住下就跟马原热乎起来,闲了去他那儿坐坐。我发现,他写稿子很怪,八开的大稿纸,铺在桌子上,一次成稿,很少改动,偶有改动,也是剪下个小纸片,贴在稿纸上挡住错了的字,整个纸面干干净净。我就问他,要是这句话错了,要补上半句可怎么办?马原诡谲地眨眨眼,憨厚地笑笑,说别人不会这么问,老兄你是行家,我就不得不从实招来。他说,就不会有这种情形,写小说,只要写下第一句,不管有怎样的缺陷,都不要管,只管往回找补,就写下去了。这样写下去的句子,才有个人特色,也才是小说语言。我一听恍然大悟,心想,这小子果然聪明。这里我无法复述马原小说里的语言,但我可以随便举上个例子。比如我是昨天后晌来的,傍晚去了市里的戚城公园,且以此为开头写篇小说。第一句话写下:来到濮阳的当天傍晚,我和老伴去了戚城公园,我们是从南门进去的。刚写下就知道错了,这个公园只有东门没有南门。要是写散文,非得改不可,但我是写小说,要的就是语言的生动活泼,非同寻常,于是就不改了,接着写:进去以后,发现影子正落在身后,才知道方才进来的不是南门,而是东门。一落笔就写来到濮阳,直截是直截了,总有些突兀,那就再找补,说这次来濮阳非是旅游,是应出版社之邀给我的一本新书造势的。这样一写,又留下个缺口要找补:什么书呢?又拐到《边将》上,这样这篇小说就铺开了。过去教学生作文,在山西谈写作,把这种办法叫“推衍”;也可以叫“推碾”,就像个碾子似的,将情节碾开了,给人的感觉,像是先设下一个又一个扣子,再一个一个地解了开来。等于你所有的关节,都是预设的。明明知道进的是东门,为了绕个弯子,偏说是进了南门,再借个由头纠正过来。自然了还好,不自然了就让人觉得是在卖关子,矫揉造作,故意卖萌。马原的办法是,拿起笔只管扣住预设的思路写下去,顺了就写下去,不顺了再扭回来找补。这是被动的,错了才找补,不错就那么一口气顺下去。这样一找,常会出现意料不到的文字效果,看似零乱,而筋骨相连。
不知你们注意没注意,那些有名的大作家的小说语言,多半是破碎零乱,有劲道又有意蕴。这与他们随意为文的习惯是分不开。别小看了这个随意,这是大本事,不是绝大的自信,不敢这么下笔。比如鲁迅在《祝福》里,写已经成了乞丐的祥林嫂,拄着一根竹竿,头上都劈了,挎着一个篮子,里面有个碗。写到这儿,已写出了祥林嫂的乞丐模样,总觉得还不够,本来该写句号了,写了个逗号,再加上两个字:“破的”。谁看到这儿也得拍案叫绝:真大师也!写小说,语言至关重要,宁支离破碎,也别齐齐整整。全是标准句式,主动宾,主动补,那不叫文学语言。过去有个专用名词,叫报章文字。而报章文字,是没有文学性可言的。
举钱锺书的例子,是要说语言的穿透力。不好说,还是直接说例句吧。前些日子,网上流传《〈围城〉里的金句》。一共六十句,且举一句为例。有个事,先说一下,各人都想想,你会怎么说。现在时兴出全集,好些跟我一样的,只能算个三流作家,凑上十万八万,出上个三卷五卷的全集,殊不知这等于将早年幼稚的作品,像考古挖死尸一样,挖出来丢人现眼。这样的比喻,我们总想有本体有喻体,一句话说清楚。钱先生不是这样,他总是不厌其烦,说个明白,将比喻中的刁钻刻薄,全都展现出来。上面提到的这个比喻,在《围城》里是这么说的:
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构成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死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
我们平常写一个比喻句子,总是先写下本体是什么,接着说像什么,即喻体是什么。钱先生不,先将喻体说个透,再将本体说个透,再将本体与喻体合在一起,让你看出是多么的可笑。这还不算,到了这会儿还要往前推进,来个更为辛辣的断语——双重的“自掘坟墓”。这只是一个比喻,可在他老人家的笔下,几乎成了一个精辟的小品文;用现在的话说,差不多是一个段子了。这就是钱氏语言的穿透力。语言的穿透力,体现出的是作家思维的深度。而小说,直白的语言谁都会说,有深度的语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语言。
举这两个例子,我是有用意的。马原的例子,想说的是语言怎么铺排开,可说是语言的宽度。钱锺书的这个例子,想说的是语言的穿透力,也就是语言的深度。有了宽度,有了深度,才是真的文学语言。掌握了,或者说是修炼下这样的语言能力,就可以说是成功的作家了,想不出名都不行。
好了,今天就谈这些,谢谢,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