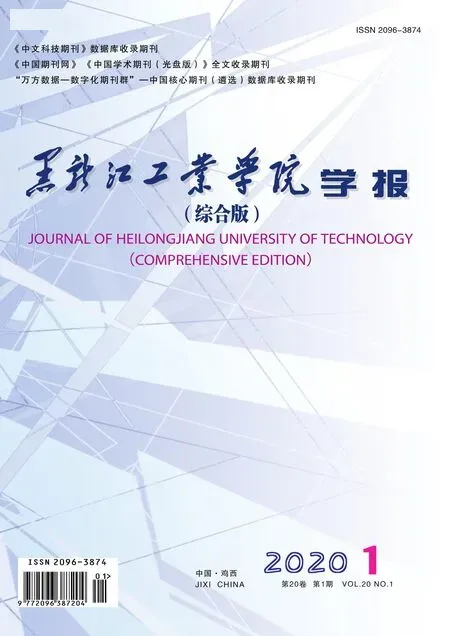从“销售金额”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未遂
贾巧巧
(贵州师范大学 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5)
一、问题的提出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实务中一直争议比较大,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否存在未遂在法院的审判中出现了矛盾。在周德年等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一案中,周德年等人在没有生产烟叶的资质的情况下,擅自组织工人有偿给江明中生产假冒伪劣卷烟,在周德年等人组织工人生产完成后,江明中将该假冒伪劣卷烟销售至各地,销售金额已达五万元以上。在本案中,法院基于其认定的事实,对参与生产的周德年等人以“生产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①然而,在方学文一案中,方学文等人并未获得生产审批批号,擅自生产伪劣卷烟,但尚未销售。其未销售的货值金额为2545452元,本案经过一审和再审,最终以“生产、销售伪劣罪”(未遂)定罪处罚。②方学文一案的判决与《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伪商解释")的规定相互印证。但是,周德年一案的判决并未遵循《伪商解释》的规定。以上两个案例包含着生产尚未销售的两种情况——一是以销售为目的的生产行为;二是以赚取加工费为目的的生产行为(比如:国外品牌代工厂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
对于《伪商解释》中关于未遂的规定,在司法实务中适用并不合理。根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罪状描述,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是可以独立进行评价的。以未遂来认定可以单独定罪的行为是否合理呢?生产且销售但销售金额不足五万时,应该认定为未遂还是不成立犯罪呢?其次,货值金额不足十五万或购入后尚未销售的,这种情形又应该如何去定性和处理呢?是犯罪未遂还是不成立犯罪呢?这些争议的出现还是源于“销售金额”要素的性质和地位的确定。将“销售金额”的性质和地位确定之后,本罪是否存在未遂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所涉及的相关问题概述
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实行行为类型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实行行为存在争议,主要争议有——多种实行行为类型说和复合实行行为类型说[1]。两种学说的争论点在于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和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是否应当单独进行评价,对于生产后,未进行销售的行为是否应该评价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
多种行为类型说是我国通行的学说,三种实行行为的模式更符合立法者不仅惩罚生产并销售的行为也要惩罚销售行为和生产行为的立法原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审判活动中,也多是采用这种学说,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问题在于,销售金额作为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生产尚未销售,就不存在销售金额的问题。那么此时应当如何进行定罪处罚呢?为了解决这种情况,《伪商解释》将生产未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定性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这样的规定出台,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无法合理地予以定性和处罚的情况。但却使多种行为类型说陷入了一个困境。按照多种实行行为类型说的主张,生产行为是可以被评价为独立的犯罪行为,《伪商解释》对生产伪劣产品的规定,实际上否认了生产行为的独立性,也是对多种实行行为类型说的否定。
在《伪商解释》出台以后,就有学者在看到多种行为类型说的弊端以后,继而提出复合行为类型说。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成立是复合行为,而不是单一行为。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实行行为进行综合评价。根据该种学说,生产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行为属于犯罪未遂,这就很契合《伪商解释》的规定。复合行为类型说,虽然解决了生产未销售行为的性质问题,但其存在的问题更是突出。首先,根据该学说的说法,成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要求行为人实施生产并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缺一不可[2]。若是只有其中之一,只能成立犯罪未遂。但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未实施生产行为,购进伪劣产品并销售,且销售金额已达五万元,此时成立犯罪未遂,那么这样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未遂是否合理呢?根据犯罪既遂模式说,销售金额是既遂标准,已经销售且销售金额已达五万以犯罪未遂处罚,对于犯罪既遂模式来说,是不是有点难以自圆其说呢?其次,在司法实践中,生产而未销售的行为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以销售为目的的生产行为;二是以赚取加工费为目的的生产行为。该学说能很好的解释以销售为目的的生产行为,但是对于无销售意图以赚取加工费为目的的生产行为,却无法给予合理解释。总而言之,复合行为类型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多种行为类型说存在的问题,但是它却不能够全面和完整的评价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实行行为。
除以上两种学说以外,有学者提出单一行为类型说。该学说认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罪状描述中,生产伪劣产品行为和生产并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均不是本罪的实行行为,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为本罪唯一实行行为。该学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解决了销售金额的存在对于生产行为无法合理定罪量刑的情况;其次对生产行为根据不同的情形做出了不同的定性:1.在生产者与销售者分离的情形下,将生产者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定性为本罪行为人的共犯;2.在销售者即为生产者的情形下,生产行为为本罪的预备行为。这样的设置对于不同目的的生产行为均能予以定性。以上可知,单一行为类型说很好的解决了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与销售金额的冲突,也对不同生产目的的生产行为进行了相对合理的定性。但笔者认为该种学说的弊端却是不可逆的。“……的”为罪状描述是学术界的通说,生产者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存在于本罪的罪状之中,且条文明确地描述了生产者、销售者的行为,二者是并列关系不是包含关系。所以对于生产行为应独立评价,生产行为也是本罪的实行行为之一。论者将生产行为的罪状描述认定为立法者的日常用语习惯的理由十分牵强,本罪罪名的设置必然包含生产行为,若只是对销售行为进行否定评价,为何本罪不直接叫销售伪劣产品罪?此外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这一章节中均是采用这样的形式,表明立法者所要强调的是销售行为必然伴随着生产行为,将生产行为在罪状中进行阐述,已足以表明立法者对生产行为进行独立评价的意图。所以单一行为类型说违背了立法原意。不论是刑法第140条的规定还是《伪商解释》对本罪未遂的规定,均可体现我国刑法对生产行为持否定评价,且对于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最低评价也是犯罪未遂,司法实务中也出现了以生产伪劣产品罪定罪量刑的情形。而单一行为类型说将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以从犯或犯罪预备进行定性,不能达到刑法中所要达到的惩治力度,容易出现量刑畸轻的情形。
综上笔者认为,多种行为类型说相较于复合行为类型说和单一行为类型说来看,更具合理性。虽然复合行为类型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多种行为类型说对于生产尚未销售且没有销售金额,无法准确定罪量刑的问题;也给予了《伪商解释》关于犯罪未遂的相关规定的理论依据。但该种学说所存在的弊端,远远大于其所能解决的问题,且这种学说不能体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原意。而单一行为类型说虽然能解决以上两种学说所存在的缺陷,但却存在不可逆的缺陷。所以,笔者还是倾向于支持多种实行行为类型说。将这三种行为都进行定罪处罚才符合这个罪名设置的初衷。而多种行为类型说所存在的弊端也完全可以从别的方面予以解决,在此不再进行赘述。
2.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选择性罪名
在我国刑法中,关于罪名的分类,可大致分为三类——选择罪名、单一罪名与概括罪名[3]。我国学界中,本罪通说一般为选择性罪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刑事实务中,既可以概括的使用又可以单一使用,符合选择性罪名的要件[4]。
通过笔者在裁判文书网分别以“生产伪劣产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为检索条件进行检索。发现在司法实务中,对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适用是概括适用和单一适用并存的,所以我们可以认定该罪名是选择性罪名,这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具有多种实行行为相对应。
但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位为选择性罪名存在一定的问题。就该罪名本身及其侵犯的法益来看,将伪劣产品进行销售的行为,社会的危害程度远远大于生产伪劣产品或购进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行为。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在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中,对两种行为的刑罚规定的是一致的,对于两种社会危害程度不一样的犯罪行为适用同一量刑幅度是否会出现罪刑失衡的情况?
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销售金额与犯罪未遂
1.销售金额的地位
对于销售金额的地位,在学术界一直备受争议,主要有:客观处罚条件、既遂标准、构成要件要素、非独立构成要件要素不需要独立评价等几种学说。客观的处罚条件说认为,销售金额与犯罪构成无关,只是刑罚的发动权,有了该要素才能发动刑罚权。既遂标准说认为,销售金额是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犯罪既遂的标准[5],也就是说,满足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金额条件,即该犯罪既遂;构成要件要素说的学者认为,销售金额作为罪状要素,是犯罪的构成要件,符合销售金额条件,代表着犯罪的成立,而不是代表着犯罪既遂,是犯罪的成立条件[6]。非独立构成要件要素说认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行为犯,生产、销售行为一完成即代表犯罪成立,并不要求有数额的标准,数额的设立,是为了根据其社会危险性进行处罚,不用独立评价。
根据我国罪状要素的要求,罪名的罪状是在描述罪名的犯罪构成。由法条可知,销售金额被规定在罪名的罪状之中,属于该罪名的构成要件的范畴。所以,笔者认为,客观的处罚要件说和非独立构成要件要素不需要独立评价说不能成立,不符合该罪的罪名要求。那么销售金额既然属于犯罪构成要件,那它究竟在犯罪中处于什么地位,是犯罪成立条件,还是犯罪既遂条件呢?笔者认为最为合理的学说就是构成要件要素说,销售金额属于犯罪成立条件。
2.数额犯是否存在未遂
数额犯是指在我国刑事法律法规中以一定数额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罪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是典型的数额犯。数额犯是否存在未遂,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对数额犯的研究,还涉及了刑法分则立法模式的研究。根据犯罪成立模式说和犯罪既遂模式说分为了否定说和肯定说。部分学者在这两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折中说。
肯定说认为,作为构成要件的销售金额,一旦达到法条中所规定销售金额的标准,那么该犯罪也达到了既遂状态,反之则是未遂,生产未销售的行为也是犯罪未遂。这种学说看似很合理,但实际上并不合理。首先,《伪商解释》中对生产未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做出了货值金额达销售金额的三倍以上才成立犯罪,那么在货值金额不到销售金额的三倍的情况下,从司法解释来看是否就不成立犯罪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根据肯定说的观点,只要是生产且尚未销售的情况均是犯罪未遂,那么《伪商解释》关于犯罪未遂的规定就略显多余。其次,我们来看看司务中常见的盗窃罪,根据其司法解释可知,盗窃罪的成立也有一定的数额限制,可是该数额并不是犯罪既遂,而是犯罪成立,因为未达该数额标准的,不成立盗窃罪,而不是盗窃罪的未遂,且盗窃罪的既遂标准按通说来看,是得手即既遂。最后,从以上两种情况来讲,单纯的以肯定说来认定犯罪行为,可能难以自圆其说。按照肯定说的观点,只要未达法条中所规定的犯罪数额,即成立犯罪未遂,那么《伪商解释》中有关犯罪未遂的规定将没有存在的必要。盗窃罪中的数额,不管在实务还是学术中,都是作为犯罪成立的标准,这也与肯定说的理论不符合。笔者认为,肯定说是不合理的。
折中说以犯罪既遂模式说为基础,提出数额犯的未遂的认定不应当一概而论,应该将数额犯根据不同的情形分别考量。同时将数额犯分为行为数额犯和结果数额犯,行为数额犯应当有犯罪既未遂的区分,结果数额犯中的数额是犯罪的成立条件[7]。折中说的观点看似全面,但却经不起推敲。首先,以犯罪既遂模式为基础,那么倡导结果数额犯的数额是犯罪的成立条件是违背犯罪既遂模式的基本原理的。其次大多行为数额犯,均是以行为所导致的某一犯罪结果的发生为犯罪构成要件。在实务中,这类犯罪的犯罪结果尚未到法定程度时,并未以未遂犯论处,而是采取行政处罚的形式予以处罚。所以,笔者认为折中说也不合理。
否定说认为,罪名中的数额仅仅只是犯罪的成立要件,不是犯罪的既遂标准。该种学说是基于犯罪成立条件说而来的。根据犯罪成立条件说来看,数额犯中的数额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既代表着犯罪的成立,而不代表着该犯罪达既遂状态。否定说基于犯罪成立条件说理论,强调认定犯罪既未遂的前提必须是犯罪已然成立,倘若犯罪尚未成立,如何能越过犯罪成立去讨论犯罪的既未遂呢?
除以上三种学说以外,还有学者在提倡肯定说的同时,看到了肯定说无法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金额不足五万以及未销售的货值金额不足十五万而不以犯罪论处的情况做出合理解释的缺陷。于是论者提出,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以犯罪情节轻微为由,解释为何不以犯罪论处[8]。但是这种解释十分的牵强,并没有从根本上弥补肯定说的缺陷,而是采取迂回的手段试图模糊肯定说的缺陷。
综上,笔者认为,否定说才是更为合理的学说,针对盗窃罪成立的数额问题、受贿罪受贿数额的问题以及多次抢劫等涉及数额的罪名,使用否定说能更好的解决当中的疑难问题,也更符合司法解释以及刑事实务中对于以上几个问题的处理。
3.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不存在未遂形态
经过之前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相关问题的简述以及对数额犯的分析,笔者坚定地支持刑法分则的立法模式是犯罪成立模式,销售金额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成立条件,且不存在未遂[9]。
(1)刑法分则中关于“销售金额”的规定,明确地规定在罪状之中,是犯罪成立要件。从该罪名的立法原意来看,将销售金额定为犯罪的成立条件,实际上更为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明确了犯罪的处罚条件和限制了犯罪的处罚界限。并且从罪名的设置来看,五万元的销售金额实际上是立法者认为犯罪行为所导致的犯罪结果达到五万的程度,其社会危害性才达到了应受刑事处罚的程度。倘若认为五万元销售金额的设置是为了区分既未遂,那么就将销售金额不足五万元纳入了刑事处罚的范畴,有扩大刑事处罚的范围的嫌疑。如果销售不满五万元就达到了应受刑事处罚的程度,那么刑法条文中的数额的规定是不是有点多余呢?所以从立法目的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来看,销售金额是犯罪成立的条件,该罪名不存在未遂的情况。
(2)根据刑法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量刑是有一定的量刑幅度的。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销售金额五万元就是该罪最低的量刑幅度了。在销售金额未满五万元或者并未销售且货值金额不足十五万的情况下,如果按照既遂标准说和肯定说来看,该行为构成犯罪未遂。根据《伪商解释》,货值金额达到十五万才成立犯罪未遂,会出现情节较轻的货值金额不足十五万与超过十五万同罪同罚、销售金额不足五万与货值金额达十五万以上同罪同罚的情形。若货值金额仅仅为十五万这样的量刑勉强合理,倘若货值金额上百万上千万,与五万已然没有可比性了。这样的规定不合理且显失公平。
(3)购入伪劣产品且尚未销售,此类行为并没有刑法条文所规定的生产行为、销售行为。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该行为根本就不满足本罪的犯罪构成。但是根据《伪商解释》和肯定说却认定该行为为犯罪未遂,这已然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如果坚持既遂标准说和肯定说,没有办法合理的对购进伪劣产品且尚未销售的行为进行处理。
(4)我们还需要的注意的一点——什么是犯罪构成要件?根据学术界通说和实务来看,犯罪构成是指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犯罪,是犯罪成立的标准,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而既遂未遂是犯罪的形态,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衡量罪的轻重问题。故犯罪形态建立在犯罪成立的基础上的,只有在犯罪成立的前提下,才能去探讨犯罪未遂的问题。犯罪成立不能与犯罪既遂等同,二者并不是同时存在而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四、问题的解决
笔者已经充分论述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不存在未遂的状态,销售金额也是犯罪成立的条件。但正因为不存在未遂的情况,所以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具体阐述如下。
1.在多种实行行为类型说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合理地解释生产伪劣产品罪的犯罪构成。即使认定销售金额是犯罪成立条件,不存在犯罪未遂的形态,也无法解释生产伪劣产品罪的犯罪构成,不存在销售金额的生产行为不能达到犯罪成立的标准。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其实也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这一点在《伪商解释》中是有体现的),但是生产而未销售且货值金额不满十五万元的情况没有办法予以准确的定性,不仅如此对于购入伪劣产品且未销售的行为也无法合理定性。《伪商解释》中采用货值金额对上述两种行为进行定性,但货值金额的性质和定位又是什么呢?是犯罪的成立条件?对于购入伪劣产品且未销售的行为可以用犯罪成立条件说进行判断,从而得出不成立犯罪的结论。但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依然无法准确定位。
2.作为选择性罪名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实务中罪名的适用有独立适用和概括适用的情况。这几项罪名的社会危害性和对法益的侵害程度是不一致的,但它们的法定刑却是一致的。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将危害程度不一致的犯罪行为同罪同罚是否显失公平呢?
在确认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选择性罪名、多种实行行为、不存在未遂等性质以后。将这些性质结合在一起,其实不太能够合理的解决以上问题的。所以,笔者提出大胆的想法,将该罪名拆开各自成罪,分别为生产伪劣产品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属于生产伪劣产品罪的范畴,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属于销售伪劣产品罪范畴,而生产且销售的行为触碰了两个罪名,实际上是属于连续犯的范畴,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处罚,按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即可。购进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实际上是销售伪劣产品的预备,按刑法总则关于预备犯的规定定罪处罚即可。首先,将生产伪劣、销售伪劣产品罪拆分独立成罪,更符合刑法惩罚犯罪的立法本意,全面的囊括刑法所规制的犯罪行为,同时不会出现漏罪也不会扩大其规制范围。将罪名与行为进行拆分之后,对各自的罪名制定相应的法定刑后,也不会出现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与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出现同罪同罚、有失公平的情况。其次,在单独设置生产伪劣产品罪的时候,可以借鉴《伪商解释》的货值数额,作为其犯罪成立的条件。[10]这样的设置,更能够保证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在实务中充分准确的囊括所有的生产行为,尤其是不以销售为目的的生产行为。最后,对于刑法条文中所规定的数额就是犯罪的成立条件,未达条文的数额标准就不成立该罪。采取这样方式更能妥善的处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所存在的问题。
结语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不管是在学术理论上还是司法实务中,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罪名。起初,笔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是在研究该罪名是否存在未遂的情况,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该罪名存在的问题一一暴露在我眼前。于是,我发现不能仅仅只关注是否存在未遂的问题,仅仅关注未遂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罪名所存在问题。所以笔者大胆的提出了将罪名拆分的方案,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使该罪名在适用的过程中更加的符合立法目的以及应对司法实务出现的各种情况。
注释
①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江明中等非法经营、销售伪劣产品二审刑事裁定书(2013)川刑终字第959号。
②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方学文、方二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再审刑事判决书(2018)豫11刑再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