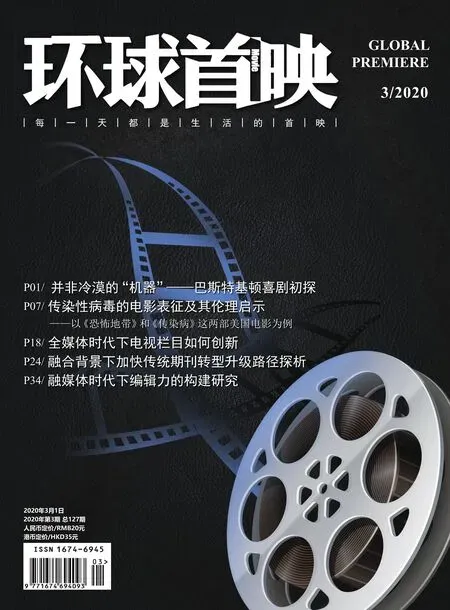并非冷漠的“机器”——巴斯特·基顿喜剧初探
陈圆圆 北京电影学院
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千高原》中提出了“机器”“连接”“生产”等概念。他们认为“机器”并非暗喻,生命和现实本身就是“机器”①,它们没有家园、没有母体,而是一种内在性的生产和持续的解域。德勒兹的“机器”不再只是工程学、建筑学、物理学意义上的概念,它包含了对机械、时间和人伦的观照。作为默片喜剧大师的巴斯特·基顿,其与“机器”有着一种紧密的关系——他将身体当作“机器”,与绳索、木棍、滑轮、磁铁、汽车、火车、船等相连。由此,他的喜剧世界靠这样两种“机器”的连结而被创造出来。受到基顿触碰的机器似乎和他血脉相连、相互庇佑,他们一起运作、舞蹈,完成一个个纯粹而连续的弹道轨迹和机械笑料。
一、“小题大作”和“大题小作”
德勒兹认为,喜剧片基本属于“小形式”的范畴,而基顿往往把“大形式”引入喜剧片这种“小形式”中。“大形式”即主角总是处在一个宏大未知的环境中,然而主人公却往往是一个孤独的“小人物”。“大环境”被巧妙地融和进喜剧片这种“小形式”之中而产生对比反差。然而,基顿作品中的火车、轮船等“大形式”的机器装置的功用却被减弱。因此,基顿在填埋这个空间间隙时,他的做法便是不断发明荒谬、无厘头式的“机器”。譬如,《航海者》中的叙事空间是一个能容纳成百上千人的游轮。一般来说,游轮是喜剧片难以驾驭的“大形式”,而在影片中它主要是作为两个主角的避难场所。游轮作为一种机器装置的功能被缩小,为了填补这种间隙,基顿充分利用游轮的构造为主人公设置重重障碍——两人几次擦肩而过、床的坍塌、窗户上的恐怖照片、海底历险、自动播放的碟片机、自动开合的门、食人岛惊魂等。基顿将琐碎却连续的笑料放置到作为“大形式”的游轮里,将“断裂-连接”装配成新的“机器”,让“小”连接成“大”。
二、身体——默片喜剧人的“机器”
詹姆斯·埃基认为,喜剧最伟大的时代是声音未曾到来的默片喜剧的时代,优秀的默片喜剧演员们也积累了一套独特的肢体表演方式。无论是查尔斯·卓别林、哈罗德·劳埃德还是巴斯特·基顿,他们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丰富的肢体动作来制造笑料。然而,肢体元素则在基顿的作品里得到了极致的发挥,并且成为他喜剧运作中的最显著的“机器”——雕塑般的“脸”与高速运作的“身体”。
招牌式的“石板脸”透出希腊雕塑般的单纯和静穆,成为身体机器运作的一部分。基顿“无表情的表情”,是一个优秀的喜剧演员对自身的严格要求。通常,喜剧演员在制造笑料的时候,几乎都是面无表情、十分克制地沉浸式表演。“石板脸”也作为一种表演“面具”,成为了基顿电影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别样的喜剧效果,并与他塑造的单纯天真的人物相得益彰。
此外,快速、大强度、精准的身体运作,也是基顿喜剧的关键要素。在一次访谈里,基顿提到,他在极少数自己无法达到专业技术高度的时候才用过替身演员,比如《大学》里面有一个高难度撑竿跳入二楼的镜头。实际上,基顿的身体每一处都有不同程度的骨折。跳出电影情节来看,基顿的作品中似乎有一种疼痛的内隐。也许是剧烈的运动造成的心理冲击,也恰如其电影中总是透出些许忧郁的底色(如《大学》结尾出现的墓碑),但却绝不是悲观的情绪。基顿的疼痛似乎被那张喜怒不形于色的脸所冲淡了,甚至可以让观众相信,他的确坚硬如磐石、拥有金刚不坏之身。的确,他只为给观众创造最单纯的喜剧情境。他总是能以敏捷的身手和精准的动作让人目瞪口呆,比如,在《囚犯》中基顿的身体如弹簧一般准确穿过刑台上的小洞、《邻居》中的叠罗汉和倒插秧、《稻草人》中和狗的追逐、《爱巢》中与水平线呈九十度角地站立在桅杆上,《将军号》在火车、铁轨上的连续追逐,《福尔摩斯二世》中精准地穿过窗户裹上毯子等。基顿电影中的一种笑料——弹道噱头(“笑料-轨迹”)与身体的基础密不可分,人在此刻作为机器的一个部件承受着高速的运转和压力。在《福尔摩斯二世》中从基顿被恶棍们追逐的时候开始,基顿将一颗弹丸一样把自己发射出去,跳上警察的巡逻车在马路上逃逸,成为一个交通意外的肇事者,接着遇到一个拔河队、穿越木桥……最终弹进小木屋完成了“最后一分钟营救”,缔造了一段精彩绝伦的连续轨迹。这条轨迹本身也构成一台“机器”,基顿和机器系统中牵连的人则是机器中的“零件”,并不断寻找新的“连接体”以生成新的“机器”。
究其喜剧的狂欢语境,所有的符号皆化作欢快的因子,演化成一种插科打诨式的笑料。喜剧本身是作为一种制造笑料的“机器”,也是引发基顿“狂欢式”追逐的“机器”。一切结束之后,喧嚣的世界停止了表面上的运作,只剩下基顿一个人,忧郁也由此显现出来。正如,喜剧理论所言——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三、被“发明”的机器装置
德勒兹认为,基顿的作品把“机器”提升到“大形式”的高度,创造了独特的“机械笑料”。基顿认为“机器”是自己最值得信赖的盟友,同时他也创造和发明“机器”。“机器”被他的电影主角创造出来,同时,这个主角也是“机器”的一个“零件”。这些“没有母体的机器”可以逃避人物的控制,变得极其荒谬。正如约翰·马克思所说,“一切事物都是一个机器,到处都有生产”。
首先,机器可以作为连接和生产的装置,“房屋-机器、船舶-机器、火车-机器、电影-机器……它们都是机器。”②另一位默片喜剧大师卓别林在塑造电影人物的时候,总是表达了一种“人与机器对立”的观念,主人公甚至受到机器的“愚弄”。然而,基顿塑造的角色却乐此不疲地生产、创造“机器”,并且将身体与之相连。基顿的电影主人公们和火车、游轮、房屋、街道、等“机器”产生连接,并生发出一个个联动的机器。其在与人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为主人公们建构出种种新的运作“机器”和抵达快乐的纯粹连续轨迹。
其次,机器作为想象力和造梦的装置。基顿在电影中创造了一个个神奇的机械系统,想象力被转化成荒诞和惊奇。影片《稻草人》中吃饭的餐桌、炉子与留声机、浴缸与沙发,这些精巧的小设计仿佛一支机器的舞蹈;《鬼屋》“房间-机器”开始呈现出一种全自动化的模式;等到了《电气化房屋》“房间-机器”变成了一个全自动的机器装置,但是当人因各种原因失去对机器的控制后,装置就会带来杂乱和无序。不过,基顿的电影中的机器并不是像卓别林、雅克塔蒂一样强调“机器”对人的“异化”,而更多是为了建立单纯的喜剧情境。
基顿很重视布景,很多场景设计元素是荒谬、超现实的。比如,《福尔摩斯二世》中下楼的杆子有弹拉功能,《大学》中围栏变成了梯子。这种精巧而独特的设计,构成影片内部叙事的荒谬。此外,“梦”是基顿在影片中常用的元素:《囚犯》的追逐打闹只是熟睡的人的梦境而已;《福尔摩斯二世》则在影片中呈现了“银幕世界”和“真实世界”的错乱和融合,影片的后半部分都由基顿这个电影放映师的梦境建构;在《倒霉》中,结尾基顿牵着他的中国妻子的构思透出一丝近乎魔幻的色彩。
最后,机器作为制造灾难和麻烦的装置。基顿的电影中总是出现很多灾难性的场面,这些灾难来自大自然、社会以及作为导演的基顿自创的机械世界。他的电影描写洪水、飓风、暴风雨、漂流、岩石跌落、建筑物被摧毁,有战争、死刑、盗窃、仇杀、情敌、抢劫。基顿给我们展现一个个荒诞不经的世界,电影的主人公也总是在与灾难抗争。在《一周》中新婚夫妇历经磨难,飓风房子把刮得东倒西歪;《我们的待客之道》中的暴风雨和瀑布救人;《福尔摩斯二世》中汽车终归要沉默;《小船》终归要漏水;《小比尔号汽船》中,一场风暴刮走了主角威利,房子坍塌在他的身上,最后又掉进河里;《警察》中倾巢而出的警察追捕基顿。基顿的主人公们抗争的方式、执着单纯的品格表明,与灾难抗争搏斗到底、不愿屈服才是想要表达的主旨。电影中的灾难情节,也体现了基顿些许宿命论的精神内核——房子必然会坍塌,小船必定会沉默,爱情终归走向坟墓……
四、镜头语言作为基顿电影创作的“机器”
基顿电影中超前的现代意识体现在对镜头语言的丰富把控。他擅长运用长镜头、景深镜头以及画外空间,为他能够在镜头前充无拘无束地表演、创造笑料提供便利。比如,电影《将军号》中对长镜头就有很成熟的运用——前景是约翰持续地砍木头给火车加燃料,后景则是正在撤退的南方军队,士兵们正四处逃窜。镜头表现了两个方向的错位,两种状态的对比悬殊被表达得淋漓尽致。此外,他偏爱实景拍摄,很多高难度的动作都是在真实的逆境中完成,甚至还为此差点丢掉性命。时至今日,这些作品还能给观众带来很多“惊奇”。
五、“机器”的束缚和被束缚“机器”
好莱坞作为电影造梦的“机器”,曾给基顿带来了辉煌的成就。然而,也正是它机械化的大制片厂的运作模式,让基顿的电影生涯逐渐走向没落,导致其灵活生动的表演“机器”逐渐走向坍塌。1928 年,是基顿电影生涯的转折点,老板约瑟夫·申克把与基顿的合同卖给了米高梅公司。米高梅公司不允许演员表演过于惊险的动作,狭窄的布景和摄影棚限制了他的运动。这对偏爱身体表演的基顿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基顿的“机器”被束缚了起来。
巴斯特·基顿的全盛时期也是默片时代的末期,他所推崇的一套默片表演体系也逐渐不再适用于即将全面迈入有声时代的好莱坞。人们甚至认为在银幕上出现片刻沉默就是不可思议的浪费。有声对白的运用,使得真正精通默片表演的喜剧演员反倒没有了用武之地。就像基顿在卓别林的《舞台春秋》中说的:“从未想到会沦落到这般田地!”
《时光快车》中基顿再也无法驾驭一个像将军号那样的机器了,他沿着漫漫铁轨,作为时代的旁观者,在小小的火车头上生活、栖居。快速疾驰的火车、巨大的轮船都和基顿的小火车头形成鲜明的对比。时光快车本身似乎已经不是在制造笑料了,而是在缅怀一个时代的逝去。一九六五年,巴斯特基顿驾驶着迷你版的“将军号”穿越时光隧道,完成了他的电影生涯的最好谢幕。
注释
① [英]科勒布鲁克.导读德勒兹[M].廖鸿飞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70.
② 吉尔·德勒兹著.运动 影像[M].谢强、马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277.